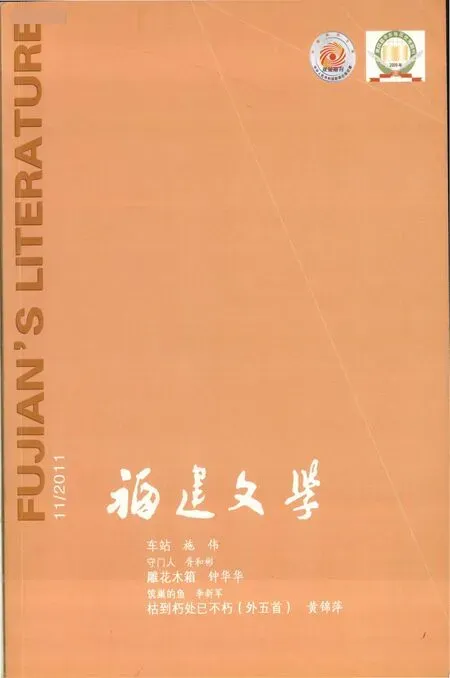他让后工业时代变得柔软——读哈雷诗集《零点过后》
戴冠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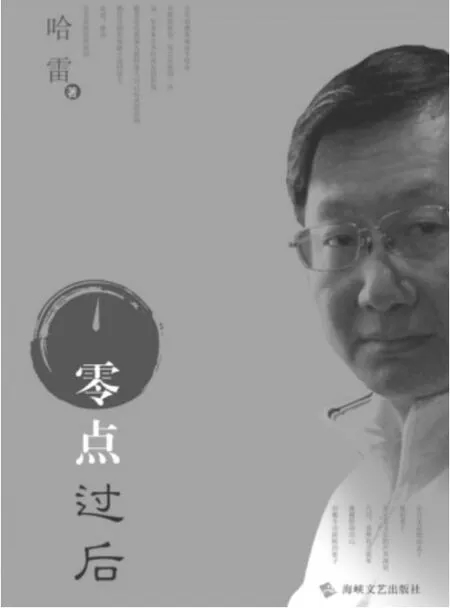
当我们在后工业时代的水泥丛林中左冲右突,感觉灵魂越来越累,心儿越来越老,可是,能安顿灵魂的诗意家园似乎越来越远,能抚平心灵皱纹的自然之风也总是遥不可及时,我读到了哈雷的诗。
哈雷的诗里有嘶鸣的蟋蟀,有低唱的秋水;有麻雀的眼神,有老杉的年轮;有“一夜塘前月色/舞动清秋”(《秋天的树》),有“柔软的草叶丰茂的雨季丰饶宁静的土地”(《苔树》);有“像手指”“像风”“像音乐般抚摸我的心”的“那树条上的茸芽”(《故园春来》),有“高高的岩壁上”,像“长长的、像清洁的飘带/就这么长年挂在你的胸前/有限地舞动 那曼妙的音阶/潺潺垂落在无限岁月中”的瀑布(《瀑布》);还有“以爱的无畏,投向你”的爱情岛(《爱情岛》)和“站在土屋前等着她的心上人”的“很老的乳娘”(《村庄》)……
这些美丽而又忧伤的意象,唤起了我们久远的记忆。它们曾经是那么真实,那么亲近,在我们赤着脚四处追逐嬉戏的童年的田野,在我们无数次从潜意识里浮现出来的迷人的梦境,在我们背着行囊风尘仆仆地徜徉在远山远水的风景。但在后工业时代的浮躁和焦虑中,许多人已经淡忘了,视而不见了,或者顾不上了。这让我们惆怅和无奈。但是今天,哈雷的诗让我们惊喜。他悄悄地拾掇着这些美好的意象,把它们珍藏在《零点过后》的诗匣中,让每一个读者一打开就会感受到一阵扑面而来的清新的风,领略到一个动人的唯美的意境,如《秋天的树》:
“行走在秋天里的两条道路/都通往荷塘,而坡上/一株翠绿的树/在另一个时间意象出现之前/开始怀旧//喘息是从内部开始的/秋水之上,风把树叶握得更紧/而残荷还在江南挣扎着/松软的身躯/垂落了最初的誓言//有些声音将季节撕开一条裂痕/要让黄叶将它覆盖/就像睡梦想要覆盖记忆/我和你来到山道上,触摸落霞的体温/秋心变得感动//你依在边上的影子更加清晰/草色弥漫的脸上/传递着一瞬浓似一瞬的秋意/酒过千觞,回望眼,一夜塘前月色/舞动清秋”
一棵怀旧的树,一株柔软的残荷,一塘淡淡的月色,一瞬浓浓的秋意,就这样把我们那颗被世俗和功利煎熬得快要硬化的心浸润得酥酥的软软的,变得感性、纯真和怀旧。
不仅如此,哈雷的诗更以一种忧伤的悲悯抒写,带给我们一份久违的感动。他为被草遮埋的小路而悲哀:“这条小路被草遮埋了/像睡在荒野上的细小的孩子/无法躲开来自山口的风,还有雨水/冲袭着他悲哀的记忆/更为悲哀的是,一整个冬天里/没有落叶和飞雪的记忆/没有凛冽的冰凌的记忆”(《从冬天的小路回来》)他为受伤的老杉而悲愤:“它碰撞到了狂野的天风/却把根扎得更紧/它让乌鸦在枝头经营 攀援的花/恣意缠绕着开放/稀疏的叶片拍打着云朵/时空远隔的心映照星辰/因为它让所有的斧手颤栗/还因为它是老杉 依然/长出新生的绿芽”(《老杉》)他为果实的掉落而牵挂:“当风带来了秋声/鸽子成群飞去,我的世界充满了别离的苦恋/生命如果可以这样送达/我愿意把自己风干,然后从枝头/跌落在地”(《悲情英雄》)在哈雷的世界中,不管是小路,还是老杉;不管是树的果实,还是轮回的季节,都是一种生命的形式,都有一份悲悯的情怀。于是,生命的残缺,生命的受伤,生命的失落,在他的审美观照中,便染上了一种独特的忧伤,这份忧伤让我们读出了一种呵护生命的渴求和希冀,让我们心疼,更让我们感动。
更耐人咀嚼的是,哈雷的忧伤还蕴藉着一种反思的力量和批判的精神。在这些美丽的诗句中,我们读到了情感的力度和审美的深度。最喜欢那首《村庄》:“七步,和曹植的诗一起/走进我的童年的村庄/一座石磨压成的村庄/扁扁的村庄 福州往东两百公里/有廊桥跨过河面/木杵敲在青石板上/水车在不远处转动……”在这首诗中,哈雷深情的抒写先是把我们带进了他的村庄,跨过河面的廊桥,敲在青石板上的木杵,在不远处转动的水车,袅袅飘荡的炊烟,驮着柴禾的农夫,站在土屋前等着心上人的乳娘,无一不美得让人心疼。然而,当这个美丽的村庄被开发成了景区,当成千上万的观光客涌进景区戏耍照相时,那纯粹的原生态的美丽却再也不见了。这种对审美错位的揭示,对纯朴美的呼唤,对原生态被破坏的谴责,在哈雷这些动人的诗句中被表现得蕴藉而感伤,字里行间涌动的人文力量让我们回味再三反复咀嚼。
哈雷是一个资深诗人,上大学时就开始写诗。那时他很年轻,浑身洋溢着激情,情怀里涌动着浪漫,诗中更是充满了理想和追求。后来他去编刊物和报纸,曾经有一度停止了歌唱,直到三年前他又开始写诗。他自己曾说:“我的诗歌创作一度断层:2007年5月我在鼓岭脚下一片飞流直落的瀑布面前重新找回了灵感,14年来未曾写诗,突然这一天内心有了冲动的渴求。我至今依然可以感到那个瞬间带给我奇妙的感觉,是真正诗歌意义上的一次神性的交汇,这种瞬间触动,就像米沃什说的那样:给我一个莎士比亚的瞬间,是神来之笔。”(《哈雷论诗》)是的,十四年的蛰伏,带来的是一次非凡的超越。在这本《零点过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诗艺的精进,“和过去不同的是,我开始叙事,开始用名词和动词写作。一方面想让诗歌变得含混,在意义的层面上游移不定,而另一方面又被那些难以捉摸和不断自我构造的东西所诱惑;一方面对清晰、柔美、简洁、有力的语句充满了渴望,另一方面更加迷恋那种跳跃的、通透的语言,并能为此获得欣喜若狂”,更看到了他在审美上的自觉。他已经不再仅仅迷恋于浪漫的倾诉和理想的传达。他开始更理性地审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更深入地思考生命的存在方式,从而更独特地传达他的审美发现和情感把握。
于是,在这个坚硬的后工业时代,哈雷力图用自己独特的诗意传达把它变得柔软。他曾在《柔柔的……》的这首诗中写道:
我第一次听到浪的声音/在你的怀里呢喃着/海上的帆船远去了如飘向天际的纸鸢/沙滩延伸出的臂膀/像金色的梦裹着我/感动的心/柔柔的……//秋阳中传来你的声音/爱语缠绕在绿树花影之中/音乐洒落的小径上,十月的歌/穿过了岛屿,奏响了庞大的钢琴/青藤和老树都仰起飞花的笑脸/吟咏的心/柔柔的……//我的步履在倾斜的坡道上慢了下来/那许多现实和不现实的想法/全都放下了,只想着一个人,一丛三角梅/一只相隔不远的小船/然后全都把这些装进今夜的诗句里/思念的心/柔柔的……
就在诗人“柔柔的”的吟咏中,我们的心开始变得柔软,变得温情,变得善解人意。于是我们明白了,在这个硬朗的世界里,我们不仅要懂得奔跑,还要懂得减速;不仅要懂得开发,还要懂得守望;不仅要懂得别离,还要懂得思念;不仅要懂得“许多现实和不现实的想法”,还要懂得“一个人,一丛三角梅/一只相隔不远的小船”。
就这样,哈雷用自己独特的审美认知和动人的诗意传达,让这个世界的一切生命从此变得柔软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