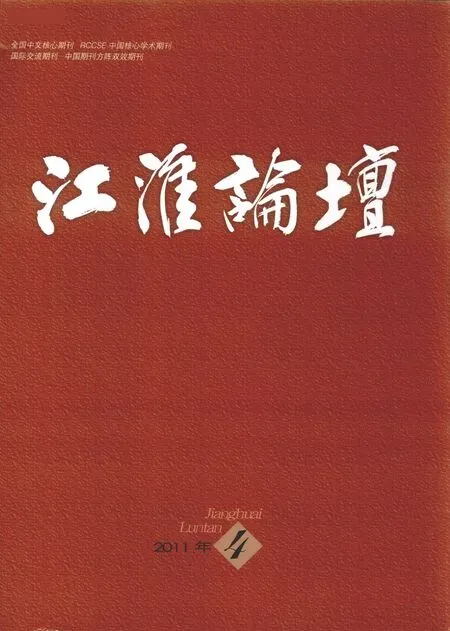论当代河洛文学的父子叙事伦理*
刘保亮
(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河南洛阳 471023)
论当代河洛文学的父子叙事伦理*
刘保亮
(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河南洛阳 471023)
当代河洛文学的父子叙事伦理有着浓郁的父性崇拜。阎连科小说的父性崇拜表现于苦难父亲、权威“天父”和道德父亲形象的塑造,而李佩甫则善于描写家族历史的父性怀恋。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以叛离传统的父子伦理,潜隐着弑父情结。他们站在文化守成主义的民间立场,展开生存背景下的父子叙事伦理,唤醒我们内心渴望的原始久远的父亲情结,重新复活也许一度失落的生命记忆。
当代河洛文学;叙事伦理;父性崇拜
父子伦理蕴涵着人类深刻的生存体验,也成为文学富有能指意义的叙写标的。在当下欢度“道德假日”的欲望化时代,“审父”“弑父”“丑父”成为文学叙事新潮,父亲好像是子一代的绊脚石和挥之不去的诅咒,他们颠覆传统的父权秩序,解构父亲的权威和子辈的孝道,传达出价值虚无主义的思想伦理。然而,无论如何,“父亲”不应成为一个海德格尔所言的“存在的被遗忘”问题,因为父亲形象的破碎与缺席,也即意味着失去了历史、传统、权威、秩序,毕竟父亲还标志着子辈的身份认同和未来时态,毕竟没有父亲的状态是一种感情创伤。由此,以阎连科、李佩甫、刘震云为代表,审视当代河洛文学的父子叙事伦理,其父子之间具有传统文化的等级关系和相互指证的文化身份,它突出表现为浓郁的父性崇拜,这在当前文化语境中既卓然独立又意味深长。
一
父性崇拜在阎连科小说里表现为先爷、司马笑笑、丁水阳三类不同父亲形象的塑造。《年月日》里的先爷虽然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但他坚守村庄使其后继有人的行为,具有类似史前文明时代的父亲原型。面对岁月被烧成灰烬的千古干旱,先爷甘愿忍受缺粮断水的饥渴,独自留下来守护象征希望的唯一的一颗玉蜀黍,最后不惜埋葬自己,以身躯做肥料,让其根须与自己的肉身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小说有意淡去故事发生的时间,或者说时间问题在文本里处于悬置状态,这使其增添了神秘的寓言化色彩,可以解读为此类故事、此类困境可能会发生于人类的任何一段历程。先爷,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守护和喂养具有隐喻色彩的玉蜀黍,这种用铁的脊梁为村人后辈遮风挡雨的行为,呈现出无畏抗争的苦难父亲形象。
《日光流年》里的司马笑笑,也许是阎连科耙耧世界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小说里他有两个举动印象至深:一是抛弃残废孩娃。当饥饿不可阻挡地危及三姓村的传承时,他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地策划了一场骗局,诱使母亲们去东山沟挖野菜,而带领男人们把自家的残废孩娃丢弃在西山梁野沟。他以冷酷的人生智慧,使三姓村避免亡村灭顶之灾。二是以身饲鸟。当离麦熟还有一、二十天而三姓村民已经熬不下去之时,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招引乌鸦和鹰,让村民捕鸟充粮以挨过最后一段难熬的时日,并在走向生命终点之际嘱托儿子:“你当了村长就领着村人换换水土吧”。无论是“我是村长,我就是王法”的话语霸权,还是教导村民抛弃残废孩娃的生存决择;无论是生命结束时对儿子的教诲,还是不惜身死诱鸟的牺牲壮举,它们都在广义上生动地展现出一个作为村长的政治权威父亲,一个承诺让村民“活过四十岁”的精神权威父亲,一个司马蓝内心仰慕的家长权威父亲。他既扮演了一个马克思所谓的“天然酋长”的角色,又表现出一个充满自信、富于侵犯性的天父原型。
《丁庄梦》里的丁水阳是阎连科小说里最具道德感的人物。对其教师身份的特意设定,潜隐着乡土社会的伦理视域,一方面使前前后后从丁庄小学校里走出的晚辈村民成为他的学生,他也自然地“德高望重”起来,另一方面,“德高望重”的自我身份认同,也极大地唤起了他内心的道德意识,进而产生了后来强烈的道德归罪。如果说道德归罪主要有他人归罪和自我归罪两种,那么昆德拉认为两者中更可怕的是自我归罪,因为“自我归罪是个人的一种生存状态,由社会的或意识形态的他人归罪来审判自己,自己让自己变成有罪的人。”[1]174丁水阳就是一个自我归罪的忏悔者,他曾经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组织村民到蔡县参观,谁料想随后引发的卖血狂潮埋下“热病”传染的隐患,使十年之后的村庄变为一个死神频频光顾的地狱深渊,同时,儿子丁辉创立的“丁庄血站”是“热病”大面积传染的罪魁祸首。这双重原因使其内心饱受折磨,充满原罪意识。虽然他的孙子小强即小说的叙述者“我”被村人毒死,丁家在民间意义上已经遭到报复或报应,但个体的道德良知以及对自己罪性的认识使丁水阳依然不能原谅自己,不能减轻自我良心的谴责,从此便踏上了忏悔与赎罪的心灵苦旅。他先是苦劝甚至哀求儿子向村民认个错,向有热病死亡的人家磕个头,再是将所有患病村民集中在学校,试图过上一种儒家先贤梦想的“大同”生活,后是把丁辉孝敬自己的东北野人参拿出来,假托是儿子让自己转交给乡邻的,乞求乡邻收下熬喝了抵住那热病,然而,这一切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有罪所以需要救赎,而救赎带来的是责任伦理的强化,强化的责任伦理则令他进一步赎罪,这种伦理递进循环的结果是,丁水阳在结阴亲的仪式上举起栗木大棒一棍打死了儿子,并且还挨门逐户地 “报喜”:“我把我们家老大丁辉打死啦”。这里溢出常规的“杀子”演绎为一个尽管残酷然而向善的叙事伦理,文本平添了伦理探寻的深度,它既以无望救赎揭示了毕希纳所谓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也最终凸现与定格了丁水阳悲悯的德性,这是一个有着基督色彩的道德父亲。
无论是苦难父亲、权威“天父”还是道德父亲,他们无不闪耀着魅力人格的神性光辉,共鸣着父性崇拜的文化记忆,不仅让我们感性地直观苦难、伟岸、责任和慈爱,而且也使我们对“父亲”这一称谓油然而生温情与敬意、依恋与希冀。由此,阎连科小说中的父性崇拜充溢着浓重的孝亲情怀。阅读阎连科的《瑶沟人的梦》、《欢乐家园》、《情感狱》、《母亲是一条河》以及《我与父辈》,会不时相遇奉养敬长、返本感恩、祭祀追远的伦理场景,感受父母子女之间血脉相连的生命依偎。
二
如果说阎连科的父性崇拜表现于父亲形象的塑造,那么,李佩甫小说则善于描写家族历史的父性怀恋。“家族”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乡村社会性组织,它以血缘和地域为生存的基础,以谱碟、祠堂或礼仪作为存在的表象,以成文或俗成的制度界定行为规范。《羊的门》里的呼家堡具有家族专制统治的性质,呼天成既是“主”的形象也是一种天父的形象,而对于呼国庆来说他还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典型的教父。若对《羊的门》存而不论,单以《李氏家族》为例,其父性崇拜也异常醒目。
《李氏家族》的叙事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第三人称叙述的大李庄的现实图景,二是追思先祖的“奶奶的瞎话儿”,在现在与过去叙事时空的穿梭之中,它们共同组成了完整的李氏家族的历史志。文本开篇的“引子”罗列并配以图表介绍了族谱的概貌:卷一的“七续族谱序”、“命名编”,卷二的“功名卷”,卷三至卷八的“脉线卷”,卷九的“人丁卷”,卷十的“坟茔卷”。族谱的嵌入小说,形成一种不同体裁的文体杂糅,对此巴赫金认为,小说可以包容各种不同的体裁,如文学体裁 (诗歌、戏剧片段等)、非文学体裁(日常生活的、演说的、科技的、宗教的等),使文学语言、不同体裁相互指涉,以一种新的关系彼此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世界。[2]这样,族谱作为一种叙事元素进入《李氏家族》,它的局部纪实性与小说整体的虚构性和想象性,形成明显相异的行文风格,其相异不仅使族谱以不和谐的音调在小说总体进行曲中得到十分突兀的彰显,而且也奠定了它非同一般的文本地位,具有笼罩全篇的意义。尤其文本对以家谱为主的“引子”实行单独标页(6页),使“引子”与之后的356页文字构成互文性对话。由于族谱的编修热潮是在宋明理学的盛行时期,族谱的内容与体式是理学的一个直观的微缩的生动表达,它的父系传承路径既隐喻着“寻父”的伦理诉求,也伸张着“尊父”的伦理法度,这样,如果说家谱不仅具有一种使后代明祖明宗,知其家族血脉之渊源的伦理作用,而且它还以丰富的“能指”和修辞而承载着父子伦理的道统,那么,小说里的“李氏族谱”就不再只是一堆满足民间思古怀幽情结的故纸,而是一个家族满怀对父系祖先的敬仰执着追问“我从哪里来”的“共同体”想象,它既埋藏着叙述者的伦理基调,也暗含着有待展开的伦理实像。
如果说“李氏族谱”是一堆尘封凝固的文字记忆,那么七奶奶的“瞎话儿”则给大李庄的后代子孙们以鲜活流动、无限遐想的传奇故事。这里所谓的“瞎话儿”,实为李氏家族如何一代一代相连、一支一支接续的“千古大事”。从大李庄的第一代远祖季和,第四代淼,第六代嬴,第七代衡,第八代子顺,第十三代发祥,第十六代盖儿爷,一路追寻下来,会发现七奶奶的瞎话儿并不“瞎”,它不仅仅是一个李氏家族所遭遇挑战与发展的个案历史,而且也浓缩了整个中华民族甚或人类家庭社会的文明进程,从中我们既听到了生命破碎的呢喃,也看到伦理如何整饬生命经纬。刘小枫认为,“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1]7以此考量李氏家族的先辈,既有季和、衡、发祥等的“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它看起来围绕个人生命,实际让家族目的变得比个人生命更为重要,同时也有嬴、盖儿爷等的“自由伦理”的小叙事,它关注偶在个体生命的人生变故和叹息想象,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无论是大叙事还是小叙事,如果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那么,“奶奶的瞎话儿”里诸如关于苦难、关于功名、关于财富、关于罪恶的家族神话,为我们呈现了逝去岁月里多样化的伦理景观和哲思,它不仅有助于阐释大李庄现实的伦理困境,而且也预示了未来的伦理走向,因为家族神话“往往体现了生命密码的递转和文化基因的重编。这种递转与重编并不就等于后来者和先在者的断裂和决绝,相反,倒有可能为后来者寻获新的生长点和支撑点。”[3]于是,有了小说结尾之处超越时空的款款叙说,“时光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血脉是连着的,永远连着”。于是,对七奶奶的祭奠场景也别有哲理:死人静静地躺着,活人默默地站着;生与死仿佛是一道分界线,又似乎没有;无论是躺在地下的,还是活在阳世的,全有那血缘的“脉线”穿着,这“脉线”便是一部家族的历史。如果说家族神话的建构与传递过程,象征和隐喻族人沿着时间的河流上溯寻找精神之父的过程,那么,“奶奶的瞎话儿”并不是简单地编造家族神话,而是自然地流淌着“寻父”的叙事潜流,那一个个的男人在叙事中如此充满激情、生命盎然,不仅让今天的李氏后辈足以骄傲,同时也给予复杂的伦理启迪。
三
父性崇拜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中比较常见的原型之一,它潜藏于我们内心感情深处而被文学艺术时时唤醒。然而,“父亲”作为伦理关系中意蕴丰富的意义载体,不仅象征着权威、力量、秩序与尊严,还代表着专制、主宰、残暴甚至愚昧。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父亲”是个不同寻常的概念,它决不仅仅表现为一个男人在家庭血缘中的位置,还“意味着在社会文化中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强壮、威严、荣誉、家庭的主宰、对于女性的占有。这些都是儿子们对于父亲力量的感受,儿子们对于这些特权满怀嫉妒,父亲作为一种特权对儿子们来说是一种永恒的深深的压抑”。[4]因此,父性崇拜与弑父情结都矛盾地埋藏在人类的心底。
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以叛离传统的父子伦理,潜隐着弑父情结。在《头人》、《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里,“故乡”既不是人生疲倦时可以停泊的港湾也非心灵的原乡,那里看不到所谓的田园画卷,也没有想象的民风淳朴,它不再是一个安宁、自足、和谐、自然的乡土世界,而是充满着利欲熏心、无赖卑鄙、不择手段的权力争夺,上演着残杀流血的日常剧情,那乡村惯有的伦理温情无处体验,那父子之间的精神默契难觅踪影。在《温故一九四二》里,饥荒使人恢复了狼的本性,活人吃活人,亲人吃亲人,“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还有易子而食的,易妻而食的”,生存导致人们对基本伦理道德的背离和自身属人本质的丧失与异化。这种触目惊心的行为即便从约瑟夫·弗莱彻的境遇伦理来看,虽然可以由“境遇决定实情”给予理解,但它不可宽恕的是严重匮乏“爱的旨归”。[5]如果说伦理赋予经历残酷“丛林法则”之后人类家庭社会以意义,那么,如此重要的道德伦理却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基本空缺,那司空见惯的父子关系处于悬空状态,似乎寻觅不到那份日常伦理的感动。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要留在“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悬置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它的道德”。[6]刘震云小说“外聚焦”的“冷眼旁观”叙事达到这一要求。“冷眼旁观”叙事是一种非人格化叙事,以作者的隐退追求叙事的中立性和冷漠性,叙述者对故事人物和事件无动于衷,与叙述对象在情感倾向与道德立场上保持清醒的距离,成为故事的旁观者与局外人。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均为“冷眼旁观”叙事,文本充满着反讽与戏谑,是以“零度”抒情的方式观照曾经熟稔的故乡,故乡好像是一个取景框,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物在其间尔虞我诈鲜血淋漓地表演,但他们的悲喜与叙述者似乎毫不相关。然而,叙事与伦理亲如手足的关系,决定了小说不可能不进行伦理言说,哪怕如罗兰·巴特标举的“零度叙事”的小说也难逃这一宿命,这使作家作品里的父子关系空缺,其实也是一种伦理立场。由此,刘震云小说叙事视点的“冷眼旁观”,是对故乡毒辣而透彻的洞察,其反讽戏谑的写作姿态将文本纳入弗莱所谓的“冬天的叙述结构”,[7]而那骨子里“沉重的轻佻”和“泣血的玩耍”,[8]则有力地再现了故乡伦理的荒野景观。
如果说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意在伦理颠覆,那么《一句顶一万句》则既有对父子伦理的继续解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开始了尽管微弱的建构。对这部小说,陈晓明曾评论道:“刘震云无疑是最激进挑战家庭伦理的当代作家。我们无法在这里详尽地去梳理他的写作谱系,他过去的作品里就把血缘亲戚关系加以戏谑,给予荒诞性。在这部作品中,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再次被解构,遭到深刻的质疑。”[9]但细究起来并非完全如此。杨百顺的家庭充满暴力。杨百顺十三岁那一年秋天,家里丢了一只羊,“老杨兜头抽了他一皮带”,他辩解“爹,我打摆子发烧哇”,老杨兜头又是一皮带。还有一次杨百顺把听到的别人捉弄他爹的话,告诉了老杨,而他爹听后不信,便“兜头扇了杨百顺一巴掌”。也许正是青少年时期生活在这样的父亲日常暴力之下,家庭成员之间缺乏关爱与交流,一肚子的怨气与悲愤无处诉说,才使杨百顺一生都渴望在家庭之外拥有能 “说话”的朋友,即便他一次次更改姓名(父权的符号)诀别旧的伦理关系,但最终也没能实现“说话”的愿望。杨百顺曾经做豆腐、杀猪、染布、破竹子、沿街挑水、到县政府种菜、“倒插门”嫁给一个寡妇后卖馒头,在这些职业生涯中,他之所以苦苦寻找“说话”的朋友,是因为无边无际的人生孤独,而之所以身处孤独的围困,又一定程度上源于少时父亲语言倾听的中断和拳脚的出击。于是,父子关系既带来心理的伤痛与语言的压抑,也预示了杨百顺后天的治疗和释放,那便是终身涌动的“说话”情结,即说话交流的强烈欲望以及对能“喷空”者的推崇,其表现之一就是他对“喊丧”者罗长礼的五体投地的崇拜,甚至他出走咸阳时把自己改名为“罗长礼”。“喊丧”在生与死、在场与不在、个人与亲属之间构成一种多元的奇妙关系,它借用死者的权威和恐惧,利用鬼魂的超自然超现实的力量,来规划和建构血缘亲属的共同体,无论是一声长喊“孝子就位”,还是有序安排来客祭奠,其实质是远远近近的伦理亲情的梳理上场,由此,“喊丧”场景即为伦理场景,杨百顺对罗长礼“喊丧”的痴迷,既是对现实父子关系的否定与批判,也是对内心理想亲情的吁求和希望。如果说小说叙事包含“后向预言”,“正是因为结尾才知道它是开端”,[10]那么,掩卷之后再回顾全文,无论是吴摩西的“出延津记”还是牛爱国的“回延津记”,其在文化象征意义上是一种寻子或寻父,虽然两者都是无果而终,但他们行为艺术的“奔走”,不仅表达出“千年孤独”的痛楚,而且深蕴着伦理关怀的期冀。
亨利·詹姆斯认为,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有他的伦理核心。[11]由于河洛地域是二程“伊洛理学”的发源地,是历史上所谓的“理学名区”,其理学传统作为一种宏阔深厚的文化源泉与背景,因了艾略特所说的“过去的现存性”而注定穿过岁月的风雨在当代降临、复活与再生,这使当代河洛作家的文学言说一定程度上沾染着古旧的河洛理学气息,散发着对传统伦理的“怀旧”情绪。李准的《黄河东流去》通过描写李麦、海老清、蓝五等七户农民悲欢离合的命运,对基于土地、茅屋、农具和牲畜之上而产生的伦理亲情深为认同和赞美,认为这是我们民族“伟大的潜在的生命力”。 张宇的《晒太阳》、《乡村情感》里,那做父亲的对逝去的女儿的心理愧疚,那做子女的听从父亲安排嫁人的无悔选择,都呈现了乡土伦理的“老照片”。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里面对惨绝人寰的“大饥饿”,置身于无法后退的生存底线,父母子女之间风雨同舟的人伦温情构筑起家庭的避难之地,点燃黯淡生活的希望之光。如果说任何作家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资源背景下写作的,那么河洛理学自然地成为当代河洛作家创作的心理文化底蕴,这使他们不约而同地站在文化守成主义的民间立场,展开生存背景下的父子叙事伦理,不断唤醒我们内心渴望的原始久远的父亲情结,重新复活也许一度失落的生命记忆。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41.
[3]杨经建.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父”母题[J].文艺评论,2005,(5).
[4]颜敏﹒破碎与重构[J].创作评谭,1997,(3).
[5][美]约瑟夫·弗莱彻﹒程立,译,境遇伦理学——新道德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7-21.
[6][捷克]米兰·昆德拉﹒余光中,译,被背叛的遗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7.
[7][加]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M].广州: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277.
[8]葛胜华.沉重的轻佻,泣血的玩耍——评刘震云长篇新作《故乡相处流传》[J].当代作家评论,1994,(4).
[9]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干叙事新面向[J].南方文坛,2009,(5).
[10]华莱士·马丁﹒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5.
[11][美]亨利·詹姆斯﹒朱雯等,译,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文论选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55.
(责任编辑 岳毅平)
I206.7
A
1001-862X(2011)03-0176-005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洛文化与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2008FWX013)
刘保亮(1968-),男,河南新野人,文学博士,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