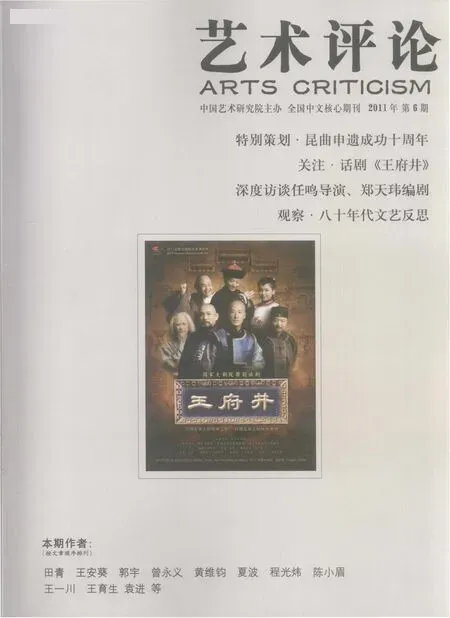评童道明的剧本新作《秋天的忧郁》
王育生
童道明的第三部剧作《秋天的忧郁》,于2010年年中杀青,并于同年九月在《剧本》杂志发表。2011年6月初,由天津人艺在北京蓬蒿剧场首演。至此,童先生在《我是海鸥》、《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发表、上演之后,一鼓作气又创作了他的第三个话剧。
众所周知,童先生是著名的戏剧评论家,他晚年改写话剧,仍然坚守着他的戏剧理念和创作原则。童道明认为,写剧本无非是写戏剧评论的一种“延伸”,只是在戏剧大厦里挪动了一下,转换一个角度,继续发出他的声音,发挥他的作用。
关于“为知识分子写戏”
要为知识分子写戏,是童道明的主要的创作动因。触发的由头,虽然是于是之退休后带有反思性的一次谈话:“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北京人艺没有演过一出真正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戏”。但更深刻的内因,还是童先生自己想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多舛,作“不平之鸣”。在童道明看来,从屈原始,中国知识分子是有“谱系”的,延续至今,忧国忧民的社会良知依然存在于当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群体之中。因此,“把中国知识分子理应获得的主体意识交还给他们”,便成了童先生自觉尊奉的创作理念。
在践行这一可贵的创作宗旨时,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童道明身上焕发出来的使命感,他仿佛是承受着一种时代性的巨大压力的催迫。初始童道明弃评论而搞创作,我还深感意外,现在才多少明白了一些,原来有许多东西他久蕴于心,积郁多时,已然形成负累,到了“不吐不快”的程度。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冯至先生去世了,季羡林也走了。写出了反思性的《真话集》的巴金的溘然长逝,使得童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给中国文化带来荣誉而又备受命运煎熬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已接近于整体性消失”(见童道明:《知识分子和戏剧》)。于是,紧迫感油然而生。于是他奋然命笔。于是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中国剧坛便由此多了几部与众不同、个性鲜明、为知识分子说话的话剧新作。
关于“喜剧”
童道明一再申明自己的创作师法契诃夫和曹禺。但是,如同契诃夫说《海鸥》是喜剧,曹禺说《北京人》是喜剧一样,人们对于剧作者童道明说《秋天的忧郁》是部喜剧,也可能不大容易理解和接受。好在童先生自己对此进行了阐释。他说:“我以为契诃夫和曹禺是把喜剧性情景与他们喜爱的戏剧人物最终的精神升华的喜剧性心境关联着的”。童道明还引用曹禺的原话,把这种“喜剧性心境”做了具体的界定:“流着眼泪又怀着喜悦,抱着哀痛的心肠和光明的希望,追惜着过去,憧憬未来。”
我也是曹禺的门徒。我完全能够接受这种说法。遗憾的是,剧作家们的这种阐释,与眼下通行的编剧法、教科书以及一般人心目中对喜剧的理解,毕竟存在一定距离。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作家有权对自己的作品做出各式各样的阐释。由于这种阐释是作家自己直接提出来的,是第一手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理应得到读者、观众,乃至评论界的理解和尊重。但是,由于作者阐释会存在某种主观性,它与社会上人们普遍的客观认同之间,有时可能出现若干差别、参差。读者、观众未必全都接纳和采信作者自己的阐释。当然,对喜剧概念理解上的这种差异,丝毫也不会影响对作家作品的欣赏和评价。
“文化三部曲”的价值和品位
童道明把他创作的三部话剧,统一冠名为“文化三部曲”。实际上这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标示和规范了作品的样貌、品位、以至它的美学属性。《塞纳河少女的面模》是正剧,《我是海鸥》是悲剧,《秋天的忧郁》是喜剧。这三部话剧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都不着意于一般意义上的戏剧动作性,而更注重表现主人公的精神生活,侧重于展示人物内在的心灵之美。
在《向契诃夫和曹禺学习》这篇创作心得中,童道明还具体列举了他在戏剧构思上,在表现手段上,是如何向戏剧大师们努力学习和“靠拢”的。由于原文较长,这里不加引述。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童道明对传统虔敬的学习是有成效的,从《秋天的忧郁》确实可以品味到一股契诃夫的气息和味道。
我十分看重《秋天的忧郁》高雅的文化品位和格调。“女演员”和“画家”这两位已届中年的主人公,都有过不幸的婚变,经受过感情的挫折。童道明把这两颗带有伤痛的心灵,满怀希冀、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探寻着幸福之路的历程,描绘得兴味盎然,极富情致。作为喜剧,显得十分温馨,得体。在剧中作者还巧妙地设置了一只善解人意、又心怀嫉妒的鹦鹉“宝贝”。这只雌性鹦鹉被作者赫然写在了该剧“人物表”里,被当做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是别具匠心的。剧中“宝贝”数次出人意表、画龙点睛式的“点题”,令主人公陷于尴尬,却使剧情充满了机巧,谐趣,增加了这部喜剧“谑而不虐”的幽默,成为“童道明式喜剧”的精彩之笔。
总而言之,《秋天的忧郁》作为喜剧,充满了高贵的文化气息,显得优雅,智慧,知性,从而远离了市井庸俗之气。此外,作者的人文关怀、悲悯情怀,弥漫在《秋天的忧郁》里,无疑也提升了这部喜剧作品的格调。
也算“尾声”
我是否对作品也有不满足之处,对戏的演出效果有所担心?对此无须回避。艺术个性突出肯定是优点。但童先生在张扬艺术个性时,有时可能过于率性了。比如,主人公们每当议及契诃夫和曹禺的作品、议及他们所钟爱的戏剧人物时,往往就刹不住闸,缺乏必要的节制;作者渗入的叙述性成分,内容也未必都是读者感兴趣的,因而剧中人围绕着某些生僻的艺术问题“高谈阔论”时,就难免会被认为并非全是出于塑造人物的需要,而是作者在那里“掉书袋”了。
每当读到这些地方,我就不免要为该剧的导演发起愁来。有人批评童道明的剧本是文人“案头剧”。我以为这并非全然没有道理。《秋天的忧郁》确实还需要接受舞台演出的考验和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