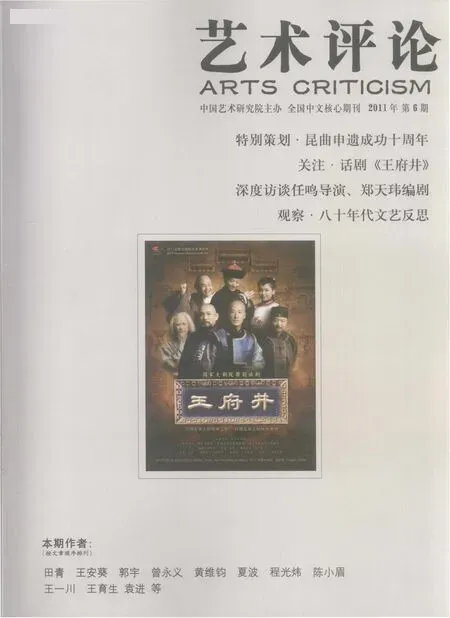光晕下的地貌:80年代中国电影文化走向
左 衡
在反思、怀旧的思潮下,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近年来被不断重述和重估,注定要在中国文化地图上占据重要位置。然而,至少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这句话却必须做两种理解:一种是在艺术思想方面,那一时期所达到的深度和成就,这方面已经为世人基本接受,论述众多;另一种是在文化身份确认、产业转型方面所绕的弯路和付出的代价,这方面则探讨不足。正是由于前一方面的辉煌,一度几乎完全遮蔽了后一方面的艰难和困惑。在天国的炫目光晕下,人们有时会看不清地貌的起伏态势,毅然前行,走入孤绝之境——这对个体无疑是种悲壮,对作为一整体存在的电影而言,则更多的是遗憾。
“代”的意识
70年代末80年代初,谢飞、郑洞天、杨延晋、张暖忻、黄健中、丁荫楠等二三十人成立了小沙龙式的“北海读书会”,在北海仿膳或是某位成员家中吃饭、饮酒、探讨电影的本性,并写下宣言:“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的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莫道海角天涯远,但肯扬鞭有到时。”中国第四代电影人以学院派的面貌进入创作领域,他们对理论的兴趣和运用程度远远超过前辈,他们的作品也明显地向中国电影的传统作别。
当北京电影学院78班毕业、走上电影创作道路时,他们对于传统的态度更加决绝,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更加热切。围绕着78班形成了中国第五代电影人,他们的神话和迷思(Myth)投射在中国电影身上,影响之深,至今未了。短短数年,中国电影界崛起了整整两代,面貌风格迥异。
中国电影开始有“代”的意识并且进行“代”的划分,正始自80年代。此前中国电影人属于几代的所谓划分,不过是削足适履的追认,并且一直没有共识公论,实际上恐怕也不会有。“代”的意识出自寻找归属感的心理。伟人和英雄的年代过去,传统在现代西方面前显得老旧,年轻而又无产无资本的“我”到底是谁?新的电影观念和创作风潮既是应大时代之运而生,同时也是主动寻找、塑造的结果。当第四、五代成为中国电影现代化的标志时,他们制造出与传统之间的巨大代沟。
从电影思潮的角度认识第四代、第五代,把他们的崛起、成名和流散看作一场特定时空条件下电影运动,才更加符合历史真相。正像意大利新写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左岸派、德国青年电影运动风潮过后,不再有群体式存在的作者,第四、五代运动过后,原来的和新出现的中国电影人也不存在“代”的整体身份标志。尽管大众媒体兴致不减地试图以自然纪年而不是思想成果为坐标寻找第六代甚至第七代,有的电影人也浪漫地希冀能扛起第N代的旗帜,但在创作多元化和制作市场化的今天,这种姿态已经远远不是悲壮而是滑稽,只在一定程度上袒露出对电影史学的无畏无知。
第四五代导演在中国新时期文艺坐标上的位置
单从中国电影变迁的时间坐标来看,第四五代运动确实是革命性的,并且革命的实绩空前。但如果承认中国电影是中国现代文艺的组成,是打开国门后受到西方现代电影刺激的结果,那么也应该看到,第四五代成绩的取得并不是天才的产物,而是总体文艺思潮所催生的结果之一。
譬如“伤痕”文艺。文学上始于刘心武1977年的《班主任》,卢新华1978年《伤痕》为这一文学现象命名,此后代表作如周克芹1979年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叶辛1979年的《蹉跎岁月》、古华1981年的《芙蓉镇》等纷纷涌现。“伤痕”一词也被用来命名其它艺术领域的新动向:1979年,以程宜明、刘宇廉、李斌创作的连环画《枫》、高小华的《为什么》、程丛林的《一九六八年×月×日·雪》等为代表的美术作品,被称为“伤痕美术”。同为1979年出现的伤痕电影则有《泪痕》(北影,李文化导演)《苦恼人的笑》(上影,杨延晋、邓一民导演)《生活的颤音》(西影,滕文骥、吴天明导演)。此后,伤痕文学热潮过去,退出大众视野,演进为反思和寻根文学,而伤痕电影则因为谢晋不断深入的精致创作一直延烧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第四、五代电影在叙事方面对传统戏剧的时空结构模式有很大的突破,1981年的《小街》以其强烈的现代感令人瞩目。然而类似的实验在戏剧界也已开始了。1980年由上海工人文化宫话剧团首演的《屋外有热流》(导演苏乐慈)在心理时空的自由营造上有强烈的先锋意识。在视觉方面,第五代的影像造型为电影史学家津津乐道,而如果与中国新时期绘画做一比较,则这种变革也不能算早。试比较1985年影片《黄土地》中老父亲在窑洞里哼唱酸曲的造型与1979年罗中立的著名油画《父亲》,其相似非常明显。80年代初罗中立、陈丹青、陈逸飞等美术家的“乡土现实主义”创作即为中国现代视觉艺术找到了新的表现对象,也以鲜明的民族特点吸引了来自国际的关注。
从上述粗略的陈述中可以看出,第四五代中国电影人首先是新时期中国文艺界的组成部分。忽视这一前提来谈他们的成就不免会高估。从文艺思潮和创作实绩看,总体上,第五代电影思想大体同步于文学,而创作则落后于文学。这其中的原因在意识领域里找不到答案,而必须去物质层面发现。相对于文学的单纯,电影创作需要多个工种合作,每一工种都有复杂的技术手段,而电影技能的获得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训练,此其一;相对于文学的成本,电影生产制作需要太多太昂贵的资源,这也不是刚刚进入电影圈的人能轻易获得的。
但第四五代电影人的迟到从另一些方面获得补偿。首先,他们的创新真正大量进入影院时,舆论环境已经相当宽松,而且业内的批评导向对他们有利。其次,影像的传播和接受毕竟更广泛和容易,所以中国电影反倒先于文学获得了国际影响力。第四五代电影人的海外成功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80年代中后期,全球化进程开始了先导时期,各国文化交流得以更加平等、自由的进行,西方发达国家流露出对所谓东方奇观的兴趣;二,第四五代电影人师承西方现代电影,因此电影思维上便于沟通。炫目的化学反应基于极简单的物理定律。文艺现象的热烈也同样基于简单的人文科学规律。
80 年代娱乐片的遭遇
现在很多人愿意回忆和怀念8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国电影的黄金年代。一个不断被引述的数字是:1979年,中国电影观影人次达到279亿。成就这个神话有太多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因素,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特例。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人的娱乐方式极端贫乏,而且饥渴多年。改革开放后,电影新作涌现的同时,大批中外经典旧片复映,供需双方的关系可谓天作之合。当时计划体制内的放映机制也是一大助力,公益性质的农村放映、露天放映等招致大批对电影充满期待的观众。低廉的票价也使得多次观看电影成为可能:1981年有位老汉竟把戏曲片《白蛇传》看了40多遍!这在今天恐怕是难以负担的消费。
也是同一时期,出现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又一次娱乐片风潮。这从历年发行拷贝数量居前列的影片名单中可以看出:1979年谍战片《保密局的枪声》,1980年惊险武打片《神秘的大佛》,1981年戏曲神怪片《白蛇传》,1982年伦理剧情片《喜盈门》和武打片《少林寺》,1983年武打片《少林寺弟子》,1984年古装武打片《岳家小将》。这一波娱乐片高潮很自觉地追求商业诉求与意识形态的共赢。以当时火爆一时的武打片为例,最常见的两种情节元素是打擂和复仇,前者代表作有《武林志》《武当》等,后者代表作《少林寺》《少林寺弟子》《木棉袈裟》《自古英雄出少年》等。前者反帝,后者反封建。像《大刀王五》《南拳王》更是把维新革命等宏大叙事加了进来。之所以这样做,固然是创作者的历史观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应对各种批评指责的考虑。痛打洋人的民族主义,反抗皇权王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武术、风景等传统文化元素,在武打片中打成一片,成功地赢得当时观众简单而又纯净的心。
然而这波娱乐片生产的潮流却和历史上几次商业电影遭遇一样,虽然观众极其喜欢,却始终没有舆论和理论的支持,相反,遭受到来自主流观念和精英话语的漠视。前者认为,这些影片只是“刀光剑影,拥抱接吻”,“低级庸俗,迎合观众的不健康情绪”,后者往往在引述西方电影人的言论之后指出,娱乐片对电影艺术性和思想性有百害而无一利。得到的批评和责难远远多于褒奖和承认。钟惦先生那种平实、理性的声音在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人愿意倾听。这难道不是另一种中国文化传统吗?正统的儒家文艺观始终鄙视轻视娱乐功能,十七年文艺思想仍然是“文以载道”的变奏,第四五代电影精英们则追求“诗言志”的个体表达。当时的电影热潮与观影人次神话基本上与第四代第五代无关。
电影精英信奉的“作者论”在80年代里长期统治了电影创作和生产,导演中心制是当时大多数电影制片厂的原则。作者论成为新的激进左倾思维,他们既对旧有意识形态批判,对文化传统反思,同时也对娱乐片、对广大观众群说不。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作者至上论未尝不是谋求权力(话语权)的说辞。吊诡的是,他们最早的表达机会和资金,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给的。广西厂郭宝昌、西影厂吴天明两人充分运用了自己的行政权力,把第五代电影人推上了舞台,他们长袖善舞,在扶植艺术电影探索的同时也制定了娱乐片生产计划,从而平衡了收支。
这里不妨与商业片的主要出品国家和地区比较一下。美国新好莱坞、香港新浪潮电影在略早的时间接受了欧洲现代电影的熏陶,从而成功地把陈旧的主流电影语言推进到现代阶段,从而建构起电影产业的主流。几乎同时,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电影人则醉心于电影的个体表现空间和哲学韵味,忽视了主流电影和大众趣味,导致本土电影市场被好莱坞占据。全球化首先是经济一体化,这一前提下,电影产业的经济考量当然是第一位的。欧洲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使得它与美国处在同一竞技场内,经济体本来规模就小,却又不愿也不屑遵从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所先天具有的游戏规则,到了90年代后唯有追悔莫及。
80年代早期到中期,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和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滞后的大众传媒进程帮助中国电影抵挡了一段时间,但无法永远抵挡下去。80年代后期,电影产业的改革启动后,实际的压力促使相当多的电影精英尝试制作娱乐片。滕文骥导演了警匪片《飓风行动》,周晓文拍了警匪片《最后的疯狂》和犯罪片《疯狂的代价》,田壮壮拍了歌舞片《摇滚青年》,张艺谋也拍了反恐片《代号美洲豹》。这些影片的问题倒不在于成功者少,而是创作者仍然不愿接受,艺术片仍然是他们的首选和最爱。当美国的卢卡斯、斯皮尔伯格、斯科西斯和香港的徐克、吴宇森等人相继转型成功、创造出全新的商业片模式时,内地却还在为娱乐片是否低级争吵。
由于没有做好迎接市场挑战的准备,电影产业改革启动后,第四五代电影人丧失了制片厂方面主要的资金来源,又无法得到市场的充分保证,必须寻找新的创作资本。张艺谋的《红高粱》提供了一种模式,即先转战海外获奖,再杀回本土。但这等于放弃了本土观众,也无法长久吸引国际眼球。展示东方奇观也好,咀嚼中国社会边缘也罢,一旦做成了唯一的卖点,也就没出息到了极点。
在娱乐片与艺术片的两级之间,被认为是第三代的谢晋成为当时中国电影真正的神话。他创作于新时期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等影片屡屡创造上亿的观影人次,观众用上万封来信,甚至血书、万言书来表达他们对谢晋作品的热爱。现在看来,谢晋作品奇妙地把中国民间文艺的叙事传统和人物身份设置同现代社会学和心理学融合在一处,它们既是古典的,同时又流露出现代气息,通俗而毫不庸俗,这是同时赢得普罗大众和知识界喜爱的奥秘所在,也恰恰是主流电影最重要的原则和最难达到的境界。令人吃惊的是,谢晋及其作品在1986年遭到上海文艺界的激烈的攻击,“煽情”、“俗”、“五四精神大步后撤”、“中国电影的悲剧现象”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判落到谢晋及其影片头上。学术话语是新式的,文风还是大字报。最后,还是钟惦先生不温不火的文章掀过了这一页荒唐。在今天,当我们视野里只有恶搞戏说闹剧、山寨大片和生冷的所谓艺术片时,谢晋的神话已经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延续中国电影的本土传统。
80年代最后一个娱乐片现象出现在1988年,这一年时称“王朔年”,这位“痞子文学”的开创者有四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一时间巨大的斥骂声从文学界蔓延到电影界。然而王朔作品之所以受追捧,只是当时社会文艺走向的一种结果。因为我们今天可以看出,王朔作品也达到了一种诡异的平衡。一方面,是他对社会灰色面的批判姿态,这种姿态与精英们思想者的面貌非常不同,但却因其冷静自嘲和尖锐讽刺赢得更年轻知识者以及大量平民的激赏和共鸣。另一方面,王朔作品具备了一些商业元素,语言的快意调侃,故事的曲折,人物的本真,这些都更加符合大众口味。不知道是王朔太狡猾,还是一些知识分子太不明智,他同时拆解了旧有的意识形态话语和精英话语,同时激怒了原本处在对立面的两方,结果在王朔的拥趸看来,批判王朔反倒成就了他的智者形象。从大众文化的立场看,王朔的问题不在于反动和流氓,而是他过于彻底的拆解使得很长时间内没有关于主流价值观的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表达,后者本来是大众希望在文艺中得到的。
中国电影市场化和产业化过程至今没有完全结束。80年代的半市场阶段是最艰难、最危险的,因为两种规则并存,反倒会出现两种规则都无法保证的局面。作为个体的创作者深受其害,黄蜀芹导演的娱乐片《超国界行动》大卖特卖,她本人却没有得到回报;喜剧明星陈佩斯创办私营电影公司,也用到了现在所有的营销手段,但由于市场不规范、监控未建立,终于无法维持,从此退出影坛。各地方制片厂的萎缩,私营电影企业的艰难起步,与央企的集中程度加强,构成了中国电影产业进程的主线,也是整个文化产业进程的写照和缩影。
电视与录像厅
我们过去往往把中国电影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危机和问题,简单归结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见解至少不全面。如前所说,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出现过相当不错的娱乐片和艺术片。当然从长远看,计划经济体制有时会不利于电影产业化和现代化,但在那个时候,这两者的关系并没有对立到不可调和。相反,计划体制过快的退出和生产销售被过快地推向市场,倒使得中国电影措手不及。
实际上,当时对中国电影行业造成直接冲击的,是电视和录像厅的普及。曾经发生在美国、欧洲的媒体变革,终于在20年后,在中国同样发生了。这种冲击是摧毁式的。电影必须重建属于它的家园。美国人建立了电影分级制,用小众、分众策略对抗大众化程度更高的电视;同时,采用巨片策略,用技术来造成观影和收视无法弥合的视听差异,从而留住观众。实践和时间都证明,这两种策略是后来好莱坞得以自保进而攻占全球市场的法宝。所以,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最大的命题不是如何同过去决裂,而是怎么同电视竞争。由于我们当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它已经蜕变成很多问题,如:中国电影的科技水准,电影电视社会传播功能上的分工,中国电影观众对电影电视差别的态度,中美电影的差距,等等。
几乎同一时间,录像厅在内地迅速普及。电影观众获得了一种观看电影的新渠道。大量的港台电影电视录像进入,打开了内地电影观众的视野。大众发现港台的娱乐片更加精致、现代和刺激,他们毫无困难地给国产娱乐片打了较低的分数。社会现代化程度对文艺创作生产的影响再一次得到证明,今天内地影视行业规模虽大,在现代化和专业化程度上仍然不及港台。
至此,通过录像媒体,因为历史原因导致隔绝分裂的华语电影终于有了整合出一张文化地图的可能,尽管在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内地发展出的乡土结合革命的传统,台湾发展出的文人结合历史的传统,香港发展出的市井结合都会的传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形貌各异、理路不同的思维和经验。整合格外艰难,但也格外有价值。但如果我们不能科学理性公正的看待这些已有的传统,而是固执其中,那么还是会出现话语对事实的遮蔽。
对于行走的人来说,地貌永远比光晕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