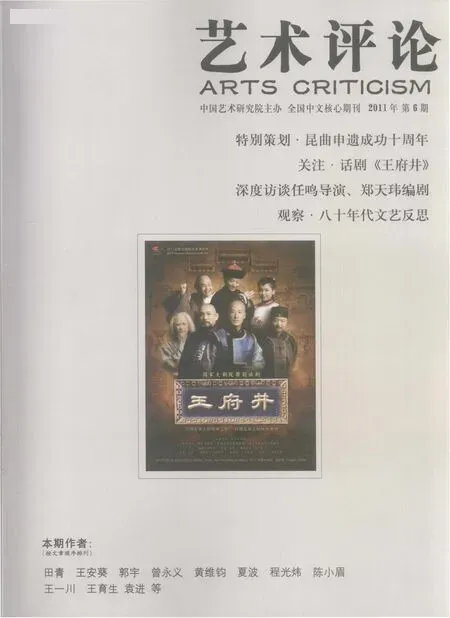序《曲韵兰庭》
曾永义
2004年2月间石头出版社所制作的《长生殿》在新舞台演出,4月间白先勇和樊曼侬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家戏剧院演出,都非常轰动,一票难求。圣诞节前后,国光剧团首部《梁山伯与祝英台》昆剧由本人编剧,由本地演员在国家戏剧院演出,居然造成十九天之前票房净空的纪录。于是戏曲界兴奋地说:昆曲在台湾已生根矣!昆剧在台湾已成立矣!
我常向学生说:昆腔曲剧是中国最优雅文字和最精致艺术的结合。其歌舞乐的完全融合无间,使得一个成功的演员必须集戏剧家、歌唱家、舞蹈家于一身,必须深切领会曲词,将其意义情境,透过肢体语言和歌声音乐旋律的诠释与衬托,在虚拟象征的表现程式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所以昆腔曲剧堪称为我国艺术文化的瑰宝。
昆腔曲剧的源生和形成
那么这堪称为我国艺术文化之瑰宝的昆腔曲剧又是如何的源生和形成呢?这是学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个人探讨所得是:作为“腔调”而言,只要昆山有居民、有语言,就会产生具有一方特色的“腔调”,但一般只称作“土音”或“土腔”;必须等到具有流播他方的能力,才会被冠上源生地作为称呼而称“昆山腔”;至若见诸记载者,则其声名与影响必已相当可观。而腔调之载体为语言、为歌谣、小调、诗赞、曲排、套曲等,又必须通过人之发声器“口腔”传达出来,则腔调的提升也必须经由某声乐家“唱腔”之琢磨。因此,就昆山土腔而言,其源生必与当地人群相源起。记载中的“顾坚”乃元末之声乐家,曾以其“唱腔”改良过昆山腔;而“周寿谊”所歌的“月子弯弯照九州”,正是以歌谣为载体所呈现的昆山土腔,所以明太祖视之为“村老儿”,而他既以高龄生于宋代,则可视此“土腔”于宋代即已如此。
昆山腔在明代正德之前,和海盐、余姚、弋阳等腔调一样,都只有打击乐,祝允明甚为不满,由于他是同属苏州府的长洲人,所以对昆山腔“度新声”有所改革:他的改革应当偏向散曲为载体的清唱。另一位长洲人陆采更作《王仙客无双传奇》,从戏曲上提升昆山腔艺术。这样的昆山腔在嘉靖间已经有了笛管笙琶等管弦乐伴奏,而且在邵灿《香囊记》的影响下,如沉采、郑若庸、陆采等也附庸而兴起骈丽化的风气。于是昆山在与海盐、余姚、弋阳并列为南戏四大腔调之余,用昆山腔来演唱的明代“新南戏”剧本,被吕天成改称为“旧传奇”,而著录在他所著的《曲品》就有二十七本之多。这时的“昆剧”或“旧传奇”都已趋向优雅化了。
到了嘉靖晚叶魏良辅和梁辰鱼更衣钵相传地作为领导人,为昆腔曲剧更进一步的改革,创为“水磨调”,那是“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的腔调。我们现在所谓的“昆曲”、“昆剧”,其实指的就是昆山“水磨调”的嫡裔。
魏良辅将“昆山腔”改良为“水磨调”,是通过与同道切磋和对乐器添加改良而来。其同道可考者就有二十五人。他们又加入三弦、筝、阮等乐器,使之成为以笛为主的管弦众乐合奏,一方面强化了“水磨调”的音乐功能,一方面也解决了“北曲昆唱”的捍格。
梁辰鱼直接继承魏良辅衣钵,由于他为人风格风流豪举,精于度曲,一丝不苟,名声大著;虽然同时的汪廷讷《狮吼记》、张凤翼《红拂记》、高濂《玉簪记》等也都以昆山“水磨调”演唱,但终被梁辰鱼所创作的散曲《江东白》和戏曲《浣纱记》所淹,而独享“昆剧开山”之名。而此后用昆山“水磨调”来演唱的戏曲,便被吕天成《曲品》称作“新传奇”,也是今天我们一般所称的明清传奇。
由以上可见,就“昆腔”而言,实经历“昆山土腔”、“昆山腔”、“昆山水磨调”三个阶段。“昆山腔”如就元末顾坚首度改革算起,迄今已六七百年;如从祝允明(1460-1525)再度改革算起,也有四五百年;而从魏良辅约在嘉靖三十七八年(1558-1559)第三度完成改革为“昆山水磨调”,距今约四百五十年,他主要用来歌唱散曲;梁辰鱼约在嘉靖四十年前后著成《浣纱记》传奇,若以他使用“昆山水磨调”来演唱传奇而号称“昆剧”,则也差不多有四五百年。
两岸共创昆腔曲剧新局面
像这样在我国流传四、五百年以上的昆腔曲剧,不只集我国戏曲文学音乐艺术之大成,而且对于往后滋生的地方戏曲剧种,提供了所需要的营养,因此昆腔曲剧也堪称是“百戏之母”,则其历史地位是何等的祟高,其艺术价值是何等的贵重!也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5月18日公布“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十九项中,中国昆曲亦被列入其中。这些获选的文化遗产,将可向联合国申请经费,协助保存,并振兴这些传统,以免消失在时代潮流之中,则昆腔曲剧已被人类列为必须保存的共同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人,焉能不更加重视而努力薪传!
然而若抚今追昔,昆腔曲剧之所以能有今日的局面,实有赖于两岸有心人士二十年来的共同努力。
昆腔曲剧虽然优雅和精致,但也不免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就大陆而言,如果不是1956年浙昆以一出《十五贯》为当局所赏而轰动海内,昆剧恐怕难以起死回生;如果不是“文革”浩劫之后,六大昆剧团在政府扶持之下,重拾旧业、培植新秀,昆剧恐怕也已成余烬残灰。就台湾而言,如果不是徐炎之、张善芗伉俪,“一笛横吹八十年”,一骑单车,怀抱昆笛昆谱,在北一女、台大、政大、文化、东吴、中央、中兴、艺专、铭传、西湖、复兴、华岗等校园中,无阻风雨,来往奔波,循循善诱,使弟子视之为师傅、奉之如父母,而有“ 昆曲同期”清唱雅集迄今一千数百期,而有“水磨曲集”业余剧团时作演出,则昆腔曲剧恐怕也难能一脉东传。
然而在外来文化的冲击里,在急遽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无论如何,两岸的昆腔曲剧总是知音难得,观众零落,年轻人甚至视为“畏途”。
直到1990年7月间,酷爱昆曲的贾馨园小姐举办“昆曲之旅”,集合同好到上昆观赏演出,洪惟助教授与我同行。在五个夜晚里,我们观赏近二十出戏,戏中包含各种角色的绝活,我第一次看到如比古雅优美的舞台艺术。在激赏感佩之余,我邀请上昆成员餐叙。其中好几位得过“梅花奖”的一级演员,都说年已近半百,艺术已到个人顶点,往后只有“每下愈况”,很难再有突破和提升。而他们的“艺能”无法像博物馆中的“展品”,不得已只能录像保存,可惜计划未达,经费无着,徒叹奈何。
听了这一番话,我们不禁黯然。因为像这样精美绝伦的民族艺术,理当世世代代相传,纵使难以再度融入民众生活,起码也要像日本能乐、歌舞伎那样作“动态文化标本”,活跃于国家艺术殿堂之中;而对于那些身怀绝技的艺人,更应当即时“抢救”他们的绝活,使之薪传不辍,使之透过镜头永存人间。有见及此,我们返台之后,就积极进行两件事,一是成立研习班,一是录像工作,都由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筹划和执行,文建会则支持经费和验收成果。
昆曲研习班于1991年3月成立,分高级班、初级班、笛子班,学员几为大专院校学生和各级学校教师,后来也有意安排名额,训练国光、复兴两京剧团的演员。授课老师皆为两岸名家,更多的是大陆著名演员。十年间我们举办六届,培养了数百名学员,洪惟助教授将学员成立“台湾昆剧团”,活动力相当好。我所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昆剧,也多亏他们担纲演出。
录像计划于1992年6月完成前期计划,录有上昆、浙昆、传字辈老艺人之绝活二十九剧六十三出;后期计划于1997年1月完成,录制南京昆剧院、苏州苏昆剧团、浙江杭州昆剧团、湖南郴州昆剧团、北京北方昆曲剧院的代表性剧目计四十五剧七十二出。这两度录像共录一百三十五出,可以说把大陆六大昆剧团的经典剧目都搜罗在内。我们使用三机作业,经过剪辑,配上唱词字幕和剧情说明,使之成为可供观赏、教学和研究的影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友工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国戏曲美典初论——兼谈昆剧》里,有这样的话语:“昆剧录像计划,首集共十七卷记录了上昆和浙昆演出六十三出昆曲折子戏,造福全世界的戏曲研究者,贡献可以说是永垂不朽了。”高教授还谦虚地说,他这篇文章“若没有这套《昆剧选辑》,显然是无法完成。
当我们正努力于昆曲研习班和昆剧录像工作的时候,新象基金会的樊曼侬女士则于1992年10月使上海昆剧团成为第一个“登台”的传统戏曲剧团,翌年浙昆亦获来台;贾馨园女士也同样不惜血本的要培养昆剧人口;于是苏昆、江苏昆乃至永嘉昆、湘昆、北昆,在两位女士主持下,都来台公演过,使昆剧流派都能呈现于台湾。其间1997年11月间五大昆剧团在台北连演十一天十四场与2000年12月11日至次年1月14日的跨世纪全球昆剧大展,是樊曼侬的两度壮举,也成了两次年度艺文大事。从而使得昆剧的观众在国家剧院里,由五成、六成、八成、九成而至于近几年来的满座。而这期间学界领袖许倬云院士、文学泰斗白先勇教授也加入对谈昆曲、对谈《长生殿》、对昆腔曲剧的推广,更起了风吹草偃的作用。
回顾二十年来昆剧在台湾,由于政府、学界和热心人士的推广,在两岸合作之下,已经培养了许多观众,水磨曲集之外,也成立了台湾昆剧团和台北昆剧团。于2000年4月更以“台湾联合昆剧团”赴苏州参加大会演,博得许多好评,我当时就宣布昆剧艺术已在台湾奠立;而这十年来,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美好,不只“昆剧事业”蒸蒸日上,而从事昆剧艺术的,更如雨后春笋,已经有十几个团队,就中以兰庭昆剧团最为杰出,其创意新颖,佳作连连,不只广受好评,而且屡屡获奖。这次北京昆剧汇演,它是台湾唯一受邀的团队,其所提出的《狮吼记》和《长生殿》两本经典是他们精心的改编,相信北京的观众都会刮目相看。而其《曲韵兰庭》一书,是希望使北京的观众了解昆曲艺术在台湾发展的轨迹特色与现况,因此我在本序中也“敲边鼓”似的予以呼应。而最后我要自我吹嘘的是,我既为此次兰庭总顾问兼与会领队,拙编昆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江苏省昆剧院也把它当作此次与会之代表性剧目于5月12日夜在北京大学演出,则我是何等的荣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