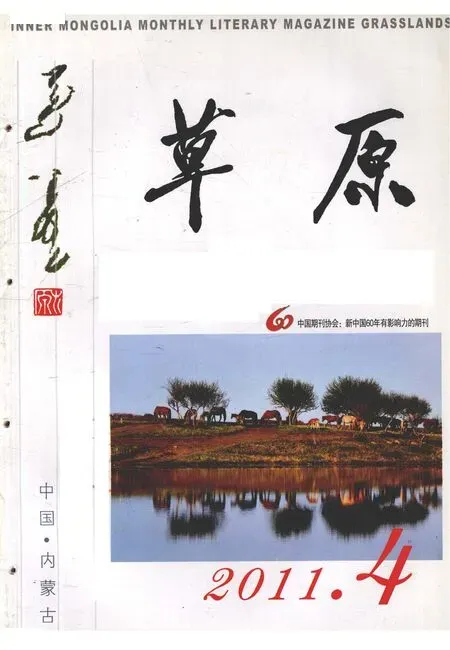那年·那狗·那故乡
□侯伊玲
那年·那狗·那故乡
□侯伊玲
远山、白雪、矮屋、炊烟,我又将回到那远在塞外边镇海流图的家了。每到大雪纷飞的季节,家乡的一切便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我知道,无论我人走得再远,灵魂依然留在那片荒凉的土地上,那里的日日夜夜已融进了我的生命,我怀念健在的、逝去的一切……
大白狗没有名字,它来到婆婆家是在十几年前的一个寒冬。一天清晨,北风卷着鹅毛般的雪片呼啸着,仿佛世界都被冻住了。零下四十多度的气温,是这个塞外边镇冬天常见的天气。那天,婆婆准备上早班,突然听见一阵清脆的敲门声,她赶忙裹上棉衣打开院门,昏暗中,一只雪白精瘦的大狗立在门前。那白狗细瘦的四蹄插在冰冷的雪地中,身体不住地在寒风中哆嗦,暗红的舌头呼出一缕微弱的气息,仿佛是为了证明它仅存的体温。它用哀求的眼光怯生生地看着婆婆,仿佛在说:“我饿,我冷!”
“猫来穷,狗来富”,这是只念过两年级书的婆婆朴素的“唯物论”,大白狗的出现冥冥中让婆婆感到温暖。她连忙闪身把大白狗领进屋,赶紧弄了些热腾腾的吃的,饿极了的大白狗吃完后,依着炉灶团起了瘦弱的身体,像块发足了的起面,舒服地摊在地上很快便睡着了。
令全家人没想到的是,从此大白狗就成了这个四口之家的一分子,它不仅是看家护院的好手,还成了婆婆的“贴身保镖”。
婆婆工作的小镇车站每天清早6点上班,从家里到车站,要走十几里的土路,还要翻越一道大土坡。对于年已50多岁,一辈子也不会骑自行车的婆婆来说,这是每天都要面临的一道考验。她独自一人走在荒凉的大坡路上,全家人都非常担心。尤其到了深冬,雪厚路滑,很是危险,家人都希望她提前退休。可为了孩子们,她固执不听。大白狗来到家中的第七天,婆婆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突然,发现大白狗紧跟在身后。大冷的天,婆婆坚持撵它回家。但一次又一次,大白狗像铁了心似地从身后跟上来,目光坚定地盯着婆婆。婆婆没办法只好任它跟着。上坡下坡,大白狗呼出的寒气像霜雪一样挂在头面上。每遇到有坑洼的地方,大白狗一个箭步冲上前,引着婆婆绕开。十几里的土路,大白狗一直把婆婆送到汽车站。到了单位,婆婆招呼它回去,仿佛能听懂话的大白狗冲着婆婆摇摇尾巴,按原路返回,转身时像一支银色的箭飞快地消失的茫茫的夜色中。
从此,大白狗每天清早都要送婆婆去车站上早班。婆婆心疼它,关上门不让它出来,它情急中用两只前蹄抓住门板,叫声凄惨,连绵不绝。没办法,婆婆只好带着它走。
海流图的冬天,地上积雪常有一尺多厚。大白狗四条腿和整个身体都没进雪中,只露着径直伸长了的脑袋,穿梭在一望无际的雪地里,为主人冲出一条前行的路。
五年间,大白狗就这样默默地陪伴着婆婆上早班。大白狗和婆婆成了那年月、那小镇、那道山路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有了大白狗的时光里,婆婆觉得日子过得飞快。
我是与爱人恋爱时听到这个故事的,于是就一直很想见见那条知恩图报的大白狗,但爱人说那白狗护主认生,生人进院它会狂叫不停,急了还会扑上来撕咬。第一次去他家,我提心吊胆,又有点按耐不住内心的兴奋。走进院子的一刹那,我看到了那只传说中的大白狗。全身皮毛雪白,性格温顺,它昂首挺胸、目光迥然地注视着我。我努力怀着一颗自然的心魄走近它,它直直地站立在原地,仿佛在时光的隧道里已等待了我许多年。没有听到丝毫叫声,我们相互注视着对方。这时,婆婆迎出来,大家都奇怪大白狗的反应,婆婆继而微笑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亲切地对我说:“它认下了你是咱家的人!”
婆婆一边领我进屋,一边惊异地说:“你大舅是家中常客,天天来,天天喂它,它不但一口不吃,反倒咬他咬得更凶了。”爱人在一旁补充道:“大舅,每每酒后涨着红脸找父亲排解心中郁闷。我估计,大白狗可能误认为大舅在与它的主人争执不休,对主人不恭。于是,便一跃而出,呼之扑之。”由此说来,大白狗还是一位护主的 “侠胆忠义”之士!这时,从厨房中走出的小姑子也惊诧大白狗面对生人的到来 “从容”、“淡定”的表现。她一手捂着嘴笑弯了腰,一手拉着我娓娓道来:我大哥上学时就是有名的校园诗人,好几个女生仰慕大哥,于是以借书、问题为名上门找他,结果都在大白狗一阵狂扑乱叫的“轰炸”中,一个个夺路而逃。小姑子边说,边冲着他大哥诡笑。就这样,许多故事还没有展开,便就画上了句号。我和小姑子都心照不宣会心地笑了。得到充满灵性的大白狗的认同,我就算正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了。
由于第一次的友好接触,从心底我喜欢上了这只充满灵性的大白狗。为它的忠贞,更为它的慧眼,让我与它相遇、相识,我开始深信人与动物之间是有灵犀相通的。我顺利地走进了我一生最温暖、最和谐的家。然而,就在我和爱人离开家乡的第二年,大白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一年,家乡大旱,夏日酷暑炎热,大白狗把水桶弄翻了喝不到水,忙碌了一天的家人下班走进院落,却没有像往常一样看到大白狗欢天喜地地迎出来。找遍了院落,也没有见到大白狗的踪影,全家人立刻感到很意外。夕阳下,婆婆房前屋后,一遍又一遍地找,仍不见它的踪影。“大白白!大白白!!”踉踉跄跄地走着呼喊着。小姑子后来对我说,那一瞬间,婆婆就像离开了自己最疼爱的孩子,更像丢失自己一样悲绝、茫然。最后,在井边看到了大白狗的蹄印,全家人马上明白了……打捞不上来它,只好将小姑子放进篮子系到井底,小姑子哭着抱出了已死去多时的大白狗……
站在故乡的地头,我怀望小镇那条通往车站的土路,空寂的院落,我知道,我已经无法找回从前。
那一年,井封了,婆婆也退休了……
〔责任编辑 阿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