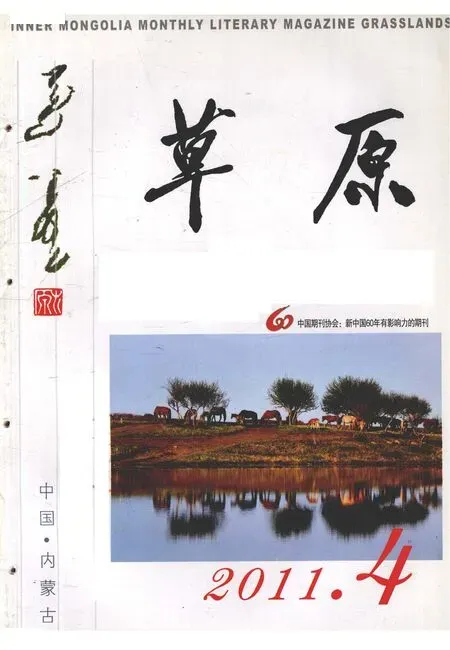散文三篇
□汉 梓
散文三篇
□汉 梓
流淌二十八年的美丽
老婆跟他二十八年了。
刚一开始时,觉得她还可以。红扑扑的脸,脖子虽然短了些,头发也有些稀疏,但梳在脑后的笊篱把小辫儿,翘得还蛮有一种劲气。她的眼很大,但上眼皮有些鼓,让人看上去有些紧绷绷的气氛。
刚嫁过来,远门一个兄弟与她逗,说了声“牴牛眼”,那一阵上牙咬住下嘴唇喷出的唾沫星子,他得借一把雨伞才能遮住那兄弟。
真的,家里穷得连一把雨伞都没买过。新婚燕尔,他们还是浪漫了一回。
他们去了趟早就是省会的石家庄,逛了回中山路的人民商场。她帮他挑了身上海服装厂出品的警蓝的卡外装,也就是跟当时的警察制服款色一样的衣裳,花了二十几块钱。她要了两条白底蓝方格的褥单,好像还不足十五块钱。
他想,往后的日子,风里来雨里去的。不像娘,一辈子没干过多少农田的活儿,五八年大跃进捉懒汉,娘才被迫去深翻了几天几夜的地,秋雨绵绵,总披着爹让给她的一张用石灰水泡制过的老羊皮。
他有老婆了,自家还有了地,该给她买件雨衣。绿色的,正品的,细帆布内挂胶里军用雨衣,才二十几块钱。
她就不买。他说,“今儿不买,这辈子恐怕也穿不上了。”
她说,“俺在队里干十来年活,没穿过那东西!”
是年她二十四岁。
八三年一个女儿,八四年一个女儿,八六年又生下三女儿时,她哭得倒噎了气 。
娘当时虽已病重,却还有说话的气力。劝她,“闺女也不赖,也是你两口子的福气。”老婆不受劝,哭得更伤心了。
后来计划生育大突袭,省里来检查,全县的乡镇干部、公安、法院、计生委,加上县直机关各单位,总共不下三千人的队伍,入夜把一个不足三百户的小村包围得水泄不通。
他都吓傻了,更不能明白,老婆挺着快七个月龄的大肚子,怎么就能翻过大队部的院墙,闪过村边上几乎能手拉起手来的包围圈,潜入村东黄了梢的麦田里,躲了整整三十六个小时。
下午还在起拔满是棉桃的花秸,准备抢种最后一块麦子,到晚上十点半,就生下一个七斤多的胖小子。
她说,“这老生子了,跟拉泡屎一样,不用找人。”
娘前一年去世了。
她在炕上一边呻吟,一边指使他,备下白酒泡过的扎脐带绳儿,酒火烧过的裁衣裳剪刀,缠肚脐眼儿的口罩布……当他捏着小脚丫提起满身羊水的孩子,让她听那一声哭时,她确定自己有儿子了,如释重负地一声长叹,两眼合上,却泪流满面。
他说:“咱应该高兴。”
她说:“是,可我不是为你,是为俺娘家姐妹们争脸。”
因为她八姐妹嫁出的三个都只生女儿,小妹们的婚事早为此受人挑剔了。
还真让娘在早年就说中了。四个孩子仨大人,最后分了十几亩地,那日子再穷,也比连老婆都没赶上分地的一家四口二亩田的日子好弄多了。
可真实的日子,是计生罚款把牛尾巴都割下来交出去了。
还有孩子们上学的学杂费年年在涨。老师逼孩子回家帮爹干活挣钱交保险,她黑了眼圈儿跟人吵:“不知道使用童工犯法?……你还老师哩!”
西风呼号三九天,老婆腰前缠了麻袋片,跟他上山开石头;闷如蒸锅三伏地,玉米叶子刷脸蛋儿,蹲下麦茬扎屁股,撅起屁股来,颈后的汗水直往脸上流……从麦茬里抓起成片的马唐草,把草根翻搭在麦茬上,她的手,不是血肉模糊,就是老皮纷飞。
儿子的新婚之夜,老婆在梦呓中都是劳累的呻吟。老婆的头发越来越稀,红扑扑的脸蛋儿换上了一张油腻腻的黄皮,短脖子间的赘肉不知啥时都瘪了,亲一口全都是咸呼呼的粘皮……
他在灯前看一本什么破书 。她在被窝里强忍着龋齿留下来牙根的疼痛,不时探出几近秃顶的头来,把头前放着的一大瓢生凉的水大口地啜饮。
她说:“火牙,冰一冰,拉泡稀就能泻下去。”
比以往,日子是真好起来了。她已学会了天天刷牙。而且就是这治牙疼的凉水,也盛在金黄晶亮的大铜瓢里。
他坐在书桌前,且不去看她,只听得咕嘟咕嘟喝下凉水的声音,忍不住眼睑一眨,睫毛间闪过一道大铜瓢一样金黄的晶亮……那不是折射灯光的泪色,而是老婆在他心田上流淌过的美丽。
老鼠节与柏翎火
正月十二,俗谓老鼠节。入夜,鞭炮齐鸣,万家灯火,爆竹惊天,礼花璀璨,大村小镇,各家门前,篝火熊熊,老少开颜。
老鼠节,起源不详,愚以为当起于《晏子春秋·问上之九》:“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可见鼠于国运家道,瘟邪奸狡是也。其托庙墙神器,灶堂仓廪,投鼠忌器,无法除灭。每于佳节新春,祈年开岁,所忧鼠患,百姓咸忌,不知何年何代,始有人家门前笼火,退小人之阴鸷,祛瘟邪之所害。凡此民俗,或由乡巫所起,或由官祈流变,史料不详,概难确认。
如果单凭记忆,在我二十五岁以前,也就是1980年以前,农家门前还舍不得装电灯,更甭说现在的大红纱灯。早年春节,在门前挂的纸方灯笼,已都在“文革”之初被当封建“四旧”砸烂了。大队电工在沿街线杆上装的路灯,一般也只给亮到正月初五,之后的街巷,入晚都是黑咕隆咚的。只有正月十二的晚上,家家门前篝火,阖家拱暖,添薪加柴,禳灾祈福。便是在“文革”之前,除了大村集镇上有龙灯社火,山村野堡,几十岁的人连个礼花炮都没见过。
最早的记忆中,每年正月十二,母亲都会把晚饭做的早一些。吃过晚饭,不待天黑,父亲就把高粱秸、玉米秸之类堆到街上,等母亲洗刷完毕,我早与姐姐妹妹在门前的石板台阶上跳得额头冒了汗。天渐黑下来,我只要看到父亲拿着小板凳,脖子上挂了长烟袋,从院子里往外走,我会像猴子一样连蹦带跳地钻到门后边,去拽早就备下的一大捆柏翎。姐姐妹妹也会帮着母亲把一年积存下来的荆条、柳条、秫秸颈杆儿编制的旧炊具,漏了洞的蒲草锅帽子,统统搬到父亲点起来的火堆上。
火旺起来,母亲说,燎了杂灾病恙,火旺日子越旺!
街上通明,家家火旺,父亲说,火旺日子旺,红火好年景!
我把柏翎分着一枝一枝往火上添。姐姐把一枝柏翎烤热了,在我们一家人的身上,从头到脚逐一扫过。姐姐边扫边说,柏翎柏翎烤烤,明年换一件新袄;柏翎柏翎扫扫,百病吓得快跑。
柏翎在火堆里燃烧着嗞嗞咂咂地响,噼噼啪啪迸着一簇一窜的火星子,阵阵沁人心脑的香气,氤氲心田,氤氲街头,氤氲夜空。
去,烤百家火,添百家福!母亲撺掇我们去烤别人家的火。街上的孩子们东奔西突,欢呼雀跃。这时手上要有一把鞭炮,每到一家门前便投进火里两枚,“噼啪”爆响,该是多么惬意。便是把火堆另一边的老祖奶惊个倒仰,也不过被骂“你——嘻,小兔崽子!……头遭拜你丈母娘,准得忍不住放响屁儿!”可惜我与大多数男孩子一样,父亲过年只给买两把小炮儿,一把响在大年五更,一把响在初五黎明(谓之“破五”,也叫“震五穷”)。
村上当然有放二踢脚的,但是很少。多数人家街前火光明亮,院里幽幽香烛,一种神佛素习的静谧,藏在院门向里的深处。
待我们烤过百家火回来,父亲坐着小板凳,在火苗渐熄的熟火前抽他的长烟袋。母亲把大年五更供神剩下来的枣花大卷,还有黍米黄面的年糕早烤好了。一家人分吃着酥脆的饶有焦煳与柏翎香味儿的年食儿。妹妹就向父亲打问,老丰大伯说,今儿是老鼠节,半夜以后,鸡叫以前,男孩子嘴里含了驴粪蛋儿,到磨坊里,耳朵贴在磨眼儿上,就能听到老鼠娶媳妇儿,笛儿喇叭的,还放三眼枪呢!还说——不让小闺女听;要哥哥不含驴粪蛋儿,能不能听见呢?父亲禁不住笑,却给我们讲起另一个故事。
说是关公关老爷,山西蒲州人,原本天上火龙。不知玉帝听谁谗言,说蒲州人,穷不贤,富不仁,人道禽兽,伦常伤败,要火龙下凡,烧尽蒲州官民。火龙下凡,先往玉泉山玉泉寺探问。玉泉和尚嘱他,自去察看一番。火龙便化作一孤身少妇,于荒郊野路拦车搭乘。遇一富商,锦帽貂裘,香车骏马,轻尘遥至。少妇佯作脚病,求与搭乘,车主竟是让车自步,直到蒲州城下,更无丝毫轻慢。火龙深感其德,道出行藏原委,并嘱蒲州百姓,于正月十二入夜,各家在街上笼起大火,以惑天庭。嘱罢回见玉泉和尚。和尚知他心动恻隐,律犯天条,后必被斩天庭。便在寺中备一大瓮,内垫黄纸新棉,问斩当日午时,摆在寺院当中,接下龙血一团。和尚覆以黄纸,供之佛前,柏翎文火在下烘暖,每日焚香祝颂,七七四十九日,化育成婴。是为关老爷,天下第一义士。
这故事在我心中憋了几十年。今又正月十二,万家灯明,礼花祥瑞,篝火映天,柏香氤氲。不禁想起父母,街坊老辈,扛着那个时代,生计维艰,悲辛一世,犹给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生活,留下许多动人且温馨的回忆。
现在柏翎是越来越少了,五块钱只能买到一小把儿。如果冯骥才先生建议申报中国春节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得实现,我更建议园林部门,为正月十二多种些柏树。
童年的冬夜
夜
在1961年的冬天,父亲去修水库,不在家,母亲摇着纺车哄我们入眠。半夜,妹妹醒来,饿得哭叫。母亲用三块砖头支起个三只尖脚儿的小锅。家里一点能吃的油星也没有,秫面糊糊倒进去就巴锅。幸有下秋从渠岸上捡回的蓖麻子,剥皮捣烂了,拿白布包成枣儿大的块儿,向锅底上擦出油光,碗口大的秫面咸食,才能摊出三五张来。妹妹吃两个,我吃三个,姐姐的肚子咕咕叫,却一个也不肯要。为此,我的启蒙老师直到去年去世,也不明白他教“孔融让梨”的典故时,我竟旷了几天的课。
纺 线
棉条在母亲的左手,中指、食指、拇指,轻捏着出线的一头。另一头弯过无名指、小指,向外翘着,长短粗细正像一条猫尾巴。纺轮被右手的搅把儿摇动,嗡——嗡——嗡,正转三圈儿后,线子被锭子尖儿从棉条中拉出够长。嗡,紧切地倒转半圈儿,母亲的左手在一起一落之间,将二尺多长的棉线射在线穗上。没数过二两半的线穗,要这样射上几次才能够个儿。只知道纺一斤线子五毛,买成洋油能点灯多半年,买成咸盐,够一家吃两个月。
催 眠
母亲不知道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有个小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母亲给我们讲的,是“门墩墩,钌铞铞,开门来,娘到喽……”要不,就还有“货郎担儿哥,货郎担儿哥,上坡下坡你等等我……”。其实,催眠的不是这顶级而地道的童话,是嗡——嗡——嗡的纺车声。妹妹总比我先睡着。待我睡一觉过来,要是听不到纺车声,那就是先睡在姐姐被窝里的妹妹,光着屁股被母亲掏出来,正往红泥瓦质的尿罐里把尿。
尿 炕
后半夜油灯熄了亮。老屋的土墙,泥皮簌簌地落着土末。老鼠在檩条上椽间儿里啃着苇箔,咯吱咯吱作响。神灵降临,总带着夜的肃穆;鬼怪入梦,反穿着缀满星光的衣裳。孱弱的我,不敢爬下炕来,向系着草绳的瓦罐里撒尿,憋在被窝里,又睡着了。梦见一个仙子,带我到一个花园。到处是穿红戴翠的仙子,傍花依柳,荡着牵牛藤的秋千,簪着蒲公英的金黄,有的还手绢招摇,裙裾飘飘地追逐嬉戏……我紧尿得又急又臊。找不到院门,根本也没有院墙,花木矮矮的,满地阳光 。最后,我攥住一簇枸杞的枝条,不敢看是否有人在看我,自以为拿手里的枝条影住了,就用另一只手把小鸡儿捏起来,好像并不知道穿有短裤还是长裤,……结果是,第二天,母亲在阴冷的冬日里晒炕。
〔责任编辑 阿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