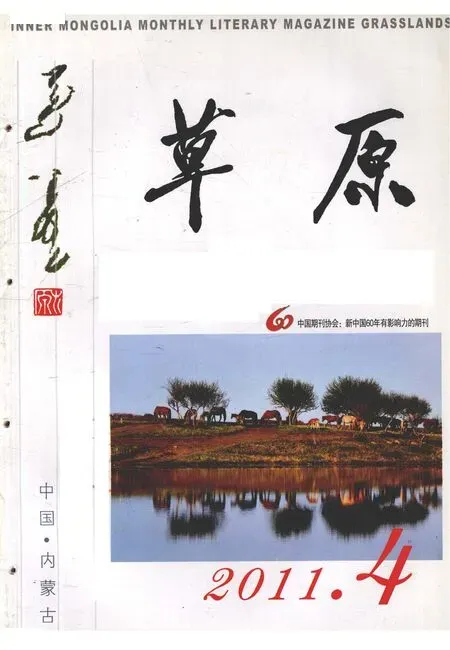自问自答:一个失去了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张天男
自问自答:一个失去了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张天男
一、诗人的影响
哪怕是最伟大的诗人,他对生活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道理很简单,多数人不喜欢诗,主宰历史的英雄权贵往往把诗人当作奴仆,诗人自己呢,既然他们想砸碎一切,他们当然也就砸碎了自己。在中国,屈原倒下了,在俄国,普希金倒下了,在西班牙,洛尔加倒下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伟大的诗人不是悲惨地死去,就是遭到放逐,或者被关进疯人院,剩下的都是二三流诗人,这些贪生怕死的模仿者之所以把神圣的火炬举过头顶,是为了有效地保护自己。而伟大的诗人本身就是烈火,他只能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二、关于纯诗
纯诗是一个梦想,是摆脱现实的精神鸦片。如果一首诗让我们震惊得忘记了生活,如果它闪电般铲除了记忆,只留下赤裸裸的激情,那就是纯诗。总之,纯诗是天边外,是不可能的可能,是水底的火焰和最近的远方。
三、百分之九十九
没有一个活人是最优秀的诗人。优秀的极限是百分之九十九,那百分之一是死。在我们的时代,有些人主动完成了最后的百分之一,比如海子、昌耀,有些则是被动的,比如我的朋友雁北。苦难、流亡和耻辱代替不了这最后的百分之一,狂暴的谩骂和无耻的下流更不行。没办法,我们只能赞美那些死去的伟大诗人,就好像死去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那些死去的诗人,变成了我们的尸体。
四、关于激情
激情是不可摧毁的,在贫乏的日常生活中,激情遭到压抑,却从未真正消亡。河流穿过旷野和巨石下的阴影,耐心的人,会在壮阔的入海口重新听到它的歌唱。写作使我拥有了双倍的时光,我可以在春天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提前站在那里。不朽的诗歌必是不死的激情,它把我从平庸和习惯中解放出来,并且让我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诗歌不在诗人双脚站立的地方,而在诗人的目光到达的地方。
五、生活目标
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目标的人,如果有,那就只有一个:推倒一切既定的目标。想想看,生活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好好想想,不要急着回答,因为就连伟大的爱因斯坦,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中国的房价涨上去了,人民网开通了直通中南海专栏,朋友们鼓励我在荒寒之地坚持。我乃内蒙古最不优秀的诗人(注意:没有之一),这几首小诗不过是一个最不优秀的诗人写出的最不优秀的诗歌之一。我一直记得海明威在 《非洲的青山》里说的那句话:“如果某人对他出生之地以外的一个地方有一种如在家里的感觉,这就是他注定该去的地方。”而我是一个对出生之地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有浓厚兴趣的人。我的出生地每隔几年就要开膛破肚刨马路,刨闹刨闹,不刨咋能闹上?刨掉了老建筑,刨掉了大树,也刨掉了一座城市的根。这就是我的出生之地,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就是所有人的出生之地。当然,它并没有给我带来如在家里的感觉。
六、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八十年代,人民还需要诗歌,而诗歌也在表达着这种需要。有时候我就想啦,你说祖国和诗人,人民和诗歌,到底是谁拒绝了谁?今天,诗歌离现实越来越远,而现实也正在坚决地抵制诗歌。“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鲁迅《摩罗诗力说》)如果有,我愿为之助阵,如果没有,我愿努力为之。
〔责任编辑 阿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