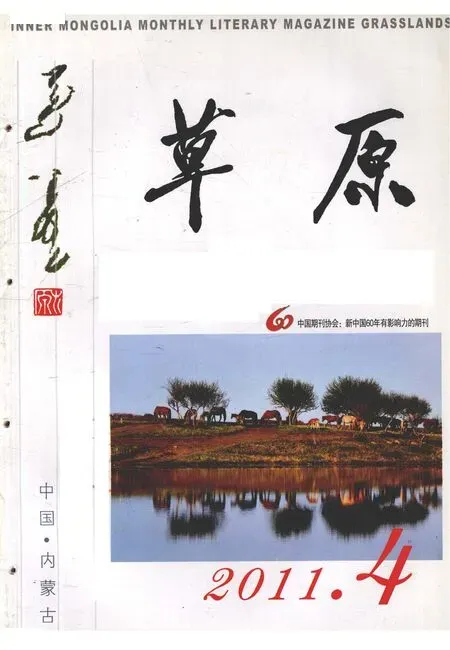一路歪斜
□易 书
一路歪斜
□易 书
1
母亲提着篮子从外面回来,随后从厨房里端出一盘草莓来。那草莓大得有些不可思议,好像被人施了魔法一般。我忽然想到一个故事,古时候,一妇女见树上有李,大如鸡卵,摘下吃了后,感觉甘美异常,后受孕产下一条小龙,原来这李子是龙受罚后被割掉的耳朵坠地幻化而成的。我笑了,为自己想到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而好笑。难道我潜意识里也盼着吃到一个香甜可口的龙耳朵,然后生一个龙子龙孙出来么?但这草莓之所以如此茁壮,也像那些个大得奇异的桃和杏一样,只是被施了化学肥料而已。母亲说,快吃吧,刚从超市里买的,看多大,多新鲜。看着这草莓,我不由得冷笑了。我想对母亲说,这些都是骗人的,但又懒得说,而且即使说了她也未必信。
中午,我懒懒地从床上爬起来,餐桌上放着一盆烩菜,看到菜里的豆腐,我赶紧背过脸去。母亲瞅了我一眼问,怎么了?我说,说的别放豆腐。母亲又问,豆腐怎么了?我说,不是早说过了嘛!我扭身回了小屋,躺在床上,眼前又出现了一条黑森森的毛腿和从这毛腿上扒下来的石膏,那豆腐就是用这石膏做成的。这是我看到的一则新闻报道,我把这新闻告诉了母亲,母亲就不买豆腐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豆腐便又出现在了我家的餐桌上。我质问母亲,母亲只淡淡地说,那黑窝点不是早端了吗?我说,你以为就那一个黑窝点呀,谁知道黑旮旯里还藏着多少呢!但母亲显然没把我这威胁当一回事儿。
躺在床上,我听到母亲叹着气说,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真不知道能吃点啥。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吃点啥。当那些肥姐胖妹为减肥而苦恼的时候,我却早已成了骨感美人了。
晚上,我没吃饭就躺下了。枕边放着一本书,书名叫《绝对惊悚》,同学说,现在的年轻人都看,特别刺激。我拿起书,打开书页,眼睛像一尾入水的鱼在黑色的字体间游走着,随着这游走,我进入了一个个鬼影纷乱的故事中,和一个个鬼怪纠缠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醒来后,一看表,已经是早上九点多了。每个星期天,我都赖在床上睡懒觉。从床上爬起来,我打开了电脑,博客里,两位成功人士正打着一场口水仗,他们像两只脸红脖子粗的公鸡,直斗得口水四溢,唾沫星子乱飞。我赶紧撤出来,生怕被这汪洋口水淹没了。之后,到菜园子种了菜,出去偷了一圈,又上了QQ。心怦怦地跳着,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遇到文海。
文海是我的一个文友,那时,我经常在《星火》杂志发表小说,他也在这家杂志发表小说。一天,报社编辑给我打来电话说,文海想和我交流一下写作方面的问题。几天后,文海发来短信,并且要了我的QQ号。我们约好每天晚上8点上网,聊看过的书,聊彼此听到和看到的一些好笑的事情,也聊内心的一些困惑。聊了一段时间后,我便像吃了鸦片一样,每天不到8点,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等待着文海QQ头像的闪动。
一天,文海说,谢谢你,好久没有这样开心了。我说,我也是,很开心。不知为什么,打出这句话后,我的心里酸酸的。好一会儿,他没有回应,之后打过来一句话,刚才断线了,早点儿休息吧,明天还得上班,别累着自己!接着,就下线了。
之后的一个星期,我每天上网,文海都不在线。我给他发短信,他回复说正在写一个长篇。他以前说过,如果我烦他的话,就说正在写长篇呢,他也许忘了自己说的这一句话了。我猜测着,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以前聊天时他说起过他的儿子,但没有说到他的妻子,当然有儿子就肯定有妻子,难道是他的儿子或者妻子出了什么事儿?
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文海,想着他和我聊天时说的每一句话,其实他连我想你这样的话都没有说过。但我觉得,这些话都藏在他的心里,就像这些话都藏在我的心里一样。我们都曾一遍遍地打出,但都没有发送出去。我似乎感觉到了他手指的犹疑,每次我都等待着。我确信,这些话在他的犹疑中被删掉了。
此后的日子里,我每天晚上都上网,但再没见到文海。我给他打手机,手机提示,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和文海一起消失的还有他的文章。我给杂志社编辑打电话,编辑说,他们也联系不上文海了。几天后,我收到了文海的电子邮件:“已经不年轻的我认识了你这样一位年轻的朋友,真的很高兴。你很年轻,也很有才华,你要珍惜这一切。好好地写作,好好地恋爱、结婚。忘掉我吧,一个曾经的朋友!”我呆呆地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这几行字,眼泪哗哗地流着。
不久后,我所在的城市举办了一场相亲大会,母亲风尘仆仆地赶去,收集回一大堆信息,然后对我威逼利诱。之后,每个星期天,我便被母亲强迫着和一个个形形色色的男子见面。我想逃离但又无法逃离,感觉自己跟出卖肉体的妓女一样,所不同的是,妓女可以重复选择,而我的选择却是一次性的,选择了哪个男人,就要一辈子献身于哪个男人。
我该怎么办呢?我想到了文海,但文海已经结了婚,而且我连文海长什么样,干什么工作,挣多少钱,有没有房子住都不知道。
2
《百年孤独》中的失眠症像瘟疫一样传播时,惊恐的马孔多人封闭了村子,不让人进出。如今,失眠症已成为现代人的通病,但是,当它四处传播时,人们没有像“非典”肆虐时那样紧张地去封闭小区、街道,因为非典能致人死亡,失眠症却不至于要人性命。所以,失眠症便有恃无恐地四处蔓延着,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几乎每个都市人都被这现代病折磨着。那一个个表情木然、神情倦怠像幽灵一样走过的中年人,还有那一个个虽然年轻但已头发花白的年轻人,都是失眠症的受害者。他们每天躺在床上,瞪视着屋顶,烦躁的星星吵得他们无法入眠。
我是一个都市人,所以也没有幸免于这失眠症的折磨。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我虔诚地呼唤着睡眠的造访,有时,它像一只有翅的精灵,我甚至感到了它翅膀扇动的微凉。那时,我也曾幸福地合上眼睛,但是这精灵很快地飞走了,我又掉进了失眠的枯井里。我圆睁着双眼,星星像一群嗡嗡乱叫的蜜蜂,在耳边聒噪着。
那一天,我努力闭上眼睛,抗拒着星星的聒噪,经过一番抗争后,终于闭上了眼睛。不知不觉中,我来到一个地方,第一感觉是,这个地方真美,青草、绿树、鲜花,像儿时的某一处鲜活记忆,在心头弹奏着一曲欢快的乐章。
继续往前走着,周围越来越陌生。但受了好奇心牵引,我继续往前走着。我看到了一座宫殿,抑或是一座庙宇?反正是一个古旧的建筑,但古旧的只是风格,外表却没有一点颓废的样子。飞檐还是那样轻灵地飞动,色彩也是那样鲜明活泼,还有那周围射出的乍长乍短的光芒,不由得让人心生敬畏。
这让人敬畏的建筑似乎有着一种吸力,我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它的里面。这是一个巨大的屋子,屋里没有窗户,只墙边点着些蜡烛。正面是一个高高的台子,台子上坐着一个威严的君王。这君王黑衣、黑帽,像一座黑铁塔,一张脸也油黑发亮,两只眼睛像随时鸣响的铃铛,发着白亮的光芒。不知怎么,这君王让我想到古戏中包公的形象。
站在高台下,我仰望着这黑而威严的君王。忽的从左边传来一阵呻吟声,我扭头一看,原来左边的柱子上绑着一个人,细一看,这人却是我们村的王五。我不仅疑惑着,王五去年就死了,怎么会在这里。
我看到,王五的身上爬满了赤身裸体的婴儿,这些婴儿鼓着血红的小嘴,在他的身上使劲地啃咬着、吸吮着。再一看,王五的身下也围满了这样的赤身婴儿,这些婴儿嘴里流着口水,仰望着王五,好像仰望一个巨大的乳房。上面的婴儿啃咬、吸吮一番后,鼓着小肚子离开了王五的身体,下面的婴儿便急不可待地爬上去,继续啃咬、吸吮。当那些婴儿都离开后,王五像被万箭穿了身一般,全身上下满是血红的小洞。
王五忽地睁开睛睛,我不知他认没认出我,反正没有求救于我,但我又怎能眼看着他遭受这痛苦的折磨。我觉得,王五的性命是握在上面这个威严的君王手里,于是向前一步,深施一礼说,我和王五是一个村的,从小一起长大,他纵然不好,也不能让他受这个罪。君王冷笑一声说,你也知道他不好,那你知道他怎样不好吗?这我知道,王五原本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后来办起了奶站,因为往牛奶里掺假,害了人命,被法办了。君王生气地说,那些个孩子,都是被他害死的。他往牛奶里掺大烟,那些个孩子喝上了瘾,都买他加工的奶粉。另一个奶业公司知道后,也往里加大烟。为了抢夺市场,两家公司都加大了牛奶中大烟的剂量,结果喝出了人命。这些孩子都还没有成人就被他害死了,你说这个仇该不该找他报。听了这一番话,我无言了。回头再看王五,他正被一群蚂蚁一样的婴儿啃咬着,我虽然知道王五不对,但又不忍看着他受罪。就说,虽然王五伤天理,但他只是一时的贪念,其实那生产奶粉的企业才是真正的害人者。那个君王说,俗话说得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上天是公正的,那些人以后会受到比王五更厉害的惩罚。
看来,我是救不了王五了,与其站在这里看他受罪,还不如离开的好。我正打算转身离去,听到右边有动静。扭头一看,一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地上,正眼泪汪汪,呵欠连天。男孩头发上系着一根绳子,头往下一垂,就呲一下牙,睁开眼看一看又闭上眼睛,头又垂下去,又呲一下牙,然后再睁开眼睛看一看。他的眼睛红得像个桃子,里面布满了红血丝,是严重睡眠不足。
难道这男孩也犯了罪不成,我又掉转身站在了君王面前,说,这孩子有啥罪,咋不让他睡觉。君王说,你知道他的父亲是干啥的吗?我说,干啥的。君王说,他的父亲把别人的孩子留在网吧里几天几夜地上网,没钱了,这些孩子就上街去偷去抢。就因为孩子上网,一些夫妻离了婚,有的还走上了绝路。你说,那些孩子有啥罪,那些家长有啥罪。我说,有罪的是他父亲,又不是这孩子。一报还一报,他伤害别人的孩子,他的孩子也要受到一样的伤害。君王叹了一口气说。
听着左右两边传来的呻吟声和呵欠声,我不由得满心怨恨,既恨王五,也恨那个开黑网吧的父亲,但是看着他们受折磨,又不由得心生怜悯。我对君王说,你又不是上帝,怎么能决断人的生死?君王说,即使我不了断你们,你们也会自相残杀。我说,你胡说,我们怎么自相残杀了。哈哈哈,君王仰天大笑,说,我胡说了吗?那“非典”不是你们吃出来的,还有那地震、沙尘暴、泥石流还不是你们自己作的孽。我也知道,这些灾难和人们的贪欲有直接关系。为了修路、盖房,人们砍光了树,铲光了草,可那树和草也像人身上的汗毛,人的皮肤靠汗毛透气,地球则靠了树和草来透气,人不透气就会生病甚至死掉,地球不透气也会生病死掉。地震、泥石流、沙尘暴就是地球得的各种病症。许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贪欲面前,他们便丧失了理智。君王站起来说,是不是你们作的孽?我,我一时无言以对。君王一边追问一边像一座黑森森的铁塔向我压过来。我赶紧往外跑,但两腿软软的怎么也迈不开步子……
当我从这个荒诞怪异的梦中醒来时,窗外已是一派阳光明媚。这怪异的梦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全身哆嗦着,紧紧地用被子包着身体,生怕再掉进那个可怕的梦里面。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我发现呈现在眼前的一切都歪斜着。镜子、门框、书柜、电脑,等等,无一例外。我赶忙喊来妹妹,问她那门是不是歪了。妹妹说,哪歪了,门好好的啊。我又问镜子是不是斜的,妹妹说,你有病啊!我扭头一看,妹妹也歪斜着身子。妹妹以为我和她开玩笑,待我问完后,就匆匆离开了。
3
我爬在床上想了一会儿,难道我是病了不成。我决定去看医生,但先不告诉家人。我看了眼科、内科、外科,都确诊不了是什么病。我不甘心,一次次地去找眼科医生,眼科医生烦了,说我不是眼睛有病,是心里有病。从医院出来,走过一条条歪斜的街道,看着一个个歪斜的身影,我忽然想起眼科医生的话,他虽是在讽刺我,却也给我提了个醒,我决定找心理医生试一试。
心理医生是一个40多岁的男子,歪斜的脸上荡漾着歪斜的笑容,似乎还有些迷人的样子。他问我做过心电图吗?我说,前几天做过,挺正常的。我有些紧张,因为我从没找心理医生看过病,而且感觉心理医生都神神秘秘的,让人捉摸不透。
心理医生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一个斜斜的听诊器,接着把一个凳子放在面前说,坐这儿来。我尽管有些害怕,还是乖乖地坐了过去。看我坐过来,他笑着说,把衣服撩上去。我犹豫了一下,把衣服撩了上去。随后,一块冰凉的铁落到了我的胸上,与这冰凉的铁一起落到胸上的还有一个热的手指,稍后,手指在扩大,之后成了半个手掌。
我的心“怦怦”地跳着,好像要跳出来推开那手掌。心理医生说,别紧张,怎么有杂音。我看他的神情越来越专注,越来越严肃,便想着,难道我的心脏真出了问题。他又说,得把这个摘掉。看我犹豫着,他温柔地笑着,轻轻地说,要不听不准。我把胸罩摘掉后,心理医生的眼睛一亮,之后又像看到了一束刺眼的光似地眯起了眼睛。冰的听诊器和热的手掌在我的胸前游移着,一会儿停顿,一会儿向前摸索。我的一颗心好像停止了跳动,整个人似乎掉进了漆黑而漫长的梦里。
当听诊器和手掌终于从胸前撤走后,我才从黑而长的梦里醒过来。医生歪斜着脸先是干咳了一声,然后舔了舔嘴唇。我背过脸去整理衣服,那一刻我特别想哭。心理医生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只看见那一张歪斜的脸在不停地抽动。
从心理医生那里出来后,看着歪斜的街道上一个个歪斜的人影和车辆,我一时感觉茫然无措。汽车站牌前站着许多等车人,歪斜的人群中有一个胖妞,上身是红的外套,下身是粉的裤子,脚上蹬一双绿的半截靴,远远望去,像一株不知名的植物。她的头上顶着一个歪斜的鸟窝,鸟窝由一些打着弯的黄草筑成,我忽然升起一股欲望,想拨开这草堆从里面找出几颗鸟蛋来。金黄的鸟窝下面是一张白面饼子似的胖脸,上面是黑的红的描画,像一块调色板。胖妞的旁边是一个男孩,那男孩歪斜着身子,像蛇一样缠绕在她的身上。男孩头上的鸟窝相对要小一些,但也是蓬蓬勃勃的样子。
不一会儿,公交车来了。两个头顶鸟窝的男女一跃而上了公交车,待我上去时,车里已是满满当当的了。车厢里荡漾着难闻的气味,我站在车门口,都被熏得无可奈何。一个歪斜的女子跃入我的眼帘,很清纯的样子。她的身后站着一个30多岁的男子,那男子歪斜着身子贴在女子背上,歪斜的脸上是一副无比陶醉的神情。到站后,又有人上车,只听司机喊叫着,往里走!都挤在前面干啥呀!慌忙往里走着,那喊叫还是重重地打在背上。回头一看,那司机的背影也是无比歪斜着。
后来,母亲和妹妹都知道了我的病。一天,我正对着歪斜的电脑发呆,母亲走过来,坐在床边问,咋样了。我知道母亲是问我的病,就说,还是那样。母亲顿了一顿说,以后,少操心那些没边没沿的事。再说,你操心也得能操过来。你说豆腐拿石膏做的就不吃了,那白面里还加了吊白块,大米里还加了工业油,照你那样,还不都饿死了。你放宽了心,该吃吃,该喝喝,再不要自己折腾自己了。说完,母亲叹一气出去了。
母亲走后,我又流了一枕头的泪。这个世界上谁能理解我呢,包括母亲,她也不能够理解我。在我的眼里,曾经美好的一切都没有了,天真的孩子、慈祥的老人、妩媚的女人、健壮的男人,这人性的健康之美在慢慢地消逝,但所有人都是一副熟视无睹的样子。还有那蓝天、白云、晚霞、朝阳,我在哪儿才能再看到它们原本清纯的模样。有时,我怀疑病的不是我,而是这个世界已病入膏肓。
我想尽快治好这病,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歪斜扭曲的世界里。但是哪里能治我的病呢,想着那个一脸淫笑的心理医生,我又该相信谁呢。
一天上网时,忽然想到,网上有没有治这病的办法呢?我开始在网上查找,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在网上竟然遇着一个同病相怜者。他听了我的描述后说,他也得了这个病,现在正在一个地方疗养。我决定到这个疗养院,于是便和领导请了一个星期的假。领导歪斜着身子说,你也知道咱们这儿的请假制度严,一个星期后尽快来上班。
母亲和妹妹得知我看病的地方是从网上了解到的,都瞪大眼睛看着我说,网上的东西你也相信。我也知道,网上的东西不可信,但现实的东西又有几分可信呢?那超市里出售的水灵灵、鲜嫩嫩的草莓,还有那一个道貌岸然的心理医生,我的信任一次次地被现实强奸,我还能相信谁呢。我只想看好我的病,别的我都不在乎了,哪怕被人贩子卖掉,被山里的野人蒸了煮了吃掉,我也认了。
4
疗养院位于我所在城市的北面,在大山的深处。这天,大巴载着我向着远处的山峦进发。那山在我印象中一直模糊着,现在随着大巴的行进,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原来那黑的是一片片的树木,白的是一条条的道路。我想着,原来这山也藏着许多秘密,如果不走近它的话,也是不能了解它的。但是,即使走近它,也只是看到它的外观与轮廓,它许多内里的东西,照样无法透析。尽管这看到的一切还是歪斜着,但我的心里已跳动起了快乐的音符。
大巴车里的座位严丝合缝地排列着,除了过道,所有的空间都被利用了赚钱。我是去疗养院看病,我不知道,这车里的许多人是要到哪里去。看着那一个个歪斜的身影,我想着,难道他们也如我一样要去往某一个疗养院?只是他们不知我是一个病人,而我也不知他们中的哪一个是病人或是好人,或许我们都是面似好人的病人。
大巴车的正前方安装着一个电视,一对歪斜着身子的男女正在里面说笑着。他们说的是一个个黄色笑话,但车里的人都表情木然地坐着,每个人都似撑着一把油纸伞,那说笑声仿佛一串串雨珠落在伞顶上,虽叮叮咚咚地响着,却进入不了他们的身体里。
一路上,电视里的男女毫不知趣地说着、笑着,油纸伞下的人们歪斜着身子坐着,有的忧郁地想着心事,有的急躁地接打着电话,有的东张西望,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
我被卡在窄小的座位里,不断地调整着坐姿,试图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姿势来对付这长长的旅途,但是我的努力失败了,不管以何种姿势,都像被捆绑了一般难受。身体被捆绑着,心便也瑟缩着,虽然外面是一派阔大无比的景象,我却始终无法获得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终于,大巴车在一个小镇停下来,我被人流夹裹着下了车。身体刚刚松了绑,却又遭遇了另一场考验,一双脚刚落地,一帮人就歪歪斜斜地冲到我的面前,瞪着眼,张着手,嘴里极快地说着什么。我提着包慌乱地向前走着,几个人拦在我的面前。我终于明白了,这些凶神恶煞的人只是在拉客而已。我摆摆手说了声不要,他们便拖着歪斜的身子散去了。
我来到路边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把包放在地上。我不知道,自己此去疗养的地方在哪一面,是西面、北面还是南面?此时,我才感觉到,我要把自己交给一个未知的地方,一些未知人的手里。
一辆马车斜斜地停在一条土路上,一个男子和赶车人坐在车上。我提了包向那马车走去,那男子也从马车上下来,向我走来。这男子约30多岁的样子,穿一身白色运动服,戴一顶白色遮阳帽。原来他就是我网上认识的我的同病相连者,不知怎么,第一眼见到他,我便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更奇怪的是,他是我这些日子见到的第一个不歪不斜的人。他帮我把提包放到了马车上,然后把一个坐垫放在车厢里说,上去坐吧。我小时候在老家坐过马车,现在坐着这马车感觉很新奇。他看我坐好后,也利索地跨上了马车,我们便向着更远的山峦进发了。
马车不紧不慢地走着,路边是一座座寂寞的歪斜的山,马脖子下拴着一串铃铛,那铃铛发出的声音虽细碎,却给寂寞的旅途带来一丝慰藉。坐在马车里,我感觉自己像躺在了童年的摇篮里,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正当我昏昏欲睡时,马车停在一处土墙木门的院落前。我的同病相怜者叫吴明,看车停下来,他便招呼我下车。
吴明领我走进了一处院子,低低的院墙,木格的窗扇,窗扇上贴着花花绿绿的窗花。推开屋门,首先进入视线的是一盘大炕,接着是锅台、躺柜和水缸。我像掉进了一个古旧的记忆里,这门后的水缸,靠墙摆着的躺柜,还有锅台和大炕,我都是那样的熟识,只是它们都一无例外地歪斜着。
5
就这样,我在这个疗养院里住下来,也许是累了的缘故,晚上睡在宽大的炕上,我第一次没有失眠。早晨,在一片欢快的鸡鸣狗叫声里醒来,看看白亮的窗玻璃,我才记起,昨天没有拉窗帘,也没有锁门。我把自己交到这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却丢掉了平日惯常的戒备。
我在院子里一边做操,一边大口呼吸着空气。空气非常新鲜,像刚挤出的牛奶。天空像披着一件透亮的蓝色纱衣,太阳好像刚从大海里沐浴出来,新鲜如水蜜桃,连周围的光线也湿漉漉的。鸡、狗、羊、牛都欢快地叫着,好像在欢呼、迎接着这带给他们光明、温暖和无限生机的火热球体。此时,我真想跑到一览无遗的山顶上,去喊、去叫,去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吴明一手端一个碗,从院门外绕过来,进了我的屋子。他端来的是一碗小米粥和两个馍头。他说,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种的,你多少吃一点,吃完了,我带你出去转一转。我只喝了几口米汤就放下了碗,他看我放下碗也没有再劝,只是说,过几天就好了。
我随吴明走出院子,返身要锁门,却发现门上没有锁头。他笑了笑说,这里的门都不锁的。我们出了院子,关上了木栅栏门。这里和我见到的村子没有两样,只是好多人的穿戴都不像农民。难道他们都是像我一样的病人吗?他们见了吴明都亲热地打着招呼,还指着我问,新来的。吴明笑着说,新来的。吴明领我去了村子外面,初春的田地像铺展开的一块块绿桌布。
一圈走下来,我才知道,这里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不但种着粮,种着菜,还养着奶牛。吴明说,这个村子原先住得满满的,后来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光剩了老人和孩子,后来老人死了,孩子们被父母接到城里去后,这些房子就空下了。房子不住人就都朽败了,但村里的年轻人宁愿在外面租房也不愿意回来住。后来,城里一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来了村里,再后来,像你我一样得了城市病的年轻人来村里疗养。我说,我们这病还有名字?啥病没名字呀!像非典一样,本来是流感,因为症状不典型,就起个非典型性流感。尽管得的都是城市病,但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这种病农村人是不得的,所以就叫城市病。我说,这种病是怎么得的?要说这种病的病因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咱们这些人都比较脆弱和敏感,而这个世界又时不时地在为我们提供着让我们脆弱与敏感的事物。其实,这大可不必。像你,看了新闻报道说,豆腐是拿石膏做的,就再不吃豆腐了,别人还不照样吃?如果我们像许多人一样睁一眼,闭一眼,不那么认真的话,就不会得这个病。我的病因和你又有些不同,我本是乡里的干部,要是不那么较真,也许能混个副乡长当当,我却不能。下乡时,看到那些个少吃没喝的农民,心就颤颤的;回来以后,别人该吃的吃该喝的喝,我看着满桌的鸡鸭鱼肉却怎么也吃不下。几年下来,我不但没有混上一官半职,还把自己搞得病恹恹的。后来,无意中听到这个地方就来了。来了,病也就好了。后来我想,何苦呢,眼不见,心不烦,就干脆辞职,彻底来到了这里。那你妻子让你来吗?还有孩子。我问。我还没结婚呢,哪来的什么妻子、孩子!
快中午时,吴明领我走进一个塑料大棚,塑料大棚里面热热闹闹地长着各种蔬菜,那菜叶上的露珠一滚一滚的。吴明说,你想吃啥菜就自己摘吧。以前住在城市里,菜都在超市里买,头一次到地里摘菜,我有些不知所措。吴明说,这个柿子生吃最好,还有黄瓜,你看都是顶花带刺的。咱们今天中午吃莜面咋样。我说,怎么都行。吴明说,以后可不能这样,想吃啥你得自己拿主意,只有你想吃的东西才能吃出滋味。我们又摘了香菜、茄子。吴明说,茄子烧熟了和莜面一起吃最好。
往回走时,许多房子上的烟囱已经开始冒烟了。吴明说,就到我这边做吧,我这里东西齐全些,我便随吴明到了他的屋里。他的屋子和我的屋子一样,也是大炕,躺柜,水缸。吴明说,他在农村长大,做饭和农活他都不在话下。一会儿,热气腾腾的莜面端上了炕,吴明招呼我坐到炕上,他也脱鞋上了炕。吴明指着莜面说,你看,这是我们自己种的莜面,这莜面一点儿化肥也没撒。接着又指着黄瓜和西红柿说,你看,这是你亲手摘的,是我们亲手种的,也是一点化肥也没有撒。你要相信我,你就吃点儿。到了明年,我带你一起种粮,种菜,到那时,你就知道我没有骗你了。
我拿起一个西红柿,这西红柿不像超市里卖的西红柿那么红亮诱人,它的皮子有一些黄有一些绿,我咬了一口,有一些酸,有一些甜,难道这就是西红柿的本来面目和本真的口味吗?还有莜面也不是我以前吃到的莜面那样白,那样细,它是黑色的、粗糙的,难道这也是莜面的本来面目和本真味道吗?听着吴明的介绍,看着有些诱人的饭菜,我的胃还是反抗着,因为我还是不能掌握这些食物的真实情况,但我却不再幻想那些制作流程了,因为这西红柿、黄瓜都是我亲手摘的。吴明看我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低低地说道,慢慢会好的,慢慢会好的。我也心里默默地说着,慢慢会好的,慢慢会好的。
不知不觉,我来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只一个星期,我的厌食症便好转了,我也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而且最让我欣慰的是,现在,凡是进入我眼里的东西似乎不像先前那样歪斜了。这说明,我的病有治好的希望,但治好我病的,不是什么心理医生,也不是什么药物。
看到我心情好了,吴明领着我去劳动,然后摘菜,做饭,我和吴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时,我也会问,你真的要在这里呆一辈子吗?吴明有时回答说,当然了,有时又好像不愿回答这个问题,我也就不再问他。
母亲打了好几次电话,第一次她只是嘱咐我好好养病。后来再打来时,说有人给我介绍了对象,听到这里,我就想挂断电话,她好像猜出了我的心思。等她说完了,我马上说,我的病还没好,就挂断了电话。夜里,我又想到了文海,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他知道我病了吗?
没到这里以前,我是离不开书的,现在却不再看一本书,我有意要告别以前的生活。我发现,这里的人好像都不怎么看书,吴明也不看书,只是那天我在他屋里看到一本《星火》杂志,而且正好是刊发我和文海小说的那一期,也就是这一期出来后,我们开始了有了联系。第一次见到吴明时,我就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他,我现在明白了,他就是我梦里见到的文海。
那一天,吴明带我去爬了近处的一座山。他在前面爬着,我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跟着。他不时扭过头看着我说,加把劲!我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背影和文海的背影重叠在一起。我惊喜地喊着,文海!文海!他扭过头愣愣地看着我,笑了一下,然后扭过头,继续爬他的山。我继续喊着、喊着,泪就流了下来,然后便软软地跪在地上。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走过来搀着我,艰难地向山上爬着。
终于到了山顶,这山从下看着很陡峭,山顶却平平展展的。坐在山顶上,我已停止了哭泣,只任风吹干脸上的泪痕。吴明站在山顶上向着南面眺望着。我想,他是文海吗?他如果是文海,那南面应该是他的家乡,他是想念自己的家乡了吗?
单位领导催我回去上班,说再不回去的话,就要解雇我。我没有说回去也没有说不回去,后来,我妈给我打来电话说,你结不结婚我不管,但没了工作怎么行,这会儿工作这么难找,丢了工作,你吃啥喝啥呀!
就这样,我走了,尽管很不想回去。临走时,我对吴明说,明年春天,我还要来,和你一起种咱们的粮和菜。他没说话,只是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
〔责任编辑 刘广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