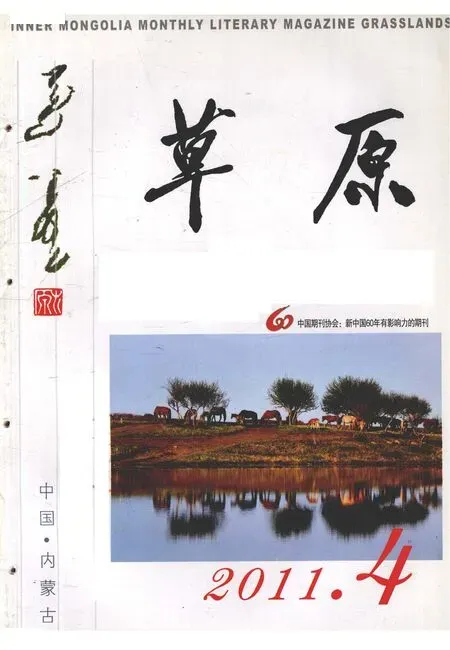瓦蓝青稞
□李万华
瓦蓝青稞
□李万华
与小麦比较,青稞更显得松散,没有章法,虽然它们同属于大麦类。小麦从钻出土壤的那一刻就显现着它严谨、自律、内敛却又要强的品质。它的叶片、麦芒、秸秆,以及它有着柔韧筋骨的面粉,时常显得庄重自恃,美好无瑕,便是麦田,也具有诗意的光芒。但青稞不同。青稞的格调如同它所生长的环境:高寒、清阔、寂寥,它更接近简单与清贫。我所熟知的白青稞,它出土时的叶片带着病态的萎黄,长大后又宽又厚,有着村人壮实身板的质感;它的秸秆倒在伏天的暴雨中,任凭水流在身体上肆虐,无知无觉;它的麦芒长过穗头,四散纷披,依旧可以把它想象成不加修饰的毛糙乱发;穗头上排列的四纵或者六纵籽粒之间,留有空阔间隙,这给鸟雀啄食带来方便;而青稞面粉,天生不具备筋骨,有着粗糙寡淡的口感。小时候揉青稞面擀面条是件令人恼火的事情。青稞面不认凉水,烫水勉强可以和匀,但在擀面杖下无法成为圆形,往往碎成破旧花瓣的模样,惹人生气。于是不用刀切,直接把擀薄的青稞面片随意撕进锅中,叫“破布衫”。“破布衫”现在成了一道青海风味小吃,腊肉切丁,加葱姜在菜籽油中爆出火色,注入沸水,用手指撕进大小不一的青稞面片,煮熟,加入菠菜,出锅。它的调料极其简单,一把青盐。
青稞成为我童年生活的具体内容。戴着黑“滚头”毡帽的爷爷驾着他的大轱辘马车吱吱扭扭地走在旷野中,车上是用牛皮绳扎起来的庞大沉重的青稞捆子,箍着蓝头巾的奶奶坐在青稞捆子的顶部,危而高悬。他们的身边是尚未醒来的深秋大地,黑灰,天边朦胧,那是即将到来的黎明。一束碧绿的亮光跟随他们,跨过塄坎,穿过溪流……有时车子停下,那束绿光便也停下,车子行驶,绿光再次追随,始终保持着距离。奶奶抖擞,但不敢告诉爷爷,说我们的身后跟着一只看不出毛色也看不出凶残的狼。这是我最早听到的故事。我稍大之后,在春天会掺和到大人之间,忙碌在田间地头,看一把把拌着家肥的青稞种撒进新翻的黝黑的土壤中,会嗅到浓重的猪、牛、羊粪和化肥混和的气味,跟着犁尖来回行走,我甚至以为那就是种子的气味,或者是春天的气味。端午节前后锄草,拿把小铲子蹲在青稞地里,铲出灰灰条、娘娘菜和铲铲草,这些杂草带回家,焯去土壤的腥味,依旧是饭桌上葱绿的可口饭食。在青稞地中长久蹲伏后起身,会有短暂的眩晕自腹中升腾而起,直抵大脑。于是我看见素净的蓝天,看见祁连山的冰雪和山腰的云杉,看见孤绝盘旋的鹰,看见土黄轮廓内丢失色彩的经幡,看见明亮水流和浓密青杨,也看见大片匍匐的青稞田,它们在高原清凉的阳光下旋转,渺远却又逼近。八月收割,我在阳光烘烤的中午,穿过河滩给母亲送去最简单的饭食:两三个青稞面烙的饼子,一暖瓶加盐的茯茶。母亲坐在地头喝茶,面色通红,散乱的头发沾满细碎麦芒。我在参差的青稞茬地上拔薄荷和荆芥,它们和烧红的土块、葱根以及老姜熬成热汤,是治疗风热感冒的良药。辛辣的草药气息若有若无,偶尔回头,我看见成排的青稞捆子,戴着它们破旧的大草帽,成为孩子的模样,站立的姿势随意又亲密,而山坡,正显露出颗粒落尽的空阔与辽远。农历十一月,寒冷琐碎的月份,路面冻结的,依旧是前一个季节留下的车辙印记,它们凹凸不平,覆盖濡染尘色的薄雪。母亲在黎明的微光中起身,走出院门,到门外场院摊场。我记挂劳累的母亲,偷偷起身,去场院帮母亲打下手。秋天的青稞捆子,并不能及时打碾,需要集中起来运回。现在要把它们一个个解开,抖匀,摊在场上,驾起牛马,用沉重的大碌碡反复碾压。戴着薄薄的脏棉线手套,我的手指和耳朵在疼痛的基础上逐渐麻木,黎明的寒冷如同冰碴,头顶依旧是昨夜清冽的星辰。如果我不去学校,我还可以接过母亲手中的缰绳,赶着一对黄牛碾场。碌碡滚过厚厚的青稞秸秆,发出持续不断的吱扭声,揭起一层秸秆,会看见脱粒的青稞平铺在硬实的地面上,并无损伤,仿佛一些裸露而又无辜的幼小孩子,而温顺的黄牛拖着大碌碡,顺时针一圈又一圈。我并不知晓这沉闷的周而复始是黄牛的命运,当然我也不会思索母亲的一生将如同这沉默的老牛。打碾的程序细密繁多,摊场、起场、晾草、扬青稞、背草、装仓。凌厉的麦芒戳红肌肤,晚间回家,要在煤油灯下拣去窜进内衣的芒尖。农闲时候晒青稞需要耐心,选择阳光灿烂的日子,将潮湿的青稞摊晒在院中台地的大塑料布上,人光脚踏在青稞上,一撮一撮翻拣其中的碎石、泥块和老鼠屎粒。一天下来,持续俯向青稞的面庞肿胀疼痛,眼球充血。如果跟随母亲去磨青稞,我便会进入一个逼仄昏暗的摇荡空间:四根牛皮绳吊起的石磨阳扇上散发出的微光是磨房醒目的光源,它悬在磨房中央,与阴扇严丝合缝。我看见磨缝里流出的面粉,丢失向下的重心。它们轻舞,落满屋顶粗壮的梁柱,圆木拼就的板壁,磨去色彩的地板,低头箩面的母亲,以致到达磨房门口,那里放置的木槽里正有过于干燥的青稞等待再度潮湿。无处不在的面粉颗粒在悬浮、碰撞,仿佛日光照耀下的尘埃……童年的青稞,有时是故事,有时是伙伴,有时是玩具,有时……它使我看到母亲在大地上从早到晚的艰辛,以及与大地一样的沉默,仿佛母亲自身就是一粒微茫的青稞,来自大地深处。而我在青稞的光芒中,在青藏高原冷硬的风中逐渐裹上成长的色彩。
西藏的古老传说中,人是一只神猴与罗刹女的后代。观音菩萨为了哺育这些后代,从须弥山岩缝间取出了第一粒青稞和其它粮食种子,在雪域广为播种,小猴们吃了谷物后,毛和尾巴渐渐缩短,学会讲话,变成了人。奇异的传说带着朴素的进化论思想,青稞在故事中有着神性的光芒。但是青稞并不因此获得过高的尊崇,它依旧是用来温暖我们肠胃的边缘食物。绿色的青稞籽粒刚刚饱满,我们折下它青涩的穗头,放在大铁锅里煮熟,凉冷后搓下籽粒,用簸箕簸去麦芒,装进小石磨中,一阵吱吱呀呀,便可以得到青黄不接时期的美食:麦梭。拌些葱蒜和芫荽,调些菜籽油,盛在大碗中,可以用指头抓着吃,也可以和刚刚成熟的洋芋熬在一起,成为粥,带着青禾的浓郁气息。有时我们直接揪下青稞穗头,用手掌揉出籽粒,吹去麦芒和外皮,放在嘴里咀嚼,这样零打碎敲的吃法总是发生在别人家的地头,带着盗窃的恐惧,显得贼眉鼠眼。黑铁锅炒熟的青稞,微黄,肚腹裂开细微的口子,我们装在口袋里,捏一粒出来,它们在唇齿间发出清脆的碎裂之声,那是我们幸福的童年零食。青稞炒面做成的糌粑,我更喜欢用烧热的菜籽油替代酥油,加入白糖。这样的糌粑更多带着农业的气息,而不是藏民族的糌粑。如果是夏天,老人们会闷出一盆甜醅,将青稞去皮洗净,入铁锅煮熟,沥出凉冷,加入甜醅拌匀,装进坛中密封。老人会将坛放在温暖的热炕角落,盖上棉被,发酵,过几天便可开坛食用。说甜醅清心提神,壮身暖胃。我喜欢沥尽甜醅颗粒的汁液,醇香、甘甜,如果加入几勺白糖,便是童年唯一可以喝到的珍贵饮料。相对于白面,被我们称作黑面的青稞面是那么卑微、贫贱。我们用粗糙、松散、黝黑的青稞面蒸“油花”,烙三角干粮,散“拌汤”,擀面条,不论怎样变换手法,入口的黑面总有着贫贱植物的苦涩与干硬,而我们盼望着的,是绵软、细腻、有着美好口感的白面,以及由它揪出的面片,烙出的饼。我第一次看到青稞的宝贵,来自那时经常可以见到的货郎。甘肃永登天祝一带的货郎,挑着他的针头线脑,摇着拨浪鼓,向西走过大通河的吊桥,爬过十二盘坡,翻过时常云雾弥漫的黄垭壑,便会换到我们村子的鸡蛋、大姑娘的头发或者猪鬃。他们更类似于一种流浪者,天在哪里黑就在哪里睡,肚子在哪里饿就在哪里讨要。我从家里拿出几块青稞面干粮,送给蹲在门口青杨树下的货郎,他从自家纺织的黑粗布衣袖中伸出手来,躬下明显僵硬的腰背,我记得他黝黑如同煤炭的手,青筋暴绽,长指甲乌黑,他的肤色已经与褐土成为一色。我同时看到地面上的他的双脚,破旧的解放鞋布满泥点并失去形状。他接过青稞面饼子的姿势如同接过一块足以改变命运的金子,然后大口吞咽,带着极其欣慰的神情。1980年,我吃到一种金包砖的花卷,将和好的青稞面和小麦面分层卷起来,白面包住黑面,这是我最后吃到的青稞面。如同展开一幅水墨画卷,我揭下并吞食掉外层的白面花卷,留下的青稞面花卷重又卷起来,如同卷起一团小小的虚荣,放回书包。其实那时的青稞已经是名叫“白浪散”的白青稞,接近于小麦的色彩,口感稍稍绵软。真正的黑青稞,那时已难见到。
我熟悉青稞地,如同我熟悉它们发散的幽微蓝光。夏季,从闪烁耀眼的白光的村庄出发,穿过灌丛密布的河谷,便会进入青涩旺盛的青稞田地。遍布车前子、蒲公英的细长田埂在纷披的青稞叶子中难以寻找。低下身,可以看见无数带着透明骨节的青稞茎秆纵横林立。折一截中空圆润的茎秆,将一头捏扁,咬在嘴里,便会吹出低沉的“呜呜”之声。如果干渴,嚼一截嫩茎,唇齿间是类似甘草的香甜。
钻出田埂,我看到青稞生长的家园,如此辽阔:高远的天空濡染深蓝,云朵低垂,阳光给它们绣上金边。嗓音嘹亮的云雀,它起飞降落的身形如同音符跳荡。覆盖云杉和白桦的山坡背阴处,便是潇潇松涛,我了解那云杉底下的细碎部位,蚂蚁爬行的蘑菇,枯草,宿茎,开白花的野草莓。夏季也清凉的山风,河水,它们一起奔跑。当然还有牛羊,经幡,那些攀岩在青色崖壁的白色山羊,有人说它们到了南方,以狗肉的身份挂在饭店。虫声鸣叫,优雅又狂放。无数青稞的麦芒同时撒开,如同清晨阳光扯出的万道光芒,灼射、激越。我于麦芒间放眼,看见迅速庞大的青稞穗头,遮去远山峰顶的白雪,那是我一年四季都可以仰望的白色花朵。
〔责任编辑 阿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