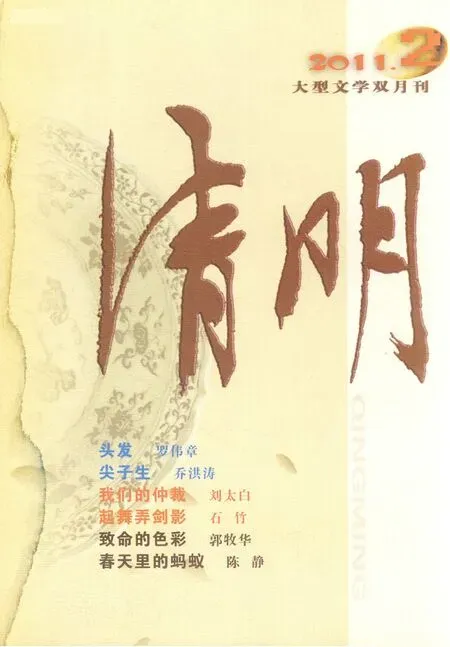堂客
杨继光
堂客
杨继光
摸堂客
这天夜里,下放在刘屋的男知青胡奖状正无聊的没事干,同村两个与他年龄差不多大的小伙子来邀去他看电影。听说是放《地道战》,胡奖状说看过多次了,没啥好看的。有个小伙子悄悄对他说,去看吧,乘人多好摸堂客。胡奖状问摸堂客是怎么回事?那小伙子伸手在他胸口摸了把,俏皮地笑着。胡奖状明白后也笑了。
来到李屋放电影的地方,电影已放了。胡奖状在人群中找个地方站着看起来,同来的两个小伙子眨眼工夫挤得没影。正看得乏味,他发现身边不知何时挤来位扎着辫子的女人。他让一下,可能有人挤的缘故,那女人往他身边挤一下。不知不觉,那女人的身子与他的身子贴饼子了。他闻到了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趁着换片子灯亮,他看了那女人一眼。那女人胖胖的,眯着眼,不丑也不漂亮。从长相与衣着,他判断她是位姑娘。再举目望望,他见同来的一个小伙子正挤在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身边抽烟呢,忍不住一笑。
电影又接着放了,他感到身上有点痒,伸手去挠,无意间碰到了姑娘的手。挠好痒将手放下,那姑娘也挠挠腰间,与他的手碰在一起。出于礼貌,他将手拿开了,再放回原位时,又碰到了那手。这次他没拿开,那手也没拿开。两只手的手背就这么挨着。他试到那手背热呼呼的。抱着开玩笑的心态,他拉住了那手。那手也没动,这让他很高兴。他动了动手指,那手仍没反应。他挑逗地捏了一下,那手马上做出回应,也捏他一下。他越发感到有趣了,张开手指搅住那手的手指。那手也随他搅,直到电影放完,才松开。姑娘回头望他一眼,转身挤出人群跑了。
胡奖状兴奋极了,长这么大他还是头次与姑娘拉这么长时间的手呢。晚上睡在床上,他竭力回忆姑娘的样子,可越回忆越模糊,后悔没多看几眼。
几天后,另外一个队放电影了。这次,胡奖状没等队里的小伙子来邀就主动去了。因为到得早,电影还没放。他到处望,想再次遇见那姑娘,可望来望去没望见。电影放了,目光盯在银幕上,可他心里仍希望能有艳遇出现。这次他身边站的都是男人,没女的。换片子后再放时,有两个女的挤到他身边来了。从头型和衣着,他马上认出那高个子姑娘就是上次的那个,忍不住朝她身边挤去,姑娘发现后,也往他这边移动。两人身子贴住后,他一把拉住姑娘的手,姑娘竟展开手指像上次他套她的手指那样套住了。这举动让胡奖状很惊喜,想到队里的小伙子说过可以趁机摸摸,动了心思。他正处在青春期,渴望了解女人的神秘。他将手指退了出来,双手抱着手臂,放在姑娘胸前,先有意碰了下姑娘那鼓鼓囊囊的部位,见姑娘没反应。又将手背悄悄贴在姑娘的乳房上。他试到了一种柔软,心里激动起来。姑娘的身子哆嗦了一下,马上用手将他的手推开。他不但没收敛,索性隔着衣服在她的乳房上摸了把。姑娘伸手将身边的小姑娘拉到身前,将身子移了一下。他当她躲避呢,等姑娘站好,才发现她这样站目的是将背靠在他身上。瞧她的后背贴着自己的前胸,整个人在自己的怀抱里,他就用双手从下面揽住她的腰。见她没反对,胆子更大了,偷偷将一只手伸进她的衣服里。他估计姑娘会推开他的手,可姑娘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勾着身子将前面的小姑娘抱得更紧了。当他意识她这样做是避免身旁的人发现时,心里一喜,便得寸进尺地将手顺着姑娘的肌肤一点点往上移。摸到那只热呼呼的乳房,他的手指哆嗦了,心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这时,灯亮了。那姑娘忙牵牵衣服站好。原来电影放完了。灯光很亮,他看清了姑娘的脸,姑娘也看清了他,还对他羞涩地笑了下,拉着同来的小姑娘走了。
这一夜,胡奖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从那以后,只要听说有哪个地方放电影,他的心马上就飞到姑娘身上了,不管多远都去看。使他欣喜的是每次那姑娘都来,并与他在一起,任随他抚摸。尽管他不晓得那姑娘叫什么,是哪个队的,连话也没说过,可他每时每刻都在想她。让他欣喜的是那段时间周围常放电影,在一起次数多了,他从她身上逐渐了解了女人的一些秘密后,忍不住产生出非分之想,并多次在心里揣摩与幻想与她发生关系时的欢快情景。他估计只要自己提出来,姑娘肯定不会拒绝,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姑娘愿意让他摸隐秘的部位,就等于愿意将身子交给了他。
在犁湾塘看电影那次,他打算拉着姑娘离开放影场地,找地方去干那事,脚都抬起来了,可他还是狠心遏制了步子的迈出,因为他担忧发生关系后,姑娘万一怀孕了怎么办?此前公社男知青中就发生过这种事,结果那男知青被迫与那位农村姑娘结婚了。他家就他这么个儿子,父母等着他招工回城,他不愿步那男知青的后尘,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尽管克制欲望是件痛苦的事,但从前途着想他还是守住了心猿意马。
双抢过后,有天队里安排他与劳力一起往公社粮站送公粮。当他将一担沉甸甸的稻谷快挑到公社粮站门口,实在挑不动了,就将担子歇了。这时迎面过来位挑着空稻箩的姑娘。他认出了她,她也认出了他。他想挑起担子往粮站里去,可起肩时竟差点跌倒了。那姑娘见状,将空稻箩一放,过来将他的担子挑起来,一气担到公社粮站门口,歇住后示意让他挑进去,并说:你是九队的啊。胡奖状点头问她在哪个队,姑娘红着脸没回答,担着空稻箩低头走了。
再次看电影见面,电影还没放。他问她是哪屋场的,她轻声问他可认识张丽萍?他说认识啊,张丽萍与他是同学,他还到她队里去过一次呢。姑娘说张丽萍就下放在她们队。胡奖状这才晓得她在哪个队了。因放电影用的发电机坏了踩不响,电影没放成。两人既失望又兴奋地分开了。
张丽萍下放的队距胡奖状所在的队有五里来路。他多次想去她那儿看那姑娘,又担心事情让张丽萍晓得后会笑话他,才没去。
春节前夕,胡奖状打算回城里过年时,看电影的机会又来了。他去了,那姑娘也去了,挤在一起后,姑娘轻轻喊了他一声小胡哥。胡奖状估计她准是向张丽萍打听他了,因为身边有人,也没说什么。冬天穿着厚厚的衣服,两人没摸,只是相互拉着手。他手心湿漉漉的,她手心里更满是汗水。他觉得通过手他俩在谈心,在享受愉悦。电影散场了,分手时,他叹息了一声,姑娘不约而同地也叹息着。
回来后,胡奖状想,张丽萍插队的那屋场叫祝家大屋,没有杂姓,有次看电影,他听陪那姑娘一起来的小姑娘喊她翠兰姐,推断她可能叫祝翠兰。他不但将这名字记在日记本上,还发挥儿时学美术练出的基本功,凭印象为姑娘画了张素描,虽画得不太像,但他觉得要将她的模样刻在灵魂深处。
那次看电影后,到了春天,知青开始大批回城了。胡奖状也顶父亲的职,离开了农村。
回城后,他在一家锅炉厂当工人,工作辛苦,工资也少的可怜。开始,他夜里老想祝翠兰,尽管他也晓得这种回忆无非是填补一下饥饿的欲望,但他还是喜欢沉浸在回忆中,因为在城里,他认识的姑娘少,也没有哪位瞧得起他,更没有摸的机会。
几年后,年龄大了,正为婚事犯愁时,有位热心人给他介绍了李芸。李芸比他小十来岁,长得漂亮,从农村刚回城,户口没按好,家里生活也困难。见他家有两间房子,他有工作拿工资,人也本分老实,家里日子过得还可以,没谈恋爱,就匆匆与他结婚了。
婚后,倒霉的事接二连三的纠缠着胡奖状,先是他父亲患癌症去世了,后来就是厂倒闭了,他成了下岗职工,再后来他母亲突发心脏病也死了。让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李芸在他家最困难的时候,与昔日她的一位同学联系上了,勾搭成奸后,与他离了婚。最令他伤心的是与他相依为命的女儿又遭车祸惨死了。
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他只有靠路边的那个小报亭卖报刊艰难度日。郁闷中,他也写点小豆腐块文章,发表在报刊上自娱自乐。这期间有好心人给他介绍对象,他都没睬,因为日子过得这么艰难,找了老婆也养不起。万般寂寞中,有时他对过去的生活进行评价,想来想去,觉得最值得留恋的时光仍是农村下放那会儿。尽管那段岁月很遥远了,可想到祝翠兰的手和她那令他心跳怦怦的乳房,他感觉那情景历历在目,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有天,他在家里寻找那个记有祝翠兰名字与素描的日记本,却怎么也找不着了。
命运再一次将他推进苦难的深渊,在一个春夜,抽了许多烟喝了许多酒的他竟中风了。幸亏被隔壁的大妈发现,及时将他送进医院。
胡奖状躺在病床上呆呆地看着输液管里的点滴一点点往下坠落着。打完点滴,护士过来取针头时,给他送来张催款单。见还要交2000元,他绝望了,因为他的积蓄全用光了,家里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可变卖的。他正考虑出院的事,病房里进来位胖胖的中年女人。
那女人一下子冲到他病床前,急切地喊他一声小胡哥。瞬间,他认出来了,这女人正是当年的祝翠兰。望着她,他激动的一时竟想不起她的名字,只是念叨着你……你……
祝翠兰笑着说我是翠兰啊。她当他还没认出自己,一把拉住他的手,套住他的手指。
胡奖状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
祝翠兰将带来的水果放在床头柜上,说:我是来看你的。
胡奖状问她怎么晓得他在这儿住院?
祝翠兰没回答,而是坐在病床边关心地问他还好吗?
到了这地步,胡奖状还能说什么呢。他苦笑着自嘲了一句:好什么好,等着去见毛主席了。祝翠兰见他左半身虽偏瘫,但比预想的好,就拿只苹果递给他。胡奖状接过她递过来的那一只苹果,又问她是怎么找到他的,祝翠兰仍没回答,而是拿起催款单看了看,问他要不要交钱?胡奖状咬了口苹果,不停地嚼着。
祝翠兰从他的表情中预感到了什么,拿着催款单出去了。
回来后,她告诉胡奖状,刚才问医生了,医生建议他出院,以后在家康复治疗。胡奖状望着她,一副为难的样子。祝翠兰干脆地对他说,既然医生这么说了,你就出院吧,我送你回家。这话说到胡奖状心坎上了,他答应了。
住了两个多月的院,胡奖状家里灰扑扑的。祝翠兰将他搀进家让他坐好,利索的将屋里收拾干净,然后就忙着生炉子点火烧水做饭。热腾腾的饭菜摆在胡奖状的面前了,这让他很感动,因为他很久没得到这样的照顾了。吃饱喝足,胡奖状再次问她怎么找到他的,祝翠兰这才坐在他的身边说开了。
原来,胡奖状回城后,祝翠兰一直不愿意出嫁,后来年龄大了,在母亲一再催促下,她才嫁给了一个外号叫大头的砖匠。生孩子时因难产,她命保住了,却丧失了生育能力,孩子也没活下来。大头这人性格暴躁,常骂她打她,两人生活在一起毫无感情。大头在外面打工时找了个四川女人,与她离婚了。回到娘家,她陪着年迈的母亲一起生活。母亲劝她再嫁,她不愿意。母亲去世后,她不想独自在家里呆,就来到这座城市打工。当年张丽萍内招回城,是她送她回家的。进城后,她找张丽萍打听到他的下落,得知他已结婚有了孩子。她曾偷着到他家附近去看过他。见他生活的还不错,就没惊动他。后来她又到另外一座城市去打工,飘泊了许多年,才再次来到这座城市打工,这时她才晓得他离婚了。她现在一家个体饭店里打工。打工之余,她多次在他的报亭附近徘徊,因为她也打听到他独自生活的艰辛,想与他联系,可想到自己的境况,又顾虑重重的放弃了。不久,她路过他的报亭,见门锁着感到奇怪,问他家附近的人,才得知他中风了。这让她震惊,立刻就赶到医院来了。
祝翠兰抹着泪水问胡奖状:这么多年,你想过我吗?
胡奖状坦率地承认常想,特别是与前妻吵嘴打架时,他情不自禁地就会想到她。他话音一落,祝翠兰当即拍手应道,她也是这样,每逢大头打她,她就会想他。她接着向他说,当年她俩在一起看电影,每次过后,她都焦急地盼着下一次早点见面。那时她心里想的全是他,尽管她晓得他俩不可能走到一起,可她还是常梦想能与他在一起,甚至多次想将姑娘的身子给他。他回城后,她苦闷了很久很久。她所以要来到这座城市里打工,因为她晓得他就在这座城市,只要想到他,她就感觉他在她身边,精神有了寄托,日子也过得充实。
说完这些,祝翠兰张开双臂将他揽在怀里,激动地说:
小胡哥,你不知道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做你的堂客……
瞬间,许多往事都涌上胡奖状的心头,他抱着祝翠兰嚎啕大哭……
换堂客
周家屋有五十多份烟,在香茗山下是个不大也不小的屋场。
屋场里有大大小小二十几个伢儿,可女伢少的可怜,这些伢儿有念书的也有不念的。
这天下午,队长照例在喇叭里喊出工啦出工啦,过了好一会儿,社员们才三三两两地朝屋场前那棵大枫树下聚拢而去。
有两个半大的伢儿赶着黄牛从屋场里出来了。那男伢矮墩墩的,叫葫芦,十四岁;那女伢瘦高瘦高的,叫迎枝,也十四岁。在屋场那群伢儿中,像他俩这样半大的,只有三个,唯独迎枝是做种的女伢。过粮食关那会儿,屋场的女伢大都饿死了,当时迎枝的舅舅在集体食堂里烧饭,常偷点锅巴悄悄给她妈,所以捡了条小命。还有个同龄的男伢在公社中学读初中,因为他父亲在大队当会计。
葫芦的爷爷解放前夕买了十来亩水田,所以他家是地主成分。爷爷死后,葫芦那老实巴交的父亲成了地主阶级的继承人,葫芦也成了地主家的狗崽子。“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会儿,有天夜里迎枝的父亲拉肚子,急着上茅房,随手撕几页红宝书用了,两天后队里一个造反派小头目在他家茅房里解手时发现了,由此,迎枝的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葫芦与迎枝读完小学三年级就歇学了,“地富反坏右”家的子弟念那么多书干嘛呢。他俩都没满十五岁,算不上半劳力,队长按队里的规定不许他俩干活挣工分,他俩只有放牛。两人的父亲常在一起挨批斗,一起被罚到大队去做义务工,伢儿们与他俩划清了界限,不同他俩玩,他俩就在一起作伴。
太阳烈烈地照着,将牛赶到山坡,葫芦与迎枝来到树下躲荫。两人又玩起过家家,葫芦扮当家男人,迎枝扮烧锅的堂客。葫芦学着大人的样子大大咧咧地说,过年了,怎么不杀鸡杀鸭做年夜饭啊?迎枝随即应道我这就来做,拿个石头当鸡,做出个杀的动作,又找根树棍子当鸭,杀了。然后将石头与树棍子放在葫芦面前说,年夜饭做好了。葫芦将脸一唬:酒呢,怎么没酒?迎枝笑着说酒在烫着呢,我这就拿来,说罢,找来两个瓦片,又用一个石头做酒壶,做出筛酒的样子,对两个瓦片筛了筛,说,喝吧。葫芦拿起个瓦片对迎枝说:堂客,我俩一起喝。迎枝拿起瓦片笑嘻嘻地说:祝你新年快乐,伸手与葫芦碰杯。葫芦笑着说,来年给我生个儿子啊。迎枝咯咯直笑。这时,有人喊牛跑进地里了。牛跑进地里踩坏棉花棵要罚工分的,两人将手中的瓦片一丢,赶紧跑去牵牛。
将牛牵到河边让牛吃草,瞧身上大汗淋漓,葫芦把小裤头一脱,往河里一跳。迎枝也将短袖褂子脱了,光着上身下到河里。迎枝个子比葫芦高半个头,可瘦的像个芝麻架子,胸脯上骨头一根根暴着,两个奶晕如铜钱花般平展展的,奶头子也干瘪干瘪的如枣核,上身与葫芦的没啥区别。也难怪她瘦,家里有点吃的都让她哥吃了,用奶奶的话说,哥吃饱了要干活,你个女伢,喝点米汤吃点山芋皮,饿不死就行了。这次她没像葫芦那样光屁股下河,而是穿着裤子。前两天她打光腚与葫芦在河里玩水,被一个回家给孩子喂奶的堂客看见后,向她奶奶告了状,奶奶骂她了。迎枝的妈有年冬天在塘边洗衣服不慎跌进塘里淹死了,迎枝的父亲被管制,家里的事都由奶奶说了算。奶奶叫迎枝向东她就不敢往西。
小河不宽也不深,杂草丛生。葫芦会划澡,迎枝陪他玩水玩多了也会划。两人鸭子般在水里玩了一番,葫芦就扎猛子沉入水底拉土巴子禾。土巴子禾是一种水草,长得青乎乎盈嫩嫩的,是喂猪的好饲料。他拉一把往河坝上丢,迎枝也扎猛子拉,也往河坝上丢。两人就这么乱丢,不分谁是谁的,等拉好上岸再拢在一起分,谁多谁少并不重要。
葫芦正拉得带劲,迎枝忽然惊叫着从水里窜上岸,哭喊着蛇钻进裤裆里了。葫芦赶紧爬起来,问在哪儿?迎枝边跺脚边牵抖湿漉漉的裤子,说在里面。没等话说完,她哎呀一叫,一蹦多高,叫着蛇咬她了。葫芦顾不得许多,一把将她的裤子扯下来。裤子里果然有条手指头那么粗的水蛇在搅动身子,葫芦一把抓住,使劲往地上一摔,然后用脚后跟往蛇头上一跺,用力一转。那水蛇卷曲着挣扎一会儿,身子就直抖了。
迎枝哭着叫疼,葫芦索性将她的裤子拉掉,问咬在哪里?迎枝指指胯间说咬在那儿。葫芦低头一看,她胯裆的腹沟处有蛇咬的牙印子。见她疼得直叫唤,忙跑到田埂边扯来一把叫地金黄的草,用手揉成团,按在水蛇的牙印子处,替她轻轻搓揉着。葫芦的父亲告诉过他,被水蛇咬了,地金黄的汁液能止疼,葫芦的腿去年被咬了,就用这草揉好的。迎枝晓得这事,就咬牙任随葫芦搓揉。常在一起光屁股下河,葫芦对迎枝胯间那“小沟沟”看多了,也不觉得稀奇。揉着揉着,当迎枝瞧见葫芦的“小胡椒”翘起来了,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抓起短袖褂子遮住下身,不要他再揉了。
不揉就不揉,葫芦瞧那蛇的尾巴还在动,拎起来边骂边将蛇皮剥了,甩在石头上让太阳曝晒,然后又将迎枝的湿裤子拧干,挂在树杈上。来到树荫里,他让迎枝替他刮背上的痱子。
迎枝见裤子干了,穿在身上,说要回家。葫芦将拉起来的水草拢在一起,分成两股,用草绕子捆好,每条牛背上搭一捆,牵着牛与她一起往回走。迎枝走路一拐一拐的,葫芦问蛇咬的地方还疼吗?迎枝说有点,要他别将这事对她奶奶说。
队里在立秋前忙完了“双抢”。趁有新米吃的高兴劲,队长请公社放电影的人来放电影。放电影是大事,屋场各家各户都请亲戚来看。看电影时,葫芦在人群里找到迎枝,问她怎么没去放牛?迎枝说她家来人了,奶奶不许她去。葫芦问谁来了,迎枝说一个是她舅舅,另外一个老头子不晓得是谁。葫芦家当晚也将他姑姑接来了,因晚饭吃得太饱,葫芦说要拉屎,走了。过了片刻,他又挤进来硬将迎枝从人群里拉了出来,说看见好东西了,要她去瞧。迎枝当是看什么好东西呢,跟他去了。
葫芦将她引到刘麻子家窗下,要她望。刘麻子是石匠,正月里被队里派去修水库了,一直不在家。迎枝趴着窗台朝里望,是刘麻子的堂客贵萍在生伢。生伢这事,迎枝没见过,葫芦更没见过。他俩见满头大汗的贵萍双手抓着床档在用力,吓得气都不敢喘。贵萍在喊叫着使劲,随着哇的一声哭啼,娃儿生下来了。葫芦松了口气,迎枝也松了口气。就听贵萍问是男伢女伢?接生婆对她说是女伢。刘麻子的娘伸手接过那才离开娘胎还在哭的婴儿看了看,二话没说,往门旮旯的尿桶里一丢,将盖子“叭”地一下盖住,拎出去了。见状,葫芦与迎枝惊的眼珠子差点儿掉下来了。
离开刘麻子家窗户,走远了,葫芦问迎枝,伢儿才生下来,干嘛丢进尿桶里淹死?迎枝说贵萍生了大毛、二毛都是女伢,现在生的又是女伢。还告诉他,前几天根宝家堂客生的也是女伢,没过二天就死了。葫芦伸伸舌头不吭声了。
第二天葫芦就听说迎枝说婆家了。迎枝的哥比迎枝大十岁,好端端一个英俊小伙子就是说不到堂客,一是他父亲是受管制的现行反革命,二是方圆好几十里没有合适的姑娘。迎枝是与她哥换亲的。对方那家有一对姐弟,那弟弟与迎枝的哥哥年龄差不多,可那姐姐都二十六七岁了。那姐姐之所以在家当老姑娘,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合适的人家换亲。放电影那天,迎枝的舅舅与那老头一起来说这事,队长从中做媒。说年龄时,奶奶告诉对方迎枝满十六岁了,队长也说满了。换亲的事说定后,奶奶就将迎枝关在家里养身子,那儿也不许去,房门都不准出。葫芦到迎枝家找过她几次,每次没见到人影就被她奶奶呵斥着撵了出来。
到了下冬天,有天,迎枝家办喜事了。对方开来一辆手扶拖拉机,将那位大姐送来后,下午将迎枝接走了。离开屋场时,迎枝穿一身红衣服,扎着红头巾,哭哭啼啼坐在拖拉机上。葫芦穿着破棉袄跑来看热闹,迎枝望见他,低下头哭得更伤心了……
葫芦二十岁那年,娶了比他大一大截子的贵萍做堂客。刘麻子在水库工地,不慎被开山放炮飞起的乱石头砸死了。成亲那天,来喝喜酒的队长拍着葫芦的肩膀,对他说,像你这样人家的子弟,能娶个过家嫂,不打光棍,就是福气啊。葫芦连连点头说那是那是。
第二年春天,贵萍带来的大毛害脑膜炎死了。
年底,贵萍给葫芦生了个白胖白胖的男伢。伢儿生下来时,贵萍也不顾痛,拍着巴掌大笑,说她到底生男伢了,并给宝贝疙瘩取名叫金狗。
金狗两岁时,八岁的二毛出麻疹发高烧。夜里见二毛烧得手脚抽筋,葫芦急着去找队长借钱送二毛到公社医院治疗。
贵萍却阻拦说:诊啥诊,反正是女伢,死了拉倒。
葫芦将脚一跺,冲她大声嚷道:
你晓得个卵,二毛死了,金狗长大了,拿什么换堂客?!
责任编辑 陈晓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