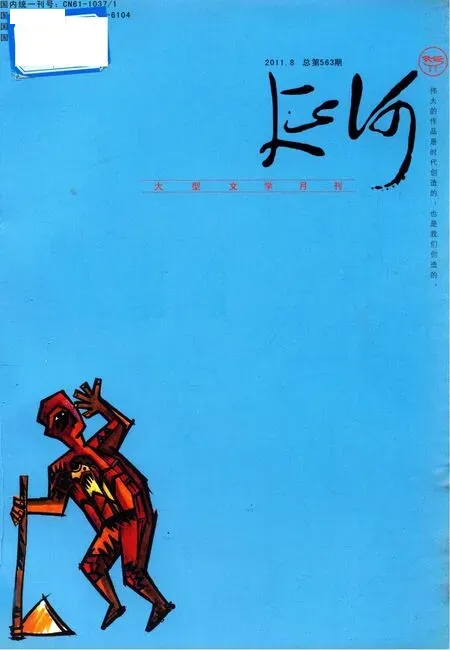我的故乡消失在时间深处
岳 静
清明时节,总听人说要去某个地方祭奠某个亲人,去时拎着纸火茶点,回来时一双眼红红的。我心中也有想祭奠的人,却没有这样的去处。
今年又是这样。清明节,看见一位妇女在河畔燃起纸火,哭得很凄惨,引来一些围观的人。她的儿子外出去山西煤矿打工,在乘坐渡船时,船覆人亡,尸首无回,她每年都在河畔为儿子招魂。
我想,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在相距遥远的故乡日夜守候,灵魂深处却游荡着思乡者的记忆。
童年种种
姥爷有五个孩子。大舅在文革中不明不白地被人谋害致死,二舅在文革中武斗,获罪入狱,被判刑期20年,母亲、三舅和小姨分别远在陕北、新疆和东北支边。老伴去世得又早,他的悲与痛无人能解。所幸有我在他身边。那是些孤寂而艰难的岁月。
在我七岁要读书的时候,因没有北京户口,不准借读,只好离开北京。大人们老早就提醒我,准备随父母去陕北。
我们走的那天,我和母亲坐上了平板车,周围堆放着行李。就要动身了,却不见姥爷,显得很寥落。
姥爷为什么不来送我们呢?我假装口渴,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回屋看姥爷在干什么。
姥爷坐在床边,背朝着我。我奔向八仙桌的茶盘,端起那个盛凉开水的天蓝色搪瓷壶,对着嘴一气猛喝。我弄出了很大的响声。很奇怪,姥爷仍不看我,却抬起右手,擦眼泪。
年幼的我,一下子充满了恐惧,不知如何是好。我立刻逃离了,奔向多年来并不熟悉的母亲。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抚育我整整七年的姥爷,那个需要安慰的老人!
我离开四年后,姥爷去世了。当时,母亲因我们姐弟仨衣食无着,无法回京奔丧,父亲回去代母亲料理姥爷的后事。
隐约地听大人们讲,姥爷的晚年很悲惨。那时,小姨已经返城回京,并已结婚生子,她和姥爷住在一起。由于屋子小,外面就接出了半间,姥爷就住在这半间。小姨夫嗜鸽如命,他饲养了几十只鸽子,把卫生条件搞得极差;小姨夫脾气不好,姥爷也是性强之人,其间有许多摩擦。姥爷去世了,身边竟没有一个儿子为他临终收气。二舅和父亲也没有在公墓给姥爷置一个牌位,而是在山脚找了个没有人看管的地方,将火化的骨灰就地掩埋了。现在大家都忘了那个地点。
那个年代,人真是太贫穷了。
姥爷是最疼我的,他一边上班,一边带我,下班后给我带回冰棍、小人书和两只手抓都抓不过来的水果糖,包着各色各样的漂亮彩纸。我被马蜂蜇了,又不愿敷药,姥爷给我涂药时,被我咬破过手背;姥爷责打过闯祸的我,但我只记得他滴在我脸上的懊悔而温热的老泪;姥爷牵我走在合欢树下,那弥漫花香的夜晚……在那些缺少父爱母爱的日子里,我在一个老人那里得到过怎样的温暖啊。
每每游荡在记忆的小巷,搜寻从前的故人,掠过的往事如那云烟似的,难觅踪迹。
又是清明时节了。陕北有吃摊黄、捏燕雀的习俗,但我知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追忆家谱、祭奠亡灵的传统。
老妇人在河畔燃起纸火。我脑海里却想起那古旧的中国诗词。笼罩在夕阳里的傍晚灰絮翻飞,寒鸦在始终不倦地做着凄惨的啼鸣。据说,河水与黄泉相连。她的牵挂与祝福,亲人们会听见的。
就在月下焚一柱心香吧,让那缭绕的清烟抵达姥爷居住的天国。
我怀念那些失去的东西。包括那些小女孩心中珍藏的童年。
我孤独的童年在北京渡过。
六五年,父母远离故土北京,去陕北支边,后来,他们在那里结了婚,有了我们姐弟仨。当时,父母并不在一个县,我随外祖父母,大弟寄养在陕北当地农村,小弟弟跟祖父母,一家五口人天各一方,彼此不能见面。我五岁时,外祖母去世了。
童年的记忆中有外祖母的歌谣。外祖母为我梳头。用来给梳子蘸水的细瓷小碗儿,碗里的水清亮,闪着细碎的光。
记忆中没有爸爸,没有妈妈。
没有北京户口,我没有入托。外祖父上班,就把我锁在七平米的昏暗的小屋。蜘蛛一样的寂寞,幼小而忐忑不安的心。房屋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是熟悉的。几本翻腻了的破旧不堪的小人书。看烦了窗外灰朦朦的天,多想做天空中间那朵飘逸的云儿。冰凉的雨水潲进来,打湿了我垄断已久的的世界。后墙的窗台上。一只避雨的花猫盯着我,“喵喵”直叫,是想让我为你打开那扇高高的天窗么?顶棚上的老鼠“吱吱”地打闹。外祖母的骨灰盒就在那上边。那个孩子把头埋进床角的被垛里,呢喃着:“小静没妈妈,小静没爸爸。”她是在伤心的哭泣中睡去。
外祖父下班回来了。我有一些跟伙伴们玩耍的机会。常听伙伴们讲外面的精彩,就求外祖父带我出去。外祖父的工作没有星期天,便把我送进月坛公园的阅览室,嘱咐我别乱跑,下班时他来接我。我独自在阅览室看图书。出去玩,总被人欺负。玩木马挤不上,荡秋千没人推,溜滑梯没人接,好不容易排队排到跟前,不敢溜,被有父母在底下接的孩子一路抢过去。
我忍受不了开心的笑。五岁那天,我从月坛公园孑然回家,坐在门台上等外祖父。竟一直等到天黑。外祖父下班接我,却怎么都找不到,无奈,只好报了案,回家等消息。晚上,我挨了一顿老拳,早早地上床,装着睡着了。外祖父用热毛巾给我敷脸。我知道他从来舍不得打我。从此,外祖父上班,我就被深锁在小小的四合院。
我每天都在编织一个幸福的梦。玩具,漂亮衣服,偎依在父母身旁,听到父母的声音。
母亲回家为外祖母奔丧。我和她并不熟。母亲坐在小凳上,把我搂在怀里,用脸蹭着我的小鼻子,她的呼吸像一股热浪,缓缓地涌进我的身躯,在那一刹间,我残损的心终于被缝补起来,那是多么的甜蜜啊!母亲伏在我耳畔悄悄地说:“你知道妈妈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吗?”我知道是大红枣,是我唯一可以向伙伴们显摆炫耀的大红枣。外祖父说,北京的枫叶红了的时候,陕北的枣也开始红了,你妈妈就带大红枣回来看你。但在母亲生疏的怀里,我不敢笑也不敢说话。我盯着母亲慈爱的眼睛,一下子挣脱了她的怀抱。我跑回屋子翻着母亲的行李包,找红枣吃,有些花花绿绿的小票子,新新的,纸质很好,非常漂亮,我悄悄拿了几张,藏在身边。那几张是五市斤的全国通用粮票,是母亲省吃俭用以两倍的陕西地方粮票换了路上急用的,加上钱,那就是一个人近半个月的口粮。那个年代,没有粮票就没有饭吃。母亲急着找,可哪都找不到,最后从我的裤兜里翻了出来。母亲满院子追着打我,我围着鱼池转着跑,母亲追不到,便拿起鱼池边的半块砖头吓唬我。一不小心,我把鱼池上的一块砖碰得掉进了鱼池,砸伤了一条金鱼。
我的境况是我们姐弟仨中最好的。祖母是祖父续娶的上海人,脾气乖戾,加之语言不通,对我那个小弟非常苛刻,大弟的奶父母是陕北当地成份最好、生活最穷苦的人家,把大弟养得面黄肌瘦。直到上学年龄了,天各一方的几个孩童才聚在一起。
母亲把我骗到陕北,她说带我去吃一种很甜的红面。其实就是高梁面。我知道,我走了外祖父很孤独,就和他说好,过两天就回来跟他玩。但他总是偷偷地哭,临走也不肯送我。四年后,他去世了。
陕西的日子并不好过。父母工作很忙,常常下乡,但对我们要求很严,时常把我们锁在家里。年幼的我们要做许多家务:烧火、挑水、煮饭、洗碗等。我们姐弟仨都贪玩调皮,总是犯错误,所以经常挨打。邻居们都说父母不疼爱我们。看看周围的孩子,都比我们快乐。
回想起来,父母的爱其实一直就在身边。记得有一次,我得了急性黄胆肝炎,父母一直在医院守护着我,眼睛都熬红了。当知道我想吃蛋炒饭时,父亲跟邻居借了两个鸡蛋,给我炒了满满一大碗香喷喷的白米蛋炒饭。父亲说,家里只有羊油了,凑合着吃吧。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父亲那歉意的目光。可他哪里知道我是故意得病,专门多次找有病的孩子传染的。在我康复后,父母不放心,又带我回京检查,所花费的财力是非常可观的。
那时候父母每隔一、二年就要回京探望双亲。父亲风趣地说把钱都给修了铁路,支援了国家建设。一家人要吃要穿,我们要上学,加上母亲身体不好,常常买药,他俩每人三十七块半的工资一发下来就先出门还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从来没有宽裕过,老是跟单位借钱。父母的严厉使我们不同于周围的同龄人,我们很早就有了独立自理的能力。
父亲这代人,无论是对理想的献身,对事业的执着,还是对工作的热情,都是无与伦比的。为了响应毛主席支援边区建设的号召,母亲多次写血书未被批准(按政策,她必须留京照顾年迈的双亲),便擅自偷偷地注销了北京户口,毅然加入到支边大军中。和父母一起到陕北的支边人员中,有的想家想疯了;有的挨批遭斗,身体致残,卧轨自杀;有的为了回京,私自逃离,一路沿讨,沦为乞丐……我的父母却在当年拼命劳动,落下了一身疾病。他们在陕北扎根四十年,为这里的林业建设奉献了青春。作为工程师的父亲,曾受到国家林业部的嘉奖。
该是燕子南迁的季节了。传说,燕子南迁时要过一条很宽很宽,辽阔无垠的大江,飞到这里,老燕子已无力再飞,要靠子女驮过江去。
一直在想,屋檐下的那双燕子只育得一个孩子,他们如何过得江去?
我的女儿听见了我的话,笑嘻嘻地说:先驮妈妈一程,再来驮爸爸呀!
黑白两色的滋味
生命中见到的第一台电视机是在姥爷的单位——北京广播事业局。电视很小,黑白的,里面的人能说话,会唱歌跳舞,是当时见到的最神奇的东西。
母亲曾工作的蚕种场,七十年代末效益很好,要拿钱买台电视。因母亲老家在北京又搞出纳工作,所以特地选派母亲去办,母亲回京找关系买好电视后,被安排坐飞机把电视带回来。那个年代坐飞机可是件大事,母亲沾了金贵的电视机的光,不知有多少人羡慕呢。
电视机受到夹道欢迎。它很大。黑白的,熊猫牌,放在一个高高的特制的电视柜里,平时上着锁,有专人负责。只有在周末或假日的晚上才打开来看。这个拿钥匙的人,牛得不得了,谁都巴结他。
后来,我们一家人离开蚕种场住到了父亲的单位,就跑到很远的畜牧站去年看《血疑》,每次看完,眼睛都会哭肿。山口百惠的歌声至今一直记得。她和三浦友和这对金童玉女演绎了男女之间的不朽爱恋。在我情窦初开的时候,这架黑白电视带给我无限神往。
《霍元甲》热播的时候,万人空巷。孩子们把播出之前的广告词倒背如流。“长城电扇,电扇长城”、“西铁城手表,为您报时”、“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那时父亲单位已有了电视,而且有一个时期,我拿着电视柜的钥匙。不论迟早,只要我拿着折叠椅出来,就会有欢呼声。很多孩子都等着那一刻。会议室里的人黑压压一片,但会给我留出最好的位置。不过,每遇停电或是信号不好时,就很麻烦,有时要去楼顶扭转天线杆和微调,往往不起什么作用,忙活半天,电视节目只剩个尾巴,能急死人。
电视机大举进入普通家庭是八十年代末的事。记得我家的电视是父亲背回来的,电视箱上缠着一层层的绒毯。父亲神情庄重地把电视仔细地拿出来调试,并不许我们动。那时看到的是《渴望》、《四世同堂》、《红楼梦》。那个时候,春晚的每一首歌都会红遍大江南北。每部电视剧或电影的插曲同样是要大红大紫的。
我做了陕北小县城清涧县里的第一代电视播音员。最初的节目制作是两台录像机对剪,灯光是两根三角木架上竖起的四根日光灯管,如今的演播大厅灯火辉煌,电视节目从制作到播出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电视机也早已更新换代,大尺寸的背投、液晶和等离子电视也不算稀奇了,电视信号从模拟到数字,频道由一二个变为百余个。但是,再没有谁像我们那代人一样对电视机如痴如狂。
我们这代人就像那片高原上濒临旱季的枣树花。从第一次睁开眼,就目睹了炽热的磨难。
在我的故乡,叫枣花的是我的邻居。她出生时,正是黄绿色的枣花飘香时节,便得了这个名儿。枣花是姊妹中的老大,还有个妹妹和小弟弟,放学后,枣花要干很多活,但她功课好,深得老师器重。她长我两岁,却矮我一截,天生一副俊俏可人的模样,能干,麻利。
枣花家有一株老枣树结果不稠,但个大肉厚,又甜又酸,好吃极了。我和伙伴们经常爬上去摘枣吃,被枣花或是她妈撞上,并不怪罪,还找来挠钩,帮我们打枣,弄得我们反倒不好意思再偷嘴了。
枣花的父亲死于摆渡,为了多赚些钱,船严重超载,水又急,一船的人都被涛浪吞了进去再也没能出来。
我怕看摆渡,怕看枣花那双凄兮兮的眼。
顶梁柱倒了,却留下无尽的债务。使枣花家本就不景气的日月更是一落千丈,她干更多的家务,流更多的泪。
都说:晚上,枣花家进去了野男人。村里的女人都不理枣花妈。小伙伴们也经常欺负枣花,骂得难听,还用石头砸。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挺身而出,但我们寡不敌众,总是落得鼻青脸肿。额头也磕出血,至今仍留着疤痕。
天寒地冻的早晨,雪后,枣花挑水。路又陡又滑。摔了一跤,一对小桶滚到沟底。我飞快地跑向沟底,拣回瘪了的桶,打满水,想帮她挑,她不让。我使劲一拽,要抢担子。她突然“哎呀”一声,一手捂住另一只手,泪珠在眼眶里转。我慢慢掰开她的手,发现这双紫红发肿的小手上刻满了一道道深深的、正渗着殷红鲜血的口子,那是冻伤的裂痕。我扯痛了她的伤口。
她急急地抽回双手,用嘴吮了吮,说:“不要紧,不疼!”
我拉过枣花的双手,放在嘴边,不住地呵着气。我脱下自己的兰布棉袄给她披上。她低着头,不好意思地用手遮盖着自己又破旧又短小的花袄。她咧嘴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很美。
后来,我转学到城里,节假日才能回家,看到的枣花,仍是匆忙而憔悴。我考上初中这一年,枣花也考上了,这可是县立中学,于她是多么地不易啊!开学日子临近了,枣花肿着眼,问她,她说没睡好。动身这天,枣花老早就等我在村口了,她说:“我不能去了。”她指着树上的小枣说:“别忘了,回来吃枣啊!”
枣花果然没来上学。枣红时节,家乡的亲人们举着挠钩打枣和提着筐子捡枣的情景总是在我眼前浮现。石畔上摊晒着颗颗清涧大枣,无边无际的红色海洋中,一定有枣花的身影,她那条浅篮色的丝巾非常显眼、非常漂亮。
枣花嫁给了城郊的一个农民,那年,她才十五岁。再见枣花,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一张脏兮兮的脸,一头乱蓬蓬的发,衣衫褴褛,眼神暗淡而无光,活像一座未完工的泥雕——她那俊俏可人的模样哪儿去了呢?
母亲说,枣花生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儿。公婆浅看,男人待她也极刻薄。为了孩子,枣花才活到今天。母亲说:没法子,命啊!
好多年一晃就过去了。岁月的流逝不断激起我更切的乡情,被牵绊的心日日企盼着归巢。我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回乡之路。
扑面而来的是泥土芳香、古朴亲情。昔日的故乡河,依然流淌,却瘦了这么多!老远就见枣花家硷畔上那棵枣花点点的老树……这些年,枣花怎么样了?脚下,是那口老井,井口四周没有了淤泥,不见了挑水人。延伸的小道已经陌生了许多,各家都起修了新窑,院院竖起了绕着井绳的轱轳。
见了乡亲,便“大叔”、“大婶”地挨个问好。“哟,都不敢认了!我算是有福气,回趟娘家竟赶上你回来,”枣花家硷畔上一位少妇在打招呼。
看到她,我一愣,四目相对,恍若回到了儿时旧梦——是的,真的是枣花!容光焕发的脸,粗粗的发辫整齐地盘在脑后,一袭干净可身的套装,代替了我记忆中那件破旧而短小的花袄。我惊诧于她脆生生的甜美嗓音。枣花说,她如今领办着一家私营枣产品加工厂,不再受穷了。
“快喊阿姨,”枣花领着她的女儿玲儿来见我,那小模样儿简直活脱脱一个小枣花,尤其是笑起来眯成缝的那小眼睛。“玲儿,学得怎么样?”我拉着玲儿的小手问,玲儿只是笑,露出嫩嫩的白牙,不肯答。
“还不错,你知道,我是叫娃们一心念书的,”枣花满足地说,满脸洋溢着浓浓的笑意。“玲儿,让阿姨好好教你,将来好有出息。”
“别忘了回来吃枣啊!”望着她娘俩儿,往日那好沉好沉的负重感终于坍塌。
依稀夜风送过淡淡的枣花清香。远处传来河水的动荡撞击声,如我波澜的心潮。消瘦了的故乡河,依旧流淌在我心里……
食不语
清涧煎饼。清涧一种独特的地方风味小吃,用荞麦做成。元代王桢《农中》就有荞麦“治去皮壳,磨而成面,摊作煎饼,配蒜而食”的记载。煎饼的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先要将荞麦粗磨去皮,得了糁子,再将糁子用水浸足,入布袋反复揉搓,挤出浆液,按一定的比例兑水后,在特制的煎饼鏊里摊制而成,配以姜蒜烫汁或熬制的蕃茄酱汁蘸而食之。煎饼晶莹如白雪,轻薄似蝉翼,柔韧绵冽,其味沁人心肺。
我在清涧长大,拥有了故乡。在这山沟沟里生活了几十年,难保骨子里不渗进去些异域的饮食文化,皇城根儿的许多名吃,比如,烤鸭、煎灌肠,我就吃不惯;豆汁、莲子羹,我更咽不下,前者太腻,后者涩苦,来一碟清涧的煎饼,那才真正地叫爽呢!
年幼时,我们姐弟仨偶尔会用攒了很久的私房钱在煎饼摊前偷着解解馋。钱大都是买纸笔所剩或是卖废品所得的几分钱累积的。每次都吃得格外香甜。
摊主大都是些老者。一位老大妈,在矮矮的屋檐下,盘腿坐在火炉旁,边烧风箱,边摊着煎饼,一摊一拣,一折一卷,再放到我们的蘸碗里。煎饼虽不夹卷着些什么,但已是人间美味了。
摊子少,每个煎饼摊前都会聚拢了一些人。不富裕,人们很少有闲钱来天天吃煎饼,所以每日所聚的人不一样。虽比不得下馆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洒脱,但也是很侈奢的享受。
京城一些老字号的小吃让人觉得真是老了,清涧煎饼却力求创新。卖煎饼的人不再由老者垄断,煎饼摊子不再拘于房前檐下、小筐小担,街道两边的煎饼馆比比皆是。清涧煎饼的吃法越来越多,仅蘸汁就有几种吃法,煎饼里面还可卷进各式蔬菜、豆腐干、猪头肘子肉等等。提到这肘子肉,不能不说其中一位刘姓师傅制作的酱肘子,真是香软酥烂,他家卤肉的配料是祖上留下来的,据说那卤汁的老汤传了几辈子了,轻易是不带给买主的。他家的酱肘子常被人三、五百块钱地买了,与煎饼一起送给外地的亲戚。
我每年都要送出不少的煎饼。父母兄弟返京十余年了,而对清涧,除了亲情,最为放不下的就是这煎饼。节前父母和二弟夫妻回来小住的这几天,煎饼自然必不可少,二弟妹还说,这午饭煎饼晚饭煎饼,早餐也是煎饼,怎么就吃不够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在大冬天里,光着屁股裹着被子围在一起吃煎饼,或是蜷缩在热炕头的被窝里期待挑煎饼担子的小贩吆喝声响起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那时,要找一口吃的,只是个难啊。
煎饼,粽子,都是多么奢侈的东西!
小时候吃的粽子真的很香。那时,包粽子是一件盛事,端午节前就早早地预备着了。每家都有三五个孩子,再加上礼尚往来的人情门户,所以,免不了要请张家婶婶、李家婆婆来帮忙。
父亲便是常被人请去帮忙的包粽子能手。
一般人家,粽子都是女人包的,而我们家,母亲偏偏一辈子不会包,父亲却包得又快又漂亮。端午前后,父亲常常是出张家、进李家,红得不得了。有时,他直到初五这天才能赶出自家吃的几个粽子。父亲乐此不疲。
父亲包粽子的用料非常讲究。对于红枣,他一看成色就知道产地,他专挑个大而无虫无损的清涧东河畔红枣,皮薄肉厚,绵软甘甜。他宁肯多花钱,也要选用上等的宽大粽叶。糯米是头天晚上用水浸好了的,包的时候,粽叶要先放进大盆里用开水烫一烫,叶片才会柔韧起来,不再容易折裂。父亲包的粽子棱角分明,叶子与叶子一个方向毗邻地挨着,并不花插开,吃的时候,系带往开一打,粽叶往上一提,整个粽子就骨碌到了碗中。
父亲是林业工作者,常年在野外下乡,很少回家,但是每个端午节都赶回来包粽子。父亲包粽子的时候,我们姐弟仨就蹲在旁边,跟父亲学。我们听父亲讲说故事。抱憾投江的古代诗人,吃粽子、龙舟竞渡等习俗。母亲会在一旁拉风箱,对着我们微笑。
许多年后,老邻居们都四分五散地迁入新居,居家也独门独院,或凭窗相望,彼此往来极少。
卖粽子的一年比一年多了,少有人再来请父亲上门包粽子。
父亲时常追忆那些逝去的岁月。我们感受到了父亲内心深处的那份失落,我们的粽子仍由父亲来包。端午节这天,我们都会回父母家,依旧围在旁边打下手。父亲的粽子依然漂亮,但看得出,手脚慢下来了。父亲腰椎间盘突出症严重了,自己罢手不包。
没有父亲包的粽子,端午节是不完整的。从小商贩那儿买的粽子,根本就没有当年粽子的香甜味道。端午节淡之又淡了。再要吃父亲包的粽子已经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奢望了。
但我们还在期盼着父亲的年夜饭。
父亲的厨艺有点小名气。父亲做年饭都是很正式地写出菜单,权衡每道菜的取舍,然后按照菜单在腊月二十六带着我们进城备料。这是年前最热闹的一个集日,未来得及购置年货的人,大都要赶在这一天进城,要不,到腊月二十九就物价飞涨了。腊月二十六的清涧,人山人海。每次我们都被挤得浑身生疼,谁也找不着谁,就为了一年一次的年饭和一个正月“足鸡豚”的饕餮之乐。
父亲张罗的年夜饭总是很丰盛,十道八道的,满满一桌。我们穿了新衣,贴了对联,放了炮仗,便迫不及待地坐在桌旁,在“噼噼啪啪”的炮声里,一家人猜灯谜,打杠子,好不热闹。
父亲做的京味儿菜很诱人,并且擅于自创。记得有一次父亲用猪肠衣自制香肠,卤了满满一大锅,香远益醇,还没熟透,我就蹲在灶台边吃。
如今生活好了,父母却年迈了起来,我们也如纷飞的劳燕,远隔千里,无暇时时回家守候在他们的身旁尽孝。放假了,年关也悄然而至了,一票难求加之旅途劳顿,回京探亲,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然而呆在自己的家里,又彼此饱尝思念牵挂之苦。
去年终于有空,总算踏踏实实地守着父母过了一个春节。大年初一,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闲散地聊着。父亲突然说:“丫头啊,都全了,就把你一个扔在了那么远的穷山沟。”
没人接这个话茬儿,热乎乎的气氛顿时凝结了一般。父母在陕北支边近四十年,返京已十多年了,独把我留下了,这是父母长久以来的心病。我笑着说,你们在那里开花结果,总得留下种子吧。母亲开始哽咽,泪顺着她抽搐的颊、嚅动的唇滴到了饺子上。
关于饺子有一些颇深的记忆。
《白毛女》中的杨白劳,怀中藏着一点白面,在大雪纷飞中,赶大年三十儿躲债归来,就是想让女儿在这天开心,有顿饺子吃。杨白劳临死都没吃上一个饺子。被喜儿当作无价之宝的一根红头绳铭刻在我的脑海。
我有一个好母亲。记忆里的饺子是圆的。
母亲包的饺子薄皮大馅儿,色香味浓,还捏着花边儿,或是小老鼠的模样,又可爱又好吃。母亲擀皮很快,父亲领着我们全家上手包,她都能供上。我们姐弟仨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母亲做饭了,只是擀不会饺子皮,长的方的三角的都有,就是擀不圆。
母亲伴的饺子馅很香,有鸡蛋韭菜的,有猪肉或羊肉大葱的,还有香菇海鲜(不过是虾皮)的,像芹菜莴笋茄子豆角南瓜西红柿等等各种蔬菜在母亲那里皆能入馅。茴香和韭黄的最好吃,但当时的小县城没有卖茴香和韭黄的,母亲回京探亲时会特意带回来。
每次包饺子前,人人都要说定自己准备吃多少个。报几个,包几个;包几个吃几个,不多备一个。等刀案瓢盆都拾掇好了,母亲开始做蘸汁,她用小擀面杖在小碗里把蒜加盐捣成泥蓉,捣好后还要将擀面杖头舔一下。烧好的水也要先灌满两个暖壶才能煮饺子,下锅煮的时候“一五一十”地仔细数着(直到现在我都有煮饺子数数的毛病)。饺子在锅里随着笊篱不停地推啊推。到完全熟透出锅的时候,留出了送街坊邻居的,才能盛到举了好久的碗里。等的人涎水都流出来了。
记得有一次,母亲为我们包了五彩饺子,饺子皮儿有红黄绿白黑五种颜色,很漂亮。白的是普通的面,黑的应该是掺进了巧克力,但想来那时应该没有那么多的巧克力,或是母亲倒了些酱油,也记不清了。黄红绿三色是用蛋黄、西红柿和菠菜的汁液和面做剂儿,捏出来的饺子,黄的像元宝,红的像晚霞,绿的像翡翠,晶莹透亮,非常诱人食欲。母亲一边做着,一边非常有成就感地微笑着地看着我们。
常常想起当我们咬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时,唇间留存的饺子特有的香气和味道。很久没有体验这样温暖的意味了。
“我的故乡,”这个艰难的命题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完结。现在,我一天比一天更深切地体会到:我的故乡似乎只是一堆模糊的记忆,在逐渐泛白的时光里,它经常就要进入漆黑一团的漩涡。
当我写下这些凌乱的生活,我不能说得更多了。对过往的一切,我昨天已经得知,它那令人敬畏的力量才刚刚绽放。
我们在相距遥远的故乡日夜守候,灵魂深处却游荡着思乡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