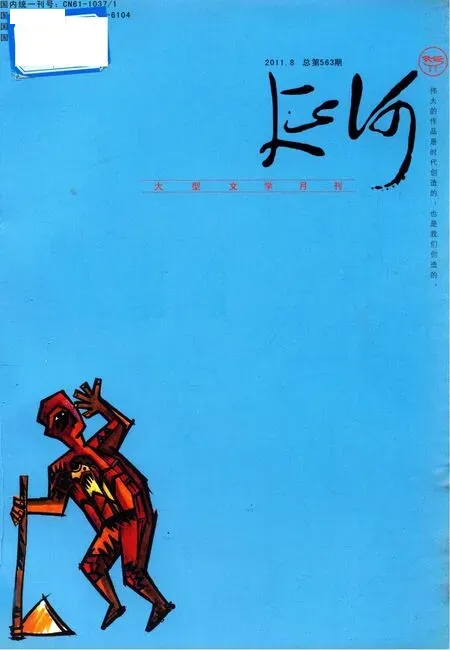闲 庐 谈 艺 录 (之七)
熊召政
乡愁是一次匆匆的登临
昨日,南昌的秋老虎肆虐,据说为百年之最。我们几位作家受南昌市政府邀请,前来参加首届滕王阁世界华人作家笔会,尽管阳光照在身上如油泼,但这并不减我们一行在滕王阁上凭栏远眺的雅兴。我们一行中年龄最大的是余光中先生,在六层的回廊上,他面对滔滔赣江,感慨系之,言道:“一千三百年前的王勃,在这座楼上,为南昌的文苑风流,写下了第一笔,只可惜我此时置身于此,却看不到秋水长天的景色。”
的确,《滕王阁序》可称为千古妙文,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更是脍炙人口的绝唱。如今阁内二楼大厅里,还悬挂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这两句,笔走龙蛇,是阁内最为大气磅礴的楹联。没有滕王阁,就没有《滕王阁序》;没有以上这两句,《滕王阁序》也就没有了灵魂。大凡写文章的,决不可找不到诗眼,或者妙句。没有它,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岂不是行尸走肉?
我理解余先生此番登滕王阁的心情,就是想通过槛外的秋水长天,来与王勃的灵魂契合。所谓思接千载,就是灵魂间的超越时空的相吸、相悦与相思。登楼之前,应主办者的邀请,余先生与南昌的少儿们一块朗诵了他的诗歌名篇《乡愁》。这首诗的朗诵,我听过多回,但听作者自己朗诵却是第一次。余先生略带南国乡音的国语,读起来更平添了乡愁的韵味。我的太太一旁听了,眼角溢出了泪花。这首诗非常浅显,几乎可以当作儿歌,但它感情的容量却是巨大的,我、新娘、母亲、大陆四个意象,层层推进,把一个人的飘泊生涯写得淋漓尽致。通过个人的乡愁可以感悟家国的沧桑。余先生的这首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会是中国诗史里不朽的名篇。
现在,与余先生一起站在这座滕王阁上,听他的惆怅,我便仿他的乡愁,对他笑道:“余先生,乡愁是一次匆匆的登临,我在这头,王勃在那头。”余先生听了,先是一笑,继而略作沉思地点点头,回答说:“王勃言‘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是初唐的乡愁。如今你我,以及这满楼的游子,尽管是他乡之客,但却不会是失路之人。”听其语意,可以揣度余先生要“翻新杨柳枝”了。可以期待,他将会为南昌的风流写下精彩的第二笔了。
2006年9月3月匆草
奕博的散文
中国有几个城市是适合文人居住的,像苏州、杭州、成都、西安等。所谓适合,当然是相对而言。最基本的条件是,这个城市必须有深厚的人文传统,城市周围有好山好水,城市的街巷里有雅致的酒肆茶楼。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的居民中,始终有一个欣赏文学艺术的阶层。老人有阅读的兴趣,年轻人有学艺的冲动。我在这种城市里,常常有如鱼得水的感觉。饮酒品茶,谈文说艺,每每得到娱心怡情的快乐。
今年春上的一天,我在西安与文友相聚。《美文》的执行主编穆涛先生将一个小伙子领到我跟前,介绍说:“他叫陈奕博,是名高二的学生,喜欢文学,尤其是历史散文。”我听了并不觉得奇怪。西安的风气滋养文人,在这座至今荡漾着汉唐风韵的古城里,官员作家、少年作家比比皆是。陈奕博拿出他出版的一本散文送给我。我随手翻翻,便觉得这位虽生得健壮,满脸却洋溢着稚气的高中生确有一股灵气,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成熟。我便同他闲聊了几句,发觉他的语气也像那种小大人,便有些诧异了。因席间人多,寒暄则可,深谈不易,便嘱咐他可将新写的文章通过电邮给我。过不多久,我收到了他传来的十几篇散文。大约因为我热衷于历史文学写作的缘故,奕博传给我的,几乎全是描写历史人物的散文。
不单西安城里,时下中国文坛,少年作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才华上都显露出锐不可挡的气势。但是,由于阅世不深,经历太少,他们的创作多半局限于校园文学或青春文学。像陈奕博这样超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生命的体验而欲解析历史中那些震铄古今的人物,在少年作家中虽不是唯一的,却也是非常少见。
试看下面这几段文字:
长安皇城,紫金宫殿,不仅拒绝为艺术家提供最朴素平实的理想土壤,也同样摧残着文学家施展政治才能,落实经世抱负的自由极限。
《长安的隐喻》
对高地的敬畏,往往成为人们行走世上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对高地的恐惧,也禁锢着人们遗世独立的生命理想。然而,总有人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孑然独立……
《高地的孤独》
太史公写项羽这个人,成在他的意气,也败在他的意气上。
《人文欣赏》
这种思考,这样的立论,出自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之手,着实叫人惊诧。我们说一个孩子的早熟,既指的是生理,亦是心理。但若用早慧这个词,则纯然指的是心灵了。
奕博的历史散文,选择剖析的对象是李白、王维、苏东坡、韩愈、项羽这样的人。这些人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理由,除了才华,还有他们的悲剧性的命运。生于锦绣时代的年轻人,喜欢和亲近这样一类历史人物,似乎可以望见他生命中的茂然气象,显出的不是常态,而是那种悲天悯人的孤峭。
奕博的散文,又让我想到了西安。历代许多文人的才情,堆砌起这座城市文化的高度。每一朝每一代,注定会有一些人站出来,接续这座城市的文化香火。奕博会不会是这种人呢,在他的文字中,似乎看到了某种端倪。
2010年8月21日
于力的把式
八百里秦川,两种人居多,一是庄稼人,二是文艺人。这两种人放在江南,便有天壤之别。但搁在陕西,倒像是兄弟两个。庄稼人重礼节,好佛道,爱秦腔,粗野中透着风雅;文艺人也是重礼节,好佛道,爱秦腔,风雅中掺着粗野。如果统一服装,你便分不出谁是庄稼人,谁是艺术家了。
就像本文要说的画家于力,乍一看,就是个庄稼人。见了生人,小眼睛眨巴着,显得局促,但酒杯子一端,见谁都不生分了。二两烧酒落肚,便无拘无束地与你谈笔墨与绘事。
于力转益多师,最后投到赵振川门下,这归宿尚好。赵先生的令尊乃“长安画派”创始人之一的赵望云。如今,振川已是长安画派的翘楚。于力投到门下八年,耳提面命,受益良多。
于力画山水,欣赏他的画,便看得出庄稼人的味道了。长安画派有句口号,叫“一手伸向山河,一手伸向传统。”反映在绘事上,就是要有扎实的写生,要有活泼的笔趣。于力的画作中,无论是八尺整张还是尺幅扇面,都是熟稔的三秦风物,都是典型的终南气象。在他的笔下,岩石也罢,烟岚也罢,树木也罢,都不是神仙的栖居,而是庄稼人的道场。庄稼人从土地上要收获,于力从笔墨中要精神。他要的精神,不是雅人的高蹈,也不是逸人的遁隐,而是农人的牧歌。
传统的笔法,功夫在线条上,而墨意,则存于晕染。有赵振川这样的严师指点,于力笔墨中学会了十八般武艺。犹如庄稼人,该使镢头的时候用镢头,该用犁锄的时候用犁锄。十八般武艺会了,就叫把式。我在于力的画中看到了他的把式,即将眼前的故乡变成心中的道场。
诚然,于力不是那种天分很高的人。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只是执著地追求他想要追求的,每天只想着一头撞到南墙上。这种犟性,就是不拿奸耍滑。
有造诣的画家,首先是涉笔成境,再往下走,就是涉笔成趣了。于力的画,还在有境无境之间,有些灵气他似乎拿住了,稍不注意又从笔缝里溜走了。往后,于力要像养宠物一样,把灵气养在心里头,化在手指上。画的真趣,必然就会流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