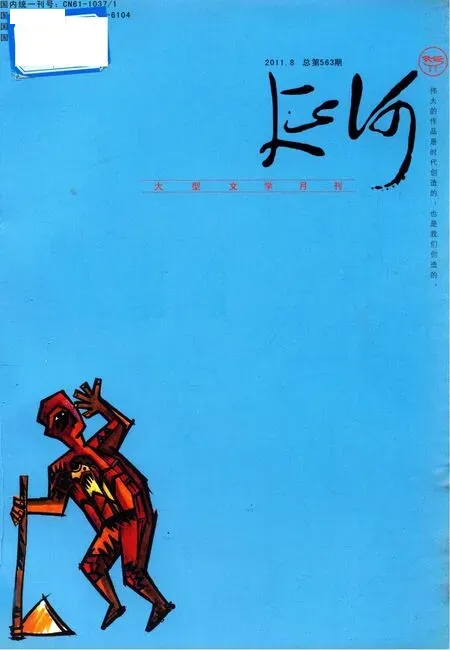无定河湾
马语
“呜哇…呜哇…呜哇”,一连串警车从无定河边的油路上拐下来,开进了草木深处的磨坊村,刹车急,在村子中心地带的村委会门前荒草丛生的土坪上晃荡了几下停住了。放学的孩子们数见,一共要有七辆翻转着红蓝灯的车呢。
此时,住在村东这个青石片垒墙小院里的牛德权老汉,也在腰里缠了一弯草绳,疾步出了院门,去了村南的山梁上。头一天晚上,村长就来过这个小院了,也许是因为有在县里当水务局局长的侄女女婿吧,村长只是淡淡地对牛德权老汉说,全世界才有十来八只的白天鹅,你就给弄死了两只,这回恐怕难说了。老哥呀,你总是不听我说的,又不是过不了日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什么逼你着了嘛?
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野物,牛德权向南山里逃遁而去。他爬上山梁,在他解下腰里缠着的草绳,把它拴在老杏树的枝杈上的时候,他回没回头呢?望一望山下村委会门前那七辆警车上红一团蓝一团转动的鬼火一样的东西,那条无声地翻卷着流向远方群山间的河流,那覆盖着无边枯叶的河边的田野……
当村里上山搂柴的光棍汉牛五发现时,那棵老杏树枝杈上,一根破草绳吊着德权老汉。
白天鹅回来,才是前一年的事。其实有好些动物早就回来了,或新出现在无定河湾,只是动物们多是昼伏夜出,不让人类见到它们。
隔两三天,老汉就得赶着驴车上一回山,到山上的苜蓿地里给羊割苜蓿。苜蓿地里有羊的蹄印,还有羊粪蛋儿,苜蓿枝条上有啃过的印痕,好怪啊,是谁赶着羊到他家的苜蓿地里来放牧呢?
一个有月的夜里,当他悄无声息地转到自家的苜蓿地边上时,他才看清楚了,是野羊。几只灰黑色的大山羊,但从它们那蹄脚和乍着的耳朵上看到,它们不是农家的山羊。见上了野羊,后来又看见了火狐。那是一场暴雨刚刚过去,阳光从乌云的缝隙射下来,一丛桑条边,一只锦鸡似乎被这刚出的阳光激发了美好的幻想,前跳跳,后退退,左右转着圈儿,脖项下那羽毛似金色的缎子,那长翎在身后划着优美的弧线,一辈子种地的一个老汉人,又怎么明白这样的动作是什么?在文人们眼里,这就是舞蹈,这该是大自然中多么美丽的生命之舞啊!突然,锦鸡上下扑腾,一只红狐随着锦鸡的扑腾在地上连翻几个跟头,就死死的噙住了锦鸡的脖子。这让老汉一下想起了儿子小时候,家里来的那只火狐,那年月,鸡窝是庄户人家的摇钱树,春夏之交地里的粮菜瓜果都没下来的那些青黄不接的时日,连点灯的煤油都要用卖鸡蛋的钱去打。就是平日里,几个孩子上学的铅笔、粉笔、书本子,都是用娘卖鸡蛋的钱换来的。大英小英的花布衫、印花棉袄,也都是用鸡蛋钱去供销社买的棉布。庄稼人哪容得狐狸夺走他们这活命钱,每年都要加固一回鸡窝,每天熄灯前,大人小孩总是会习惯性地去查看一遍鸡窝门关好没有,即使是这样,每年总有那么几回,要被狐狸抓走几只老母鸡。
当德权和他儿子在青山庙梁的山崖上发现狐狸的窝和那几只幼崽时,他们没想别的,只一个念头就是这就是捉吃他们家母鸡的家伙的幼崽,把它们给一窝端了。父子俩用筐子把四幼狐崽都给捉回来了,接连几夜都看见一只黄红的狐狸在他家院墙头爬着。但它没去抓他家鸡窝里的鸡。三天后,他们把小狐崽捉入筐中,放在屋门外,他们刚闩上门,忽然看见那只火狐从院墙上跳下来,嘴爪并用连拱带咬将筐子弄着架墙一跃而去。
后来的这二十来年,不仅他们家的鸡没再给狐狸抓走,德权在山里也再没见着这野物。老鹰也是这几年回来的,平时它们在青山庙梁背后的山岭上空,无声无息地盘旋着,常常是等你看到它们时,老鹰和一只挣扎着的野兔已在你身边离开了地面,一眨眼就飞的很高了……
这些年山里人只顾去城里走了,即便去那里扫街、钉鞋子、蹬三轮车,租住着城里人厕所旁的窄小的房子,去市场捡菜叶子回来做着吃,也不愿在农村住了。没办法啊,为了让孩子享受城里人的优质教育,就是那些城里人办的私人学校,也比乡下山村的学校教的好。
没有人知道德权老汉走进了这个世界。
这些新回来的野生动物之间的打斗掠夺,开启了老汉一辈子没见世面的智慧,上山割草所获,远远没有捕猎这些野生动物换到的钱多。即便套几只野兔或山鸡,送到城里的饭馆,也是能卖一些钱的。要是能捕到那只火狐,那就值钱多了。冬天,山上的苜蓿都枯干了,但老汉还是一样地上山,给羊搜罗些枯草枯叶,套几只山鸡,心里梦想着那只火狐。肩头搭着布褡连,褡连里装着卸开的猎枪和干粮,上了马头山,从马头山翻下去,进了野芦沟,一天要走二十多里路,沿着无定河边回到村庄时,天就要黑了。
可是那只火狐再没有出现。
世道再乱,可谁又能把他德权老汉怎样?谁还不让他在这无定河湾里种田?都一辈子快下来了。这些年农村的政策放的很宽,这两年农村的皇粮国税全免了,没人管老汉种田的事,他也不去管任何人的事。赶着驴车去河滩、上山梁,送粪,收庄稼,打草,是德权老汉生活的全部内容,那头青黑色壮如俊马的公驴,是老汉最好的帮手,也是伙伴,他说什么,它都能听懂。他叫它青黑,走,去河湾,德权老汉在车辕上坐着,青黑拉着车一出院门,就向村东走,而后拐村北,一路小跑着来到河湾。老汉说上山割草,青黑拉车出村后便向村南走。拉着一大车柴草爬陡坡的时候,他没有骂青黑,更没有打过青黑,自己套了绳子,肩头与青黑的肩胛死死扛在一起,腰身躬向土地,和青黑一齐发力向坡上拽着大车。实在拉不上去的时候,他就会让木架车站住停稳,把柴草卸下来一些,并对青黑说,好好用力上,今天回家一定给你吃好的。老汉从没把青黑以牲口骂。
但他不能不想儿女的事,不能不管儿女的事。
最让老汉揪心的是小儿子,老伴给他生了三女一男。子女是前世的仇人吗?活到57岁了,什么时候坐下来享过儿孙们的孝敬呢?遇头疼脑热感冒,从未去买过个药片片,就连他的老胃病都硬扛着,疼的实在扛不下去时,就去镇上开几副草药回来让老伴熬了喝。为子女操尽了心,可老汉并不责怪他们,他常常是这样反过来想的,儿孙也要在世面上活人啊,他们没有给子女创造下好条件,让他们在这个世上活的这样艰难、卑微。这些年老两口没明没黑牛马般劳累,土地上收入的钱,一分一分都贴给了小儿子,还是远远的不够。村里人都笑话德权老俩口过日子太抠,平时的节日连个肉都不买的吃一点,只有过春节才吃肉。一领老羊皮袄穿了二十多年了,其它衣裤鞋子全是几个女婿穿退下来的,常年四季高瘦的身材套着不合体的破旧衣裤。外孙子上大学回来,找不到工作,女儿大英一次次来磨坊,回娘家,每次从田里回来,老汉都能看见大英的眼圈红肿着。女儿女婿几年前就一同下岗,他不是不知道女儿需要钱,他不是看见女儿不亲,他不是不知道外孙找工作的重要,实在是手里没多少钱啊。庄稼地里土坷垃里能刨几个钱呢?为什么村里人都跑城里去了呢?就是在城里捡垃圾都比在村里种地挣得钱多。
几次从田里回来走到院门口,都听见大英和她妈在屋里争吵,大英哭泣着埋怨娘,挣一分给了他,挣二分给了他,这些年你们给牛军贴进去多少?他在城里买房子哪来的钱?村里人和亲戚朋友谁不知道?他的孩子上大学哪来的钱?他的孩子是你们的孙子,我的就不是了?尽管大英一次也没有在德权老汉面前开口,但他这个当父亲的心里是很难过的,他怕看见女儿的那双红肿的眼睛,后来大女儿一回来,他就躲在河湾的西瓜地庵子里不回家。庄稼人的命像黄土疙瘩,但也有着淳朴的感情,野生动物都是有情的,在山里打猎的时候,受了伤的成年野生动物护着幼崽的那情景,一幕幕出现在老汉心头。谁知道他一个人在这河边心里那煎熬呢?
尽是这龟子孙儿子惹的祸,让老汉操尽了心,气坏了肺,整得一家人常年四季不得安生。
孙子上大学虽不像大英说的一年就得几万,可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单靠他们老两口在土地上的刨挖是供不起的。大学是不能不上,可你到哪里弄钱,也不能干犯法的事啊。怎么能想起设骗局和人家耍赌?咱牛家祖宗几代谁干过这样的事?结果落得个捉鸡不成,反被啄了一口,不仅被公安局罚了钱,还抓进去坐了一星期牢。德权老汉想着想着,眼泪就上来了,几滴浑浊、冰凉的泪,从那干枯的眼框背后渗出来,淌过干瘪的脸夹,砸在黄土地上。

出嫁了 高宏 油画 2.2m×3.0m
这个农家出身、从乡下来的县城机关小职员,连板房都坐过了。是老二家女婿刘振华出面找人,牛军少坐了一个星期被保出来了。但从城里捎回来话要钱交罚金,老汉气的几天没吃饭,最后还是拖着像被雹子打过的禾谷一样的身子跑村里土财主牛大年老汉家二分钱利息借了五千元。
让德权老汉在村里抬不起头的是三女儿小英,她和老二家女婿刘振华的传闻,早在前两年就传回磨坊村来了。没有人在老汉当面说,但老汉出村回村,能窥察到村道上那几个长舌妇见他走过时相互拉话那神态。哟,真丢人啊,世上死的没男人了?和自己的堂姐抢一个男人,干那种不要脸的事。老汉走着没回头,在侧身的一瞬间他似乎都感觉到那个长舌妇指着他的后脑吧戳了几下,急忙收回了手。二狗家的日子过得像破箩到处都是窟窿眼,二狗媳妇都敢这样小瞧他。田里,路旁,风也能把这些话传到他耳朵里。这两年,他在村里很少和人们搭话。在河边的田里劳作完,他就上到山里,把自己走失于这个草木的、动物的世界里。
每次,看到野兔、山鸡们的腿死死地卡在他设下的夹子上,不动等死,动一下能疼死那可怜相时,德权老汉的心里很不好受,并不是猎人去收获猎物时那喜悦,一点点都没有,他甚至不敢走近它们。他甚至看到它们都是一些穷人家的孩子。
可一想到家里的子女们等着用钱时,他还是走到夹子下,并用手中的铁家伙致它们于死地。
每次,在他举起枪,对准它们——山坡上吃草的野羊,或小猕猴跟着大猕猴尽情撒欢,或年轻的公鹿与母鹿在一起尽情嬉戏,他紧紧地闭上了他那两只干瘪的似乎没有了眼球的眼睛……
走累了,德权老汉就在向阳一些的山湾的草丛上躺下来,暖阳很快就会把他晒的睡着。在睡梦里,老汉常常会梦见那些被他打折了一条腿的褐马鸡、苍鹭、野鹿,或领着幼崽的猕猴、漠猫、兔狲,跪在他面前,用可怜巴巴的目光哀求他,一下一下给他磕头。每当这时,德权老汉准是会被惊醒,他慌忙爬起来,对着北山梁上那座风雨剥蚀、倒塌的快要不存在的破山神庙磕上三个头……
其实,这山乡河湾人的生命,与这些山里奔窜、捕食的野生动物没什么大的区别,说不准哪阵儿轻易的就结束了或被结束了自己的性命,57岁的牛德权老汉,在这个深冬里,在这个无人知晓的山梁上,在一棵老杏树下,用一根破草绳,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管这个生命生前在这个世上是尊贵的还是卑微的,不管他生前在这个世上享尽了荣华富贵还是受尽了冷眼屈辱,作为他的子孙后人,都是要给他举行一个仪式的,无论是盛大的告示天下的仪式,还是简单的一顿油糕,一口薄木棺材送其上山。他们的后人至少要让走了的人入土,乡间谚语一辈一辈这样留传下来——入土为安。
第二天上午,距磨坊村40多公里县城的人们都回来了,老汉的三个女儿女婿和小儿子牛军一家人,随后回来的还有老汉弟弟德宝的大女子大女婿一家人(牛月琴在两家人的姊妹弟兄中排行老二,弟妹们就叫他们二姐夫二姐)。摆在这群子女面前的当务之急是,现在老人还在村外的一个干草窑里寄放着,很快把老父亲给搬回村里来,让老人在去那面世界前,最后再看看这生他养他,无数次走过的村道和院落,还是只在院子里搭个空的灵堂。这事最终是由德权老汉的弟弟德宝定夺,德权老汉走了后,他现在就是这族人里辈份最大的人了。按乡俗,非正常亡故的人,是不能回村里来的,事情很快就这样定了。
老人一个人躺在村外那个冰冷的土窑子里,几天没吃没喝了,德权老汉的三个女儿女婿由小儿子牛军领头,披麻戴孝,从老屋出发,一路嚎哭着去山上给老人点纸去了。
摆在这群乱的像一窝蜂一样的子女们面前的第二件事是,一家人要尽快商议,就这样让老人入土了,还是要去问公家讨个说法?德权老汉的三个女儿,呼天喊地,老父亲死的冤屈,一定得去向公家讨个说法和公道来。这事,整个家族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德宝老汉的大女婿刘振华身上了,他是县里的部局干部呢,他知道这里头的深浅和政策界线,现在只有他的话最具权威。
结论是,没必要向公家讨说法去了。刘振华几乎是不假思索就给所有亲戚、家人、子女拿出答案:不要说来了七辆警车,就是人家来了七十辆警车,人家还没上你的门,一句话都没问你,你怎么能和人家粘上?混乱中所有人都忽略了德权老伴的这句话——好些日子了,老汉总是在凌晨早早就醒来睡不着,爬在炕头抽着旱烟,有一天,老汉说他想娘了,不想在这个世上活了……
听了刘振华的话,最不高兴的是德权老汉的几个子女,为两只鸟,父亲送了一条命。要是公安不来,他会跑到山上去上吊吗?他们甚至认为父亲的弟弟老二家这一门人,有意不帮他们这一门的忙。先是二爸发话,不许父亲的尸骨回宅院来。后来是女婿也不能站到他们这一面来,出主意撑腰去和公家讨公道。
就说现在,老爸不幸辞世,刘振华能这么早赶回来,他们老大这一门还是十分感激的,说来说去,往后还得求人家帮忙办事。虽说在与公家讨说法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不合,作为老大家唯一的男儿,牛军还是掌罗了酒席,宽待他们的局长姐夫。
陕北高原上的人喝酒,从来不是就着下酒菜,边拉话边品酒,而是拼酒,赌酒,用打麻将用的那骰子,在瓷盅下扣了,吹牛,看谁把谁赢了。即便是在今天这样悲痛的日子,一旦玩上了这种具有赌性的喝酒,桌上的人还是一会儿就喝光了几瓶烧酒。酒大了,说话就开始口无遮拦。用骰子吹牛,输的多的德权老汉的大女婿说话舌头已不展,明明自己输下酒,却开始耍赖,硬要刘振华代他喝,说他虽是亲姐夫又是老大,但在这个家没地位,大家都尊着抬着刘振华,就叫刘振华喝。谁知他是真喝醉了,还是借酒装疯卖傻,过了一会,他又说,老丈人这丧事,他们家干脆不管了,这些年,老丈人不给他们家贴一分钱,儿子安排工作那么大的事上,都借不来一分钱,他赚的钱,给了谁,就让谁来操办这丧事。
明明看大女婿已喝成了这样,酒桌还是收停不了。
对刘振华不满的三女婿王海林挑着还要跟刘振华拼酒,三女婿的难过是来自他的工程,从春忙到冬,受了个贼死,现在血本难回,自己折了不说,民工工资开不了,大门上围了要工钱的人,一家人有家不敢回,天天东躲西藏。为了这座拦洪坝工程,不只他跑,老婆小英也多次找姐夫说这事,好话几乎说尽。秋末工程竣工,省里下来验收,怎也通不过,只付50%的工程款,连工程材料费都不够。他跑着把全县其它几座同时修筑的拦洪坝工程都看了,和他的工程没任何区别,人家的都通过验收,冷子(冰雹)就掉在了他的头上,急得他跳崖。他知道工程验收前,人们都跑上面,送好处,刘振华却不让他去送,说没事。王海林现在脑子里只剩这一根弦,要是刘振华能挺身而出,到处找人求情,这个难关也许是能过的去的。可问题是二姐夫为了自己当局长,对这事只推不揽,只怕粘他身上,老局长阳历年过罢就到站了,排在老局长后边第一位的副局长就是刘振华。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日,三女婿想最后捞一把,看二姐夫刘振华能不能动了同情之心。他出外面解手,两只眼喝的像猫屁股,他还是把老婆小英给叫来了,要小英给二姐夫好好的把铁炉子里熬着的浓酽砖茶倒上。牛小英心领神会自己男人的意思,她就坐二姐夫旁边,不停地给他的二姐夫倒茶水,看二姐夫输多了酒,就端起来替喝几杯,每咽下一杯酒,辣得她张开红红的嘴唇直呵气,主要是给二姐夫看。面对清粼粼的无定河水养育大的女子,面对那陕北崖畔上红山丹一样的口口,这个二姐夫必定也在三小姨子明眸里读到了什么。这个时候,与桌上的人赌酒的劲头比刚才大多了,本来就打了两个通关的刘振华,现在主动又开一个关,每输下酒,并不用别人多劝,左手端一杯,右手端一杯,头一仰就都喝下去了。
小英刚才本来是和几个姊妹一块在东边的一孔窑洞里安慰娘,还有二姐牛月琴,剪裁孝服,准备丧事上的米粮菜果。牛月琴见喝的摇摇晃晃的三女婿来把小英叫走,好一阵子了还不见小英回来,就向院子中间喝酒的这孔窑里来了。
牛月琴进得窑里,一看小英在刘振华身边坐着,一只胳膊快要挽着刘振华的一只胳膊了,还娇声娇气地叫着二姐夫,她的胸腔和喉咙里哗啦就冒上来了烟火。此时满屋子烟笼雾罩,酒气熏天,这是什么场合啊?老人都亡故了,你们还在这里花天酒地。你们脑子不满了,脸也不要了?
她走到炕栏边,叫小英走,小英还不走,如若面前根本就没存在着这个二姐,而伸过手去二姐夫手里夺酒杯,用迷醉的眼神去看二姐夫,好像这还是外边的生意场的酒桌上。不过小英跟着二姐夫一块到外面的朋友场上,这样的举止也不知多少回了,只是牛月琴没见过罢了。有关刘振华挂上了他三小姨子或者是牛小英钻到她二姐夫被窝里的传闻,早两三年就传回磨坊村来了。在脚地下越看越起火的牛月琴,出口就骂牛小英,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我看你还要干什么?牛月琴得理不饶人,你个小婊子,越骂越难听,牛军下去劝说,她的骂声更高了,劝说间,牛小英从炕上跳下来,借着酒劲两人就撕扯在一起了……小儿子牛军因是在自己家里招待人,他因买房子还欠着二姐家几万元,不管二姐骂的多难听,只是劝架,硬往开拉架,主要责骂一娘养的自己的三姐。当看到自己的二叔从隔墙操着木棍虎悻悻地跑过来,将木棍抡向小英时,他就顾不了那些身外的事了。就在这个地方,只有去了另一个世界的牛德权老汉没有参与进老大牛德权和老二牛德宝两家人大打出手,恶战一场的事件,在这里笔者就不再叙述下去了,说出来也没人会相信;没有读者会相信人性里面会存在这些。
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磨坊村。
老二牛德宝的大女婿一家开车走了。老大牛德权三女婿一家也开车回县城了。大女儿牛大英也要走,丈夫在拉架时头上被砸了一棍,头疼的厉害,要回县城做CT。大英心理原来就有想法,儿子大学毕业,却找不下工作,去年县政府几个单位招人,几次考试都落选,学习不如自己儿子只上了专科的同学都考上了,有人出主意,花上十万八万,就能考上,保准能安排了。自己和丈夫先后都下岗,供儿子上大学现在还欠着丈夫妹妹家钱,家里实在是拿不出来了,她来到娘家门上哭了又哭,明知父母手头有钱,就是一分不给。女儿没用,钱都给了小儿子,那就叫牛军一个人抬埋他去吧……生活将人情、亲情逼得如一块铁一样硬,一样冷。
陕北高原上,一冬没下一场雪。
那些去城里打工的人都还没回来,灰黄的冬日,村里几个老汉,将他们的这个侄子、老哥,抬上了山……
在半山腰的一块缓坡上,薄木棺材被临时放地下了,六仁伯从他老羊皮袄的兜里掏出半瓶酒,是他自酿的高粱酒,浇在棺木的头上。都老了,不歇一歇,怕是抬不上去了;谁还没有这一天呢?此时磨坊村的这几个老汉心境也许是一样的,德权只是先他们走了一步。也可能是他们想让德权在这里站站,再看一眼他曾在其间劳作了一辈子的无定河湾,和他哭着来哭着去的山下的这个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