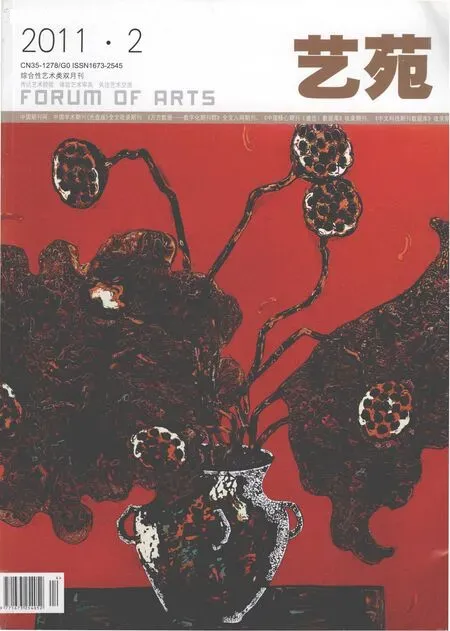略谈戏曲民俗研究的成就与学科意义
文/王学锋
中国戏曲与民俗之关系是在20世纪的中国戏曲研究中越来越凸显的一个论域。随着认识方式的日益转精、文献检索手段的不断强化,戏曲与民俗的互动研究在今天逐渐显示了较为强劲的学术生长能力。如果说一个学科的成立需要具备较为固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需要一批较为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话,那么“戏曲民俗学”已经历史地、自然地具备了这些条件,并在为促进中国戏曲研究的发展积极贡献着独特的学术资源和研究成果了。但今天,笔者在这里提出“戏曲民俗学”的学科建立主张,并非“事后诸葛亮”式地作一些多余的概括,而是希望适时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深化我们的认识,并组建“自己的园地”,集中探讨“戏曲民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期为未来有意识、有计划、有理论地进行“戏曲民俗研究”打下良好基础,从而积极开掘中国戏曲研究的深层学术意义。
一、20世纪戏曲民俗研究的主要成就
(一)1949年之前
自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开创戏曲的现代性研究之始,其中国戏曲“自巫、优二者出”的说法就显示了从民俗文化角度研究戏曲的视野,这一点在后来的戏曲起源或发生研究方面都不断地激发新的思考。鉴于中国现代戏曲研究的初创,研究者大都“异想天开”,很少受到固定、单一模式的戏曲史观的影响,由此很多研究成果其实蕴涵了多向的研究可能,如许地山的《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闻一多对“《九歌》是巫歌”的研究,孙楷第、顾颉刚、孙作云对傀儡戏、影戏的研究都在一个民俗文化的视野下更宽广地关注着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形态等各个方面,这些被其后的戏曲史研究逐渐漠视、甚至排除的成果在今天也同样受到了戏曲民俗研究者的重新审视和借鉴。
“粗陋”、“小道”的民间戏曲在“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向下看的“民间情结”中被“发现”了。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宣告开展的现代民俗学运动为戏曲研究引入了“民俗”视角,虽然这一视角还不免带有知识分子对“民间”的浪漫想象,但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20世纪30年代的李景汉的《定县秧歌选》关注到了以前被遮蔽的民众的戏曲、娱乐、生活与想象,这一编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俗学界回顾自身传统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我们还可以在周作人的《中国戏剧问题的三条路》一文中看到现在非常熟悉的戏曲民俗研究观:“依照田家的习惯,演剧不仅是娱乐,还是一种礼节,每年生活上的特点。”[1]这是令人惊讶的。20世纪的中国“俗文学”研究自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后,于1938年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获得了广泛影响。郑振铎的“俗文学”定位是包括戏曲在内的,虽然没有在其《中国俗文学史》中专门论述,但开辟了戏曲作为“俗文学”的研究新视野,大量的戏曲等“俗文学”文献在这一视野之下得到了收集,在与敦煌变文、宝卷、弹词、鼓词、民歌俗曲、诸宫调等相类的“俗文学”文类的比照中,也启发着研究者重新认识“戏曲”在民俗文化氛围中与其他演艺形态的共生性。在对俗文艺的研究方面,李家瑞在1931年出版的《北平俗曲略》对说唱鼓书、快书、蹦蹦戏、傀儡戏、湖广调、福建调、马头调、四川歌、打花鼓、跑旱船、儿歌、秧歌等大量民间说唱文艺的研究奠定了与戏曲相类的俗文艺研究的基础。在今天看来,《北平俗曲略》将戏曲民俗研究从戏曲研究扩展到对戏剧形态研究的关照下,其价值无疑是很大的。
在戏曲习俗研究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齐如山的京剧研究可谓颇具代表性。齐如山出版于1935年的《戏班》,分“财东”、“人员”、“规矩”、“信仰”、“款项”、“对外”等方面对京剧戏班习俗作了详细考察和探讨,这一对京剧所作的“外部”研究对仅仅眷顾于简单的京剧“艺术”的“内部”研究是一个启发。齐如山“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风俗、习惯、人情,以至婚丧、庆吊、酬应、来往、买卖、工艺、技术、娱乐、游艺、饮食、游逛等等,都极感兴趣,悉心研究”[2](P4),“访问过国剧的老脚名宿达三四千人”[2](P5),在今天看来,这些方式无疑是颇具抱负的民俗“田野考察”工作。
20世纪4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戏剧简史》的作者董每戡被认为是“国内最早把民俗学、人类学和戏剧学结合起来研究的著名学者”,在他的戏剧史著作中,确实最早专门性地对戏曲的起源、形成作了民俗学、人类学式的考察和描述。而同样撰写于40年代的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在“系统地吸收了自清末王国维以来到40年代末的学术成果”之后,也在戏曲的起源观上强调了傩仪、傩舞等“来自民间”的观念。
(二)1949年之后
20世纪前半叶的戏曲民俗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开拓,随着时间的流转和学术的积累,渐渐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研究“传统”。1949年之后,历史唯物主义的戏曲研究范式逐渐成为新的学术潮流,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和介入,戏曲研究范式变得单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戏曲研究范式逐渐非学术化,加之话剧研究思维、成熟的戏曲观以及历史研究中的线性发展观,戏曲民俗研究的领域逐渐缩小,戏曲与民俗关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戏曲俗语方言的考释,并形成了一个传统。几十年间相继出版了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1953年)、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1956年)、陆澹安的《戏曲词语汇释》(1981年)、王镁的《诗词曲语辞例释》(1986年)、方龄贵的《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2001年)、王学奇等的《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2002年)等著作,它们从语言学角度对戏曲文本中的俗文化因子作了专门而详尽的考察,开拓了我们进行戏曲民俗研究的手段和视野。
不过,造就后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戏曲民俗研究的繁荣和成果斐然不是没有原因的。1949年建国之初的戏曲民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从当时的文艺“采风”活动中获得了生存空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热闹的傩戏、傩文化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傩舞调查中就埋下了伏笔。此外,刘念兹的戏曲文物研究、墨遗萍对锣鼓杂戏的研究等也都为后来的戏曲民俗研究作出了贡献。
以《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通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相继出版为标志,中国戏曲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张庚先生的“史”、“志”、“论”的戏曲学架构为戏曲民俗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戏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戏曲通史》关于戏曲起源于民间歌舞的论述,内在地具有了戏曲与民俗之间密切关联的理论空间,并在清代戏曲史部分,大量论述了以前戏曲史用力不多的“驳杂不纯”的花部地方戏,但是这一戏曲史的架构,“在对戏剧发生的理解上,是以形式的歌舞表演为基点;而在对戏剧史的理解上,则是以内容的文学性为基点”。造成这样的错位一方面是时代的认识局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田野资料的忽略和缺乏。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戏曲研究观念的拓展和大量田野资料的发掘,对戏曲民俗研究的重视和认识的深化正可对此有所补充,而三十卷《中国戏曲志》中有关戏曲民俗资料的大量保存更是直接为戏曲民俗理论的探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都可以使我们积极填充张庚先生开拓的理论空间。其实,张庚先生戏曲理论中的戏曲方志学、戏曲文物学思想以及对傩戏、目连戏研究的积极关注,已经紧密勾连了戏曲民俗研究的诸种方向,使得其戏曲研究具备了相当的开放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戏曲民俗研究的潮流之一就是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实地考查,其代表即是台北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主持的“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调查了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众多仪式演剧,研究结果由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为“《民俗曲艺》丛书”八十种(包括调查报告、资料汇编、剧本或科仪本集、专书和研究论文集等)。这一研究计划囊括了一时的精英,并汇集了大量曾经参与《中国戏曲志》编撰的各地文化部门的学者,将《中国戏曲志》对戏曲民俗的关注引向深入,在田野的“实验场”上引发了学者们对戏曲与民俗关系乃至中国戏曲民俗文化的进一步思考。
近二十年来,由于对戏曲与民俗两者的关系重要性的认识逐渐加深,戏曲民俗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多样,重要如:廖奔的《中国戏曲史》、《中国戏曲发展史》都“试图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剖析中华戏曲,从而展示以往未曾涉及或者探之不深的研究领域”,将戏曲民俗研究积极纳入中国戏曲史的总体叙述,虽不十分完满,但却作了十分有益的戏曲史整合和重构;刘文峰的《中国戏曲文化图典》、《中国戏曲文化史》、《戏曲史志研究》在编辑《中国戏曲志》的多年学术积累基础之上,积极关注戏曲民俗研究,并自觉尝试着戏曲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努力;以曲六乙为代表的傩戏、傩文化研究,关注傩俗和戏曲民俗生态,出版了《中国傩文化通论》等;刘祯的《民间戏剧与戏剧史学论》,在戏曲文化学的框架下,大量引入戏曲民俗研究视角,他近期出版的《戏曲与民俗文化论》对戏曲与民俗的关系更有深入的思考;以黄竹三、冯俊杰为代表的研究者,以戏曲文物研究为对象,积极吸纳戏曲民俗、宗教研究,出版了《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山西戏曲碑刻辑考》等专著;以康保成为代表的研究者,则从宗教、民俗角度关注中国戏剧形态问题;此外,鲍文锋的《古代戏曲民俗与中国戏剧的渊源——中国艺术和审美意识发生的民俗思考之一》[3]、邓翔云的《试论民俗文化与中国戏曲的发生》[4]、朱恒夫的《推进与制约:民俗与戏曲关系》[5]、郑传寅的《民俗文化与古典戏曲》[6]等都对戏曲与民俗的关系作了直接的探讨。成果众多,这里不一一尽述。
二、戏曲民俗学的对象、方法、意义与中国戏曲研究的发展
(一)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百戏杂陈”与戏曲研究观念的转变
中国戏曲民俗极为丰富[7],而现代戏曲学和民俗学分作两途,在专业分工带来精细的学术“耕作”之余,也遮蔽了对中国传统戏曲真实生存状况的客观认识。如孙柏所说:“自新文化运动催生出现代戏剧意识之后,‘话剧’——或者说西方主义的戏剧观念,在极大程度上主导了我们对戏剧文化的整体认识。实际上,综观古今中外,戏剧文化的极大丰富远远超过了这种建制性规范。由于戏剧学基本上是现代戏剧意识的直接产物,并且内在于现代戏剧文化的总体格局,所以它的课题范围与治学理路,本身就是对那种建制性规范的实践和体现。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对于前现代戏剧的许多认识就难免扭曲。”[8]孙柏在这里没有将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戏剧作简单对比以显示中国传统戏曲如何独具价值,而是将问题的讨论引向现代性追求招致的“建制性规范”对戏剧学学科的“挤压”。这一“规范”和“挤压”无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甚至西方戏剧文化在“前现代”时期的丰富性,这一丰富性指的就是:“至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交,中国和西方的戏剧文化在总体面貌和根本诉求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属于百戏杂剧。”[8]这一看法并非不承认中西戏剧之间的巨大差异性,但是,它更多地从戏剧形态的组织方式、原则、面貌方面强调了两者的同构性。对戏剧形态的同构性的强调解放了我们对中西戏剧二元对立的认识的束缚,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反思和理解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中的“百戏杂剧”现象。当然,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对现代戏剧学科的反思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摈弃现代戏剧意识,因为只要其历史条件没有终结,它的存在就一定携带和履行着某种时代的诉求”[8],我们要做的只是反思反思再反思,力求在时代赋予我们的条件和限制基础上努力达到时代的最高认识水平。
在中国戏曲形成前的汉代就有涵盖音乐、舞蹈、杂技、幻术、武术、滑稽表演在内的乐舞杂技表演,可谓“百戏杂陈”。在中国戏曲于元代成熟之后,仍旧并不擅长像话剧那样的叙事演出,常以“过锦”手法组织戏剧演出。而与成熟戏曲同时的民间戏曲,更为真切地体现了“百戏杂陈”的表演特色,如山西上党地区发现的明代《礼节传簿》中显示的迎神赛社活动中驳杂狂欢的演出形态。欧阳予倩就认为中国戏曲是“杂戏”(1)和“混合”戏剧。中国戏曲中的这一“百戏杂陈”的特点正是在深厚的民俗氛围中得到清晰的体现的。戏曲民俗学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了全新的价值,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戏曲研究中忽略的部分作一种补遗,而且使我们具有了一种认识中国传统戏曲的研究理念和视角。于是,中国传统戏曲研究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方面都应该放在其生成、生存的民俗文化背景中来考察,
(二)跨学科研究
既然中国传统戏曲在许多情形下呈现出一种“混合”状态,那么,仅仅依靠单一的某个学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这里,戏曲学与民俗学的跨学科问题自然就产生了,这就是戏曲民俗学。戏曲民俗学建构的一个学科背景是,艺术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多地被实践着,钟敬文先生曾在《文艺研究中的艺术欣赏与民俗学方法——1997年10月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庆祝〈文学评论〉刊行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9]及《民俗学对文艺学发展的作用》[10]等文中提倡从民俗学角度研究文艺学,以便多角度和深入地了解文艺现象。这方面重要的著作还有,陈建勤的《文艺民俗学导论》[11]、纪兰慰的《舞蹈民俗学的艺术定位》[12]、张士闪的《艺术民俗学》[13]等。鉴于此,戏曲民俗学的提出也是适时的。戏曲学的研究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戏曲学研究是指对戏曲文化以及戏曲艺术本体进行整体综合研究的学科。广义的戏曲学指凡是与戏曲有关的学问。”[14](P2)而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15](P6)作为交叉学科,我们自然希望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能为戏曲的历史与现状提供新的解释能力。我们关心与戏曲活动相关的民俗事象以及这些民俗事象如何影响戏曲本体的生成。这些与戏曲活动相关的民俗事象包括戏曲演出戏俗,比如演出中的祭台、跳加官、打通、坐场等仪式,戏班的班规,演员的报酬、食宿,观众的看戏习俗等演出程序和演出禁忌;包括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宗教祭祀民俗等活动中的戏曲活动状况;包括戏曲活动的社会组织民俗;包括戏曲演唱中的方言民俗;包括戏曲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学等。我们还关心戏曲与民俗两者的互动关系。
戏曲民俗学研究的重心应该是戏曲的艺术本体。虽然它是戏曲学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且在研究方法上更是要广泛借鉴民俗学、民族学与人类学,但是要格外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进行戏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戏曲本体以及戏曲发展史等戏曲自身的问题而不是要解决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或者是民俗学的问题。也许在实际的操作中学科的界限不一定泾渭分明,但是学者自身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定位还是应该相对准确地存在的。当然,这里需要注意,不必轻易地画地为牢、束手束脚,过早地将自己局限于一个所谓的“学科范围”内,保守着“学科范围”,那是与跨学科方法本来追求的有效解决问题的开放性相背的。
(三)田野考察方法及反思
戏曲民俗学的代表性研究方法当然是田野考察。“田野”在中文里的意思可能会造成误解,以为这一考察必定是要到孤野村落和穷乡僻壤。其实,“田野考察”的英文单词“fieldwork”中的“field”(田野)除了“田野”的意思外还有“场地”和“领域”的意思。我们知道,最初的田野考察兴起于早期人类学家对“他者”的关注,这一“他者”的指称背后是有西方社会的“先进”对“落后”的价值优越感在内的。此后,对这一中心情结的反思和民族主义的潮流促成了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将田野调查目光转向了“本土”,直至“家乡民俗学”更深入和动态地在“故乡”和“他乡”间关心调查对象的情感变迁和文化认同的转移。由此,戏曲民俗学的田野考察对象就不仅仅是乡村里的戏曲民俗活动,它还应该包括城市里的戏曲民俗活动。更进一步的意义上,戏曲民俗学强调走出文人书斋,到异己的戏曲文化环境中,寻求对话,以反思自己的戏曲认识方式。
田野考察在近二十年的《中国戏曲志》普查和傩戏研究中被大量使用,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有些时候许多研究者也漠视了田野考察技术和理论的学习和认识,他们认为田野考察不需要任何理论的指导,不能先入为主。但任何人作田野考察都是有其“前理解”在内的,只不过能否自我意识罢了。田野考察应提倡具备“先入为主的问题”,即带着问题进入考察地点,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问题和理论,而在于具有怎样的问题和理论。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的热潮,各地“向下看”积极寻找民俗,但要把戏曲活动中的“历史遗留物”从其生成、生存的民俗语境中抽离出来,戏曲民俗的田野考察一定要历史化、地域化、语境化。
文献研究作为传统的研究方式,仍旧是戏曲民俗研究的有效手段,对田野考察的提倡不等于漠视传统的文献研究方式,两者应该相互补充。把案头文献研究和田野考察对立起来看待的方式,其实是一种二元论的思维模式,比如在对剧本的研究中,如果跳出传统的文学剧本的认识概念,注意到“口传剧本、文字剧本与符号剧本,场上剧本与案头剧本,关目本、穿关本与曲谱本,提纲本与综合本”的这一“泛戏剧剧本”的多样存在,那么在对这些剧本的考察中,就要兼备文献研究和田野考察的方法,从而进入到剧本生成和激活的民俗环境中。
(四)戏曲民俗学的未来工作与对中国戏曲研究的意义
由于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的问世、频繁的学术会议的召开以及较多博硕士论文从戏曲民俗角度选题,戏曲民俗学的学科建构有了较为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底蕴,未来的工作仍然可以从三方面加强:
1.资料积累。鉴于戏曲民俗活动的大量资料保存在地方志中,而《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编纂已逾十年,随着戏曲民俗研究越来越具体和细化,做一份按省分卷的方志戏曲民俗资料的汇编显得越来越有必要和价值。很多戏曲研究者仍习惯从《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寻找材料,而此书的编纂在当时主要依靠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大量的地方志资料还未涉及。据笔者所知,光是山西历代各个版本地方志中的戏曲民俗资料就数量很大。
2.理论意识。由于戏曲民俗资料一方面散见于地方志,另一方面又是散落于民间的非文字的“口头”资料,这些都增加了理论总结的难度。因此,如何借鉴外来的理论成果转而在零星散漫的戏曲民俗资料中进行概括,既是难点,也是从“中国经验”中建构自己的理论的机遇。
3.重写戏曲史。这一想法不是为了挑战和打倒某个权威,而是通过理论和方法的更新,吸收戏曲民俗学研究的成果,并内化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戏曲发展史的手段和武器,为我们头脑中那些难以理解的戏曲问题找到最佳答案。20世纪40年代以来,董每戡、周贻白乃至后来的张庚、廖奔的戏曲史都认真处理了戏曲与民俗的关系问题,以期成功整合进中国戏曲史,但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都留下了可探讨的余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戏曲的发展遭遇了危机,作为进入艺术殿堂的、高雅的、纯艺术欣赏性的、纯娱乐性的戏曲演出日益减少,而作为民俗活动的庙会戏、集市戏在广大农村如火如荼。这是集体所有制和民营剧团主要的演出市场,也是戏曲得以继续生存下去的土壤,戏曲民俗学学科的建立,顺应了戏曲发展的这一新局面。戏曲研究应该保持与现实生活积极对话的能力,戏曲民俗学帮助我们重新聚焦对象,也促使我们反省自己的既有研究观念和研究模式,通过努力,我们一定会做出一个理论研究者应有的贡献。
注释:
(1)载于《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
[1]周作人.中国戏剧问题的三条路[M]//周作人.艺术与生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张其昀.代序[M]//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3]鲍文锋.古代戏曲民俗与中国戏剧的渊源——中国艺术和审美意识发生的民俗思考之一[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3).
[4]邓翔云.试论民俗文化与中国戏曲的发生[J].学术界,1997(4).
[5]朱恒夫.推进与制约:民俗与戏曲关系[J].艺术百家,1997(2).
[6]郑传寅.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7]刘文峰.中国戏曲与民俗[J].戏友,1997(2、3).
[8]孙柏.清史泰西观剧录[J].戏剧,2004(3).
[9]钟敬文.文艺研究中的艺术欣赏与民俗学方法——1997年10月6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庆祝《文学评论》刊行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文学评论,1998(1).
[10]钟敬文.民俗学对文艺学发展的作用.文艺研究,2001(1).
[11]陈建勤.文艺民俗学导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12]纪兰慰.舞蹈民俗学的艺术定位[J].民族艺术,1998(2).
[13]张士闪.艺术民俗学[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
[14]朱文相.中国戏曲学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15]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