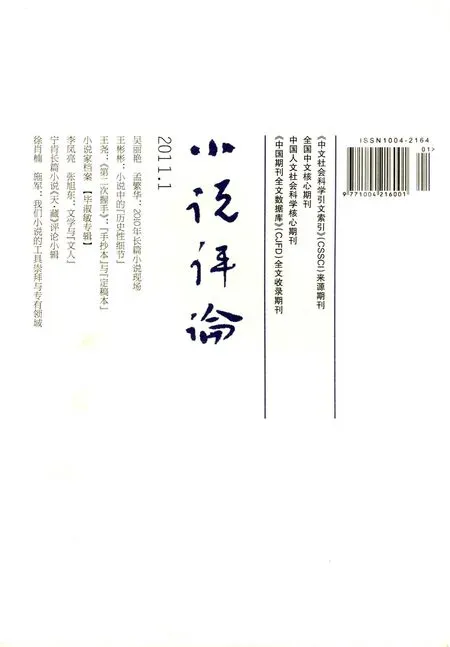在空间维度上叙述神农架——评陈应松长篇小说《猎人峰》
杨家海
在空间维度上叙述神农架
——评陈应松长篇小说《猎人峰》
杨家海
在对《猎人峰》的各种评伦中,主要集中在它的主题和社会意义上,鲜有对其叙事方式进行阐释的。本文认为,《猎人峰》之所以能够深刻地表述其主旨,是得益于它的空间叙事方式。
一、《猎人峰》的空间叙事表现形式
1、时间碎片化
《猎人峰》里的时间跨度几近百年,这是从白秀老人放弃革命70多年后在山洞里发现了他的十二个战友的骸骨中推知的,但具体的时间线索不是很明显,甚至是模糊的、破碎的。首先,《猎人峰》在开篇就模糊了时间。
“他多大?比他爹小,比儿子大。儿子多大,爹多大?他都不知道,也不需知道,知道了也记不住。”
“有人怀疑山上的宗七爹和七婆,是世上活得最久的人。因为在去年约一百二十岁上死去的巩杵子就说过,他来白云坳做上门女婿时,宗七爹就是老人了。”(第1页)
所以,在《猎人峰》中,人的生命不以时间计算,而以他的所历所想为则,该活便活,该死便死。“这里的人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年龄概念,没有生死概念。过日子就是个估估数。”(第1页)即使提到时间,也是一些模糊的时间概念,如“春节”、“青黄不接的日子”、“秋天到了”、“在很久很久以前”等。这样叙述实际上是在渲染事件发生的环境、氛围,如开篇说:“这年的春天,北风呼啸,气温陡降,狂怒的山冈上到处是惨白的冰凌,闪烁着令人绝望的死尸般的气息。”(第4页)这样叙述的重点显然不在于“春天”,而在于春天的“绝望”。
其次,把时间概念置换成空间碎片,进行跳跃式叙事,如在叙述白秀的一生历程都没有清晰的时间概念,而是通过叙述他的一些人生片断来完成的。
少年白秀:“很古老的一九三一年,那时的白秀还是个百事不晓的少年,还叫戟秀,在鄂西北房县戟家湾给大地主崔咬精放牛。”(第36页)
白秀参加革命:“有一天他舅舅杨夺水从县里背回了一块‘房县戟家湾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就成了杨主席。他舅舅说:‘秀娃,你革命吗?’于是秀娃就革命了。”(第36页)“白秀说:老子一个营带三百多人,你说是个连长,连排长都不如,十几个鸟人,凭什么杀我养父?”(第50-51页)
白秀成为猎王:“想当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白秀打的猪每天用一百多人往镇上抬。”(第12页)
白秀死而复生:“白秀死了,大地把他收走了,阎王把他招走了。”(第113页)
白秀疯了:“‘白秀又开杀戒了!’”“他就是疯子!”(第247-248页)
白秀死了:“他猛然感觉到:白秀老人死了。”“白秀老人死时,猎人峰挂了三条彩虹,这是那天的奇异天象和异兆。白秀老人给咬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惨不忍睹。”(第284-285页)
白秀的一生就是空间里的一个个事件,且事件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也使白秀从一个历时性的单面人变成一个共时性的立体人,使其形象更完整、更真实,更有生命力。
2、空间的自由转换
现代小说叙事结构的“空间形式”,“其‘空间’非指日常生活经验中具体的物件或场所,而是一种抽象空间、知觉空间、‘虚幻空间’。”④《猎人峰》在叙述人的世界、现实世界时,同时虚构了野兽世界、传说世界。神农架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原样,而是作者刻意营造的一个虚幻空间,在此虚幻空间里,各个世界可以自由转换、自由融合。因此,空间叙事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转换自由。在《猎人峰》里,人与兽、现实与传说,往往交融在一起,在给人玄秘感的同时,也引人深思。
(1)人的世界与野兽世界互置
在《猎人峰》里,人与兽之间的关系是作者描写的着力点。“在神农架,人们都知道并且笃信人一天有两个时辰是牲口。……人有两个模样:一个是人,一个是畜生。”(第45页)对这样一个说法的阐释可以有两种:一是人与兽和谐的表示,一是人与兽冲突的表示。
先就人兽和谐来看。说人一天中有两个时辰是牲口,实际上是在喻示人性中的自然性。野兽也有着灵性,它们比人还守信用,“这豹也骚怪,果然把头点了三下。白大年知道兽比人守信用,还没有学得人这么坏。”(第44页)
他们的关系本来是共处一地、和谐与共的。在白秀这个有着革命史的猎王诞生前,这里的人与兽各守其道,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红丧月”就是对这种古老关系的恪守,是人与野兽两个世界的边界。
然而,这个边界被打破了,两个世界发生了冲突和碰撞。神农架的人太穷了,要靠打兽和伐木生活,代表现代文明的国营林场工人和代表传统文化的猎人,共同扮演了虐待神农架的刽子手角色。
由于人过度的滥捕滥伐,人们把自己的衣食根据地严重地破坏了,他们也都遭到了大山的报复。曾十分牛逼的伐木工人白瑞阳,“一个国有林场的伐木工人,大家看到,如今不仅是一脸的火烧疙瘩,穿得还不如庄稼汉。”“你们这些遭天杀的伐木工人难道不活该到给农民打工吗?……”(第83页)曾经的猎王白秀也疯了,他的徒弟们在打猎难以维持生计后也都生活艰难,甚至把人的牲口模样也逼现出来了。“白大年两股颠颠地下沟去喝水,估算着与豹的距离,想跑。一看水里,让他大吃一惊:水里的影子哪是他白大年,是一只麻羊子(斑羚)!天,怪不得这豹今天非要吃我。”(第41页)因此,“在神农架,人们都知道并且笃信人一天有两个时辰是牲口”的箴言也就实现了,“我活了五六十岁,才知这一传说是真的哩,人还有另一个面目哩,人就是一只牲口。”(第45页)
人、兽,都是实在的存在体,其关系也是客观存在的。其实,不论人兽和谐,还是人兽冲突,都是虚构的两个世界,但揭示的却是人所必须解决的关系。作者通过人的世界与野兽世界之间的碰撞、转换,来质问人与兽、人与自然该如何相处?人显出牲口模样也预示了一个疯狂世界的来临。
(2)传说世界与现实世界共融
传说,虽然不是客观存在,而一经形成就可以对人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力,引导、规范人的心理。《猎人峰》中有“天地闭,贤人隐,恶兽出”(第41页)的古训,它所呈现的就是一个贤人隐退、恶兽横行的世界,这在小说的开头就直接给以明示,“山邪了,山上的所以野物都成了精”。
之所以是一个天地闭合、乾坤颠倒的世界,还是人出了问题。千百年来,人兽关系本来是比较和谐的。神农架的这些传说与现实相互作用、虚实相生:因为有神农架的渺远历史和神奇地理,所以产生了诸多引人思索的传说,因此增加了神农架的历史厚度;因为有这些引人思索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不断在神农架得到实现后,所以又给人以警示,因此进一步确证了传说的真实可靠和寓意深刻。
这些寓言性的传说,还参与、左右了小说的叙事,使得小说的叙事文本里又蕴藏着一个深度空间。《猎人峰》里鲁瞎子唱《黑暗传》的片断穿插在各个叙事环节里,共出现12次。鲁瞎子是神农架现实的隐喻,《黑暗传》是神农架传说的典范,这实际上就是传说与现实融合的隐喻。如第一章“红丧”。
作者先叙述了两个事件。一是白秀家打破了“红丧”禁忌,白秀带着徒弟们去打野猪,舒耳巴掉下峡谷,白大年被白秀当野猪打了。人兽关系破裂。二是一个来白云坳求白秀要一副野猪心肺给儿子治哮喘的不老不少女人,先和鲁瞎子交媾,又和舒耳巴的儿子糟蛋交媾,糟蛋后来缩了阳。人伦关系颠覆。
《猎人峰》的神农架里发生了一系列的疯狂事件,都是共时性的,建构了一个疯狂的深度空间。它来自原始的万物有灵论,与人们崇拜超自然的异己力量和怀疑自己的力量有关,也是原始先民对人的命运思考。
二、《猎人峰》的空间叙事效果
1、事件立体化
事件立体化,是就空间化叙述的效果而言,即相对于时间叙述的线性结构,注重事件在空间场域中的有机整体性。读过《猎人峰》的人往往有这样一种感觉,奇妙的让人难以相信,看似纷纭无序又整体效果好。他采取空间化叙事方式,没有线性结构的分裂感,反而将各个事件融合起来,给人立体感。
首先,《猎人峰》将时间概念打碎,给人时间概念上的模糊感,这样可以引导读者的关注点不是一个事件的因果关系,而是事件的发生空间和发展可能性,以及读者的感受。在这个空间里,人兽互置、传说与现实共融就成为可能,各种事件的共时发生也是合乎情理的,而不至于给人突兀感。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个神奇的神农架,读完后好久不能平息心情,有一种心惊肉跳的奇异感受。
其次,在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上,空间叙事方式让作者有了高度的灵活性。就《猎人峰》而论,它也写了作为文明代表的城镇与传统化身的白云坳,还写了人与兽、新社会与旧社会,但他没有以这样的二元划分作为阐释的基础,并得出因果式的结论,而是试图将其淡化甚至将其颠覆。通过空间叙事,将这些关系共同置于神农架场域里,它们之间没有因对比带来的分裂感,而是因事件的发展将各种可能性激发出来。如新社会不一定给人带来富裕和幸福,神农架的人们依然贫困,甚至连生理需要都无法满足;政府不一定为百姓谋福祉,而是以行政方式管制百姓,甚至镇压百姓,如文寇所长对百姓进行残酷镇压;人不一定比野兽高明、文雅,人不如野兽守信用;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光荣崇高的,覃放羊就假借革命之名可以大肆报私仇;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崔无际夫妇同样可以生出超常的老拔子。
这些事件共同营造了一个疯狂的世界,印证着开篇的疯狂征兆。因为空间叙事,他有充分的自主性,因自己的需要和事件的可能性去处理各种事件。我觉得,陈应松是在有意识地抹去这样的二元对立结构,试图把这种二元对立的分裂感推入渺远的蛮荒之际,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彻底疯狂的世界,并置身于其中从根源上探寻人的最终归宿。
2、审美场域的生成
或许是陈应松在神农架生活的久了,对神农架有切肤之感,在精神上、心态上、甚至情态上与我们不一样。他沉入神农架,与之“同情”,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宽广而厚重的神农架。神农架是宽广的,在它的怀抱里可以发生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事件;神农架是厚重的,对它怀抱里发生的一切都予以接受,给以宽容。如对第二章“人就是个草命”中因贫困带来的生存危机。
神农架的山民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里,产生了大量的光棍汉,“咱们乡镇五个行政村十九个村民小组,老少单身汉就达一百多人,占男性村民的百分之三十!”(第48页)他们连基本的生理要求都无法满足,因此产生了许多荒诞不经的事件。一是献宝,白大年想方设法捕杀各种珍稀动物,甚至抠出侄子的眼珠子献给政府,只是听说给政府献宝可以奖赏一个女人。二是换亲,“换亲你知道吧,又能比挖眼珠子好到哪儿?把自己十几岁的妹子嫁出去,嫁一个老光棍或一个傻子,自己换回一个老婆,这不相当于挖眼吗?……”(第72页)三是奸兽,“今年我已经听到有太多的笑谈荤经,都是说一些傻蛋、放羊老头奸羊的、奸牛的……”(第48页)
这三个事件是荒诞不经的,颠覆了我们的法律常识和道德观念。但发生在贫穷的神农架里,又显得是那么自然。因贫困而导致的荒诞岂止这些?整个《猎人峰》就是一个因贫困导致的疯狂世界:还有,因食物短缺而打破红丧禁忌;因贫穷而烧窑,并烧活人祭窑。神农架接纳了这一切。
这三个事件置于一起也是残酷的,残酷得让我们无力去指责和批判,因为这残酷仅仅源自人的基本生存权。神农架发生那么多荒诞的事件都是因为贫穷,如此残酷的事件迫使我们去思索在贫穷面前,人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识该如何桂芝。神农架宽容了这一切。
通过空间叙述,陈应松在《猎人峰》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作为审美场域的神农架。这个场域不仅是事件的发生地,更承载了作者对生命意识、人性意识的深切思考。这是跨阶级、超历史的。“现在,他拖着两条腿,也不能言语,以惟一可以活动的右手,艰难地在纸上写下了:恩人、仇人、好人、坏人、人、人、人……”(第49页)覃放羊对“人”字的书写,实际上写出了一个人性追问的格式:“恩人、仇人——好人、坏人——人”。这个格式一层层地剔除了人的外在,从个体的恩仇到社会的评价,最后锲入到人性的根本,在如此广阔又厚重的审美场域里追问也就张扬出更大的力度。
原来,《猎人峰》通过空间叙事方式,打碎时间线性因果关系,以虚实相生的空间构造笔法,塑造了一个诗化的神农架,使我们身临其境于故事的立体感中,专注于生命意识和人类意识。
杨家海 长江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本文所引原文出自《猎人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版),均只注明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