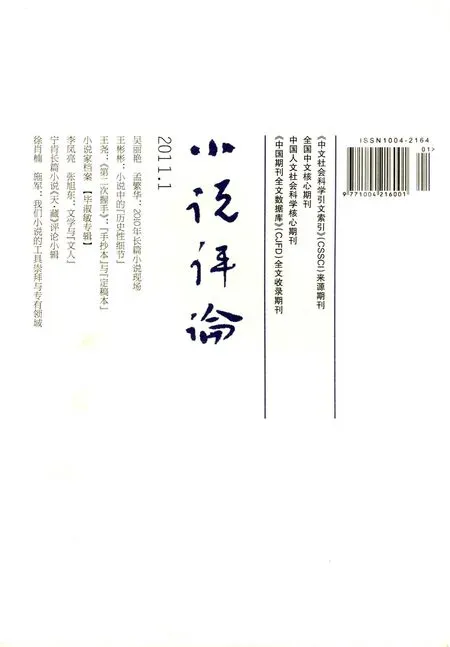挽歌的困境
——论田耳的《夏天糖》①
庞秀慧
挽歌的困境
——论田耳的《夏天糖》①
庞秀慧
曾经是短篇小说的《夏天糖》经过田耳的改写后,作品的精神意蕴彻底发生了变化:如果说短篇小说《夏天糖》仅仅是一个故事的话,那么长篇小说《夏天糖》就是由故事而升华的一曲挽歌,用作者田耳的话来说,《夏天糖》不但要写“十年间,从农村到城市变化的过程”,“也想关注一个问题。进入城市后,能不能融入,漂移的状态,无路可走。”②在这个小说中,文学佴城再次成为故事发生地,但是这一次文学佴城不再是孤立的城镇,它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佴城人身上也就折射出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特征,而《夏天糖》的成就与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和这些特征息息相关。
一
在短篇小说中已经叙述过的司机与小女孩的故事依旧是《夏天糖》的叙述重点,但是作品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者,通过“我”的成长以及活动,串联起佴城与莞城的历史与现状,呈现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佴城以及莞城的历史,另一方面是“我”和司机江标等人当下的生活。
从第一个层面来看,小说所展现的不再是一个乡下人进城的过程,而是人和城市一起脱胎换骨,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成长。出身农村的母亲和舅舅的奋斗历程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记忆。在田耳笔下,身为知识分子的父亲顾丰年和岳父范医生庸庸碌碌,一事无成:清高的父亲一辈子最拿手的事是养蟋蟀打架;逍遥的范医生总是坐在书桌前写文章,却总不见有任何成果。只有母亲泼辣能干,勇往无前,以前干个体户,剥过蛇,到福建贩过水货,现在开餐馆搞建材公司承包建筑工程,甚至还在佴城境内修过长城,成为佴城的重要旅游景点。“我”和小伙伴涤青、涤生参与了母亲的创业,几个小孩子帮母亲送VHS盒带,一起翻录磁带。在这个过程中,比“我”大四岁的涤青成为“我”最深刻的依恋,是“所有怀旧的华章部分”,这是“我”与涤青的情感起点。而且母亲的生命力极其顽强,面对经济环境的变故所导致的投资失败,她以退为进,终于东山再起;同样面对生活的打击,父亲却从此一蹶不振。
母亲的历史,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乡村,更值得重视的是连接着城市和农村的乡镇。城市文明通过乡镇影响农村,与此同时乡镇又是农民进城的首选落脚点,乡镇实际上成为乡土社会感受城市文明的第一站,而且乡镇对城市文明的看法与感受又会直接影响到乡村,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乡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道非常值得研究的景观。在《夏天糖》中,母亲通过在大城市和佴城之间倒卖水货而发家致富;莞城的发展使得城、镇、乡、村联系到了一起,连小小的佴城都有了自己的飞机场。乡土社会由一个纯粹经验性的地域变成了一个高度变化的、充满了理性抉择的空间,人无意中成了历史的创造者和参与者,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乡镇的变化中,例如母亲疏通关系把我安排在群艺馆上班;江标的舅舅把江标一家从乡村带到了城市,“我”和“江标”对这种安排既欣喜又莫名其妙,不知道母亲和舅舅为何这么神通广大。从黎照里的名言“人总是要发展的,不发展也要让别人以为你在发展……要不然赚的钱不够弥补你心头的失败感”里,我们多少能感受出来人们的盲目和急迫。
然而历史在前进,但是价值理念未必能顺应历史的脚步,正如马泰·卡林内斯库所说“历史(记忆)被表明是生活(自发行动)无法化解的仇敌。”③现代化的过程使得凝固化的乡土社会变得涣散,一切曾经深深依恋过的,自以为坚固无比的东西从此烟消云散。个体和城市一起成长,可成长之后的城市却不是和所有个体都继续维系原有的关联。《夏天糖》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者就预示了这个事实。“我”始终是母亲生活的旁观者,对时代浪潮不过是被动地应和,从来没有进入母亲生活的内在,体会母亲和大时代的精神主旨。当母亲和父亲离婚之后,大时代留给“我”的只剩下了与涤青的感情,而真正吸引“我”的却是江标所代表的当下生活。
这就是《夏天糖》的第二个叙述层面,江标代表着另外一种生活,他严肃认真,如同堂吉诃德对抗风车一样对抗着高速发展的社会。从思维上来看,江标显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他留恋在乡村土路上跑车的生活,缺乏对经济的敏感,始终维持手工制作球形薄荷糖的兴趣,全部激情都维系在当年那个躺在马路上的小女孩身上;对城市文明的理解仅仅是“城里人谁都不愿当孙子”,为了甩掉字辈,就另取个单名。为了维持乡土记忆,他不断追寻着铃兰的踪迹,不顾家庭经济现状,资助铃兰离开佴城。“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新潮人物:摄影师,时尚,有品位,还鼓励离异的父亲重组家庭,爱人涤青又是颇有影响的地下电影导演。但实际上“我”和江标分享着同一精神世界,“我”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拒绝着快速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和动荡不安的精神状态。作为第一批闯荡莞城的人,虽然四处都有发财的机会,“我”却缺乏致富动力,天天睡到自然醒,再“挣得足吃饭住宿的钱”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他和江标一见如故,同样迷恋着小女孩所代表的往事记忆。
当个体被怀念萦绕,很容易呈现出颓废哀婉的情绪,虽然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颓废是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一,但是当乡镇刚刚和城市接轨,初步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时,这种颓废实则就是在否定高速发展的现代文化,特别是这种情绪再和以江标为代表的农业文明纠缠在一起之后,城市的面貌就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在《夏天糖》中我们很难找到现代化城市的特征,没有现代工业文明的气息,在“我”的生活中,只有涤青是努力向上,奋斗不息的人。但是涤青却是“我”有意无意贬低的对象:涤青在外多年,饮食和服饰都发生了变化,甚至连佴城的俗谚都听不懂了;当“我”与铃兰偷情时,涤青身上那种由现代文化熏陶出来的“气场”竟然是“我”与之背离的原因;只有回到父亲的旧房子里时,“我”才被唤起一种同涤青相濡以沫的感情。对往事的怀念成为不断循环往复的主旋律,现实生活中的人要么随波逐流,要么就被卷入对往事的随想之中,特别是当涤青因为怀有身孕不得不屈就“我”的生活状态之后,人物情感指向一致往后,共同缅怀逝去的时间。这其实是一种希望现实固定不变的愿望,非常容易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因为在现代生活中,“现实性之显于我们面前就是历史性。永恒的现实不可被当作一种无时间的持续的他物,补课被当作一种在时间里常驻不变的东西。对我们来说,现实毋宁是一个过渡。它取得实际存在,而它作为实存又将立即重新离开它的实际存在。它所取得的形态,不是持续,也不是固定不变,而是挫败。”④这种挫败体现在很多人身上:涤青放弃了自己的理想重返佴城;铃兰见识了莞城之后,觉得自己是泥巴命,城市生活和她无关,又回到了江洋大道作妓女;江标费尽心机维护铃兰的纯洁,但最终失望,特别是他强迫铃兰身穿绿衣,躺在马路上,试图重现往事,陡然发现今非昔比,顿生杀机。而这场屠杀在作者笔下,显得极其唯美,铃兰的血是淡绿色的汁液,充满了“清凉温润的气味”,这是对往事的最终悼念,表现出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悲哀。
二
总体而言,“无路可走”的挽歌是作品的核心思想,写出了转型期的乡镇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它又暴露出作品本身的局限和困境。挽歌有多种,有的是悼念逝去的乡土,如贾平凹的《秦腔》;有的是表达赞美之情,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但是《夏天糖》的挽歌中充满了抗争的意蕴。这种抗争不但表现为“我”在现代文明面前的颓废态度,更是以江标和铃兰的故事为寓言来反抗快速变动的现代社会。由此,它又不单纯是反抗城市化带给人的精神困境,而是混杂着以历史对抗现实的意味,既不是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也不是费瑟斯通的“刻意的乡愁’(willful nostalgia)”⑤,而是一种由于缺乏了解和认同而导致的对抗,极大地限制了作品的精神境界。李敬泽曾经说过:“田耳的小说中,在参差差异的主题、经验和语调之间,贯穿着一种眼光——不是观点,也不是视角,而是复杂、含混的态度,是本能的、逐渐发展和塑造起来的兴趣。”⑥这种态度源自于作者久居凤凰小城,活动空间有限,对城市生活缺乏具体而微的感受。他对大城市人的中心意识很敏感,但无法体会大城市所代表的工业文明,所以在他眼中所有的城市和凤凰都很接近。⑦这种对城市文明缺乏认知而导致的平庸境界突出表现在铃兰对莞城的认识上:铃兰无法想象大城市的超市“比佴城所有的店子加在一起还大”,所以初到莞城时,极其兴奋,觉得自己无知是因为生活给她的机会太少,“我要努力,有趣的东西都学一学,有没有用是另一回事”。这是乡下人进城叙事中最关键的要素:农民在进入城市之后,深感以往的封闭和落后,愿意改变自己以适应城市,铃兰希望未来可以是“有很大一套复式楼,还有车,赚钱很多”;但是“我”干扰了铃兰对生活的设想。“我”在莞城的生活状况是很窘迫的,租住的屋子和纸盒子一样,可“我”还以居家为乐,以至于连铃兰都开始询问“我”的理想。可见“我”始终没有进入城市的内在空间,对城市精神的感受都是间接的,是源于母亲和涤青,“我”无法真正体会到城市文明的内涵。最后铃兰因为对“我”的情感依赖无法自立,最终回到了佴城。乡镇最终还是不能顺应现代化的潮流逐步靠拢城市文明,依旧无法摆脱农业文明的魅影。
或许这就预示了当下中国乡土小说的宿命,它将不得不和作家们一起去适应现代化城市的逐渐生成和成长,乡土作家和乡土小说息息相关,“精神的存在,决定着文学的形态、结构和品质。”⑧目前乡土作家们最欠缺的地方是无法以历史的眼光去把握城市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所蕴含的精神实质,作家们往往着力描述农民在城市的焦虑和堕落,却很少能确切地描绘出城市提供给人的特有空间,并由此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其实空间本身并不单纯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样,“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⑨乡土小说中对城市的描写有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有高楼和公交车,还有农民工在城市的狭小住所等,但是很少有人能深入其中,描写全球化对农民生活空间的影响。其实在现代文学中,对城市空间的描绘比比皆是:茅盾在《子夜》里写城市的灯红酒绿,写股票交易所,写资本家们周围的各色人群;新感觉派对上海生活的全方位描述;还有张爱玲作品中多次出现的阳台。但是在当下的乡土小说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农民在这些都市空间中活动,即便农民不断游走于城乡之间,感受到了城市生活带给他们的焦虑与孤独、失落与茫然,甚至于颓废与荒诞。但是他们的空间依旧是狭小的,因此无论乡土文学怎么关注人的生活,也无法超越前人。姑且不说精神境界的差异,单从描写内容上来说,当下的乡土作家根本无法像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一样,无法写出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新空间,更谈不上探索农民在城市的历史发展趋势。
田耳也是如此,所以《夏天糖》中的佴城虽然曾经积极投入时代的洪流中,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佴城和莞城的差异越来越大,乡镇根本没有能力承担起传播现代化文明的重任,反而被静穆的农业文化所吞噬。由此铃兰与“我”的随波逐流和顺其自然,涤青的潇洒与执拗都有一种空虚无助的味道;“我”虽然对现况不满,可抗争的方式却不是了解城市文明,并努力融入其中,而是沉溺于对往事的不断追忆,因此才会无限向往江标的故事,表现出一种价值判断的迷茫。整个小说没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再三宣扬的时代精神,却充斥着大时代变迁中的被动承受者,也就是说以江标所代表的失去精神家园的人群占据了小说的中心,滚滚而来的时代巨轮碾碎了他们的梦想,他们能做的是以一种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去与这个时代做个告别。当然,这种告别是惨重的,对于涤青来说,她放弃了她一向的理念,屈就“我”所代表的颓废生活;对于江标来说,他以杀害铃兰的方式,对于变动中的现实做出了最为强烈的抗议。但是我们不得不问,难道乡土文学也要以抗争的方式来对待逐渐逼近我们的现代文明么?
本文系2010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江苏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0ZWD017。
庞秀慧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注释:
①《夏天糖》本是作家田耳发表在2006年第十一期台湾《联合文学》并获得第二十届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的一个短篇小说,但是田耳经过长期沉淀后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写,这就是发表在《钟山》2011年第一期的长篇小说《夏天糖》。本文中《夏天糖》除非特指,皆是田耳的长篇新作。
②刘燕:《田耳:底层是个讨巧的概念》,《东莞日报》2009年5月31日。
③〔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7页。
④〔德〕卡尔·雅斯贝斯著:《生存哲学》,王玖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⑤周宪,《全球化与文化认同》,引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周宪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9页。
⑥李敬泽:《灵验的讲述:世界重获魅力——田耳论》,《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
⑦田耳、张昭兵:《田耳:语言是人最难以掩饰的个性》,《青春》2009年第7期。
⑧林贤治:《中国作家精神还乡的历史流变》,《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2期。
⑨亨利·列斐伏尔著:《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