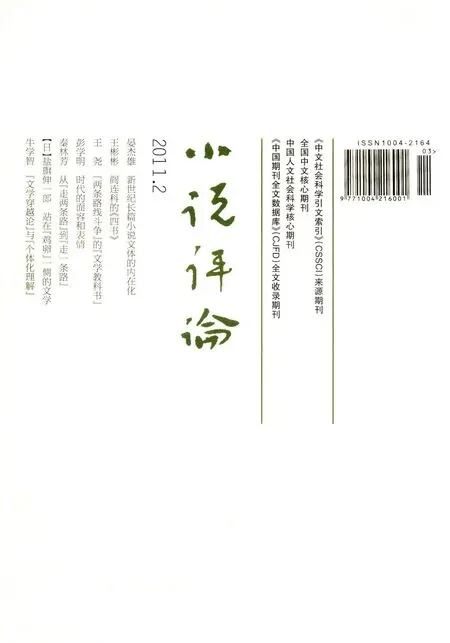从“走两条路”到“走一条路”
——论丁玲的创作转变
秦林芳
从“走两条路”到“走一条路”
——论丁玲的创作转变
秦林芳
1950年5月,丁玲借《陕北风光》修订再版之机,对自己的思想道路作了回顾,认识到自己“过去走的那一条路可能达到两个目标:一个是革命,是社会主义,还有另一个,是个人主义”;“但到陕北以后,就不能走两条路了。只能走一条路,而且只有一个目标。即使是英雄主义,也只是集体的英雄主义,是打倒了个人英雄主义以后的英雄主义”。①“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并置,使作于华北时期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表现出相当复杂的意蕴结构。真正在小说创作中谨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只走一条路”,是从她创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开始的。
一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9月初版)的意蕴结构相当复杂:一方面,她根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取到人物的设定,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另一方面,她则通过对农民精神痼疾的深刻批判、通过对地主形象和“边缘人”顾涌形象的真实描写,仍然表现出了作者的个性思想和人文精神。
丁玲创作这部作品是有其强烈的政治动机的。她曾经说过,她计划写这部小说时,“当时的希望很小,只想把这一阶段土改工作的过程写出来,同时还像一个村子,有那么一群活动的人,而人物不太概念化就行了”。②这里她所说的“写土改过程”,并不意味着作品只是对土改经过的“客观化”记录。恰恰相反,它凝聚着丁玲浓郁的主观化的政治情结。她是把这部小说的写作视为一种政治行为,把它看作是“在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点小成果”,“是为他(指毛主席——引者)写的”,要“呈献给毛主席看的”。③她所说的“还像一个村子”、“人物不太概念化”,也正好透露出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即她的写作冲动并非来自自己对客观生活的体验,而是为了表现某种先行的“概念”——所谓“村子”和“人物”,只是她表达“概念”的工具和载体而已。丁玲后来也坦言:“要写一个什么,开始要有一个主题思想,要没有一个主题作为创作的指导和范围的话,那么宽广的生活,你到底要写什么呢?”那么,贯穿这部作品的先行的“概念”(即“开始要有”的“一个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要讴歌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和农村在土改斗争中的变化(即她所说的“写农民和农村的变化”)。作者既先行确定了这么一个政治化的主题,在创作过程中,它作为一个先验图式,必然要反过来对作者产生制约。于是,我们看到,在阜平开始创作之前,为了“不犯错误”(亦即为了契合这一先验图式),丁玲“反复去,反复来,又读了些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材料,我对于我的人物选择得更严格些”④。这样,作者从材料的剪裁、情节的安排到人物的设定,就都不能不受到这一主题的影响(或者换句话说,是“土改的思想意义”决定了作品的“事件的选择和安排、它们的因果关系”⑤);而经过如此剪裁的材料、如此安排的情节和如此选择的人物,也就自然成了对这一政治化主题的图解和证明。
创作动机的政治化和创作过程的政治化,使这部作品表现出了作者“在‘党的政策观念’上的高度自觉”,即:“不仅要用党的意识形态来观察、分析一切,而且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化为自己的艺术思维,成为文学创作的有机组成”。⑥作者以意识形态化的艺术思维,通过描写暖水屯土改斗争从“发动”、“诉苦”、“决战”到“翻身”的过程,形象地说明了“一个多月当中换了一个天地”(第58节“小结”)靠的就是以工作组和县委宣传部长章品所代表的党的领导与农民内在解放要求的结合。自作品问世以来,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它的这一特点。
应该承认,以“政治式写作”来“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确实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一个鲜明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特征就是其意识倾向和思想意蕴的全部。事实上,丁玲在接受意识形态规训、传达历史理性的同时,仍然以个人化的思考给作品灌注了尊重人的价值、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的人文精神。作品也因此撇置了对单一历史视点的强调,表现出了作者的“个人主义”思想。
首先,这种人文精神表现在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五四”改造国民性传统,以“立人”为目的,对农民的精神痼疾展开了批判。主要包括:一、奴性人格和宿命观念。土地改革,对农民而言,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实现双重“翻身”的重要契机,但是,由于奴性人格和宿命观念的影响,他们或者拜伏在命运面前而安于现状,灭失了改变自我命运的冲动,或者把土改视为外在于自己的运动,而对之持旁观态度。即使在物质上翻身以后,他们在精神上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翻身,他们仍然没有“明了自己是主人”,而依然认为土改成果是别人“给”的、“送”的。二、狭隘自私的小农观念。对许多干部来说,他们参加土改,其直接动机大抵在实利方面,只不过是要像阿Q那样“拿一点东西”而已。如妇联会主任董桂花意识到,“现在又要闹起来了”,“这对她会是件好事”;而这之所以是件好事,是因为借此“能把窟窿(指为了买地而欠了十石粮食——引者)填上”(见第7节“妇联会主任”)。干部既如此,一般农民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参加土改的主动性自然与干部不能相比,但是,在眼看可以获得实利的时候,他们却又不甘人后。第37节“果树园闹腾起来了”写到财主家的果子给看起来时,有些本来只跑来瞧瞧热闹的,却也动起手来。三、残酷的暴力情结。如夏志清所说,作品确实“把一切斗争地主常见的情况,如农民的忿怒,仇恨及暴行都记下来了”。⑦在“决战”阶段,那些“要报仇”、“要泄恨”的农民,“把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暴打钱文贵,差点把他“打坏了”。丁玲以此真实地写出了农民内心深处强烈的暴力情结及其可能导致的结果。应该看到,丁玲对国民精神痼疾的批判本有其现实的政治期指;她在描写农民的思想“锁链”中所寓托的政治动机,本是为了让他们“摆脱自己身上的锁链”,“团结在一起,跟着共产党勇往直前”。⑧但是,作品在作者的主观命意和客观倾向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裂隙;其原因在于她对农民的思想状况的描写与对农民作为土改斗争所要依靠的政治力量的身份认知,事实上处在分离状态,而成了并列的两条线索。正是这一裂隙的存在,使作品的思想批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得了自足的意义。⑨
其次,这种人文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作者通过对地主形象和“边缘人”顾涌的描写,刻画出了他们在土改风暴中表现出来的复杂人性,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并以自己的解释视角对他们“时不时地做出活生生的并不符合遵命文学要求的评价”⑩。如果说作品对农民精神痼疾的批判,是从反面展现了丁玲“立人”诉求和对“人”的本质、价值的思考,那么,作品对这些人物的个性化描写,则从正面显示出了丁玲对“人”和“人”的权利的尊重。具体而言,在对地主形象的刻画中,丁玲一方面以明晰的历史理性,展示了其作为一个阶级必然失败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没有像同时期其他土改小说那样简单地从一般的政治定义出发,对他们作出妖魔化的表现,而是忠实于自我的乡村体验,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当作“人”来写。她既关注着这一历史风暴对这群特定之“人”个体命运的影响,又在一定程度上写出其复杂的人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作者对他们的人道情怀。例如,在李子俊形象的塑造中,作者就融注了对“有天资而无成就,善挥霍不善理财”的父亲的情绪记忆,通过对他的为人处世之道与其时下落寞凄凉(“好受罪”)处境的对照描写,在这一可悲人物身上寄予了恻隐怜悯之情。
与对地主形象的刻画有所不同,在对顾涌展开描写时,丁玲始终用了那“极其明显的同情的笔调”,始终表露出了一种鲜明的人道情感。这是一个来自于现实生活的人物。根据丁玲回忆,在土改时,一个富裕中农献地后让他上台讲话。她看到的是他用烂布条作成的腰带、脚上穿着的两只两样的鞋和劳动了一辈子已经直不起来了的腰。⑪这一场景,给丁玲以强烈刺激。内心人道情感的汹涌激荡,导致了她对这个处在风暴边缘、并不为风暴所倚重的“边缘人”的关注。于是,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她不但饱含同情地正面写出了他勤苦节俭的美德和以劳动发家的经历,而且以农会主任程仁等人的议论侧面写出了斗争他的不合理与不得人心。关于这一形象的意义,严家炎先生曾经指出:在当时“连‘富裕中农’这个名称也没有,许多问题都在摸索中”的情况下,丁玲“是在用思想家的眼光,独立地思考和判断生活”。⑫需要补充的是,丁玲的这种“思想家的眼光”不是来自对阶级和阶级关系的理性分析,而是源自作者可贵的人道热情;是她对可能具有此种命运的“人”的理解、关怀和同情,导致了对现有不合理的政治律令的质询和怀疑。因此,这与其说是显示了现实主义的深刻性,还不如说是显示了人道情感的深刻性。⑬
二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因“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并列、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交会,在思想意蕴上形成了这种“二元并置”、张力巨大的复式结构。这说明此期丁玲在思想上、意识上仍然走着“两条路”。但是,与之相比,《在严寒的日子里》在意识倾向上却显得极为单纯。作者对“意义”的单一化诉求(即只“走一条路”),彻底遏制了自己对生活的个性思考和独特发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纯粹的“政治化写作”,使作品的意蕴显得极为简单,因而其结构只能是一种毫无张力的线性结构。
《在严寒的日子里》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姐妹篇。早在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丁玲就“得到了一些沦陷后桑干河一带护地队斗争的材料”,并拟以此为材料来写“小说的第二部”。⑭这部小说后于1954年夏起笔,到1978年3月,共写出24章(未完稿)。它虽然在内容上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颠覆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复式结构。其线性结构的形成,源于其对“意义”的单一化诉求。1955年,她在一封信里写道:“今天我也没有写文章,我想多想一想……我的语言不好,不够生动都没有关系。可是让它有意义些。不要太浅就行。”⑮她这里所说的“有意义”,其价值尺度显然不在自我独特体验的阐扬上,而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辙上。为了凸现这种“意义”,丁玲非常理性地为《在严寒的日子里》设定了一个纯政治化的主题:翻身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斗争和流血”战胜地主阶级,“保卫既得胜利”。它一方面统领情节设计、人物刻画等紧紧围绕政治化轨道运行,使之成为对这一主题的图解和说明;另一方面,则非常有效地控制了与此不相吻合的个人体验的发生,防止了作者自己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一致的独特识见的“走火”。所有这些,都从不同层面为作品纯粹“意识形态意义”的彰显提供了保证。
为了凸现“斗争和胜利”这个单一化的政治主题,《在严寒的日子里》在果园村布设了泾渭分明的两大人物阵营;二者的对垒和斗争则构成了作品的中心线索。它所描写的全部情节内容就是:果园村的地主阶级向翻身的贫苦农民反攻倒算,而贫苦农民则严阵以待、积极斗争。于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曾经出现过的那种犬牙交错的人物关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这种极为简单、也极为分明的阶级营垒的描画。而在形象的刻画上,总的来说,不管是对哪一个人物阵营的描写,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他们的阶级属性,而丝毫没有与之不一致的人性表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像李子俊、顾涌那样具有复杂人性内涵的人物在这部作品中全都不见了。这说明丁玲对人物阵营的布设、对人物的描写,不是从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出发的,而是从先在的意识形态的规定出发的;其结果自然只能导致对人物的简化和人物关系的简化。
丁玲政治意识的强化,突出地表现在对贫苦农民形象的刻画中。与地主形象的塑造一样,作者对贫苦农民形象的塑造也是从主流政治所规定的阶级属性出发的。其区别在于:前者对地主形象的塑造所使用的是漫画化的手段,而后者则对农民作出了理想化的描写。本来,在创作初期,对他们如何把握,丁玲也有困惑,也感到左右为难:“我想了,想得很多,可是实在难写。我不能把人的理想写得太高,高到不像一个农民。可是我又不能写低他们,否则凭什么去鼓舞人呢?”⑯这种把握上的二难,说到底是由农民自身所具有的既是革命的主力军又是小生产者的二重属性所引发的。但是,由于追寻“政治意义”的需要,在反复修改特别是最后的重写、续写中,她终于撇弃了自己最初的困惑,以反“写真实”的姿态将农民形象作了理想化的处理,其结果就是她当初所说的使之“高到不像一个农民”了。在她的笔下,这些农民身上再也没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那些小生产者的精神痼疾,而是显得那样深明大义、豁达无私,表现出了牺牲小家为大家的崇高品质。
当然,根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丁玲深知在描写两大敌对阶级搏战时必须凸现党的领导。她在第十八章中曾将这一认识外化为作品人物王大林的心理活动,就是:劳动人民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抱成团行动起来,推翻剥削者,压迫者”,革命“才能成功”。因此,要写人民的革命斗争,必须写好党的领导。她在“开场白”中也交代得分明:虽然果园村的工作,在这一带并不是走在前列的,“可是这里也有人民,有了新建立起来的党,有正确的革命路线”。这是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于是,后来在修改1956发表的前几章时,她考虑的首先是“怎样把党写好,怎样把党的路线写好”。⑰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她从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定出发,将它落实到对代表正确路线的党员形象的塑造中。在对区委书记梁山青作出一般性描写的同时,她重点刻画了村支书李腊月的形象。从“把党写好”、“把党的路线写好”的目的出发,她对他进行了神化,从而使之表现出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支部书记张裕民大为不同的精神风貌。在刻画张裕民形象时,她意识到他“不可能一眨眼就成为英雄”,因而“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⑱所以,作品在着重表现他的沉着、老练和对革命事业忠心的同时,也如实写出了这位农民出身的先进分子身上还存在着的多疑、犹豫等缺点。而这部作品中的李腊月却从一开始就是在品质上一无缺点、在行动上一无过失的完美“英雄”。他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以“奔正道,跟共产党走,万匹马也拉不住我”和“为穷人千桩祸我也敢当”的正气和牺牲精神,始终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他主动出击,亲自组织捉拿枪击梁山青的凶手赵贵;在奉命去找区委领导之前,他登上高院房向全村父老发表讲话,稳定人心,激励斗志;在还乡团进村以后,他又冒着危险潜回村里,继续组织斗争……虽然作品也以有限的笔墨写到了他的情感生活,写到了他与兰池的那种朦胧恋情,但是,它却不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所写程仁和黑妮的关系那样更多地偏向于个人情感领域,而是指向了政治。兰池出生贫苦、遭遇坎坷,而且极富斗争性,最初使李腊月感动的也正是她对“吃人的旧社会”的控诉。他们的感情的扭结点不是别的,而是“我们要一辈子跟定共产党闹革命”的共同信念。因此,从作品的这些描写来看,与其说他们是情感上的恋人,还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同志更确切些。也就是说,丁玲对李腊月情感生活的表现,仍然是政治化的,其目的说到底仍然是要突出其政治上的坚定性。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丁玲对李腊月的塑造,作出了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拔高,因而具有很强的神化色彩。在丁玲笔下,神化他,就是为了凸显党的领导的正确;因此,可以这样说,他的形象越是完美、越是高大,就越是表现出了丁玲在这部作品中追求“把党写好”、“把党的路线写好”的坚决。
三
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比,《在严寒的日子里》在意蕴结构上发生了从“复式”到“线性”的巨大变化。那么,这一变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典型意义呢?
我们知道,《在严寒的日子里》是丁玲在1955年以后极左思潮所施与的长期迫害中重写和续写的。它曾被作者视作“朝夕爱抚的宠儿”,称它能够“治疗我心灵的创伤”。⑲诚然,丁玲“心灵的创伤”是极左思潮所施与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部被她视为“心灵创伤疗救者”的作品在思想倾向上是与之相对立的。事实上,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既在迫害着她,又在规训着她,使之成为自己的顺从者。法国学者福柯根据对知识系统的分析,指出:在一个特定社会的特定时期,某个方面支配着有意识的、正常的、理性的思想活动,这个方面可以称作“知识”、“认识”或“档案”。⑳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处在支配地位上的“知识系统”,丁玲从左联时期以来(特别是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就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和理解。她的不少作品事实上也成了它所倡导的、具有典范意义的代表。但是,由于早期所接受的五四文学传统影响力的强大和自我对这种影响的自觉接受,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中却仍然保留了自己的个人话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人”的关注。二者的并置,使作品在思想意蕴上形成了复式结构。但是,到创作《在严寒的日子里》时,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知识系统”,不但在丁玲那里得到了内化,而且变成了支配丁玲思想活动的唯一因素。这就不能不造成作品在意蕴结构上的线性特征。
对于丁玲为了图解作品“斗争和胜利”这一政治化主题而作出的艺术处理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线性意蕴结构,读者曾经提出过质疑。1980年6月,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对青年作家讲话时,她对此作了转述,并同时作了辩解:“前几天我收到一封信,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我把农民写的太好了,问我是不是受了江青、‘四人帮’的影响,是不是受了一九五七、五八年对我的那些批评的影响。我说很遗憾,这些文章我都没有看,现在也懒得看。”㉑稍后,日本学者杉山菜子也事实上对丁玲的这一辩解作出了呼应。她虽然正确地指出该作“继承了五十年代文学的主题”,但又根据对丁玲自己写“成长和变化”的声言的解读(即其中“被描写的人物最初是不成熟的,然后逐步成长,在成为公认的模范人物之后仍作为普通的一员出现”),提出该作“体现出她对‘四人帮’时期的‘三突出’论的批判精神”。㉒我以为,根据上文的分析,读者对她“把农民写的太好”的质疑是切中要害的,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的分析也是深刻的;而丁玲的自我辩解则显得相当苍白、相当无力。至于说那些批判她的文章“都没有看”,并以此说明自己没有受到相关影响,显然是有违真实的强辩之语。
从建国后“十七年”到“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占支配地位的文学观念作为一种权力话语,统御了这一时期的创作,并导致了此期文学创作主体性、独立性的丧失。到1976年3月丁玲执笔重写时,反右斗争中的极左文艺思潮以及作为其恶性发展的“四人帮”的“题材决定论”、“三突出”等帮派文艺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思想资源,也都摆在了丁玲面前,并对这部小说的重写发生了影响。1976年春节期间,也即她动笔重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之前不久,她“读了许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长篇著作,也读了目前的一些作品。对于我过去的作品,也作了许多检查。的确感到文艺创作上的许多问题”,表示“一定要批判过去的那种自然主义的写法”。㉓在主流话语场中,因为“写真实”就是“自然主义”的同义语,所以,稍后,她还明确表示“不打算写真实”,“实际我不是写真实”㉔——她深深知道,不管是“自然主义”还是“写真实”,都会因个人体验的掺入而导致“政治意义”的不纯粹。这里所说的“自然主义的写法”问题,是在当年反右斗争中根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给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强加的罪名。批判者曾经指出:“从黑妮和农村妇女形象的对比中,从顾涌和一大群贫雇农形象的对比中,特别是从作者对农民的落后面貌和落后情节以及脏话的偏爱中,我们都能闻到浓厚的自然主义的气息,那侯忠全形象上的刺眼的一笔,在这里也可看到,它并不是偶然划上去的”。㉕不难看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被批判者视为“自然主义”表现的这些部分,大多是作者有独特发现灌注其间因而与主流话语不相吻合的地方,也是作品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但是,在经受了主流意识形态粗暴批判以后,丁玲自己却被规训了,从而使她油然萌生出了这种悔其少作、急欲更弦改辙之感。丁玲的这一自我批判,说明主流意识形态已经真正在思想上完成了对她的改造。
如果说1957、1958年对丁玲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和创作上的“自然主义”的批判,是“主流政治”对她的负面规诫的话,那么,作为“四人帮”帮派文艺思想之载体的“革命样板戏”则是“主流政治”对她的正面引导。对这一引导作用,她没有否认。她曾经说过:“革命样板戏是好的……样板戏也的确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励。我从那些作品中也吸收了许多经验。”㉖所有这些,都在“不能做”和“应该做”方面无形地规训了她,并影响到这部作品的创作。除此之外,这种规训还以一种有形的方式出现了——这就是她在创作过程中对“领导”监督的主动吁求和自觉接受。在开始重写后不久,她在给家人的信里写道:“这次创作,我在北京时,已向当时组织领导说明,山西省委、市委、公社、大队负责与我联系的人都知道,他们替我去东北取原稿(稿已遗失),我现在的情况,大队支书也清清楚楚知道(未向其他人说)。”㉗这种有形规训是她在接受无形规训的前提下自愿作出的,这样,该作的重写在形式上也就成了在“组织领导”直接干预下的活动,因而,其创作活动的“独立性”即使在形式层面也很难持守了。
在主流意识形态这些有形无形的规训下,丁玲在《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创作中果然“只走一条路”了:她以单一的历史理性覆盖了应有的人文精神,以对一般“政治意义”的呈显来灭失自我的艺术发现,以对人物一般阶级属性极端化、单一化的展示(由此导致了对人物的理想化、神化或漫画化)来替代对丰富人性内涵的深刻挖掘。这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二元并置”、张力巨大的意蕴结构,到这部作品中就蜕化为以“革命意识”为唯一内蕴、以传达意识形态说教为唯一目的的、毫无张力的线性结构。在这样的创作倾向中,我们非但看不到“她对‘四人帮’时期的‘三突出’论的批判精神”,相反,我们倒是看到了在肉体上遭到极左路线严重摧残的作者在精神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权力话语的认同,看到了其曾经有过的“诗人的本领”的丧失。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在严寒的日子里》意蕴结构的变化中,我们既可以看出丁玲在主流意识形态规训下主体意志的弱化乃至泯灭,也可以看出同时期文学创作的一般生态。
注:本文系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两种文学传统’视野下的丁玲文学道路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A751058)、2009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种文学传统与丁玲文学道路研究”(批准号:09ZWB004)和2010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丁玲传论”(项目编号:2010SJD750011)的阶段性成果。
秦林芳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
注释:
①②③⑭⑱丁玲:《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51页、第45页、第97-99页、第45页、第98页。
④⑧⑪丁玲:《丁玲全集》第7卷,第418页、第416页、第436页。
⑤[美]梅仪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页。
⑥钱理群:《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204页。
⑦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⑨参见拙作:《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国民性批判》,《齐鲁学刊》2009年第4期。
⑩[德]顾彬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⑫严家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⑬参见拙作:《在“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之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人文精神》,《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⑮⑯⑰㉓㉔㉖㉗丁玲:致陈明(1955年3月20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117页。
⑲丁玲:《丁玲全集》第10卷,第121-118页。
⑳郭宏安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6页。
㉑丁玲:《生活·创作·时代灵魂》,《丁玲全集》第8卷,第98-99页。
㉒杉山菜子:《丁玲文学的新生及其二十年的下放生活》,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2-353页。
㉕竹可羽:《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1957年第10期。
- 小说评论的其它文章
- 揭示灵魂隐秘与生命迷津
——评胡学文《从下午开始的黄昏》 - ">"文学穿越论"与“个体化理解”————吴炫文学批评理论
- 祛积极赞同之魅
——重评《艳阳天》 - 玫瑰底色是真诚,洗尽铅华识不俗
——读叶兆言新作《玫瑰的岁月》 - 站在“鸡卵”一侧的文学
——今读《白鹿原》 - 延异的创伤与断裂的诗学
——重读废名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