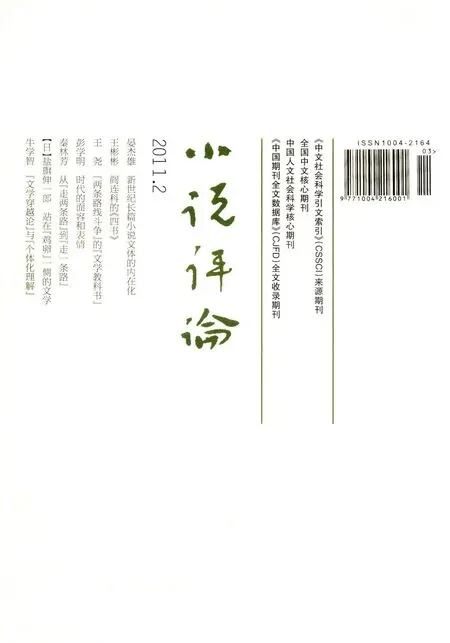"文学穿越论"与“个体化理解”————吴炫文学批评理论
牛学智
"文学穿越论"与“个体化理解”
————吴炫文学批评理论
牛学智
“本体性否定”:为何是与是什么
在与西方理性和反理性哲学比较上,我们可以简略概括出“本体性否定”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与“辩证法”的“否定”比较,“本体性否定”与人、动植物的矛盾性否定运动有不同。人有“本体性否定”是人有“离开自然界”的冲动和能力的意思,而动植物的矛盾运动和人的“否定之否定”认识功能却不具备“离开既定世界”的可能。由于人的“存在性否定”是“离开矛盾运动之否定”的意思,也因此,“本体性否定”不是人和生命现象的普遍法则,是可能性、或然性的。而黑格尔的“矛盾运动”、“辩证法”是人的普遍法则,萨特的“人学辩证法”也适合于任何人的自由选择(哪怕是不选择的选择),所以很难解释有的民族为什么不断有重大创造、有的民族却丧失创造(如爱斯基摩人)的文化现象,更可以解释中国人曾经有文化创造、却因遗忘“本体性否定”而只是强调“宗经”而不再有不同于孔子、老子这样的重大思想创造的问题。吴炫举例说,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不是辩证法的产物,其实就是指“辩证法”在解释文化的产生、重大思想创造上是有局限性。在这里,可以解释“量变引起质变”的“辩证否定”之创新不一定能解释爱因斯坦的创造,因而吴炫力图区别“本体性否定”与辩证否定“的不同,是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
其二,与“反理性”的“否定”比较,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的“感性生存”或“审美性”对抗现实,还是“回到出发点”。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视为“本体性否定”,但在实践中吴炫认为是获得虚弱的满足和形式上的欺骗行为,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所需要的“本体性否定”。他举“人”的概念为例来区别阿多诺举“狗”的例子。就“人”这个概念来说,“问题不在于‘人’这个概念遗漏了各种类型、不同层次、不同个性的人,而在于你是怎样理解和认识并解释‘人’这个概念的。”①阿多诺说“狄多是一只狗”,可是又不是一只狗(因为狗这个概念不能表达某种非狗的属性,如白的、秃尾的、矮脚的等等)。“是……又不是……”的表述方式,虽然内容很完满但没有发展,不能创造新概念;而“人”的概念并不考虑阿多诺的“非同一性”的完满,才成为可以有发展变化的“概念之间的本体性否定”。重要的不在概念能完满表达人的内容,而在于你如何切入对人的理解。追求人的完满虽然可以暴露概念的“非同一性”之局限,但某种意义上也取消了人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非理性意义上的感性生存,同样需要理性来维护。所以后现代的问题正在于重新理解“生命、感性和理性”的关系,而不是“对抗理性”。中国文化没有“让感性成为感性”的理性文化传统,所以引进西方反理性哲学要更加慎重。
那么,“本体性否定”不同于传统本体论的基本特性是什么呢?首先,它是“自发性”的、“或然性的”,不受自然性运动的“必然”和“偶然”支配。如果只知道体验“快乐”,就很难产生“本体性否定”意识;如果“不满足于”体验快乐,还想获得自我实现尤其是自我创造的价值感,就有可能产生“本体性否定”的意识。这是对传统建立在必然性和普遍性上的“本体论”的消解。吴炫的追问是:如果“本体”是由必然性决定的,我们何必担心“本体”会失落?如果“本体”是有偶然性袭来的,又如何谈得上人为努力的可能?其次,是“人的创造性本体哲学”的而不是一般的“人本哲学”的,它不问万事万物是怎么来的,而问人是怎么“穿越”自然性的现实而成为自身的,再进一步是问人类重大的思想创造是何以成为可能的,而不把解释思想的承传作为“人的本体论”的主导方面。所以吴炫特别强调人只有通过独特的创造才能安身立命。再次,“本体性否定”是“尊重现实”的,而不是传统否定对现实居高临下的、轻视的态度,这就具有中国文化和谐性的“别一种意味”,是对传统等级性文化和西方二元对立文化的告别。最后,“本体性否定”在性质上必须是一种纯粹的、独特的事物的诞生,所以它是“独在性”的,而不是一般的“个性”可以解释的。这即是他特别强调的“创造出来的个体”与“天然的个性”的“不同”②。应该承认,上述若干特性,确实与传统中西方的本体论知识有明显的区别。
“本体性否定”与“文学穿越论”
“穿越”是吴炫独创的一个术语,字面上除了含有对被批判对象“尊重并不限于”的意思之外,“穿越”从思想渊源来说,是对西方的“超越”和中国的“超脱”的批判并将其材料化加工改造的结果。与此二者相比,“穿越”因为建立在“本体性否定”哲学观基础上,所以是解决中国当代精神问题的最高理性理论。
首先,就“穿越”的特性而言,“穿越现实”不具备西方“超越现实”所讲的“进步性”,也不具备西方“超越现实”的“抽象性”。文化上,无论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辨证运动、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进化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图式;还是文艺理论上,柏拉图重现实轻艺术、黑格尔重哲学轻艺术、阿多诺重非理性艺术轻理性现实,以及西方哲学如毕达哥拉斯的“数”、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海德格尔的“在”,和中国先锋文学运动对西方“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的搬运,“超越思维”和拒绝言说、拒绝意义、拒绝现实感的虚无主义意绪是其一大特点。而“穿越现实”既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谐的一面,又给传统文学对抗现实的传统以独特理解,使文学的“独立”获得新的内涵。所以“本体性否定”强调文学对文化现实的突破性,与文化现实、政治见解、道德观念之间建立的是“艺术不同于现实”的“并立”关系,即指利用现实之材料、建立一个和现实不同的非现实世界。“穿越”作为方法论,具体呈现为“不拒绝物质现实、具象现实、意识形态现实”但又不依附它们而能以“独到理解”为其深层结构和意味的特点,所以这是中国式独创性文学“亲和现实又不同于现实”的存在特征。
同时,向内回避痛苦、向外肯定现实,是道家“超脱”在中国历史中的普遍形态,很难解释既不肯定现实、也不退回内心的中国独创性作家。所以突破“超脱”就是对中国传统文人和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中国式独创的思想资源的倡扬。如苏东坡“非儒非道非禅”的达观而不失独特进取的生命和精神状态就该继承,而陶渊明的“非儒即道”的“回避政治现实”的田园乐趣就应该有所批判;当代作家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其欲望的贪婪、欲望实现的考究和成为棋王过程中显示的超凡脱俗的智慧,就既不能完全用老子的“道”来解释,也不能单纯地依附当时政治意识形态要求的那种又红又专的知识青年来图解。王一生身上所体现出的尊重生命欲望和注重自我实现的努力,与不是无缘无故地要“独立”就是与世无争地一味“颓废”的同时期文学拉开了距离,是“穿越现实”的有价值个案。一方面,“穿越”从中国传统现代化重建的大处着眼,要求作家能突破儒家或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现实功利性要求,希望作品意蕴能延伸到文化性和人类性的领域,以重视和面对现实的精神来改造其“避世”的思维惯性;另一方面,就作家的个体创作而言,“穿越”是指作家在思想上要突破道家思想对其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的支配,尤其对西方当代人本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道家哲学结合后推出的“无为”和“惬意”的人学观做出自己的理解和批判,最后达到作品用儒、道、释均难以涵盖的程度③。穿越道家避世之道的穿越意识,使得“穿越现实”真正成了用中国现代理性思维衡估文学的哲学观,而不仅仅是具体而微的方法和模式。
其次,就世界观而言,吴炫的穿越论中统辖穿越方法的世界观是“穿越道”,而不是传统文学中虽反复变化但根本上仍属于变“器”不变“道”的“承载道”。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属于“否定性批评”的一些现象就说明了这一道理。比如发轫于当代道德、伦理、人文等细部的道德批评、社会伦理批评以及人文精神批评等,你不能说它们没有问题意识,也不能说它们没有批判性,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对文学的如此要求是功利性的。之所以批评界和创作界一直对这种批评持有保留态度,甚至于因情感上的逆反有时表现得格外“反感”。质疑的原因之一是到底谁拥有批评的“优越感”和批评的“豁免权”的问题,文化的多元、价值的相对主义可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关键是,显示“优越感”和“豁免权”的那个“道”,要么是西方人本主义的,要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这种“道”的不接受,至少说明停留在“低程度创新”层面的西方式“对接”和中国传统式“转换”,都无力解决复杂的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哪怕是最圆满的移植,只要是依附于既有观念,它的说服力就是有限的。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当后现代主义成为中西方都很时髦的思潮以来,文学的零散化、碎片化成了作家追逐的写作时尚,这个时侯,如果没有“穿越道”的更高照耀,文学的本质论虽然很振奋人心,然而在当下时代很难找到更有力的理论依据;反本质主义在反本体论、主体论、反映论时不无力量,但也很难从理论内部给文学增添多少光泽。所以吴炫在《论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文艺争鸣,2009,3)一文中批判和清理了当代西方主导性文学理论潮流中的“本质”与“反本质主义”的负面影响,也分析了当代中国批评家在这个强势理论干预下认同该理论所表现得“犹豫”的心理原因和文化原因。破对方最终是为了立自己,他分别用“穿越性”、“程度性”、“体验形态”和“成为了什么”,“穿越”了对方的“承载性”、“本质性”、“意识形态”和“成为”。这些虽主要是文学性、文学观的论析,但本质上却拷问的是批评家的脑部组织。
吴炫的“文学穿越论”的意义在于:百年来中国现代文论和现代文学转变和发展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但这个现代性培植、发育和彰显乃至于成为标志当代文学观的一个重要符号,实际上都是在文学的“表现内容”上来和中国传统文学观区别的。也就是文学的现代化在文论家和创作者那里,基本上都是自觉或不自觉按文化现代化的要求这个或明或暗的指令来进行,甚至到后来,过多的心力都集中到了文学该不该边缘、是不是中心这样无关文学性的拉锯战中而不自省。如此归类性的研究和工具性的追逐,既放弃了对苏轼等具有“个体化理解”的作家作品的当代转化、遴选,也因误把王国维等具有现代气质的文论家的艺术无用论做了狭隘理解,致使在“自娱”的性质上索求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因缺乏这样更高的思维穿越,当代批评家和作家正在进行的工作,不是摇摆在“儒道互补”中,就是吃力地跟踪在西方“形式”、“自律”论身后,却很难达到“文学作为工具从属于文化要求”与“文学作为本体穿越文化要求”并立对等的状态④。特别是,当有学者把从“本质主义”走向“反本质主义”、“文字化”到“图像化”、文艺理论范式的后现代转换等描述成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当然的发展方向时,吴炫却提出“中国现在是否需要建立自己的区别于西方的‘本质与反本质’的‘文学性思维’方式来体现对文学问题的‘中国关怀’?基于这种关怀,中国现代文论是否需要建立在中国文学自己的独创性经验上来论‘文学性’问题?”⑤
文学的本质论因拿先验的文学特征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边界,固然是死板的、不可取的;但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西方反本质主义者和中国的支持者,认为文学仅仅是其它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或者认为文学的文学性只在于区别其它学科的“文学性语言”的说法,吴炫认为伊格尔顿及其支持者的逻辑是“人类文化虚无主义”的表征。所以,他以“穿越性”穿越“承载性”,来确保“道”的个体性;以“程度性”穿越“本质性”,来强化区别于西方“形式自律”的“中国式文学性”;以“体验形态”穿越“意识形态”,来显现文学的个体化理解;以“成为了什么”穿越伊格尔顿“未完成”的“成为”,来标识文学史的观念建构性。即他一方面用“文学性程度”这个张力性概念,在中国经典作家如苏轼、曹雪芹、鲁迅那里发现既亲和“言志”、“载道”、“缘情”,又无法用这些概念实存化、对象化的现有资源;另一方面用“体验形态”替代反本质主义的“意识形态”说,用“成为了什么”和“成为何以可能”的提问方式来纠正、细化反本质主义留下的漏洞。从而通过“体验形态的丰富和复杂”“模糊掉”伊格尔顿所说的由“评价、认识、信仰模式”构成的日常意识形态,构筑起其它文化现象所不能替代的“相对自足的世界”。在此意义上,“文以穿道”所需要“穿越”的“道”,主要不是指作为文化宝库而存在的“古今中外的思想史”,而是指制约自己看待世界、影响自己从事创作的观念、方法和思维方式,是指那些制约自己走向“文学独创”的最亲切、也最致命的敌人。这显示出吴炫对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双重穿越,即文学必须以作家的“个体之道”突破、改造“群体之道”,必须以文学的“体验形态”化解观念化的“意识形态”之“道”,才是文学观的“中国式现代创新”。“文以穿道”就目前语境而言,的确具有釜底抽薪般的革命意义。
再次,文学穿越论在批评实践操作中,主要显示为一种微观方法,而不仅仅是观念形态描述。所以穿越现实的程度,即文学性程度就成了穿越论落实的最后一道工序。为此,吴炫提出了他的“准文学、差文学、常文学、好文学”的“文学性提问方式”,这是对观念形态的“文学性程度”的深化和细化。承前所述,吴炫一上场其理论就不在“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本质是什么”的逻辑起点建构。在他那里,“穿越现实”就是“文学”,“穿越现实的程度”就是“文学性”。那么,“有无现实之用”也看作是一种“程度”而被尊重为“有、弱、无现实之用”的文学性衡估之张力。这种梯度就把中国文学理论中既有的“形象因素”、“情感因素”等评价机制纳入到否定主义文艺观中来了。意思是当这些文化特性逐渐取得支配的权力并化为“结构”成为“形象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时候,文学作为“因素”才转化为“性质”,文学才成为文学。文学性质本身就是使文学由低文学性程度向高文学性程度运行的过程。注重这一过程,也就从根本上穿越了意识形态判断、道德判断、现代性判断等“弱文学性判断”。这四种文学性的分层批评法,也许可以具体地回答顾彬及中国批评家感觉好像洞悉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缺少了什么、怎么了、但除了抛出丧气话“垃圾说”后一味摇头、且无法找到理论阐说的难题。
当然,在吴炫的理论体系中,“文学性程度”的层次分析始终是统摄于他的“文以穿道”的文学观的,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另外,“文以穿道”作为文学观,它内部的细密纹理又必定得放置到“个体”的存在性状态来观照,这就牵扯到了他的文学批评价值坐标的一个重要概念:“个体化理解”。
“个体化理解”对文学批评的启蒙意义
吴炫否定主义文艺学中的“个体化理解”,在哲学上一方面指如何发现并创造、表达自己,而不是那种“个人化私语”、“独白式感伤”和“依附群体化理解的个性化解释”,是“表达一种个人性的关于自己在这个群体世界中的意义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理解”⑥。另一方面,“个体”之所以是一种“理解”,强调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与群体的对立关系,而是通过个人的创造理解努力并将之符号化来建立起和群体的“对等关系”。
如何成为“个体化理解”?“心灵依托”与“我行我的什么素”是两个关键问题。吴炫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心灵依托”不应该是依附群体来解决的事情,而是建立在群体性文化基础上又通过个体理解贡献给群体所没有的东西所获得的世界的尊敬。那么,“我行我素”作为日常生活乃至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个体观念,就成为否定主义的“改造对象”——我行我的什么素——就成了一个必需追问的哲学命题。吴炫举《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逃课者霍尔顿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霍尔顿与一般逃课者的不同在于,他给他的逃课行为赋予了自己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找一个“理由”。他给与他心灵有关的事情赋予了自己的理解是:他讨厌在学校“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但是当他自己也逛夜总会、叫妓女的时候,他就难以为自己的如此行为挖掘出意义来——这是他要离开学校的根本原因。对这一细节,吴炫看到的是霍尔顿对自己的行为充满了批判冲动和理解行为,也就是霍尔顿在自己行为中显示出“独特的理解群体化生活”所显示的意义。就此他构筑了他的否定主义“个体化理解”的内涵,这是最精彩也是对文学批评最直接有效的一种哲学批评观。
否定主义哲学所要告知人们的是:要使一种行为成为自己人生的一个亮点,你就必须发现这个行为不同于以往的意义,并且坚守这个行为所显示出来的意义。而要是某种行为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意义,你就必须搁置这个行为已经显示出来的意义。要搁置这个行为已经显示的意义,你就必须对这个行为轻易显示出来的意义持一种怀疑的眼光,所以批判和建立在此是一体的⑦。
有了对“个体化理解”的哲学解释,吴炫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就带有总括性和普遍性,至少是能够说明当代中国文学整体性局限的个案或思潮。目前能看到的论评中,他很少跟着文坛上流行的作家作品走,也很少抓堆儿似的把一批风格类似的作品捆绑到一起进行命名,他所选择的作家比如王蒙、贾平凹、张炜、张承志、莫言和张贤亮(这些作家当然也是新时期以来研究者研究频率最高的),基本上是能说明一个时代文学面向的作家。这肯定是有精英倾向的批评家的一个共识。然而对于吴炫,另一层意思似乎是这批作家更适合于做他的否定主义哲学观、文学观的审视对象。
试举王蒙为例。他看王蒙,侧重点与一些王蒙的研究者倾心于王蒙喧哗灿烂的“说话的精神”(郜元宝)、王蒙的小说技巧(郭宝亮)、革命话语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南帆)以及作为思想家的王蒙(王春林)等都有所不同。早期的王蒙对世界的基本理解主要是“王蒙式的忠诚”,因此王蒙在创作中表现出的生命活力,主要体现为对艺术技巧的探索与杂糅。这一点是多数研究者都能达成共识的一个看法。洪子诚先生所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持此判断。由“艺术技巧探索与杂糅”这一特色而造成的“王蒙将批判的敏锐化为生存的机智”——“王蒙显得很会批判了”。因此,“王蒙的批判从来不会触及世界观层面”。王蒙及其作品在这个层面上的局限、不足和圆滑、世故,或者说“老年写作心态”。批评家王彬彬曾给予猛烈的批判⑧。总的来说,早期王蒙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形象,就是本质的单一和显现形态的杂色这样一个极富有艺术感觉,又觉得感觉的变化多端背后总欠缺更有力更本质的思想深度的经历丰富的人。这一角度,王彬彬的批判是触及本质的。然而与吴炫相比,王彬彬只能是在思想层面对知识分子的王蒙的认识,这一认识要放到对王蒙后期的文学世界观上来衡量,肯定是偏颇了,而且王彬彬参照物是传统道德规范和既定的五四知识分子精英精神脉系,非此即彼对建构主体人格是有力的,却很难说此法同样适用于王蒙文学世界的评判。吴炫的《在文化迷雾后面的王蒙》因为动用的是他的“局限分析”法,他看到的是王蒙后期作品中“‘宽容’观念的局限”,即王蒙把“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不等于每个人的发言都是等值的”这两者混淆了。意思是王蒙的肤浅性不是表现在对趣味高低的“宽容”上(王蒙替王朔辩护的一个根本理由就是“一个作家哪怕是只有低级趣味,也应该有一席存在之地”,而不赞同依据传统道德来贬抑低级趣味的所谓“文化批判”),而是表现在缺乏不满足趣味的“本体性否定”之冲动作他“宽容”的支撑点。
因为“宽容”只能管束“生存世界”,但管束不了“存在世界”;我们没有权利对一个人说不该干什么(伤害他人、违法乱纪除外),但我们有权利说、也应该对一个人说“还应该干点除快乐和利益追求以外的事情”。这个“还应该”就是当代“不宽容”的含义。但这个“不宽容”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引导性的,是出于对生存空虚体验的人们自觉愿意去做的——否则就无法摆脱人生的无意义感、空虚感。“不宽容”主要不是拒绝什么(违法乱纪主要由法律管制),而是还应该人为地补充什么,使人摆脱随遇而安、随心所欲、创造与非创造都是等值的状态,因此“不宽容”是“应该”之意⑨。
在这个标准下,王蒙创新的“轻而易举性”和王蒙式宽容的“价值混乱性”,其原因就在于王蒙“缺乏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世界的‘理解点’”。
又比如,“难以穿越传统”的贾平凹,因没有“属己”的“存在”所以只能“声嘶力竭”的张承志,“没有爱情、也没有尊重”的张贤亮,“孩童化批判”的张炜等等。吴炫的批判基本上成了后来研究者研究这些作家时的一个思维惯性⑩。
还比如对小说思潮的论评,都显得与致力于“类”的归纳和对文学生产机制的文化分析批评很不一样。他认为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是一条意义链,所以西方的意义消解是针对有意义的现代主义而言的。之所以中国用同样的“现代性”或“现代主义”来反封建主义但心灵仍然空虚的原因在于,是因为中国从根本上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现代主义,从而完成对传统伦理主义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的“真正革命”。因此,中国要实现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可能不用后现代主义也能实现,这是因为后现代在中国这里很大程度是拾西方人的牙慧,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会对否定的对象构成“本体性否定”,即便消解了,等时机成熟了也会弹回原来的位置。新世纪以来,由“现代性”诉求到回归现实问题的“底层文学”,再到“正面肯定性价值”的“恬适”、“惬意”。换句话说,在这一连串的快速转换中,文学是真正以他者的形式存在着的,它只被动地听命于像伊格尔顿一样的反本质主义者的召唤,创作者既没有心思静下心来聆听内心的呼唤,又因急于追随主流意识形态的表情而耽于形式的锤炼。看起来文学似乎是一步步逼近了“独立”,创作主体也似乎离个体化理解的“个体”越来越近了。实质上,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转换中,非但创作的“个体”没出现,文学对群体之道的依附越来越露骨了。就是说,在“现代性”的诉求中虽然依附西方人本主义的“道”但还不乏有批判性,当回到中国道家文学传统“恬适”、“惬意”的时候,人物无欲、无我、无不满、无抗争的“自为”状态完全成了“超脱”的当代翻版。审美人格的这种脆弱化和虚幻化不仅没有批判性,而且就算放到现实主义的框架来衡量,因人物在现实中的有机性和血肉感在其“无争”和“惬意”的“虚”中被化解而不具备起码的真实性。这时候,如何回避了内心的痛苦、肯定了现实社会内容还在其次。这些文学现实都已经从反面证明了吴炫“穿越论”批评的重大意义。再比如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始终是“工具性”论析,认为无论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都是载道说和缘情说的两种形态,它们没有本质性差异。前者没有对群体文化赋予自己的理解,后者则停留在个人情感和感受上而缺乏个体化理解之提升。前者理直气壮但缺乏个人品格,后者纤细灵动但不能扩展为一个世界,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很注重细节但细节流合起来无非是无聊、烦恼、无意义的根本原因。就文学理论批评的建构来说,都一再表明,要从根本上扭转当代文学的匮乏,必须从世界观下手,得有“本体性否定”的原创理论做后盾。
吴炫的别样,自然是一种潜意识里比较的结果。一方面,主要得益于对哲学的看重,他提出的“第三种批评”⑪以及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根本性的贫困是“哲学的匮乏”的言论,都使得他的批评分析道德问题却不停留在道德层面,考察作家世界观但并不就具体细节做“过度阐释”。总之,他的论评都是建立在他的否定主义美学和本体性否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的。所以,做“局限分析”也罢,“穿越”现有文化观念也罢,给我感觉他一直是在做翻老底的工作。这种整体感和“打通法”,自然就有了与通常的学科内部“打通”(现代与当代,晚清与现代,或者通称“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大区别。这区别是把“新与旧”与“独立”、载旧“道”与载新“道”与真正的原创性区别开来了。也就是他说的导致中国新文学缺乏独立品格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满足于新旧思维和差异性思维导致的‘低程度创新’”,其次才是忽略从传统资源中提取中国自己的文学独立品格,和依附西方式对抗和超越观使我们走不出既定现实以及对“好文学”研究不足的理论问题等等⑫。另一方面是吴炫的任何类型的批评,比如作家论、作品论、思潮论和文学观念论等,都建立了自己的批评模式。这模式就是“本体性否定”的大框架和始终在穿越西学和中学的批评尝试,这种在别人说“是”的地方坚持说“不是”、别人说“不是”的地方非得要说“是”的执拗,虽有时略显牵强,但看多了他的论评,他的那个“不应该”或“应该”就顽强地构成了人改变自己并发出“从来如此便对吗?”的内部呼声。吴炫的“‘个体化理解’的理解”强调的就是个人如何才能成为“个体”,以及成为了“个体”的个人究竟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和日常行为的过程。特别是在成为“个体”的途中,个人内心既有观念即非存在性内容与已发现的存在性内容的冲突是相当激烈的,如果最终能在存在性场域站立起来,那么,他就彻底摆脱了“异己”思想的牵制而成为了自己,如果争斗的结果是前者战胜了后者,这个个人就仍然属于贯彻、执行他者思想的转化者、移植者并无缘成为真正“属己”思想的发现者。但是,在普通的个人、“素质性个人”与存在性个体的发展道路上,几率不会是均等的。也就是说,成功只会给有准备的人。这个有准备的人,按照吴炫的理论阐述就是那种习惯于用怀疑现状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他们的发蒙只需要“引导性”而不是“强制性”,引导或启示使人意识到“不应该”、“不宽容”其实正是吴炫所设的哲学圈套,这就是“个体化理解”对批评的启蒙意义。
这个意义上,重要的不是担心吴炫形成自己的批评模式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而是他的这个模式启迪了我们,使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生怕模式的不模式批评——那种呼唤问题意识的及时性批评,那种直接冲着所谓时代大问题而去的“直言”式批评,难道如我们所愿,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吗?反思使我们发觉,当今的文学批评其实有时真是走得太匆忙。
牛学智 宁夏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注释:
①《本体性否定——穿越中西方否定理论的尝试》,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②⑥⑦⑪《穿越中国当代思想》,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2页,第270页,第277页,第287页。
③⑨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第104页,第178-187页。
④《论苏轼的“中国式独立品格”》,《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
⑤《论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穿越本质和反本质主义》,《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
⑧王彬彬的《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再谈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及其他》两文,主要是批判王蒙及王蒙式处世之道、生存之道和文学中表现得圆滑世故、隔靴搔痒不及本质的世界观问题。见《一嘘三叹论文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第45页。对王彬彬这一点的观点另见拙文《知识分子良知为尺度:文学的心理人格论批评》,《渤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青年批评家李美皆选取“老年心态”这一视角,虽然批判的大意类同与王彬彬,毕竟以老年人的颓唐、衰败、暮气来说王蒙的作品,似乎也揭示了其作品中之所以有过来人看破一切后复为平静的某些不可逆转的主体性问题。见《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
⑩以上论评文章均先收集在2001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一书中,后又收入《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实际上是为了构成该书“穿越”的一个较完整体系。该书结构由“什么是艺术的‘穿越’”、“穿越作家作品”、“穿越文学思潮”、“穿越文学观念”和“附录”构成。单篇文章多数都在90年代中后期发表于各刊物,虽然很难考证其他这些作家的研究者著文及发表的时间,但只要涉及到这些作家后期作品的论评文章,恐怕至少得到2000年以后才能面世,这是其一;其二是,就我的阅读视野,对这些作家比如张炜的“道德理想主义”、张承志的“道德激情主义”、贾平凹的既传统又现代,实际上是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依附于儒道释并在循环中走向衰落的总体特征的把握,要么是研究者的共识,要么是相互影响。但李建军对贾平凹的批判除外,其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文章,实在也很难判断趋同的观点不是被吴炫影响,因为现在的批评文章很难说十分尊重学术价值,就算是借鉴、参照了他人判断,援引资料并不清楚,这也是当代学术混乱之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