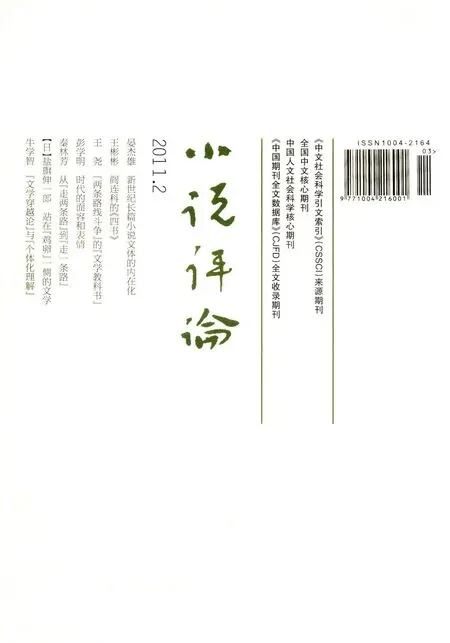乡村叙事:物与想象
——读《麦河》
李洁非
乡村叙事:物与想象
——读《麦河》
李洁非
在论文《自然、人道主义、悲剧》中,阿兰·罗伯-葛里叶写道:
事实上,比喻从来不是什么单独的修辞问题。说时间“反复无常”,说山岭“威严”,说森林有“心脏”,说烈日是“无情的”,说村庄“卧在”山间等等……不管作者有意还是无意,山的高度便获得了一种道德价值,而太阳的酷热也成为了一种意志的结果。这些人化了的比喻在整个当代文学中反复出现得太多太普遍了,不能不说表现了整个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
不久前,关仁山兴致勃勃谈起他的长篇小说近作《麦河》,那时我只是洗耳恭听。等后来终于读了这部作品,不知怎么,油然想起多年前所接触的罗伯-葛里叶的以上论述。
这种联想,并非因为《麦河》与法国新小说派有何联系,但是在罗伯-葛里叶所谈问题与中国当代小说对乡村的叙事处理之间,由于《麦河》的缘故,我感觉受到了某种触动。
中国是农业大国。历史上,若论农业文明的发达,没有哪里可同中国相提并论。有的古代文明如古埃及、古印度,种植之早虽不输于中国,但说到品类的众多却瞠乎其后。而其他地方,就更不足论。近代以前,美洲、非洲和澳洲不必说,就是欧洲,在农业方面对中国也只有甘拜下风。中国于周代以后,对其自然环境中可以食用的物种,全都引向人工种植,很少遗漏,所未种植者,像花生、玉米、马铃薯、蕃茄、棉花等,只是因为物种不在本地。这一点,看看衣食就一目了然。中国馔殽之丰无所不包,出现在饭桌上的东西,别处往往闻所未闻,至今这种差别仍旧明显;而在穿衣方面,除棉布出现较晚,像丝、麻、葛,都是在孔子时代就成为制衣材料,而同时的欧洲,除了羊毛织物,便只能直接以兽皮裹身,换言之,与他们主要从事游牧的状况相匹配,乃至未脱原始狩猎的遗风。
然而奇怪的是,尽管二三千年内中国都曾是首屈一指的农业国,农民不言而喻是这个国家最基本的群体,但中国文学却一直跟农民不相干。为什么呢?因为语言文字掌握在士大夫手里。表面上,也有与农民生活相关的作品,比如“田园诗”,陶渊明、王维、白居易、张养浩、贯云石等都写过一些,可是,这些描写骨子里是士大夫自己的情趣,他们对农民生活的玩赏,与农民自己的价值观关系不大,至于农民生活的真正内容和感受,更近于空白。所以,田园诗不能视为真正的农事诗,是裹着乡村外衣的文人诗。真正的农事诗也曾有过,基本上到《诗经》“国风”为止;《诗经》以后,属于农民生活自己的文学表现,就只存在于典籍之外,作为民歌等口头形式随时湮灭,不能进入文学史、构成文学史意义上的存在。
由此可知,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一定能够对应。中国作家终能对乡村社会和农民有所意识,是拜西风东渐所赐。近世欧洲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发生平权思想,社会视野大大打开,到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兴起,各色人物一齐涌来作家笔下。清末民初,随着西方文学大量译介,国人从中发现极大反差。梁启超率先提出小说革命,要求文学发挥“群伦”“群治”作用;到“五四”前后,陈独秀批评中国文学的贵族、山林倾向,胡适鼓吹平民文学,文学研究会诸人以“为人生”为口号……中国文学开始降尊纡贵、向整个民生敝开,而沉默的乡村社会和广大农民因此得以映入文人眼帘,引起认真的描写和表现。其划时代标志,当属鲁迅《阿Q正传》,这部作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篇小说,塑造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生活完整性和丰富性的农民形象。
《阿Q正传》以外还有一些名篇,如《多收了三五斗》、《春蚕》等。“五四”后,乡村叙事的缺失得到填补,然而又有了新问题。比如,情节是农村的,语言却不是;人物外表是农民,内心却不是。类似情况很普遍。直到赵树理出现前,同情农民、为他们鸣不平的作家大有人在,但以农民价值为价值、以农民趣味为趣味、以农民理想为理想的作家,却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原因在于,中国的作家都是读书人出身。一来往往不真正熟悉和了解农民、乡村,二来读书人在精神尺度上之于农民有难以逾越的界限,他们描写农民,是把后者置于自己视角下,而没有把自己置于农民视角下。
最明显的,是语言。很多作家,自认为对农民感情很深,农民的痛楚他们能够感受,农民的辛苦他们能够体会,农民的不幸他们能够怜悯,这些也确实可以为作品内容所证实。但是,唯独做不到用“村言土语”来写作。我在做延安研究时,读过大量延安小说,结果发现以1942年或以赵树理出现为界,之前延安小说语言是十足的文人语言(包括后来彻底农民化的柳青),人物谈吐与口吻毫无农民味,有时迹近翻译小说腔调。显然地,这些以农民和乡村生活为表现对象的作品,无法供农民阅读或了解,因为里面充斥着许多让农民莫名其妙的言语。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读书人来说,这是一种隐秘。虽然他们在伦理上、道德上,可以努力说服自己同情农民、关心农民、尊敬农民,但在价值世界深处,他们无法认同农民——或更明白地说,觉得农民并不足法。语言一物,关系到“美”。读书人不难于鼓励自己去爱农民,但若让他们奉农民的语言为圭臬,却必定唤起内心殊死的抵抗。这里头有雅俗之别、精粗之别、文野之别,甚至洁秽之别。此非朝夕所致,来自数千年来不断编码与刻写的文化基因,实际上已是一种无意识。
赵树理所以突破这种情形,根本原因在他真正置自己于农民视角之下,以农民的东西为美。当然,他的成功与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化建构密不可分,若无后者撑腰,个人无法挑战整个知识分子价值和话语体系。抛开这一点,从历史结果论,我们看到从赵树理开始中国文学的乡村叙事形成一道分水岭。此后,作家们对于农民和农民文化在伦理上的骄傲被扫尽,对乡村风物、习俗了如指掌成为值得称道的优点,与村言土语有如鱼水被视为一种雄厚的语言艺术资本。
经过“五四”时期从社会层面打开思想、取得“庶民的胜利”,再经过延安时期从文化层面褫夺知识分子价值观,中国文学的乡村叙事渐次解决态度问题、立场问题和工具问题。这样,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乡村叙事取得较大发展,一跃而为主要的文学品种(当时称“农村题材创作”),中国文学与古老的头号农业国身份间的某种不协调,算是有所了结。今天,差不多各省都有深谙其乡土文化、活灵活现运用乡村语言的作家。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与成就,是正在热烈争论的问题。这当中,有角度和标准之选。依于古典或雅正的角度与标准,当代文学有诸多欠缺,极而论之者甚至斥为垃圾。的确,当代文学的“美”与“精致”,去唐诗宋词远甚,但若瞩目于乡村叙事及其对村言土语的发掘和表现,又可以说百代以来弗如,是历史上所未有的,这一点,日后自有公论。
但是,进而求之,将近百年来乡村叙事渐渐取得跨越式进展后,它还有什么重大的不足,抑或,我们对于它还可以表示不满的地方在于何处?《麦河》所触动我的,实际是这个问题。
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乡村叙事在人物刻划和语言风格上努力贴近乡村的生活形态,举如赵树理之于山西、柳青之于陕西、周立波之于湖南、浩然之于京郊,都是充分的例子。然而,政治或政策对于叙事的掣肘与干扰始终严重,致使作品(哪怕是最好的作品)不能避免表象上与乡村生活水乳交融、内里却背道而驰的窘状,形成“两张皮”现象。《艳阳天》就非常典型。一方面,它对农民生活的描写、农民语言的运用,自然、生动、熨贴;另一方面,在农民的现实利益、情感理想方面,却以“阶级斗争”说为先行的主题,强词夺理、矫情以致违背真实。所以,当时连最好的作家也不曾真正接近农民,虽然他们完全有那样的条件和才能,但政治阻碍了他们如实、不走样地表现农民,自如地探索乡村叙事原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文革”后,捆束乡村叙事的政治绳索开始松动,乡村叙事的政策性指向一点点淡化,到八十年代中期,“农村题材创作”基本摆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浩然那种创作方式,就此新开一局。几十年来对乡村风物、语言的谙熟、当行,以及对其人情的细致表现,这样的传统完好无损,乃至更臻佳境。但中国乡村叙事另一底蕴上的欠缺,却乘虚而入。
这一欠缺,是有关社会历史思考的个人能力偏弱。当然,这是中国文学的普遍情形,不独见于乡村叙事,但乡村叙事在政策性指向淡出后,所受影响似更突出。很多作品,我们对其人物刻画、语言运用都印象深刻,唯独在思想能力方面感觉平淡无奇。
以《秦腔》为例。这部2005年问世的作品,既是贾平凹个人才华的一次总结,亦可视为近百年乡村叙事的艺术结晶,语言成就大大超越以往。然而掩卷回味,小说对转型期中国农村所抱情怀,仅在于对土地和乡土文化的眷恋。这样一种感想(或主题),明显并非贾平凹独有,毋如说近乎于“流行”。我们已说不清中国有多少乡村叙事作品在重复类似的感想,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土地和乡村就被置于物化现实、城市文明的对立面,充当抵抗商品化趋势的角色,或者成为纯朴人性、牧歌情调的象征。问题也许并不在于这种思考本身,而在于诸多作家作品不约而同作这种思考,似乎除了这种感想,乡村叙事就不能提供点别的什么。
在知识分子来说,上述主题是容易想到的。通常,知识分子对时代、现实易持怀疑主义,对历史和传统则易持感伤主义。因为,知识分子本能地以守卫民族与人类恒通价值为己任。知识分子可贵之处是不弃理想,但知识分子的问题往往也在于耽于想象,好用主观浸染现实,向客观世界注入太多的感情和心理意味。以上所引罗伯-葛里叶论述,信手拈来几个例子,“说时间‘反复无常’,说山岭‘威严’,说森林有‘心脏’,说烈日是‘无情的’,说村庄‘卧在’山间”,指出其实质并非所谓修辞,而是描写如何被“人化”,亦即如何去迎合人道主义的主体论。
在文学中,以“想象”浸染“物”的情形,不以遣词造句为限。近年,中国乡村叙事争相引入“怀旧”情怀时,没有人去说明这种情怀何种程度上与现实相契,作家不屑于讨论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巨变下中国农村“自然而然”就唤起了这种情怀。
但关仁山写《麦河》时,显然处在不同的状态下。他对乡村现实的着眼点,难得地没有放到知识分子情怀上,而是放在乡村大地上切切实实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身上。他问道:“小说到底有没有面对土地的能力?”稍微有些让人意外,终于有作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本以为中国的作家永远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因为从过去作品看,他们普遍觉得自己笔下的乡村叙事不仅紧紧围绕着土地来写,而且写得非常深入、非常哲学和文化。但关仁山却肯定不是在这个层面上提出问题的,他所指的是,不文化、不哲学、不诗意,物质而且现实地面对土地。当然,我想替他做一个小小的纠正,中国作家不是没有这样面对土地的“能力”,而是缺少这样的意识。谈到能力,我脑中会浮现好几位作家的名字,他们的能力肯定是不成问题的,他们只是缺少这样的意识——一种直观凝视于“物”而不以“想象”涂染乡村叙事的意识。
此意怎讲?约略言之,要认识到土地并不是一种审美对象,或者,只在极少的特殊的情况下,才是审美对象,例如当文人们站在一定“距离”之外感伤地打量它的时候;在大多数时候,土地所承载的是社会、历史和现实,是以之为生、为之付出汗水的人们的衣食、苦乐。土地的含义,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如铁一般坚实,而绝不虚无飘缈。商周时代人们眼中的土地,一定不同于宋明时代;而工业化时代人们对于土地的感受,同样不会重复小农经济的时代。应该说明,我并不一概反对作家诗人将土地的表现置于富于距离感的审美态度下,像“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白居易《观刈麦》)一类诗句,其淡远优美,颇悦我心,尤其陶渊明归耕之后的作品,似乎是古诗中我最具好感者。问题是,在中国这种审美化的乡村叙事历来最多,而能不事渲染把土地、农民、乡村还原到坚硬的物质状态的笔触则太少。因此,不要说古代文人笔下的乡村能够唤起农夫多少同感,就是今天的小说家们所呈现的乡村究竟能否让“乡下人”觉得真切、身在其中,也明显是个问题。
其实,阅读《麦河》之前,我本来习惯性地把它“想象”为又一部抒发知识分子有关土地的情感的作品,它从梨花板和瞎子民间艺人写起的开篇,包括封套上那幅灿烂金黄表现麦收情景的画,似乎给了我这样的暗示。我甚至准备好去接受另一本《秦腔》,开卷时,两者确实有相类的气象;那也值得期待,就像刚才说的,《秦腔》在语言和叙述上达到很高水平。然而在曹双羊出场后,我慢慢意识到《麦河》的不同。
曹双羊是个鲜明的形象,他的来历很清楚很具体,跟随邓氏改革和市场经济一道成长起来,作者没有模糊这个背景,而是明确地表达这一点。曹双羊的“土地意识”跟时代进取心或“现实利益”联系在一起,没有如知识分子乐于描绘的那样,沉浸于对土地的古老与神秘,亦即所谓“天人合一”的理想抑或悲剧性历史情感之中。他拥有以现代生产方式开发土地的强烈愿望,而非抱残守缺、把土地当成纯真的初恋情人美好地藏在心中一角(我想起了二千多年前当最简单的农业机械出现时,庄子对它的诋毁)。实际上,他尝试把资本因素引入乡村。像曹双羊这样的农民,与已经厌倦了城市文明的知识分子明显不同,并不反感土地沾惹上商品经济、规模耕作和现代技术这些东西,在他眼里土地有“物质”的属性,有“社会”的属性,是“生活资料”,不是赋诗为文入的对象。也许曹双羊并不“代表”每一个中国农民,《麦河》也写到了那种所谓“小农生产者”的旧式农民,但是曹双羊的意识或心理,应该符合乡村社会的大多数。理由很简单,这种意识或心理,是切实的,与实际生存相一致。关仁山说:“农民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也没有啥娱乐生活。天一黑就搂着老婆睡觉。偶尔会听鼓书,特别是乐亭大鼓,听一段评剧,耍一耍驴皮影,日子缓慢而枯燥。”在有些作家笔下,这样的生活每每与单纯质朴的人性联系着,而被赋予牧歌的情调。其实农民自己何尝美之?尽管现代文明弊病甚多,人人唾之,但实际生活中对现代文明避之不及者却实属罕见。城市人如此,农民岂独不然?吾人也,彼亦人也;倘以己之不欲加诸农民、单单让他们抱朴守素,难辞“以美杀人”之疑。议至此,想到前几年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以农民口吻写成,极言城乡反差,如“我们刚刚用纸擦屁股,你们却用纸擦嘴了”,着实辛辣,幽默反在其次了。
关仁山说:
“三农”的困局需要解开,我创作的困局也需要解开。我走访中发现,农村的问题很多,农业现代化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农产品价格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等等。我感觉核心问题还是土地问题。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农村走进了时代的漩涡。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村非但不能跨入现代社会,甚至会出现混乱、停滞或倒退。
显然,他所思考的是被种种现实所纠缠的当下农村困境,而非什么“世外桃源”。他的笔指向已经并随时发生“巨大变化”的农村,“一个小村庄,既拥有几十亿的富翁,也有中产户、一般户,还有很穷的农民。”这样一个乡村,具有多向性、多义性,而乡村叙事也要配得上这种多向性、多义性,就此而言,容忍那种单纯或诗意的乡村叙事,实际上极大地无视了真实的乡村社会。故尔关仁山问道:“仇视城市吗?廉价讴歌乡土吗?展示贫苦困境吗?整合破碎记忆吗?每一个单项都是片面的,应该理性看待今天乡土的复杂性。”他特别地把目光盯住土地流转问题,以为这当中包含乡村现实的根本矛盾,“这些流动的、不确定的因素,给我带来创作的激情”。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乡村叙事从无到有,复于延安时代起将乡村叙事从简单的道德同情伸展到土地、制度、生产方式等“现实主义”层面,又在五十年代中期后因政治意识形态的教条化而损伤了“现实主义”维度,嗣后为了躲避这种政治化倾向,乡村叙事渐渐投向避“实”就“虚”的所谓文化-审美格局,而让“想象”取代、驱除了“物”的表现,以致远离现实境状、无力复盖乡村生活的巨大变化和全部复杂性。《麦河》也许还不足够深刻有力,但它展现出来的意识,对于近几十年来的乡村叙事格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扭转;在《麦河》中,读者真正看见了中国乡村大地上的生活、变故甚至潜在的危机。
李洁非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 小说评论的其它文章
- 揭示灵魂隐秘与生命迷津
——评胡学文《从下午开始的黄昏》 - ">"文学穿越论"与“个体化理解”————吴炫文学批评理论
- 祛积极赞同之魅
——重评《艳阳天》 - 玫瑰底色是真诚,洗尽铅华识不俗
——读叶兆言新作《玫瑰的岁月》 - 站在“鸡卵”一侧的文学
——今读《白鹿原》 - 延异的创伤与断裂的诗学
——重读废名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