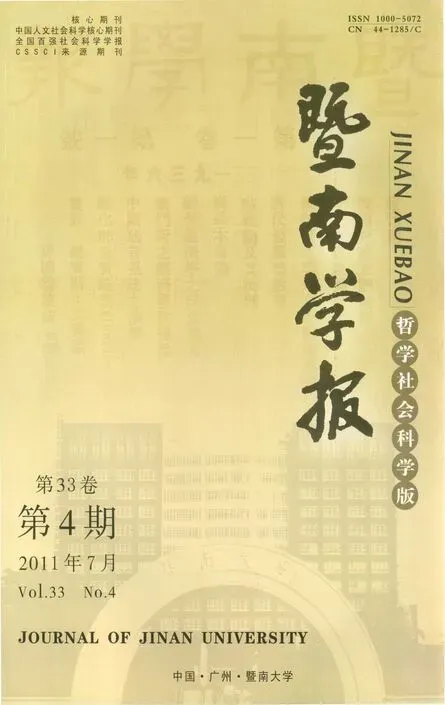对文学原理教材中之创作论阐释的思考——以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例
罗 宏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180)
对文学原理教材中之创作论阐释的思考
——以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例
罗 宏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180)
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在有关创作论的阐释中,存在着学理逻辑不够统一,对马克思有关论述误读、一些创新性的说法不够确当等现象,值得商榷。
文学活动;创作论;艺术生产;创新
一、“文学活动”的本质论阐释如何统摄创作论阐释
熟悉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下简称《教程》)者都知道,《教程》在文学本质论阐释中将文学本质理解为一种“人的活动”,在《教程》导论部分和本质论部分,都以很大的篇幅强调,传统文学理论忽略了文学的活动性,《教程》力图要纠正这种局面,将文学理解为一种“活动的过程”。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将文学理解为“活动”,是《教程》对传统文学原理阐释的重大突破。既如是,“活动论”就应该逻辑地贯穿文学原理阐释的各个章节。但是,《教程》只是在导论和本质论中抽象地讲了一番文学作为活动的重要性,在具体的章节展开中并没有体现文学一旦被理解为活动,与传统文学原理阐释究竟有多少具体内容的差异。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将文学理解为一种活动,究竟有多大意义。就本质论与创作论的关系而言,既然本质论强调文学是一种活动,那么创作论就应该与本质论相呼应,强调文学创作是文学整体活动中的一个活动环节,并且对文学整体活动的实现具有相应的地位和作用。可是《教程》似乎也遗忘了这种逻辑关系,换了一个角度,大谈文学创作的所谓生产属性,使人感觉创作论与本质论之间明显脱节。
《教程》之所以引用“活动”的概念来诠释文学本质,是受到马克思提出“人的活动”一语启发。笔者曾撰文指出,《教程》主要是从文学是多因素多环节的动态性行为构成的社会现象来理解“活动”的,与马克思强调人的能动性的原意并不贴切。换言之,《教程》是在误读马克思的背景下将“活动论”引入文学本质论阐释的,这就意味某种理论建构的先天不足。退一步说,即使我们不考虑《教程》是否误读了马克思,即使我们承认将文学理解为一种动态性的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人类活动是成立的,同样可以发现,《教程》其实也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如果把文学看作一种动态性的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人类活动,就意味着在学理上应该突出文学的活动性,并且将这种活动性贯彻到文学原理阐释的诸环节。具体言之,如果将文学视为一种活动,在学理逻辑上至少就要回答:第一、文学活动和非文学活动的本质区别何在;第二,在文学的整体活动体系中究竟有哪些主要的活动环节或要素,每个文学环节或要素都具有哪些特殊的活动性,在文学的整体活动中有怎样的地位和功能。第三、文学作为诸多环节和要素构成的动态活动系统,诸环节或要素是怎样相互作用从而实现文学整体活动的。总之,我们要围绕活动及活动的关联性展开文学原理阐释。任何学理体系,一旦出现基本考察视角的差异,其学理体系就会出现系统性的变化,比如对人的考察,从社会学角度和从生物学角度得出的有关人的学理知识体系是大相径庭的,但是《教程》使用“活动”的视角来考察文学,与传统文学原理体系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因而在学理逻辑上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再进一步说,如果把文学看作一种活动,那么,在创作论的阐述中,我们就应该强调:文学创作是文学活动这个动态系统中的一个活动环节,通过文学创作产生文学作品从而使文学创作活动与文学接受活动有了衔接点,使文学活动的整体链条得以延续下去,最终实现整个文学活动。显然,《教程》并没有意识到要围绕着活动及活动的关联性展开文学原理的阐释,在创作论的阐释中也就没有强调文学创作在整个文学活动链条中的地位和作用。《教程》在创作论的导言中如是写道:“在上一编中,我们已经指出,文学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是上层建筑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而从社会生产活动的角度看,文学又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文学创造实质上就是文学生产。”[1]95请注意,《教程》把文学创作看着生产活动时用了一个转折性的表述——“而从社会生产活动的角度看”,这表明,《教程》并不认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与文学是一种生产方式是同一个逻辑视角的考察结论,这就把本质论的考察与创作论的考察割裂开了。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在活动论的视角里统一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与文学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结论。即我们可以把文学的本质表述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活动,而把文学创作活动看作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实现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的活动特性就在于它是一种生产性的活动。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实现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本质的一个重要的具有生产性的活动环节。这样本质论与创作论就在活动论的学理逻辑上实现了统一。
意味深长的是,《教程》把文学的本质看作一种活动和把文学创作看作一种生产,都是从马克思的有关表述中吸取的灵感。这大概是想突出教程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这种苦心当然可以理解,问题是在把马克思有关论述引入文学理论时,不能生搬硬套,应该经过必要的文艺学转化。我们知道,马克思有关活动论的表述并不是针对文学而言,他提出有关精神生产的论述也不是直接针对文学创作,而且活动论与精神生产论也不是在同一个论域里提出的,这更加意味着,我们把马克思的在不同论说场合里提出的观点引入一个统一的文学理论体系时不能直接照搬,否则就会出现逻辑不统一的尴尬。《教程》的情况正是如此。在考察文学本质时,编写者孤立地引入了马克思的活动论,在考察创作论时又孤立的引入了精神生产论,忽略了两者之间如何统一的问题。可见,在借鉴他人或他领域理论成果丰富文学原理体系的时候,尤其是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原理体系,我们不能生搬硬套,一定要充分消化,才能与文学原理体系达到逻辑的统一。
二、将文学创作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是否确当
《教程》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方式,还声称这是马克思的观点。《教程》写道:“在文学艺术作品也成为一种可消费的商品的今天,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的观念就尤其显示出了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19可见,《教程》是从经济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所说“艺术生产”概念的,在《教程》看来,将文学创作看做一种可用于消费的、可带来商业利润的商品生产行为,马克思在价值态度上是肯定的。
细读马克思原典不难发现,马克思特别强调“生产生活也就是类的生活,也就是创造生命的生活”[2]50可见马克思在使用“生产”一词时强调的不是生产的经济属性,而是能动地“创造生命”的人类特性,亦即所有体现了人类生命创造力的生活形态都可归结为“生产”范畴。这样一来,马克思说的“艺术生产”,也就是指艺术是一种以艺术方式体现了生命创造力的人类行为。正如帕拉威尔所说:“文学艺术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巴黎手稿的领域。首先,它们作为一种‘人的族类行为’出现。”[3]99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等著述中,曾大篇幅地讨论过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在一般情况下,马克思总是把艺术家归入非生产劳动者的行列,即使艺术家通过艺术活动为自己获得报酬,他也不认为这是生产劳动,只是当艺术家被雇佣,其艺术作品被当作商品出售为雇佣者获取利润时,马克思才认为艺术创作属于生产劳动。马克思说:“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4]432马克思还说:“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3]63可见,第一,马克思特别警惕将艺术创作当作一般的生产劳动行为,尤其不把艺术创作行为看作是获取利润的商品生产方式;第二,即使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文学创作的商品化生产现象,马克思在价值立场上也并不认同作为商品生产的艺术创作,并视为艺术的异化。所以柏拉威尔说,马克思“第一次试图把诗人的工作视为一种非异化的活动——当然没有摆脱商业的压力,但摆脱了商业价值的从属性。”[3]63而《教程》的编写者恰恰认为,文学创作的生产性包含了文学创作具有商品生产性质,即文学创作可以是一种获取经济利润的商品生产行为,并对商品生产性质的文学创作报以价值认同。《教程》的这种认识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读。
此外,《教程》将文学创作理解为可用于消费的、可带来商业利润的商品生产行为,意味着承认文学的牟利性,意味着文学创作要考虑市场需求,要考虑投入和回报如何更有效益。但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文学杰作的创作都是作者自由意志的表达,都是作者情怀的充分宣泄,在创作中作者只是忠于自己对生命的真切感悟,并不考虑付出和回报是否协调,也不刻意考虑读者需要什么以及是否广泛传播,更没有牟利的诉求,即马克思所说的“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比如,“诗三百”、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乃至毛泽东的诗词,都没有通常理解的“生产”概念所具有的经济诉求属性,尤其没有商品生产的牟利属性——至于后人将这些作品出售牟利则与创作者无关。这显然是用经济属性的生产概念无法概括的。这就意味,如果把文学创作看作一种生产方式,很容易与经济意义上的生产交缠不清,造成不必要的理论含混,也无法解释许多“作品就是目的”的创作现象。文学原理层面的创作论阐释,应该涵盖所有文学创作现象,仅仅涵盖商品生产的文学创作现象显然是片面的。由此我们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马克思那么认真地分析艺术创作在什么条件下才属于生产劳动,就因为马克思看到了,艺术创作与一般生产劳动的性质有很大差异,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生产行为。
《教程》似乎也意识到文学创作与一般的经济生产有很大区别,因此,又借助马克思有关“精神生产”的提法,将文学创作归结为“精神生产”,以求与“物质生产”即物质产品或商品的生产相区别。《教程》认为,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精神生产是观念地创造对象世界的生产,第二,精神生产是以符号为手段创造观念世界的符号活动,第三,精神生产是富于个性的自由创造活动。可是,这三点并没有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不难发现,《教程》说的第一点是指精神生产的产品特点,马克思说过,生产什么样的产品,这根本与生产的本质无关。如果以产品的特殊性区别生产,那么生产的类别可以无穷尽,显然不得要领。第二点是强调精神生产的手段特殊性,还是不得要领,因为生产的手段同样是无穷尽的,试问,工人和农民的生产手段不同却并不影响他们的生产行为同是物质生产,何以艺术家的生产手段不同就不是物质生产了呢?再说,以符号为手段并非精神生产独有,符号是全人类的活动普遍依据的手段。第三,说精神生产富有个性创造也不确切,其实物质生产同样可以是富有个性创造的人类活动,如服装商品的生产、工艺商品的生产等等。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原则是不同的。笔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原则不同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两种生产的目的不同。精神生产的目的是充分张扬人的精神诉求,实现人的精神超越,而物质生产的目的则在于物质财富的增长。正如有学者说:“真正的艺术生产即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生产,它是以人本身的发展、个性的充实和自我实现为目的,其本质特征是生产审美价值,而非商品价值。”[5]第二,支配两种生产的规律不同。对于艺术生产来说就是审美创造的规律,如能动反映生活的规律,形象思维的规律,情感想象的规律等等,而支配物质生产的规律则是经济规律,如等价交换规律、供求平衡规律、效益和效率的规律等等。可见,《教程》在文学创作论的阐释中,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辨析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本质差异,因而也没有确当地揭示文学创作不同于一般物质生产的特殊性。
再从学理逻辑看,如果我们把文学创作理解为生产,就应该在生产的角度探讨文学创作所具有的生产性的创作规律。具体言之,至少就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文学生产与社会的消费需要之间的关系;文学生产的生产要素或生产关系;文学生产的生产流程;文学生产的社会组织机制;文学生产的生产规律或方法,文学生产投入与效益之间的考量;等等。可是,《教程》,这方面的探讨又严重缺席。只是抛出一个概念就完事了。这就不能不使人揣测,编写者更多是满足于提出某种新说法,对实质性的理论耕耘并不用心。
三、怎样对创作论进行学理创新
较之传统教材,《教程》的创作论阐释提出了较多的新说法、新概念包括新体例,如增加了有关创作特性的阐释,即把创作视为精神生产。此外,把作家论并入到有关精神生产论的一章中作为一节来阐释,并且换了一种说法,叫“文学创造的主客体”。还将创作心理论的内容融入到创作过程论的内容中阐释,等等。表面看有不少创新,但是在推进我们对文学的认识方面,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把简单明朗的问题复杂化、含混化了。
比如在创作论中,传统教材大都用“文学创作与作家”之类的标题阐释作家的地位与作用,《教程》却用“文学创造的主客体”为标题来阐释有关内容,经过一番繁琐的思辨分析和引经据典之后得出结论,文学反映的客体对象是整体性的社会生活,是具有审美价值的社会生活,是作家体验过的生活;而文学创造的主体是存在于艺术生产活动中的艺术生产者,是美的体验者、评价者和创造者,是具体的社会人,等等,既复杂又累赘。其实,像传统教材那样,简洁地说文学作品反映的是社会生活,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是作家,再适当地发挥一下作为文学反映的社会生活有哪些特点,作为文学作品创作者的作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就明快得多。
由于热衷于引入新说法,就要进行相应的解释和辩护,这都使《教程》增加了不少一般文学原理不必要的论说。比如《教程》把文学创作者理解为生产者,于是又面临与一般生产劳动者的区别问题,特别要辨析作家独立写作与作家被雇佣写作的区别。《教程》编写者是这样辨析的:“在社会主义时代,艺术创造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资本,艺术家、作家、诗人和工人、农民都是国家的主人不是雇佣劳动者,他们的职责是努力为人民提供真善美统一的精神产品,因而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创造的主体。”[1]114这段辩护显然是由于编写者把作家视为生产者引起的,如果不辩析就可能使文学创作活动混同与一般物质生产活动。可是辩析又引出了新的质疑。我们且不说编写者暗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雇佣劳动者的说法是否成立,只需质问: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不是雇佣劳动者,因而是真正的艺术创造的主体,那么在有雇佣劳动的非社会主义时代的艺术创作岂不等于没有艺术创造的主体了吗?这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况且,迄今为止,我们都不敢说所谓有真正创造主体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成就超过了有雇佣劳动的非社会主义时代,那么,有无“真正的艺术创造的主体”又有何意义?牵强的辩护,反而使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自找难堪。其实,只要有文学作品存在就有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存在,这与时代无关。
再说开去,《教程》把作家论变成主客体关系的辨析,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创作论对作家阐释的要求。我们知道,创作论之所以讨论作家,是因为作家是创作活动中的中心环节,没有作家,所有的创作环节都无法勾连成立,而且,作家的素养很大程度决定创作的成败。创作论之所以讨论作家,就是要揭示作家这个创作环节对整个创作活动的作用,要使人们明白,要进行成功的创作,作家应该具有哪些素质条件,而《教程》恰恰忽略这方面内容的阐释,进行一些与创作成败无关的作家属性阐述,我们不禁要问,作家是模仿者、是创造者,是集体人,是生产者,是美的体验者、评价者等等究竟对创作的成败有何关系?按照《教程》的观点,只要你是作家,你就自动具有这些属性。但问题是,并不是具有这些所有作家都具有的属性就能够进行成功的创作,创作论对作家的探讨恰恰是要问,同样是作家,为什么有的作家成功,有的作家不成功?换言之,是要揭示最能够保证创作成功的作家应该具有哪些条件,对此,《教程》恰恰语焉不详。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很滑稽的局面: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大说特说。
诸此种种都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该怎样创新?轻率地标新立异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创作论就是要揭示创作的基本规律,具体包括创作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创作的基本环节是什么,创作的一般心理表现是什么,创作的一般方法是什么?在我看来,创作的本质特征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艺术的基本环节就是从生活(素材)到作家再到作品;创作的基本心理表现就是创作的心理积淀、创作的动机萌发、创作的构思表现;创作的基本方法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主要形态。其实,这些问题传统教材大都做出了框架性的揭示,这是上千年来创作实践的总结,文学创作就是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的创作论也只是如何进一步深化认识的这些问题,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完善,而不是颠覆这些基本的问题另辟蹊径或者用一些新说法、新概念、新体例来重新包装。我们不能为了创新而无视前人已经做出的正确总结,就像我们不能为了创新硬说太阳是从西边升起一样,创新的最终检验就在于相应的文学实践是否产生了超越性的进步。只是满足于的推出新说法,满足于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概念、方法来重复阐释老问题,却没有实质性的学理建树,文学实践并没有因此而明显进步,这不叫创新,只能叫智慧游戏或者叫学术经营。新时期以来,我们的确提出了许多不同与传统文学理论的新阐释,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到底因此而有多大飞跃呢?或者说,文学创作实践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些创新呢?这实在令人深思。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帕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0.
[4]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李英.金钱崇拜与艺术生产[J].哲学研究,1995,(5).
I02
A
1000-5072(2011)04-0078-05
2010-04-09
罗 宏(1954—),男,湖南长沙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