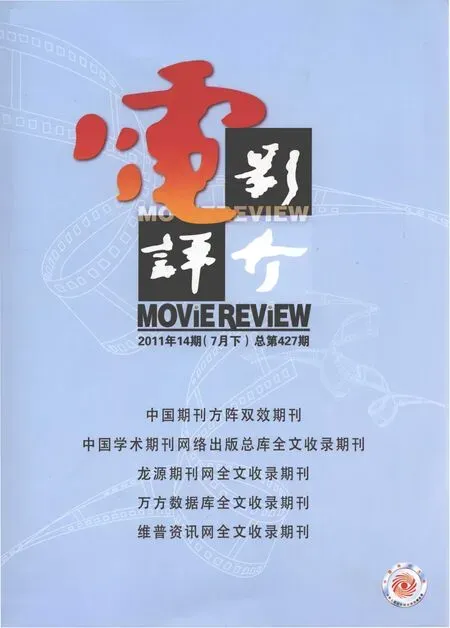打破读者期待视野:论余华小说的颠覆性
余华小说以其先锋姿态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使其成为先锋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先锋作家走上文坛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他们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西方后现代主理论家有雅克•德里达、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等人,他们的理论承接现代主义的反传统,又同趋于解构、拼贴。先锋小说作家们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开始怀疑一切既有的价值、观念,反对权威,反对精英文化,甚至唾弃人类曾经有过的一切崇高信仰。在文学上,他们放弃追求超越精神,极力瓦解文本的深度模式,阻隔文本与生活的联系,拉开能指与所指的距离,努力将旨在表现深度意义的“创作”变成私人性的仅仅作为短暂的词语欢乐的“写作”,他们制造语言的迷宫,布置叙事圈套,力图让文本成为仅仅指向自身的语言游戏。[1](P402)同时我国的评论家也开始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来评论文学作品,这些理论家有郑敏、孟悦、李以建等。[2]
余华的小说往往打破读者的期待视野,不是按照固有的小说模式来设置情节。余华小说具有先锋性质,对传统小说模式起到了解构、颠覆的作用。
一、对古典爱情小说模式的解构
传统爱情小说有着大团圆结局的模式。虽然历经了磨难,但主人公最终达到了目的,改变了状况,人物实现了愿望。因此理论家认为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没有真正的悲剧。古典爱情的叙事模式被概括为“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可归入这种模式。《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虽有悲剧因素,但却有另一种理想化的团圆结局。在灰暗的现实生活面前人们在故事里实现美好的愿望,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造就的欣赏习惯。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温柔敦厚”的美德,劳动人民也盼望着经历过种种苦难后有一个美好的结果,这是一种无可厚非的精神指向。这种情感促成了我国古典爱情小说故事的叙事模式,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爱情小说形式的多样化探索。
余华的《古典爱情》对我国传统的爱情故事进行了解构。小说的情境、人物似乎就是传统小说中的情境和人物,书生柳生和豪门小姐产生感情,小姐惠嘱咐柳生“不管榜上有无功名,还请早去早回”,可是等柳生落榜归来时,眼前出现的却是废墟和破败景象,物是人非,往日与小姐的相遇似乎在梦里。这样的情节安排已偏离了传统爱情小说的模式。柳生找到了府邸的管家,有一线希望可找到小姐惠,但管家已经发疯,只会说一句话:“昔日的荣华富贵啊。”找小姐惠的事情又遇阻隔。柳生再度赴京赶考,在路边酒店意外地遇到了已经成为菜人的小姐惠,而惠的一条腿已被卖出去,被割得破碎不堪,柳生用往日小姐惠所赠银两赎回惠的腿。柳生为了让小姐惠解脱痛苦而刺死了她。神情恍惚的柳生抱起小姐惠走出屠屋,走上黄色大道,而身后的背景是正在兴致勃勃啃吃小姐腿肉的商人。[3]
小姐惠的死无法使《古典爱情》象传统故事那样收场。但为他人看守坟场多年的柳生第三次落榜后,已经看透了世间的功名利禄,他决定为小姐守坟。这时小说已经进入魔幻的境地。他诚心地为小姐守坟时,小姐惠奇迹般地出现在柳生的小屋里,两人执手相看,泪眼朦胧,惺惺相惜。共处一夜之后,小姐又无影无踪,柳生深感奇怪,他挖开了小姐的坟墓,却见小姐的尸首如刚死一般鲜活。第二夜,小姐惠再次来临,却神色悲戚,她对柳生说:“小女本来生还,只因被公子发现,此事不成了。”随即,垂泪而别。读到这里读者会连连惋惜。这又与《聊斋故事》中的鬼怪故事拉开了差距。情节设置为又一波的悲剧。余华的《古典爱情》脱离了传统爱情小说的模式,打破了大团圆的结局模式,解构了传统的情节的设置套路,用古典爱情的外衣包裹了一场无法实现的真情。
二、对武侠小说的解构
中国的武侠小说以“爱恨情仇”为表现内容,或以比武争天下第一而争斗,或以获得某种武林秘籍而争斗,其中穿插爱情故事。当代武侠小说以金庸的最受欢迎。武打的动作名称如“九阴白骨爪”、“梅花点穴手”、“降龙十八掌”等,听来读来都让人感觉武功的魅力。武侠小说武力的神奇高超,幻想的时空,叙述的方式,语言的独特,都自成一体,有别于非武侠小说。其中的人物杀人似乎可以不偿命,没有法律意识,人物可以随着情感的波动任意行为,暗器、中毒、解毒等物品和事件频繁出现。
侠以个人力量“扶弱抑强”,侠者疏财轻生,有着儒家君子的风范。匡扶自己所认可的正义,捍卫自己所崇尚的价值,因为不是在改变和建重新的社会制度的框架里,侠者的行为往往对坏事的抗击如以卵击石,大多数情况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因此而成为令人同情和怜悯的悲剧英雄。尽管侠者的忠义善良让人景仰,但他们却难以承担社会责任。法治社会不是凭借个人义气来维持秩序的,而是以靠德治和法治并用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的。
余华的《鲜血梅花》解构了传统武侠小说的模式。阮海阔在母亲临死前交待了他要找青云道长和白雨潇清,向他们问明谁杀了他的父亲,为父报仇,他遵循母亲的遗愿,佩带父亲留给他的梅花剑,出门去找此二人。他碰到了他要找的人,却并不认识,因为他心地善良,不相干的人要他捎带打听别人的下落,他都帮助他们打听。胭脂女打听刘天,黑针大侠打听李东,阮海阔把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最后他才找到白雨潇,而白雨潇告诉他刘天和李东就是他的杀父仇人。作为一个复仇者,阮海阔似乎对几十年前曾经有过的仇杀不是很在意,复仇的意愿不是很强烈,对复仇这件事感到虚无,态度不坚定,没有发自内心的动力和热心。阮海阔象幽灵一样游走于江湖,对江湖的人事不知道不熟悉,他带着一把生锈的剑,装扮为江湖人士,而江湖是外在的,是离他的心很远的东西。“没有半点武艺的阮海阔,肩背名扬天下的梅花剑,去寻找十五年前的杀父仇人。”他很守信,请他顺便打听消息的人并没有给他什么好处,而他一旦有了消息,便专门回去告诉他们,对于杀父仇人,他没有感到十分的仇恨。但他要背负家庭复仇的责任,不管他愿不愿意,不管他有没有能力。小说的结尾是他终于打听到了他的两个杀父仇人已经死了。他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他仍旧在江湖里游荡,漫无目的。
《鲜血梅花》这篇仿武侠小说,通篇语言流畅,虚幻奇丽,看似武侠小说,实则非武侠小说,有仇杀事件,但没有刻骨的仇恨,阮海阔在寻找仇人,但是中间出现插入情节,遇见的人要他帮忙打听别人的下落,一个主干事件,加上几个旁枝事件,然后交织,结尾。小说中没有传统小说的打杀场面,寻找仇人是引领读者的主线,故事却没有传统故事的套路,传统复仇故事结尾往往是复仇者终于报仇雪恨了,而《鲜血梅花》的结局是阮海阔打听到了仇人,而仇人已经死了,与读者预感的阮海阔因为自身体弱可能不能杀死仇人的结局有了差异。余华的这篇小说对传统武侠小说的惯有模式进行了解构。
三、对地主形象的解构
解放区文学、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其中占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往往把地主的形象刻画为冷酷的、自私的、好色的、无人性的全恶型形象。《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是其中的代表。这类人强抢民女,作恶多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地主钱文贵、李子俊,《红旗谱》中的冯兰池等,他们是社会中的落后分子,逆历史潮流而行,心狠手辣,欺侮民众,横行霸道,惨绝人寰。这些人依仗家中有钱,放高利贷,搜刮百姓,蛮横残忍。影视作品中也常常展现他们的丑恶嘴脸,阴险、多疑、狠毒成为这类形象的主要性格特征。
而余华的《一个地主的死》,塑造了一个爱国的地主形象王香火,他有意把日本鬼子引入绝境,自己也惨遭屠杀。余华这种写法,打破了以阶级划分的方式来分别刻画各阶级人物形象的创作局限。这个地主是一个有谋略的爱国者,他没有成为汉奸,没有卖国求荣,他准备着自己赔上一条性命,给日本人当向导,把日本鬼子引入茫茫森林中,夜幕就要降临,而目的地并没有到,晚上温度降下来,全部人员会被冻死,等到日本军人明白他们的末日来临时,他们用刺刀刺死了他,他们则唱着日语歌,无奈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小说的结尾没有落入传统小说的俗套。这个地主形象与以往的地主形象不同,表现出了爱国的一面。
四、对英雄模式的解构
余华作品呈现出反英雄的倾向。他的小说人物几乎没有英雄形象。在创作的不同阶段,他笔下的人物,性格有变化。早期人物性格往往是变态的、冷酷的、仇恨的,而后期人物性格转变为常人的性格。
传统作品中常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梁山式好汉,或忠义豪侠的君子式的人物。在余华的作品中几乎没有这样的形象。《一个地主的死》中王香火可以说是爱国人士,但他是非战死沙场的英雄,他故意给打进来的日本军队带错路,置日本军队于死地,他不是一个正式的军人,所以他不是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式的英雄,也不是把人民救出水深火热之地的英雄。《兄弟》中的李光头虽然让福利厂的残疾人有了很好的收入,但是他的精神只是朴素的精神,他不嫌弃任何人,他并没有英雄意识,更不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语。相反他是一个小人物,小到拾破烂,小到可怜而不自知,让人看着酸楚、痛惜。他没有力挽狂澜的力量,没有茅盾笔下工业巨子的经济能力,也没有当代工业小说的英雄硬汉性格,偶然的机会他发财了,他充其量是个有些波折的小人物。《许三关卖血记》中的许三关也是小人物,他没有文化,靠卖血渡过难关,他能做的是给家里人带来些温暖,而他自己也有生气、嫉妒的时候,与英雄也不沾边。这些人物在余华的作品中已经算是正常人了,他们都不是英雄,那么那些变态的人物就更不是英雄人物了。
《活着》中的福贵,人们只赞赏他老年后的豁达、洞明,而对他早年的荒唐、荒淫却忘而不提。他的荒唐行为引起家里人、老丈人的气愤、难过,在他荒唐胡作非为的日子里,他的亲人们度日如年。实际上,他的行为让父母、妻子、岳父母遭受到了多大的痛苦!妻子家珍怀孕挺着大肚子来叫他回家,而他却为不失男人的面子而打了她,小说和电视都没有把家珍此时的痛苦心理突出表现出来,这也与作家本人是男性作家有关。这样的情节设置,读者更多注意的是荒诞,而忽视了福贵早年的荒唐无耻。在他作恶时,他身边的人是在一分一秒地忍受着活着的苦难,他们的痛苦是他给带来的,他把他的父亲气死,母亲气病,妻子为他怀着孩子却被冷落。这些坏事,不能因为他老年遭受苦难命运而淡忘不提。年轻的福贵就是一个恶棍。老年的福贵只是很无奈地生活着,也不是英雄。
《现实一种》中的人物更是非英雄,他们在复仇中忘记了一切,一家人自相残杀,皮皮这个小孩成为原罪的推动者。《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我”似乎想要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但是在荒诞的现实中,“我”的力量太弱小,在强大的对力面的逼迫下,“我”失望、无奈、悲哀。“我”感到了世界的无序可循,惊讶成人的世界里没有逻辑可循。《河边的错误》中一个疯子连续杀人,正义的警察马哲为除后患而打死了他,而马哲本人却要装疯,否则他就要担负法律责任,等待马哲的将是进入疯人院。他也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但在现实面前他很无奈。《死亡叙述》中司机撞死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但他逃跑了,没有报案,十几年后他又撞死了一个女孩,这次他良心发现,去负责,他却遭到谴责,他被人砍死了。《世事如烟》中变态的算命先生竟害死了儿子,糟蹋处女来续自己的阳寿。这些人都不正常。
余华笔下的“疯子”与鲁迅笔下的“疯子”相去甚远。虽然在创作后期他笔下的人物开始正常,但他们也不是英雄。余华小说的人物形象颠覆了十七文学中的英雄形象。
余华小说的先锋性很明显,从多方面对传统小说进行了解构和颠覆,同时又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1]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李凤玲.解构视野下的《现实一种》[J].作家杂志,2008(12).
[3]刘伟.《古典爱情》对古典爱情的解构[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