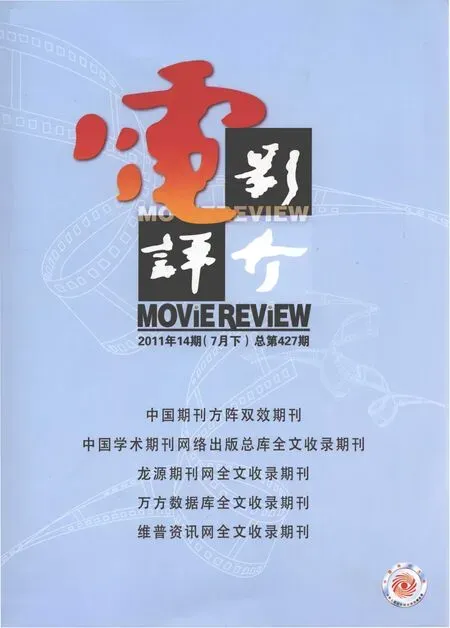艺术片与底层叙事:以《三峡好人》为例
近年来,一种在风格、叙事策略上标新立异的电影逐渐走进了观众的视野,这类影片通过其独特的声音、色彩、音乐、背景等符号和不同于传统叙事方式的碎片式的记录来刻画人物和揭示主题,将镜头聚焦在底层平民身上,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影射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本文以贾樟柯的影片《三峡好人》为例,分析艺术片的美学特征和底层叙事的深层内涵。
一、《三峡好人》:纪实手法下的平民世界
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这部影片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是来自山西汾阳的普通煤矿工人韩三明来到奉节寻找十六年未见的前妻和女儿,另一条线索是女护士沈红从太原来到奉节寻找两年在外工作的丈夫郭斌。
影片以两个寻人的故事展开。矿工韩三明十六年前从人贩手中买来了麻幺妹当妻子,不久麻幺妹被公安解救,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回到了四川老家。十六年后,出于对妻子和女儿的思念,韩三明踏上了寻亲之路。因为三峡工程的建设,前妻的家乡早已被淹没在江底,到处都是施工和拆迁景象。历经曲折后,韩三明找到了麻幺妹的家人,他们的冷漠和躲闪没有打消韩三明寻找妻子的决心,他在奉节暂时住下,和当地淳朴的拆迁工人一起辛勤地劳动,并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经过一番周折,韩三明终于在江边和前妻见面,前妻回来后一直没有安定下来,后来跟随了“船老大”,然而她对“船老大”并没有感情。一番寒暄过后,韩三明决定带前妻回到山西,可是“船老大”要求他必须还清前妻的哥哥欠他的三万元,这对于一个普通矿工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韩三明还是答应替麻幺妹还债,义无反顾地带前妻离开了四川。
另一个故事讲述的是女护士沈红来到奉节,寻找两年因为工作原因没有回家的丈夫郭斌。来到奉节后,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这一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丈夫的公务又十分繁忙,沈红起初一直未能见到丈夫。在和郭斌单位的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沈红无意中得知丈夫和另一个女人关系暧昧,内心十分痛苦。最后,沈红和郭斌终于得以在三峡大坝旁相见,没有太多的言语,一支舞曲过后,沈红向郭斌提出了分手,郭斌默默同意了她的离婚提议,二人就此在江边别过,沈红坐着客轮离开奉节去了上海。
二、艺术片:镜头中的美学符号与碎片式记录
(一)美学符号构建的真实世界
作为一部具有审美意义的影片,《三峡好人》运用了声音、音乐、画面、语言等多种符号,通过多维的符号系统为观众勾勒出了一个无论是从外在还是内核都与现实世界相接近的镜像,将“诗意”与“真实”完美地融为一体,产生了独特的视听感受。
在电影中,很少有静音的场景,噪音贯穿影片的始终。轮船靠岸时的汽笛声、江水翻涌的波涛声、拆迁区施工时榔头敲打石块的声音、闹市中人们的喧嚣叫卖声等等,这些现场同期声的运用从听觉上生动地展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场景,“真切地表现了当下的生存环境和片中主人公的生存状态”[1],尽可能地为观众呈现出一个逼真的世界。这些看似杂乱无章,与叙事主体没有直接关系的“噪音”独立成为一种特殊的声音符号,给人一种毫无粉饰的真实感和亲切感,使影片成为具有真实特征的纪录片式的影片。
除了声音符号外,导演对音乐符号的运用手法也十分独到。影片中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唱的《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小马哥”的手机铃声《上海滩》以及沈红等待与郭斌相见时的背景音乐《潮湿的心》等被人广为流传的歌曲均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贾樟柯没有特意为影片创作插曲,而是选取现有的流行音乐作为电影的音乐符号,通过影片中人物的歌唱而不是声画分离将其表现出来,在电影的语境中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这些歌曲在塑造人物内心世界、表达主题、渲染气氛、营造意境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有学者认为,这些歌曲还具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即“界定时间和再现那个时期的真实场景”。[2]借助小男孩的稚嫩歌声,影片唤起了人们记忆深处熟悉的旋律,将观众的思绪拉到了这些歌曲流行的时间段,给人身临其境之感,使电影世界同现实世界更加接近。贾樟柯发现了音乐符号的这一价值,使电影摆脱了一般影片中庸俗和做作的音乐渲染,将音乐与时代感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为电影符号的运用提供了新的思路,是为一种艺术手法的创新,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在对听觉符号的加以运用的同时,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也展示了一些独特的、具有审美意义的画面。影片开始运用了一组长镜头,画面中是一艘正在缓缓靠岸的客轮,镜头细腻地突显了船上每个人的动作和神情,正在打牌以打发旅途时间的男人、远眺江面目光茫然的中年妇女、闲谈的老人,这些没有经过特意安排的连续的人物特写“使观众获得一种逼近现实生活本身的审美效果”[3]。片中的一个镜头是男主人公韩三明和前妻麻幺妹站在拆了一半的楼房顶上,他们身后残缺斑驳的墙壁和远处高耸的现代化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幅好像是生硬地拼接而成的具有抽象色彩的画面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透过镜头,导演意在诠释画面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时代变迁和现代化所造成的物质与精神的断裂和人们内心的挣扎与抉择。在影片快结束时,当韩三明和一行拆迁工人准备离开奉节前往山西打工时,江面上空出现了一个人走钢丝的惊险画面,具有很强的视觉艺术效果,这幅画面同人物内心相呼应,暗示韩三明一行人踏上的是一条冒险求生之路。电影情节画面穿插巧妙,韵味无穷,令人回味。
语言符号也是影片的一大特色。“语言符号与现实环境的依存关系就像贾樟柯电影的其他符号一样,密不可分,缺一不可[4]”。在影片中,韩三明淳朴的山西口音和当地居民颇具特色的四川口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这与现实生活是那么接近,显得那么真实而不做作,同时凸显了影片的底层视角。
通过对声音、音乐、画面、语言符号的充分运用,贾樟柯为我们构造了一个美学意义上的多维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观众通过对这些符号的解读,感知到了一个具有层次感、立体感、原生态的真实世界,这正是这部影片打动人心之处。可以说,真实感是贾樟柯电影艺术的灵魂,借助这些美学符号,贾樟柯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全景式的真实世界。
(二)碎片式记录下的“逻辑真实”
在《三峡好人》中,除了对符号的运用,在结构展开的方式上,贾樟柯采取了一种碎片式的记录方式来叙述影片,打破了传统影片的叙述思路。以“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为结构特征的传统影片十分强调叙述结构的紧凑性和故事情节的曲折性,一切细节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围绕中心故事展开的。而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打破了这种戏剧化的电影模式,尽可能地淡化情节。尽管影片是以韩三明和沈红二人前往四川寻人为主线的,但在这条主线外,还延伸出了许多与故事无关的情节,如拆迁工人烈日下辛勤劳动的场景、三个穿着戏服的人在桌边玩手机的画面、客轮上的人们围观“白纸变美元”的魔术的情景、小马哥的意外死亡、韩三明几次向房主递烟的情节等等,这些零散的、没有内在因果联系甚至荒诞的画面细节散落在影片各处,以一种“碎片”的形态构建着影片的主体。这些“碎片”虽然平淡,却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在他的凌乱的意象和散文化甚至杂文化和意识流化的电影背后,蕴含着某种深沉的思考和真挚的情感。”[5]或许在贾樟柯看来,生活本没有过多的逻辑可言,它本身就是错落无序的,这些看似多余的细节,恰好与真实世界的逻辑相吻合,“让我们感受到电影不是在‘讲述’底层的故事,而是在‘呈现’底层的生活”。[6]
三、底层叙事:现实主义中的人文关怀与时代思索
如果说真实是《三峡好人》的感人之处,那么底层的叙事角度带给人的则是心灵上的触动与震撼。在这部影片中,贾樟柯将镜头微缩到一个个极其平凡的底层人物身上,通过对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流露出了深沉的人文关怀。
在《三峡好人》中,既没有境界高尚的“高大全”式的人物,也没有取得丰功伟绩的史诗般的英雄人物,只有一个个来自底层如泥土般平凡的生命。影片的男主人公韩三明是一个来自山西的煤矿工人,他家在农村,贫穷和卑微的身份使他只能通过从人贩手中“买”妻子这种非法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后来由于公安的解救,他的婚姻没有持续多久,对妻儿的思念使他踏上了遥远的寻亲之路。韩三明的前妻麻幺妹是一个曾经被拐卖的妇女,她被贩卖给韩三明后不久就离开了丈夫,独自带着女儿回到了家乡,然而回到四川后,她仍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选择跟随船老大仅仅是因为他能“给口饭吃”。他们的女儿十六岁就放弃学业南下打工,自谋生计,而在当地,这样的情形似乎早已司空见惯。影片展现了当地一群没有固定职业的青年人的生活,刻画了性格鲜明的“小马哥”这一形象,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最终却被人打死埋在瓦砾之中,韩三明和几个拆迁工人将他的遗体沉入了滔滔的江水,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就这样结束了。影片运用大量篇幅表现了拆迁工人这一底层群体。在贾樟柯的镜头中,他们是一群朴实善良的劳动者,为了生计,他们在烈日下光着膀子挥舞着双臂辛勤地劳动,却难以摆脱身处底层的物质匮乏和精神困窘。影片最后,为了挣钱,他们选择义无反顾地跟随韩三明去连人身安全都难以保证的山西煤矿挖煤,这样从“拆迁工人”到“煤矿工人”的结局并没能使人感到一丝希望,而是引发了人们更多关于底层群体生活状态的关注与思考。
通过对底层群体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关注,贾樟柯在电影中赋予了底层人民可贵的话语权,一个个场景,一段段对白,均是对底层人民真实生活的再现和内心世界的解读。“边缘化是贾樟柯的写作姿态”,[7]这一姿态使他俯下身来,以一颗虔诚和纯净的心深情地注视着世俗生活中千千万万微小平凡的个体。他像一个心怀慈悲的诗人,忠实地记录着这些行走在边缘上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而这往往是大多数电影最容易忽视的视角。这种“另类”的平民镜像在反映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精英题材影片充斥的今天显得难能可贵。
香港导演李翰祥认为,“艺术应该是一盏灯,照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8]”贾樟柯意识到了电影这盏“灯”不应仅仅照耀上层社会的光鲜生活,更应该照射在每个平凡人的身上,让每一个灵魂都有呐喊的权利,让艺术不再是精英阶层用以排斥其他阶层的冰冷的门槛,而应当是充满着人性关怀的、温暖的、平易近人的真正为平民大众所享的艺术。借助着电影这束“光”,贾樟柯将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放大,以此引发人们的思索,呼唤整个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关注与担忧。更进一步看,贾樟柯在电影中表达的不仅是对底层人民的关怀,还有在物质化的今天对淳朴、自然的人性的回归。
通过描写时代大背景下小人物的人生起落、喜怒哀乐,贾樟柯将人文关怀的精神注入到电影的灵魂当中,表现出了他对底层生命的尊重,期待人们通过电影这一个窗口去透视底层的真实状态,从社会视角和制度层面去探寻这一群体物质与精神匮乏的根源以及改善策略。这或许是贾樟柯电影的终极目的与最高理想。这种底层视角的影片既是对将镜头聚焦在所谓“上流社会”的“大片时代”一种反击。《三峡好人》产生的巨大影响表明,人文关怀是电影的重要思想内涵,只有真正体现对人的关怀与尊敬、“有血有肉”的电影才能产生震慑人心的艺术效果。
在展现底层生态的同时,影片也对三峡移民的时代大背景作出了微观层面的解读。在对三峡工程的展现上,影片没有从宏观入手,通过壮观的库区画面为三峡工程“唱赞歌”,而是通过库区移民的真实生活体验从侧面进行了诠释。影片开头客轮上移民远眺江面的忧伤的神情、拆迁指挥部里拆迁户与工作人员在利益分配上的争执、在废墟和现代化高楼大厦间变得支离破碎的古城,这些都是这项工程带给底层人民实实在在的影响。随着江水的不断上涨,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奉节古城即将沉入江底,移民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搬迁这么简单,还有人际关系的瓦解、生活方式的改变、离开故土的焦虑与惆怅、新旧交替中的茫然与困惑、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抉择与内心的挣扎。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他们像高楼间走钢丝的人,在貌似广阔却实则狭小的空间里小心翼翼地求生。”[9]浩浩荡荡的三峡工程,在影片中被解读成为不断上升的水位线和无休止的拆迁,然而,这些符号构建的看似平静的生活背后却暗藏着移民巨大的内心变化和对世事变迁的慨叹。没有嘶吼,没有哭喊,只有被压抑的内心和淡淡的哀伤,而这种静默却比呐喊更有力量,更引人深思。从底层视角解读三峡工程,贾樟柯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和思考三峡工程带给社会的影响,深刻理解了移民为此项工程所作出的牺牲。贾樟柯并非三峡人,而他却能敏锐地感受到三峡工程给库区移民的人生带来的变化,这都源自他看待世界的平民视角。电影给予了库区移民充足的话语权,通过镜头对这一群体的内心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这再次体现了贾樟柯电影中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时代意识。
四、平民镜像:“大片时代”的另一种精神探寻
以《英雄》、《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的出现为标志,近年来,中国电影逐渐进入了一个“大片时代”,在可观的票房收入和商业利润的驱使下,中国电影市场上涌现出了诸多“大片”,竞争可谓愈演愈烈。以追求视觉效果和故事情节戏剧化为主要特征的“大片”将娱乐化、大众化放在了首要位置,强大的明星阵容和宏大的叙述场面很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博得大众的青睐,再加之“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等长期积累的“象征资本”[10]和铺天盖地的放映宣传,“大片”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
然而,在获得高额票房的同时,这些“大片”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与批评。对画面情节的过分追求使“大片”成为了外表华丽而内心空洞的哗众取宠之物,这是商业化席卷电影行业产生的必然结果与代价。以《雷雨》为创作原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不仅削弱了原剧的现实意义与各种层次的矛盾,”“而且其中每个人物都是扁平的”。[11]这些影片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一个贯穿整个影片的核心价值观,无论是情节安排还是人物刻画,都缺乏内涵和深度,仅仅在视听方面追求单纯的审美效果,却全然忽视了电影在传达人性、启迪人生、开发心智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一缺陷是导致我国的“大片”在国际影坛影响力微乎其微的重要原因。
与“大片”侧重于视觉和听觉感官上的满足不同,以《三峡好人》等为代表的底层叙事影片更重视观众精神上的满足。它打破了“大片”的常规思维和叙事手法,引发了文艺界的一种新思潮,那就是关注底层,在电影中反映民生疾苦,体现人文关怀。在镜头视角转移的过程中,这些影片逐渐形成了与“大片”叙事风格迥异的独特底层叙事方式,并在美学上有了一定的突破与创新,这是对“大片”垄断现状的一种挑战。与“大片”提供“视听盛宴”的出发点不同,底层叙事的影片意在为观众呈现的不仅是艺术符号构建的影像世界,还有让人内心为之震颤的“心灵盛宴”。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新生代导演肩负起了中国电影转型过程中电影媒介文化内核的转向与重构的任务,我们相信,以底层视角和人文关怀为核心精神的影片定会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而打动越来越多的观众,产生更广泛的思想上的共鸣。
[1][3]张彦,刘素玉,李娟.贾樟柯电影的纪实风格研究[J].青年记者, 2010, 11: 49-50.
[2][4]卢兆旭.贾樟柯电影中的音乐符号、背景符号和语言符号[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2月,第26卷,第2期.
[5]李永东.底层镜像的诗意呈现——解读贾樟柯的《三峡好人》[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4期,第21卷.
[6][7]周爱华.贾樟柯电影的叙事策略与美学内涵[J].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年4月,第7卷第2期.
[8]陆绍阳.中国当代电影史1977年以来[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32.
[9]温长青.《三峡好人》:真诚质朴的人文情怀的自然袒露[J].电影评介, 2007, 8:32,35.
[10][11]李云雷.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底层叙事[J].艺术评论, 2008, 3: 4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