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香港居地及安葬地考辨
林幸谦 郭淑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的生平十分独特。她的一生短暂而漂泊,却创造出惊人的文学成就。她的悲剧命运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20世纪中国女性独立于社会的艰难处境,也印证了20世纪抗日战争大背景中个人与家国命运的唇齿相依。萧红逝世距今已68年,但其作品及生平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国内外许多萧红研究者和萧红文学迷,不断地寻访萧红故地,以探究她不寻常的生命轨迹。香港作为萧红人生最后的驿站,她的居地和安葬地无疑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40年代至21世纪,跨越了两个世纪长达70年,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治三年零八个月、战后经济起飞、移民潮涌等世事变迁,萧红香港居地和安葬地是否保存下来,以见证萧红多舛而又光彩照人的最后瞬间?本文就历史文献、知情人讲述、实地考察和探访等佐证材料,做一辨析。
一 萧红的文学足迹
1932年,21岁的萧红在哈尔滨登上文坛,22岁与萧军合集出版了《跋涉》,收入萧红《王阿嫂的死》等五个短篇小说。1934年6月,因《跋涉》的出版引起日本宪兵怀疑,逃往青岛。在青岛,萧红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并寄给鲁迅先生。1935年12月,《生死场》由鲁迅先生作序、胡风作“读后记”在上海以“奴隶丛书”出版,萧红遂成为中国文坛继冰心、丁玲后备受瞩目的女作家。在上海,她也出版了著名的散文集《商市街》。1936年7月,萧红与萧军情感出现裂痕,独自前往日本留学,发表了小说《家族以外的人》。10月,得知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寄给萧军信,以《海外的悲悼》为题发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萧红与上海文化人前往武汉。1938年,萧红、萧军、聂绀弩、艾青、端木蕻良、田间等作家前往山西临汾,与率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丁玲在西安相遇。在西安,萧红与萧军分手,随后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在胡风主持的《七月》杂志座谈会上,萧红在“抗战文艺”声中独树一帜,提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1938年9月,萧红抵达重庆。1939年春,在江津白朗家生子夭折,身体陷入极度虚弱。在重庆黄桷树镇居住期间,她曾以口述、整理的方式完成了《回忆鲁迅先生》。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乘机飞赴香港。在香港,身体病弱的萧红除参加纪念鲁迅的活动及其他几次活动外,全部精力用于创作,收获了两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三个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后花园》、《北中国》及一个口述故事《红玻璃的故事》,创作了默剧《民族魂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于日寇铁蹄。1942年1月22日,战乱中,萧红病逝于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红十字救护站。
二 香港与内地的文化关系
香港地理位置在中国南端,位于珠江口东,原为隶属于广东省的东南岛屿之一,又名香岛、香海、香江。清邹代钧《西征纪程》中记载:“香港,本广州府新安县南海中岛。”①陈谦:《香港旧事见闻录》,香港中原出版社,1987年,第3页。1842年,国势渐衰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港岛给大英帝国。1896年,英帝国又凭借《北京条约》强租九龙。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继续拓展地盘,借用新界,香港的范围从此大致确定下来。19世纪末,香港被英国人称作“英国皇冠上的明珠”,引起诸多爱国人士的愤慨。1925年,痛感国势衰败、立志图强的闻一多创作了著名的《七子之歌》,将香港称为“守夜的黄豹”,“身分虽微,地位险要”,将九龙喻做“下嫁的”“幼女”,身受磨难,每天都在“泪涛汹涌”。香港、九龙从此作为“被掳走的孩子”成为中国进步文化人心中的隐痛。
在大英帝国殖民统治下偏安一隅的香港,由于华人往来自由,与内地文化的关系并未中断。1927年2月,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应邀到香港讲演《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1935年9月,许地山就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教授;1937年冬天,蔡元培举家迁往香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许多内地文化人意识到香港的言论自由空间相对于内地要大得多,而且出版物注册手续相对简便,由具有社会地位的名人担保,缴交两三千元按金即可。因此,南来香港办报和书刊的内地文化人日渐增多,吸引了许多内地作家、艺术家投稿。1938年,“雨巷诗人”戴望舒携妻子女儿到香港,主持《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曾向居于重庆的萧红、端木蕻良邀稿。1939年,《星座》副刊发表了萧红的小说《旷野的呼喊》、《花狗》、《梧桐》,散文《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作品;连载了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大江》。萧红1940年来香港之前,已与香港建立了“业务往来”。在内地文化人的主持下,香港中文报刊出版业出现繁荣局面。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及综合期刊文学版的发达,客观上为萧红写作提供了良好环境,也促使她在战乱中选择香港作为栖身之地。
三 萧红到香港落地时间辨析
萧红和端木蕻良到香港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来自端木蕻良的夫人钟耀群所著《端木与萧红》一书,记载萧红到港的时间是1940年1月19日;另一提法是1940年1月17日,由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在《跋涉生死场的女人》一书中提出的。前后相差两天,资料来源均应是端木蕻良。钟耀群书中所记的文字为:
1940年1月18日,端木从萧红那里拿了买飞机票和兑换港币的钱,到袁东衣那里换到港币和两张飞香港的机票,除了告诉几个好友外,就和萧红于19日飞香港了。①钟耀群:《端木与萧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而曹革成记载得较为详细:
1940年1月14日,端木蕻良和萧红去城里,托在中国银行的朋友袁东衣购买去香港的机票。原以为飞机票紧张,至少要等十几天,没想到当天晚上袁东衣就来住处告诉明天有一张,17号有两张,这是给中国银行保留的机动舱位。②曹革成:《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第272~273页。
曹革成还特别引证了端木蕻良写于1941年的《纸篓琐记》,指出:朋友晚上回来告诉他,十五号有一张票,而十七号则有两张。而十五号就是第二天,因为只有一张,因此他并没有走,因为十七日也只差两三天。经过考虑后,端木蕻良还是签字要了两张17日飞往香港的机票。
据当年史料记载,萧红与端木蕻良1940年飞往香港时,机票确实紧张。1938年,中国航空公司由香港飞往重庆的票价为港币320元,每周二、四、六通航。到了1940年,香港至重庆的机票,无论是中国航空公司或欧亚航空公司,都已涨至港币400元。重庆至香港的机票价格也应随之上涨。端木蕻良所言托朋友买票,“原以为飞机票紧张”应是实情。曹文引端木蕻良写于1941年的回忆,距离事情发生时间并不遥远,故而,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较为可靠。
四 萧红香港居地考辨
关于萧红香港居地亦有两种说法,分别是钟耀群和曹革成的记述。首先是钟耀群在《端木与萧红》中披露,刚到香港的萧红和端木蕻良是暂住在纳(诺)士佛台:
在九龙金巴利道纳士佛台,找到一间相当大的楼房,向南,前面直通一个大阳台,空气很好,对萧红的身体大有好处。房主人是一位能说几句普通话的年轻小姐,她的家人都到西沙群岛做买卖去了。室内家俱都是现成的。③钟耀群:《端木与萧红》,第65页。
来港没多久,孙寒冰又建议他们搬到大时代书店:
孙寒冰来港办事,告诉端木大时代书店隔壁的房子已腾出了,也在尖沙嘴金巴利道(Kimberley Road)诺士佛台(Knutsford Terrace),三号门牌。孙寒冰希望他和萧红搬过去住,有利于编辑“大时代丛书”。④同①,第76页。
可见,1940年春天,由于孙寒冰的关系,萧红和端木蕻良搬进了尖沙嘴金巴利道诺士佛台3号二楼不足20平米的房间。萧红房间的对面即是《经济杂志》主编许幸初的办公室。而到1941年2月中,诺士佛台3号因要调整房子,萧红又搬到尖沙嘴乐道(Rock Road)8号时代书店二楼的一间房子里。①钟耀群文中的“时代书店”应为“大时代书局”。
以上是钟耀群的说法。而曹革成对这时期萧红在九龙住所的叙述有所不同,说萧红刚到香港后,“经孙寒冰的事先安排,他们来到了九龙乐道八号二楼,暂时住了在大时代书局里(现九龙凯悦酒店一址)……他们在这儿住了8个月”。②曹革成:《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第274页。然而曹革成又指出,到1941年“2月初,萧红又搬回乐道8号二楼,这回是住在大时代书局的另一侧。这里的房子都是办公室式的房间,一大间有40平米左右,他们共同使用一张大桌”。③同②,第309页。曹革成在文中所述前后矛盾,没有衔接。如果是1月17日入住乐道8号二楼,8个月后应该是9月。2月初又搬回乐道8号二楼,那么,1940年9月至1941年2月之间共计5个月,萧红和端木蕻良住在哪里,则没有交待,可见其中的记述有所遗漏。
在曹革成附录的《萧红年谱》中,更出现了与文中不符的记述。一为萧红和端木蕻良“到香港后住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纳士佛台3号,距大时代书局的地址乐道不远”。④同②,第403页。其二为1941年2月,萧红和端木蕻良“迁居九龙乐道八号二楼,与大时代书局为邻”。⑤同②,第411页。两人皆为端木蕻良的亲属,故而信息来源都为知情人端木蕻良。但在两人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钟耀群的叙述更符合逻辑。曹革成的叙述则出现内文与附录矛盾的情况。况且,附录中所透露的信息与钟耀群大致相同,只是略去了萧红最初曾租住那位“家人都到西沙群岛做买卖去了”的小姐在诺士佛台带大阳台的楼房。据此,萧红到香港的第一个居地应该是她和端木蕻良自己租的诺士佛台大房间。大约两个月后(春天时)由于孙寒冰到港,搬到了诺士佛台3号二楼,显然是孙寒冰从端木蕻良编“大时代丛书”工作便利以及住房经济等方面考虑,给两人提供了方便。
在诺士佛台3号大时代书店隔壁二楼,萧红住了近一年。1941年2月,搬到尖沙嘴乐道8号二楼。因此,萧红居港期间主要居住地有三个,都在九龙尖沙咀。一是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带阳台的楼房大房间,二是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3号二楼,三是九龙尖沙咀乐道8号二楼。
今天的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仍旧存在,但已有很大变化。诺士佛台,也称纳士佛台,均译自英文KNUTSFORD TERRACE。位于香港天文台附近,由于地势较高被称之为“台”。从金巴利道往香港天文台方向走,会有一个涂着黄色墙漆的门洞,标有“诺士佛台”、“私家路”字样。穿过门洞,可以看到对面建筑物上标有诺士佛台1号、2号、3号……其中3号就是萧红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门牌号还在,但楼已重新盖过,有二三十层了。这里位置相对隐蔽,已形成了九龙著名的酒吧区,可与港岛的“兰桂芳”相媲美。3号的一楼是装饰成红色的“野火”酒吧。
尖沙嘴乐道(LOCK ROAD)8号时代书店二楼,现已无存。2000年左右,原址上建有凯悦酒店。2010年,在凯悦酒店的原址上建成了几乎覆盖半条街的“国际广场”。目前的双号门牌号为乐道36—52,旧日痕迹无一留存。
五 萧红生病住过的医院考
1941年7月,受头痛、咳嗽、发烧等症困扰的萧红接受了史沫特莱的建议,去玛丽医院检查身体,却因检查出肺病住进了医院,从此一病不起。
玛丽医院成立于1937年,位于香港薄扶林道,是港府兴建的香港最大的公立医院,占地面积很广。玛丽医院是当时香港一间技术领先、设备一流的西式医院:“院中病房宽大,病床清洁,每房指定护士值班”,“院长由英国人充当,医生多数是香港大学医科毕业学士”,“院中医生处方,多用市面少见的新药”。①陈谦:《香港旧事见闻录》,第238页。从这些记述中可见其优势所在。当时一般需要留医的重病患者才可由西营盘国家医院转入玛丽医院住院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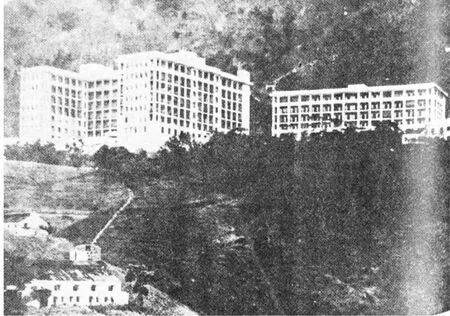
1937年建成的玛丽医院
当年过境到香港的史沫特莱因见日渐消瘦的萧红,很担心她的健康,建议她去玛丽医院检查身体,医疗费可通过香港何鸣华主教得到优惠。但若住院,则远远超出萧红和端木蕻良的经济承受能力。为萧红病况担忧的柳亚子向原东北大学校长、东北救亡总会的周鲸文求助。周鲸文在香港主办《时代批评》、《时代文学》杂志,并开办了时代书店,帮助过萧红等许多东北老乡。周对柳亚子承诺,萧红住院治病费用由他支付,让萧红尽可放心治病。据周鲸文回忆,医院检查出萧红患有肺病,“肺部患处已经钙化,没有什么不得了”,但医院坚持打空气针,把已经钙化的结核放开,以便彻底治疗。②周鲸文:《忆萧红》,见卢玮銮编著《香港文学散步》,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11页。为了能够彻底治好肺病,萧红选择了住院治疗。据当时在时代书店供职的袁大顿回忆,“萧红的病榻是在玛丽医院四楼院的前方走廊上,正面临环围着的半面海”。③袁大顿:《怀萧红——纪念她的六年祭》,见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8页。在他探视期间,见到萧红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1941年11月下旬,萧红不愿再住院,请求东北救亡总会的于毅夫帮助她回到乐道8号的家中静养。没过多久,咳嗽、头痛、发烧又加重了,萧红再次入住玛丽医院。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端木蕻良将萧红从医院接回到九龙乐道8号家中,并邀请骆宾基从港岛过海到家中照顾萧红。当天,于毅夫认为九龙不保,备好小划子,和端木蕻良、骆宾基搀扶萧红乘划子从九龙过海到港岛。12月9日清晨,萧红入住位于港岛雪厂街(Ice House Street)的思豪酒店五楼房间。
12月18日,因思豪酒店中弹,由周鲸文介绍,萧红入住港岛德辅道中16号的告罗士打酒店。当晚日军登陆港岛。
12月23日,告罗士打酒店不安全,萧红移到周鲸文设在斯丹利街“时代书店”职工宿舍的书库。
1942年1月12日至18日,咳嗽加重的萧红入住港岛跑马地养和医院。养和医院是香港最好的私立医院,位于跑马地山村道2-4号。医院不太大,但很讲究,收费昂贵。
端木蕻良用港币兑换了“军票”交住院预金。院长李树芬和弟弟李树培误诊萧红得了气管瘤,要立刻动手术,开刀后未发现有肿瘤。手术后,萧红情况恶化,发烧、刀口不愈、需用铜管吸痰,病情加重。
1942年1月18日,萧红再次入住玛丽医院。
大约两日后,日军占领玛丽医院,实施军管,病人全部离院,部分与法国医院合并。萧红被转至法国医院。又约两日,法国医院也被日军宣布军管。萧红和法国医院一起搬到半山区圣士提反女子中学,一个没有医药、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战时临时救护站。
六 萧红逝世地点及骨灰埋葬地
1942年1月22日上午11点,萧红在位于香港半山区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红十字临时救护站逝世。
1月24日,遗体在跑马地日本火葬场火化。
1月25日,端木蕻良将萧红的一半骨灰埋在浅水湾,竖有“萧红之墓”的木牌。
1月26日,另一半骨灰埋在萧红逝世地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校园,面向东北方向坡上的一棵树下。然而,埋在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这一半骨灰,随着端木蕻良的逝世,具体位置已无从知晓,而成为萧红生平中的又一悬案。

位于香港浅水湾的萧红墓地 (1942年摄),1942~1957年间萧红的一半骨灰埋藏于此
据我们实地考察,以及向相关人士询查,如圣士提反女中的图书馆馆长所提供的数据,这地点数十年来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校园内虽然仍有不少高大的树木,可惜其中大部分都已不是当年萧红下葬时留下的树木,而是后来新植的树木了。
原来,圣士提反女中附近的树木,经过数十年的风雨,原来的古树很多已因台风暴雨等因素被相继砍伐,后又种上新的树木,因此这里校园内所见的巨树很多已不是当年端木蕻良所看到的那些树木了。更糟的是,后来又因学校和巿政府的整顿规划,女中校园已被一分为二,一道围墙把原来的校园园林隔开,其中一半保留在女中校园内,另一半被划分为城西公园。萧红的骨灰,已经不知是埋在哪一个朝北方的山坡上;是在女中校园内,还是校园外公园的树木之间,也已难分辨。如今,校园内外都重新种植了十数棵高大的树木。因为端木蕻良未曾留下任何记录,所以已找不到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的确切位置。从女中校园内看到的是几棵树木景象,围墙就在树影之间。
而圣士提反女中围墙外的城西公园中,有更多高大的树木生长在那里,每一棵树木底下都有可能是萧红另一半骨灰的所在地。在女中校园外一墙之隔,城西公园中的几棵大树的位置,都可能是当年萧红骨灰的埋葬地点。在这些巨大树木的身影中,萧红的骨灰悄悄埋藏着,不为人知地度过了近七十年岁月。如今只能凭借圣士提反校园和城西公园的这些巨树凭吊萧红了。

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墙外城西花园景观,萧红另一半骨灰可能埋藏于此
七 浅水湾萧红墓迁往广州银河公墓
萧红另一半的骨灰埋于浅水湾海边,此处的萧红墓于1956年面临动土被毁的命运。事因承租方香港大酒店准备在此建一座儿童游泳池,萧红墓将因此不复存在。此事引起了香港文化界的震动,文化人纷纷就此撰文,呼吁给萧红墓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1956年12月5日,陈凡在《人民日报》发表《萧红墓近况》。随后,在马鉴、陈君葆主持的中英学会演讲会上,叶灵凤报告了萧红墓被毁的情况。由中英学会出面,香港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谭宝莲奔走于市政局和萧红墓地地产权所有人之间,获暂时停工。
1957年7月22日,浅水湾萧红墓正式发掘,下午3时找到萧红骨灰。
1957年8月3日上午10时,香港文艺界迁送萧红骨灰返穗委员会马鉴、陈君葆、叶灵凤、谭宝莲、曹聚仁等在红磡永别亭举行送别会,将萧红骨灰送往深圳,由广州作协派作家黄谷柳、诗人陈芦荻等在桥头迎候萧红归来。
1957年8月15日,萧红骨灰迁葬于广州银河公墓。
——端木蕻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