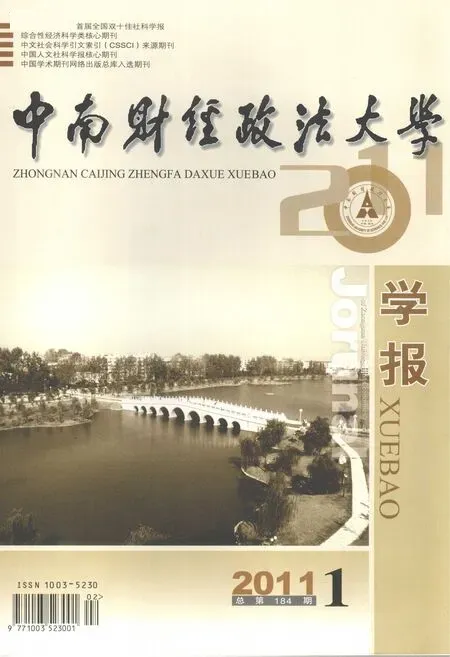能力、交易费用与企业边界
崔 兵
(湖北工业大学 经济与政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68)
能力、交易费用与企业边界
崔 兵
(湖北工业大学 经济与政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68)
企业能力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是研究企业边界的两种主要理论范式,两者虽然在行为假设、基本经济分析单位及逻辑思路上存在分歧,但是企业的本质属性要求企业边界理论融合企业能力理论和交易费用分析这两种范式。正是企业能力和交易费用的共生演化决定了企业边界,在交易费用分析中引入学习效应、治理不可分性和转化成本有助于我们对企业边界的变迁过程进行动态分析。
企业边界;企业能力;交易费用;共生演化;治理不可分性
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企业能力理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企业理论的两种主要理论范式,在研究企业存在、企业边界、企业内部组织以及生产的制度结构时,“虽然两种范式之间既存在竞争性也存在互补性,但是后者多于前者,因为事实证明两者的分歧更多是表面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当我们试图通过构建组织科学来理解复杂的经济现象时,交易费用分析和能力分析都是需要的。”[1]本文在对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企业能力理论两种范式的企业边界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两种理论范式融合的必要性和理论路径,探讨能力、交易费用共生演化决定企业边界的机制,并对企业边界变迁过程进行动态分析。
一、企业能力理论与交易费用经济学中有关企业边界理论的比较与融合
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企业能力理论都是在突破或修订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对企业 “生产”和“交易”本质属性的不同认识,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企业能力理论的企业边界分析在行为假设、基本经济分析单位及理论逻辑思路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企业固有的“生产”和“交易”的双重属性表明,具有解释力的面向真实世界的企业边界理论需要融合交易费用分析和企业能力理论。
(一)企业边界理论的比较
撇开方法论上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争论,我们主要从行为假设、基本经济分析单位及逻辑思路三个方面对企业能力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企业边界理论进行比较。
1.行为假设
所有有关社会科学的理论都隐含地或明确地建立在对人类行为的假定基础之上,经济学也一样。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假定,在很长时间内被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一个“怎么方便怎么处理”(as a matterof convenience)的问题。除了不认可交易费用经济学中威廉姆森对行为人的机会主义假设之外,企业能力理论(尤其是演化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都坚持有限理性的行为假设。两者区别在于前者的有限理性属于中等程度的理性,即行为人虽然不能实现完全理性,但并不是短视的,而是有远见的(正是对有限理性的这一界定,威廉姆森被认为没有彻底坚持有限理性假设);后者则是有机理性(organic rationality),属于弱理性,即行为人只能通过不断试错而不是事前的“精心策划”获得某种具体结果。有机理性实际上将理性降低到只“依靠社会与历史环境进行自然选择”的程度[2](P71)。
2.基本经济分析单位
与交易费用经济学选择“交易”作为基本的经济分析单位不同,企业能力理论选择“惯例”作为其基本的经济分析单位,但二者都满足选择基本经济分析单位的“康芒斯三角”原则,即“注入秩序、解决冲突、实现共赢”。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企业能力表现为由个体能力构成但是大于个体能力简单加总的组织能力。由于不同个体认知能力及学习能力的异质性,因而在组成组织时需要某种协调机制调解当事人的认知差距或解决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具备这种作用的机制就是组织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则和“共同知识”,并具体体现为不同企业的“惯例”。由此可见,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企业能力理论对基本经济分析单位的选择都是基于自身范式研究目的的需要,不同的是在企业能力理论中,“惯例”维度化的研究迟迟未能获得进展,这也极大阻碍了企业能力理论正式化的进程。
3.逻辑思路
企业能力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都是基于行为人有限理性的假设来描述企业及边界决定问题的,但由于研究侧重点不同,两者的逻辑思路存在明显分歧。企业能力理论认为有限理性意味着行为人存在认知差距,从而将能力定义为缩小认知差距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企业能力理论将企业视为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生产单位,但与之不同的是,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企业投入产出的效率关键取决于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对具有不同认知能力的组织成员进行协调的能力。企业作为一种能力集合,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不仅取决于组织成员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而且取决于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即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组织能力)。市场对具有意会性和不可分割性知识协调的失效,导致企业作为一种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制度安排而出现,因为企业创造了能使多个个体集中使用各自拥有的专业知识的环境和条件,即威廉姆森所言的组织氛围。企业协调以权威和行政命令为特征,能极大限度降低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不同专业领域人士的沟通成本,有助于意会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企业的“持续性”意味着企业不仅是组织核心成员之间暂时签订的契约的联结①,而且植入了具有长久预期的组织结构和惯例②。“企业相对市场能够更有效地协调集体学习的过程。”市场虽然也是重要的学习过程,但作为自发、分散的协调机制,市场只适合协调可分解、可编码的显性知识,而企业作为整体性和持久性组织具有整合个体认知、偏好、能力和行动的能力,由此形成的组织粘性(cohesiveness)更加便于个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意会性知识的交流③。企业营造的组织氛围和文化有利于员工在企业内部维持较为长久的人际关系,实现法律契约无法具体规定的经验分享,增进组织集体学习的效率。正是企业在协调认知差距和知识沟通上的相对优势划定了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另外,由于作为企业能力承载体的惯例是不同企业在应对环境不断变化中积累的历史经验的产物,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惯例或不同的形成路径导致企业能力分布的异质性,从而决定了不同企业能够从事的生产活动范围,即企业的生产效率边界。
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思路为:以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并将每次交易视为契约。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交易者不可能预测到未来交易的所有偶然事件并以第三方能够证实的方式签订契约,因而契约天然是不完全的。在交易者机会主义动机的驱使下,契约签订后可能会出现违约、成本高昂的讨价还价和再谈判等危害契约关系的行为。因此为保证交易的顺利实施,交易者需要根据交易的不同类型确定不同的治理结构以减少交易效率损失。由于治理结构的不同属性决定了不同治理结构在应对不同交易属性所决定的不同交易类型时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具体表现为节约治理成本),因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如何在交易类型和治理结构之间实现有效匹配。企业作为一种科层治理结构所具备的治理结构属性特征,决定了其在治理交易频率高的专用性资产交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由于企业的这种比较优势会随着企业内部交易数量的增加而产生的激励扭曲以及选择性干预的不可能性而逐渐削弱,因而企业边界不能无限扩张。
(二)企业边界理论的融合
如果说交易费用经济学中治理理论和测度成本理论两个分支的融合主要停留在“理论共识”的层面,那么企业能力理论和交易费用范式的融合已经处于可操作的层面④。现有文献认为研究能力起源和能力形成过程必然涉及交易费用因素,而交易费用范式对企业异质性和治理结构动态性的忽视正好通过能力理论得以弥补。
1.企业边界理论融合的必要性
总体而言,企业能力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中有关企业边界理论融合的必要性在于两者在理论要素上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主要体现为:第一,由于企业能力理论以企业异质性假设为前提,因而更适合研究单个企业的边界决定问题,即研究企业的交易活动数量在不同企业之间的配置导致的企业边界变化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交易费用范式的短板⑤。如果我们将研究企业边界问题类比于研究热带雨林植物生长边界问题,则交易费用范式解释的是热带雨林与温带落叶林的边界问题,而企业能力理论则侧重解释热带雨林中某类植物的生长边界问题。第二,企业能力理论以企业“生产属性”为出发点,考察了体现在企业生产成本差别上的企业能力差别,弥补了交易费用范式对生产成本的粗略处理。第三,企业能力理论在考察能力形成过程中,引入了过程分析和动态分析,注意到了在特定时间、特定种类生产活动的治理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受现已存在的生产活动的影响。对生产过程的动态分析启发我们需要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引入动态分析方法,因为新增交易的治理同样受到企业现有交易治理结构的影响。
2.企业边界理论融合的理论路径
企业能力理论与交易费用经济学中有关企业边界理论在理论要素上的互补性预示着二者合理融合的关键在于调解两者在行为假设、基本经济分析单位及逻辑思路上的分歧。由于企业能力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都给定行为人有限理性的假设,只是在有限理性的具体程度上存在分歧。而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假设可以包含在“理性人追求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行为假设中,因而企业能力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这一表面分歧便可迎刃而解。鉴于“惯例”作为基本经济分析单位本身的模糊性及维度化的困难,而且我们是运用企业完成的交易活动数量来衡量企业边界,因而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交易作为基本的经济分析单位。两者在逻辑思路上的分歧突出表现在研究视角不同,即分别从企业的“交易属性”和“生产属性”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但我们认为两者并不矛盾,正如科斯所言,“考察企业为什么会存在时,我们无需关注同样的活动在不同企业组织时存在的成本差异,但是要解释生产的制度结构,我们必须考察这种差异。”[3]也就是说,在考察什么类型交易适合于企业,什么类型交易适合于市场时,我们只需研究企业的“交易属性”,而在具体分析单个企业的边界时,则必须考虑企业的“生产”本质。由于将企业的功能仅仅定义为资源配置,交易费用经济学范畴的企业边界理论中的企业并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类聚意义上的“整体”而存在。这样的理论假设必然忽略企业的生产功能,或者像威廉姆森一样对生产成本进行简单化处理,进而忽视不同企业由于生产成本差异导致的企业边界差异。企业能力理论对“生产属性”的考察,预示着我们需要综合考虑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才能完整说明单个企业的边界决定问题。
二、企业能力、交易费用的共生演化与企业边界
前文在述及企业能力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融合的必要性时,只是强调两者在理论要素上的互补性。然而,当我们在阐述企业能力、企业异质性与企业边界决定时,进一步追问企业能力的来源和形成过程,就会发现企业能力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的融合绝不仅仅源于其理论要素的互补性,更重要的是企业能力与交易费用之间本身就存在固有的内在联系,正是企业能力和交易费用的共生演化决定了企业的边界。
既然能力是保证企业生产、研发及市场营销等活动的知识、经验和技能,而作为能力载体的惯例是组织成员之间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组织行为习惯,是异质性个体行为习惯融合的产物,因而企业能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完成一系列活动累积形成的。假定在时点1,给定企业的现有能力,企业力图进入需要进行高度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某项交易活动。根据交易费用理论,由于高额的签约和执行成本,没有独立的供应商愿意提供该项投资,因而企业只能自投资。自投资完成以后,企业具备了从事新交易活动的相应能力,在时点2我们观察到企业从事交易活动的范围(企业边界),很容易从静态角度将企业边界的决定归于企业能力而忽视在时点1交易费用的“历史”作用。由此可见,抽象掉了企业能力形成的过程,就必然忽略交易费用在决定企业边界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交易费用影响企业能力的形成,但企业能力一旦形成以后,企业能力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分布又影响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由于有限理性,任何企业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单个企业不可能从事所有的交易或生产活动,因而企业之间必然发生相互联系。从交易费用经济学角度考察,异质性企业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可以抽象为包括市场契约、混合契约和一体化契约在内的不同契约关系。契约关系的建立和维持需要耗费事前和事后的交易费用,而这些交易费用的大小明显受到企业能力占有不均衡和企业能力差异大小的影响。给定不变的外部条件,企业“群落”(firm population)会形成与之相对应的企业能力分布,在此分布下,企业根据自身能力的相对优势从事一定范围的生产和交易活动,并产生均衡的交易费用。假定企业“群落”的某个企业(focal firm)通过创新提高了自身的能力水平,扩大了与其他企业之间的能力差距,改变了原有的能力分布(譬如,福特公司在所有汽车生产商中率先实现流水线生产),能力差距的扩大导致短时间内创新企业难以劝说或说服原有的合作伙伴,比如福特公司难以要求其合作伙伴提供与流水线生产相匹配的零部件或服务。能力差距扩大导致与原有契约关系相关的交易或生产活动的交易费用增加,创新企业不能从“市场”获得与创新行为相关的产品或服务,只能通过“内部化”满足自身需求,进而导致企业边界扩张。由此可见,交易费用大小与企业能力分布相关,不同企业之间能力差距扩大会引致较高的交易费用,导致企业边界改变。
三、企业边界变迁过程分析
企业边界动态演变的本质是不同治理结构或协调机制的转化,伴随企业边界的扩张或收缩,企业治理的生产活动范围或交易数量会发生动态变化。当企业采用一体化战略扩展其边界时,会将原本由市场治理或混合治理的交易纳入企业内部;相反,企业外包战略会减少企业生产活动数量,将原本由企业治理的交易转化为非企业治理。“企业能否以最低成本从事某项特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企业正在从事的其他活动,但是我们对企业正在从事的活动对增量活动的影响却知之甚少。”[3]
在交易费用分析中,治理结构的选择只是考虑新增单一交易(增量交易)的交易属性,而未考察新增交易对存量交易的影响及存量交易的治理结构对增量交易治理结构选择的影响。而企业能力理论表明,企业能力是累积性动态学习的结果,企业组成成员的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都会改变个体认知能力和超越个体集合的企业能力,因而由企业能力决定的企业边界变迁不仅受制于现实约束条件,“历史”因素、组织学习效应在变迁过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基于此,交易的企业治理和非企业治理之间的转化并非是完全可逆的,对企业边界的分析不仅要比较静态条件下不同治理结构的效率,还要考虑学习效应和企业能力外溢对企业边界变迁的影响,并且要分析治理结构变迁过程中的转化成本(switching cost)。
(一)学习效应与企业边界
企业能力(动态能力)演化的实质是企业知识链的变化,这种知识链的变化源于企业迫于生存、竞争压力进行的内部学习或外部学习过程[4](P163)。组织学习可以分为利用性和探索性学习,利用性学习主要挖掘、利用现有的知识以提高运作效率;探索性学习则旨在开发新的知识、不断追求新的未知世界以提高组织灵活性(适应性效率)。通过学习,企业动态能力随之发生变化,进而引致企业能够有效协调的生产活动范围及协调方式的改变。对于资产专用性、复杂性程度高的一次性交易,短期内企业只能采用一体化治理,通过企业内部权威协调相关生产活动。但是,在长期,伴随交易由一次性交易转变为重复交易,企业可以通过声誉机制(混合治理)实现契约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同时,在长期重复交易中会逐渐形成基于互惠和合作的交易惯例,这些交易惯例有助于将一次性交易中难以具体规定的“剩余权力”具体化,从而降低由于有限理性导致的不完全契约的“不完全”程度。由此可见,短期最优的企业边界决策在长期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之间的能力模仿及知识外溢,导致企业对生产和交易活动所需的组织知识的相对认知能力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企业边界决策。
(二)治理不可分性(governance inseparability)
“尽管交易费用经济学始终强调签约的事前条件和事后条件……但它通常只是分别考察每一个交易联结。这样做虽然能够展现每一个契约的主要特征,但却有可能忽略或低估一系列契约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有时需要更多关注契约的多种变化形式。”[2](P393)威廉姆森的观点表明,对治理结构的分析需要综合考察所有交易,而不仅仅是单一交易,因为交易的治理存在治理不可分性。治理不可分性一方面表现为新增交易或活动的治理结构选择会受到现存治理结构的制约,即存在交易治理结构选择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治理不可分性还表现为各种治理结构(交易实施方式)之间的互补性,单项治理结构的变革会受到与之关联的其他治理结构的制约。
交易治理结构选择的路径依赖通过影响企业激励机制选择和企业能力开发,制约企业边界动态变迁的过程。企业边界变迁会导致交易治理结构的改变(契约关系改变),从而引起激励机制的改变,而治理不可分性会制约新的激励机制的选择。一种激励机制的选择决定了在该机制下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新的激励机制会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因而这种变迁可能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比如,企业的外包决策本质上是企业将部分生产活动的“低能激励”转变为“高能激励”,但这一举措由于会打破企业原有的契约承诺,从而招致“利益受损者”的反对。治理不可分性产生的严重路径依赖会制约企业选择不同治理方式的灵活性,甚至可能将治理结构锁定在无效率状态,导致企业难以选择与交易属性匹配的有效率的治理方式。治理不可分性对企业能力开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企业边界变迁内含的企业生产活动重组、衍生的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工都会导致企业能力发生改变。从能力理论中惯例的路径依赖特点还可推论,治理不可分性可能导致企业在现有能力的利用和新能力的开发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创新惰性”会影响企业边界的扩张和收缩。无论是一体化还是外包,都涉及企业现有能力的更新和存废,治理不可分性形成的能力惯性可能通过“自我强化”使企业沦入“能力陷阱”,难以对企业边界进行及时调整。
治理结构的路径依赖从历时(时间)关联角度分析了治理不可分性,而治理结构的互补性则体现了不同治理结构的共时(横截面)关联。互补性的存在意味着某一单项交易或活动的治理结构与其他交易或活动的治理结构构成一种连贯的整体,任何单项交易的治理结构在孤立的情况下都不会轻易改变。治理结构的互补性表明即使是对具有相同交易属性的单一交易的治理也可能存在多样性的治理结构,因为交易治理结构的选择不仅取决于交易本身的属性,还取决于交易所在“交易组合”的治理结构。由此可见,基于单项交易属性确定的局部有效的治理结构,在考虑“交易组合”的背景下并不一定是整体最优的。如果在治理结构互补性的基础上加入能力互补性特征,会进一步强化治理不可分性的共时关联效应。因为企业边界变迁会对企业整个能力池(capabilities pooling)产生影响,单项能力的调整可能需要改变知识交流的界面,从而要求“配套能力”的同时跟进。由于不同治理结构和不同能力的调整速度并不相同(不同的转化成本),因而治理不可分性会阻碍或延缓企业边界变迁过程。在企业难以针对交易特征的动态变化灵活选择适合自身的生产活动范围的情况下,企业难以实施有效的边界决策。
(三)转化成本
以治理结构和企业能力的历时关联及共时关联为特征的治理不可分性导致企业边界变迁过程产生转化成本。转化成本的存在意味着企业在扩张或收缩过程中,不仅要考察目标治理模式和起点治理模式的相对绩效,还要分析治理结构变迁过程产生的转化成本(SC)。在面临较高转化成本的情况下,交易可能无法实现从起点治理模式到目标治理模式的转变,或者形成不同于两种治理模式的“杂种治理”⑥。如图1所示,与交易组合A1、A2…An对应的治理结构组合为GA1、GA2…GAn,当交易组合演变为B1、A2…An,对应的治理结构组合为GB1、GB2…GBn。如果交易治理结构能够伴随交易组合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则交易治理会顺利完成从起点治理模式到目标治理模式的转化,即顺利完成企业边界变迁。但是如果治理不可分性产生的转化成本较高,与交易组合B1、A2…An匹配的治理结构难以进行整体调整,则企业边界变迁过程受阻,对应的治理结构组合沦为GB1、GA2…GAn的“次优”杂种治理结构。

图1 转化成本与企业边界动态变迁
延缓或阻碍企业边界变迁的转化成本具体包括影响成本(influence cost)⑦、补偿成本、知识信息编码成本、协调成本等。因为既然企业是以权威为特征的经济组织,就必然运用集中的控制权或决策权对企业内部资源进行配置[5]。在企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如何配置,是根据市场高能激励原则将稀缺资源配置给最有效率的部门,还是实现相对“机会公平”,缩小企业内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差距,这取决于企业权威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由于企业内部谈判力量的不对称分布,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企业权威会成为企业内部追逐个体利益的利益相关者游说的对象,利益相关者往往高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业务活动的盈利前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支持。由于企业边界变迁往往涉及企业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资源重新组合或资源用途改变不仅涉及增量资源的使用,还会触及存量资源的调整,因而常常诱发相关当事人的“寻租行为”。对于大型企业而言,企业的边界扩张或收缩可能主要涉及某部门的利益,部门会游说其他代理人和企业内部权威以获取企业决策支持。而其他部门的代理人基于“互惠性”交易的考虑,为获得对方对自身未来决策的支持,也会支持项目决策。部门的规模扩张速度越快,越有利于经理自身“王国”(empire building)的建立,因而可以获取更多的“租金”或“个人利益”。效率越是低下的部门,由于对产出的边际贡献小,因而越有动机去游说上层经理人以获得组织租金。企业内部大规模的寻租活动不仅耗费要素所有者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和精力,还会延缓企业边界决策过程。
补偿成本是对企业边界变迁中“利益受损者”的利益补偿,比如企业生产活动外包,可能需要解聘从事这些生产活动的企业成员,企业需要依法承担解雇员工的安置费用。在企业实施一体化战略时,企业可能也需要对被并购企业的管理者和普通雇员提供某些补偿以推动兼并的顺利实施。企业边界变迁意味着需要在不同活动界面之间重新进行知识编码,以提高活动效率,这一过程会产生知识信息编码成本。知识编码意味着需要重新界定知识界面,或者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知识传递效率会受制于事前能够确定的界面以及企业参与生产活动的数量。如果难以确定知识转化的界面,而且知识供给者和接收者的能力差距太大,知识更多是“只能意会”的,则编码成本较高(知识漏损严重)。另外企业参与的活动越多,单一活动所需知识编码的自我实现能力下降,需要融入更多知识才能有效实现单一活动的效率。协调成本是在企业边界变迁过程中协调不同交易组合、不同治理结构组合而产生的。由于治理不可分性,同一交易从企业治理转向市场治理(业务外包)的转化成本可能并不等于该交易从市场治理转向企业治理(一体化)的转化成本,因而企业边界的扩张和收缩可能并不是完全可逆的。
四、结论
企业能力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中有关企业边界的理论虽然在行为假设、基本经济分析单位和逻辑思路上存在一定分歧,但两种范式之间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企业边界的内生变化是交易费用和企业能力共生演化的结果。在主流的交易费用范式分析中引入学习效应、治理不可分性和转化成本,能够对企业边界变迁过程进行动态分析,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企业边界变迁的路径和机理。本文只是提出了融合交易费用和企业能力的企业边界理论的理论框架和逻辑思路,而缺乏对“融合理论”的案例研究和实证检验,这正是后续研究需要完成的工作。
注释:
①虽然企业契约(特别是劳动契约)相对市场契约是长期契约,但企业并不因组织成员的契约终止而消亡,因而相对于企业的存续期而言,任何与企业成员的契约都是暂时的。
②霍奇逊关于企业本质的认识并未完全否定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只是更加强调企业的“实体”层面,而不是“契约”层面。
③Teece最早提出“公司粘性”的概念,用于分析企业进行多元化经营的协同能力,Foss利用“公司粘性”研究组织知识演化过程中利用旧知识和开发新知识的平衡能力。
④Langlois和Foss认为企业理论未来的研究重心是用统一的模型将激励和能力模型化,解释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与企业边界选择之间的关联。
⑤威廉姆森承认交易费用范式适合研究某类(generic)治理模式选择问题,而对某类治理模式中,如企业治理模式中某个特定(particular)企业边界选择的解释则要求助于能力理论。
⑥“杂种治理”借用了樊刚“过渡性杂种”的概念,不同于交易费用经济学中的“混合治理”,它实际上是相对于最优目标治理模式的“次优”选择。
⑦影响成本是Milgrom和Roberts创造性地将寻租理论引入企业内部决策分析时提出的成本概念。
[1]Oliver E.Williamson.Strategy Research:Governance and Competence Perspectives[J].Strategic Management,1999,20(12):1087-1108.
[2]Oliver E.Williamson.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M].New York:Free Press,1985.
[3]Ronald 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Origin,Meaning,Influence[J].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88,4(1):3-47.
[4]尼古莱·J·福斯,克里斯第安·克努森.企业万能——面向企业能力理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5]Margaret A.Meyer,Paul Milgrom,Donald J.Roberts.Organizational Prospects,Influence Costs,and Ownership Changes[J].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1992,1(1):9-35.
(责任编辑:胡浩志)
F019
A
1003-5230(2011)01-0128-07
2010-09-13
崔 兵(1974— ),男,湖北恩施人,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