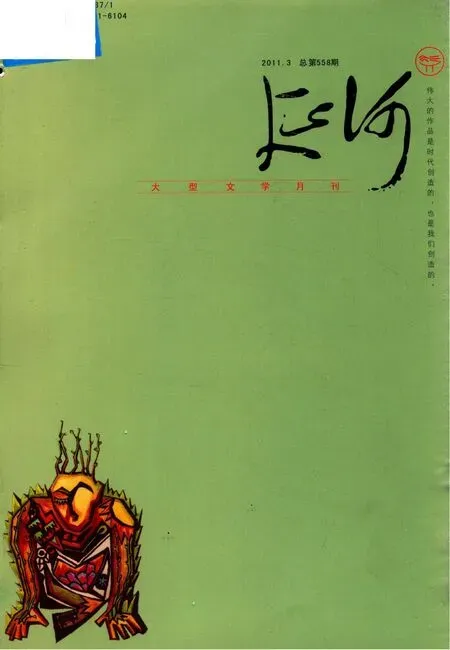杂语纷呈的乡土革命叙事
遆存磊
杂语纷呈的乡土革命叙事
遆存磊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贾平凹 《古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迟子建 《白雪乌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1910年冬至1911年春,哈尔滨爆发鼠疫,死亡数万人。《白雪乌鸦》就是根据这段史实创作的。作者以富于地域风情的笔调,讲述鼠疫流行时发生在哈尔滨平民百姓中间的种种故事,表达普通人在灾难中的生活常态和难以抗拒的惨烈的命运。根据真实历史人物塑造的华侨医生伍连德和官员于驷兴,虽然未施重墨,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白雪乌鸦》体现了作者既往的创作风格,不张不扬,一点一滴地把人物、故事和风情“晕染”出来,给读者留下绵长的回味。

李文俊 《威廉•福克纳》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威廉•福克纳(1897-1962)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现代派小说家之一。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书是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对文学大师福克纳生平与作品的全面解读。李老凭借自身丰富的研究成果,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以生动的语言,独到的见解,通俗易懂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解文学的奥义,并选有能够反映作家主要创作思想和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引领广大文学爱好者领略经典的魅力。
庄子曾经讲过关于“混沌”的寓言:“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我想若不把“混沌”看作神灵,而是一种小说叙事状态的话,那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古炉》当得起这两个字。贾平凹以散点透视的行文,巨细靡遗,将古炉村的世态民情纳入数十万言的作品中,并不因“混沌”无窍,就取巧凿之。其貌似笨拙,却有大音希声之态,与前作《秦腔》的叙事美学追求一脉相承,虽杂语纷呈,于其中却可辨出恒定的隐喻来。
《古炉》讲述了一个烧制瓷器的名叫古炉的村子里发生的文革故事。古炉村原本偏远、宁静、民风淳厚,但在时代的风潮中,村中的所有人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作品通过一个名叫狗尿苔出身不好的男孩之眼,将山清水秀的村落逐渐演变为充满了猜忌、斗争、暴力的利益场。
乡村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中曾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实质上是被边缘化了,其中亦包括文革与文革叙事。动荡年代乡村的边缘地位,以及新时期以来少见以乡村为视角的文革叙事,均表明这一片广袤的生活现实被忽视与陌生化。如今,贾平凹以一己之力重造乡土革命叙事,虽篇幅浩瀚,却不采用宏大的架构与预设的理念,避免人物与事件典型性的强调,全以紧密的生活细节呈现,杂语与碎片构成全部场景,作者不去做历史的评判,显然他更愿意将自己的价值观念隐含于这生活之流的杂语纷呈中。
《古炉》以一个身材矮小出身卑微的少年狗尿苔为叙事主人公,更有利于呈现这纷扰杂乱的乡村场景。狗尿苔不断穿梭于土屋灰巷间,脚步不消停,嘴巴不消闲,带出了古炉村诸多琐琐碎碎鸡零狗碎的“无事”之事来,虽为片断,其合体却让我们可以窥视到一个自足的乡村生活世界。自然,这乡土社会虽偏远而沉静,却也挡不住时代的大波动,虽然反应有些滞后,但外力投来的石子产生的涟漪搅动了整个村落,牵扯进每一个人,或主动参与或身不由己,旧有的秩序尽数打破,人性的明与暗亦无可遮掩了。
显然,动荡的年代给人性的恶充分展示的机会,本来乡土社会于总体的安宁下也有着形形色色的矛盾与摩擦,不乏纷争喧闹,但总有温和解决的渠道,如今却有了畸变的可能,人性的脆弱正在于此。这已不是死水微澜了,几乎是要打破旧盘子,痴想重新来过,人的希望与虚妄交缠在一起,建于浮沙之上的乌托邦害人不浅。昔日的蜗角之争,放置于这样的背景下,竟变为了性命相搏。黑色的荒谬,就在于将荒谬当作极正经的事情去做,自己浑然不觉,只能留给隔开一段时空距离的后人去凭吊。
《古炉》贵有“动”与“不动”:动在显层面,不动潜藏于底里。时势在动,古炉村虽偏辟,人事的格局却也要跟着变动,众声喧哗变了调子,尖利的政治话语出尽风头;但不管挺立潮头的弄潮儿折腾出多少浪花,搅动多少波澜,潜于村庄与人心深处的某些东西是不会动的。村庄的秩序是被打乱了,但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尽管时不时有家破人亡的事情发生,但大多人还是珍视那一餐一饭一柴一草,时代动荡自管动荡,村人的日常生活的根底还在。人心纷扰中,仍有蚕婆、善人这样的人在,他们虽处于乡村社会的底层,却并不因为自己艰难的处境泯灭人性的光亮。他们忽视派别的争斗,予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以援手,在其眼中,人的存在是重要的,其余尽可撇下另说。这表明,时代的风潮并未完全摧毁这古老的乡村,如书中写到的那棵需几人环抱的白皮松,被炸倒之后,方见其根须绵延四面,漫长不绝。
我们可以看出,《古炉》是一部描写特定时段的作品,属历史性书写。若向另一维度探究,其超越时间性亦隐约露出。时代一去不返,依旧杂语纷呈,这就是变与不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古炉在中国,中国亦古炉。贾平凹的写作重在不是故事,而是乡土生活的细节与状态,他创作之初未必就一定要将古炉村作为中国的隐喻,却在 “无序而来,苍茫而去”的书写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索可能。
古炉村虽小,但乡土社会固有的结构以及时代风潮的波动,一切都具体而微的存在,如同每一滴水珠都折射着如许的光芒。我们看古炉村,看狗尿苔,看蚕婆,看造反派的争斗,看那“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初始似乎限于一时一地与具体人事,但渐渐漫漶开来,一切触类旁通,有了他者的影子。如贾平凹说狗尿苔的形象有许多自己的经历在里面,但毕竟揉合种种,不是某一个人的自传了。因此,尽管只是一个小村落,尽管有动荡年代的背景,我们却慢慢地从“隔”中寻出不隔,发现乡土中国的缩影来。
贾平凹的书写给我们以混沌之感,初始有接受的难度,但读进去即发现一种不事雕琢严丝合缝的文体气度来。他自己也说:“年轻的时候讲究技法,年老的时候,讲究体验,语言变得很平实。”这种“没有扎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的文体与其小说内涵形成一种平衡,扎实细密的文字配合着琐琐碎碎的生活细节,且有着作者对乡土社会深厚的感情渗透其间,构成暗潮汹涌的乡土叙事。贾平凹并不是将人与事简单地叠加陈列,而是顾及层层面面的关系,筑就无结构的结构,称得上重剑无锋。他不用多线叙事,而是遵循生活的原生态,将现实的质地自自然然呈现出来。贾平凹在书写中并不去表露自己对人或事的好恶,这与其独特的叙事美学追求相关联,生活的内在逻辑不是作者可以设定的,而是由生活的潜流自己流露。因之,贾平凹不做断语,不发感喟,将创作者的悲悯和哀痛隐藏于沉寂的叙事罅隙之间。
于语言,于叙事形式,贾平凹都有古典式的追求,抹去炫目,摒弃技巧,贯穿一种无欲则刚的大度,隽永而浑然。贾平凹不避琐碎,因为他有足够的自信以充沛的文气构筑完整的文学图景,起始于生活细节,归之于朴拙的文本。在《古炉》中,他进行了一场杂语纷呈的乡土革命叙事,刻画着历史留给乡土社会的沉重创伤,虽无力挽救,亦难以弥补旧有的伤痕,但以此破碎的寓言提供警世的书写,却也暗示着历史与现实交错之际的另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