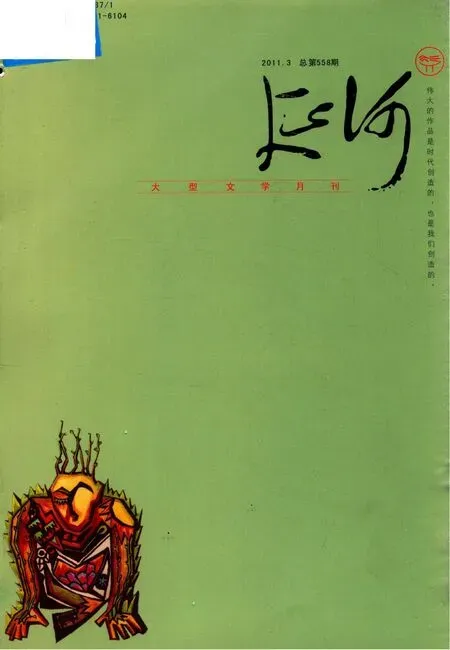被时光遗弃的鱼
王炜
被时光遗弃的鱼
王炜
空寂的午后
我们对世界的判定与认识竟存在着巨大的错误与矛盾,这是我突然发现的。他让我吓了一跳,我不知是应该庆幸自己的突然开悟还是应该诅咒自己对世界本源可怕的窥探。
在我不断亲近高原的同时却对高原越来越陌生,关于高原的许多秘密而细节的映像变得错综迷离也以至越来越让我无法陈述与解白。随着探寻的深入,高原在我的面前开始不断地显露出它的漏洞与虚幻。
关于春日漫天的黄风,关于夏日焦黑的劳作,关于深豁的地裂,关于如穴般的窑洞生活,关于地层深处那白色的骸骨、黑色的海,油海……直面高原,我在看多了高原的神奇与繁华后成了一个彻底的失语者。
一个空寂的午后,我穿着厚厚的棉袄在山谷间放羊。夏日的火在我身体中却成了冰,寒冷无处不在。宏阔的山顶没有一丝风,不远处是深深的幽谷及山谷对面土褐色的绝壁。绝壁上有一些人凿出的孔洞,那些洞高低不一嵌在石壁上。夏日的暴雨特别多,也特别猛烈,它们在山顶积聚在山峪间飞奔冲撞,那些沟谷,孔洞就成了水在山土间突围的道口。一只山羊向悬崖边走去,我拾起土块扔过去命令它返回。一团墨般的云从沟谷升起很快弥散开遮住了山顶。对面的绝壁似被施了魔法突然变成了一张巨大的笑脸。我看到那种异像心中所产生的惊奇与恐慌大得难于言表。我头晕目眩全身颤栗,那种梦幻性的呈现使我忐忑不安。
接下来的事更诡异得有些出格。一只黑色的鸟“噗”地一声撞在我的脚下,它仰起脖子说:“好渴啊!好渴。”说完向沟谷飞去。那鸟的黑影在我的脑海中定格。瞬间我的思维短路,我的神经受到了严重挑战。鸟开始说话预示着什么我不清楚,它已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我觉得似乎掉进了一个迷幻的梦中。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将自己丢失,在惊慌迷乱中赶了羊匆匆回家。怎么回去的我至今都没搞明白但是一个可怕的事实却出现了,几只羊在途中走丢。我语无伦次的辩解显得苍白、可笑,父亲根本不相信我的“异想天开”,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斥责。饱受委屈的我对自己处的环境及自己本身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这奇异的经历导致我多年后的叙述仍显得可笑而虚幻。
与那种对传统经验的反叛与颠覆性的奇异现象的遭遇,让我对高原有了一种别样的好奇与理解。它一直引导着我不断去探寻与思考。它的神秘、诡异来自何方?又将高原引向何处。我开始思索这个对我来说过于艰深却充满情趣的问题。我试图剖开黄土地在里面看个究竟,弄明白它的过去与未来,但我清楚我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我只能依靠他的自我表述,自我撕裂所呈现出的那些细微而模糊的影像来寻找他的根脉与隐密的灵魂。
那些古老的沟谷,那些断裂的山涧,那些深邃直达土地深处的洞穴都成了我探寻的地方,成了我追逐“虚幻”否定现实思维的佐证。随着探寻的深入,一些蛛丝马迹陆续呈现在眼前。我看到了在砾石中沉睡的海贝、海龟,在土层中游动的鱼。哪些动物不属于土地,它们应属于湖泊或海洋。它们也不属于现在,应该在几万年或更早的时间段。那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鱼,穿越千万年时光从大海游入陆地,从远古游到现在,被时光固化、定格。这些已固化了的生命直接把古老的高原指向大海,这些鱼们有力地陈述了高原曾经的面目、形态,曾经的驿动、呐喊。是了,在遥远的年代,伟大的高原应是浩瀚的海洋。如今那一片浩荡的汪洋已成为一种走失的存在。那些迁移与流动应有一个时间坐标,是几万年还是几十万年?那些悠闲的鱼儿在欢快的游乐中忘却了时间,在沧海变桑田的交融中来不及躲避与逃亡,从水中直接游到了土层的深处。它们忘记时间的同时也被时光遗弃,千百年来就这样在时间与空间之外游走,在深深的地层中游走。当然在这些地方游走的还有那些在玄武纪或白垩纪驰骋于大陆之上的恐龙、猛兽。它们成群结队出现在一些古老的地层与洞穴中,高原人称它们为龙骨。乡民们从山洞中将那些东西挖出碾碎用来治疗妇科病或止血,大部分都廉价地卖给了一些所谓的郎中。
这些在地层中游走的生命,绝大多数是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突然定格的。它们被挤压、燃烧、分解成了一些乌黑坚硬的石头、水或空气。他们的身体经千万年转化与储备变成了一种可以燃烧的东西,这就是人们说的能源。人们制造出了一些巨大的机器将这些东西从地层深处一点点挖出来,肆意挥霍。人类无视大自然的愤怒与警告,把那掠夺的面积不断扩大,掠夺的巨手不断伸向地层深处。石油、煤炭、天然气被源源不断从高原的地层中挖出。高原人如一个突然暴富的财主,在欢乐晕旋中守望着滚滚而来的财富。人们被眼前的利益蒙住双眼,一时还很难回过神来思索这些财富可能带来的暗伤与灾难。人们看到了滚滚而来的利益却没看到大开挖带来的破坏,人们看到了土地上日益长高的大厦却没看见地层中日益变大的空洞与裂痕。
一个3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耸立起了成千上万个井架,并且每年以惊人的数量增加。高原被钻得千疮百孔,数千米的地下空洞连接着空洞,裂痕撕咬着裂痕。若干年后那些空洞与裂痕是否会从地下撕咬高原而使它再变成大海,让人类变成海贝、海龟或鱼?
地层中黑色的油海及固化了的鱼,昭示了高原与大海伟大的联系与交接,他们背靠着背,在宇宙中行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对那一尾尾在地层中游动的鱼,我默默无语心存敬畏。生命在时光中轮回变迁,在千万年后我是否也将成为别人擎燃的一片火光。
在高原的探询中发现的疑点很多,每一个结果都足以对传统思维造成全面的割裂与颠覆,每一个发现都是一种对高原的重新认识与定位。我知道人的生命太短而宇宙的时光又太长,它有太多的秘密会被人们一点一点窥探。
曾偶遇的灵异事件似乎是一个梦幻,再无法找到一丝的佐证。只有鱼。在地层中游动,在岁月中游动。
旷野中的课堂
在旷野中的课堂度过了我童年最闲适快乐的时光。如今离开美丽的课堂,离开童真的岁月已多年,它已躲到了我的心之深地。
我出生在农村,6岁时便被送到了村里的小学读书。那座仅有三间破瓦房的学校,仅可供那些高年级的学生使用,我们则被按排在房屋旁边三棵巨大的垂柳下面,那便成了我们的课堂。
六七张缺胳膊短腿的矮小破桌凳,一块被漆黑的木板,十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一个初中还未毕业的女老师就是这个班的全部。旷野中的课堂只有柳荫为我们遮挡火辣辣的太阳,它的简陋反而让它充满了情趣。
老师正值芳龄,芳龄又遇壮男,她恋爱了。她的精神与肉体很快被那个拖拉机手占领,俩人热乎得一塌糊涂。老师无暇顾及我们。她每天一上完课便匆匆离开课堂,与男友去了那个狭小的办公室。正值贪玩的年龄,我们自然乐得逍遥自在,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游戏与打闹中度过的。
我的同桌是个女孩儿,大我2岁左手上长出了一个趾指。力气巨大,蛮横勇猛。她打起架来无人可敌,被称作“六指琴魔”。遇了这么个冤家,每每因一些小事发生口角,以至动手。每次争斗我都是伤痕累累,落荒而逃。武斗结束,我们会冷战一段时间彼此各不相理。几天后当我们忘却了矛盾,就继续玩耍、争斗。就这样总是打打停停,一直持续到我们离开那里。
旷野课堂中经历的事情特别多,但在时光的漂洗下,大部分已淡忘了。
夏日的知了总是出奇的多。田野中、柳树上到处都是它们的叫声,天越热它就叫的越凶。那天上午课一结束,老师便离开了,顽劣成性的一帮孩子开始在树下奔跑嬉闹,课堂乱成了一窝蜂。有的爬在草地上捉虫子,有的蹲到树下逗蚂蚁,有的跳上课桌扮将军,我则与邻居小强几个玩“羊吃草”。正当我们玩得起劲,突然听到柳树上知了吱吱的唱起歌来。大伙受到知了叫声的吸引,放下了手中的草叶一块围到了树下向上张望。我们特别渴望得到那个会叫的小虫,小强自告奋勇爬上树去抓知了。垂柳枝叶茂盛,小强瘦小的身影顺着粗壮的树杆很快就爬到了茂盛的叶子中去了。大伙你一言我一语的吵嚷着,给他指知了的方向。不知谁喊了一声“老师来了”。大家一轰而散,匆忙找了各自的位子坐下来。
给我们带班的女老师拿着教鞭怒气冲冲地来到了黑板前。她可能和拖拉机手交流得不太和谐,一来就用教鞭使劲敲着课桌,将怨恨对准我们发泄。她开始是训斥,后来越训越气,一边训一边开骂。我们对她的叫骂没有很好的反应与配合,这伤了她的骄傲。她一边骂着世界上所能骂出的最脏的话,一边用教鞭一个接一个的敲我们的脑袋,感觉着教鞭在脑袋上的弹性。她又担心脑袋发出的声响会给她带来麻烦,于是下令所有人不许哭。
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一些女孩子站不住开始发抖。就在这时一股水柱从天而降,准确的落在了女老师的头上,干净的新衣服上。她一下子愣住了。就在她呆呆地抬头看柳树那一瞬间,所有的嘈杂哭闹声全消失了,课堂变得可怕而安静。只有风声呼呼的响,我听到自己的心在“咚咚”跳。那仅仅是短短的几秒钟的事情,女教师很快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她像发了疯一样瞪着眼睛,冲着柳树喊:“小强,下——来!”柳树上没有一丝动静,小强藏在了树叶子里。“吱—吱—吱—”一只知了欢快地唱起了歌,似在嘲讽。女老师把教鞭甩在柳树上,打落了几片绿叶子。她的自尊受到了挑战。她由羞而怒,奔向不远处的菜地,拿了一根长长的木棍在树叶与树枝间使劲捅。小强爬得更高,她根本就够不着。一边哭一边骂,一边跳着打。她折腾了好长时间,累了,回头恰好看见神情快乐的我,便用棍子敲着我的背,让我上树把小强拉下来。我没办法只好爬上了树。出于一种顽劣的本能,我一上树便冲她吐口水,她简直是暴跳如雷。我则一边扮鬼脸一边清楚地告诉她:“你够不着”。她就在树下一跳一跳地骂,与我们僵持到中午放学。她骂一会儿又骗一会,一直又盯着我们直到日落。
现在想来她一定是气得昏了头,竟会那样不顾一切地处理一个孩子的恶作剧。在这之间有一些老师过来看了一下就转头走了,我到现在还奇怪那时为什么没人管这事,或劝说一下。天渐渐黑下来,她扬言要用一种神奇的武功将我们消灭于树上,但仍无法将我们唬下树。便一边哭一边骂着离开。见她离去我们则一溜烟的下了树跑回了家。
第二天,因为害怕,我和小强拿着书包在山上转悠到天黑,没敢去学校。父母知道后押着我们到了旷野课堂,一个清瘦的老头取代了那个女老师。从此再也没见到那个被气昏头的女子。
老头来了之后带来了大雨。旷野课堂一遇雨便无法开课只能休息。那年的雨似出奇的多,旷野课堂在风雨中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秋季。天气转冷了,风在课堂来回串,小孩冻得坐不住,学校在村里借了一孔老土窑做我们的教室。旷野课堂生活从此结束。
枕畔的月光
生命的旅程中总会有一些看似平淡的细枝末节让人感动,并如美酒般被深深贮藏在记忆的某一个秘密房间,酝酿、发酵,历久弥香。多年以后打开那扇门仍能倍感生命的美好与欢欣。
十几年寒窗苦读试图走出高原的我又回到了小镇。当梦想成为泡影那刻我沮丧到了极点,小镇那拥挤的楼房、窄小的街道逼压得我快要喘不过气来。
身板硬朗、脚步稳健的爷爷从老家赶来,他将一颗西瓜放在我家的茶几上说他的瓜要开园了人手不够想让我回去帮他照看。我便带了几本书随他离开小镇,走入了乡村那片空旷的瓜地。
一番全新而别样的野营就这样在我的生命中拉开了序幕。
为了便于看护,他用椽子柳条塑料布搭了一个三角形的凉棚,凉棚里支一张宽木板,铺上被褥,就成了我守望瓜园的小窝。
爷爷每天清晨都在瓜地摸索翻敲。那些咚咚哒哒的声音在我听来没啥分别,他却用那神奇而古老的方法准确找出那些熟透的西瓜。一颗颗摘下来装入手推车,去县城叫卖。我则按他的嘱咐在瓜地巡视守望,以防偷窃与破坏。
白天太阳火炉般灼烤着,瓜地燥热而安静。四野泛着绿油油的亮光,那是玉米、谷粒在茁长。风吹过时它们会彼此拥挤、相互触摸发出沙啦啦的声响。偶尔会有一两个农民拿着锄头路过瓜地来讨一碗水喝。没事时我就躲进凉棚在海明威、雨果、三毛、卡夫卡的世界里厮磨与游荡。那时特别迷恋三毛,羡慕她生命的远足及字里行间流泻出的那份恬淡和谐的行旅情结。
黄昏时分爷爷回来换我回家吃饭,他说晚上我不必在瓜地受罪,回家去睡。但出于对旷野的喜爱与好奇,我吃过饭还是跑到瓜地坚持和他一块在凉棚守夜。晚霞在西天燃尽最后一缕绚烂,慢慢熄灭,一丝凉爽的风带着庄稼与花草的馨香缓缓从四野深处流泄而出,劳动了一天农民拖着疲惫的身影陆续回来了。
启明星亮时,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子开始吱吱地鸣叫。夜晚是虫子的天堂,那些此起彼伏的叫声似献给夜的赞歌。天由灰渐渐转黑。一轮明月从天边的树梢上慢慢升起。那静穆的清辉将大地装扮得素洁而神秘。蚊子成群结队地来了,它们如好奇的顽童在我头上、耳畔嗡嗡地喧闹。“叭”的一声暗处火光一闪,那长长的艾绳便在爷爷手里点燃,袅袅淡香慢慢在瓜棚中散开。
几个无事的农人凑在一起抽着旱烟天南海北、信马游缰地闲聊。
坐在棚子里,特别喜欢看那钻石般的星斗。银河横陈在天幕中央,雄伟壮丽,北斗星明亮的勺形一眼便能辨认出来,牛郎与织女被银河分隔。快七月七了喜鹊将如何飞升而起将桥架在银河上呢?偶尔能看到一些活泼的星斗在天上游走或飞快地划过在天空留下一条美丽的弧线。长久地注视使我迷失在了光的海洋,感觉自己好像就飞升到了那些陆离明亮的世界中。我总在这样的阅读中进入梦乡,耳畔似有人在窃窃私语那声音却又似来自遥远的太空。
月亮有时特别的亮,有时则暗、则缺,有时有光晕。天空有时宁静,有时有云朵躁动流淌。
半夜在睡梦中被雷声惊醒,倾盆大雨从头上直泄下来。一时天昏地暗整个世界都浸泡在水中。天宇充满了千奇百怪的声响:有雷的怒吼,有风的嘶鸣,有山水的鼓点,有树们的唏嘘。那简直是一曲伟大的交响乐啊!它在我心中产生的震撼不亚于一场地震的侵袭。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乌云退去,月光钻出了云缝,我则在疲惫不堪中沉沉睡去。
月亮还在天边,东方鱼白,听到了阵阵窸窣,我警觉地向地里望去。月光下爷爷正在俯身摘瓜,空气清爽潮湿,爷爷见我醒来说:“天快亮了,我摘瓜去卖,你没事,睡吧!”
年少的我还不懂劳作的艰辛与生活的苦难,更不懂得关照长辈,便又埋头睡去。
天大亮时架子车里已整齐地放了一车西瓜,爷爷用绳子将瓜仔细绑好。月亮已跑到了西山边,如一枚古玉清亮透彻。
因为有了枕畔月光的浸润,我的心似被月的铅华洗过一般。
责任编辑:刘全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