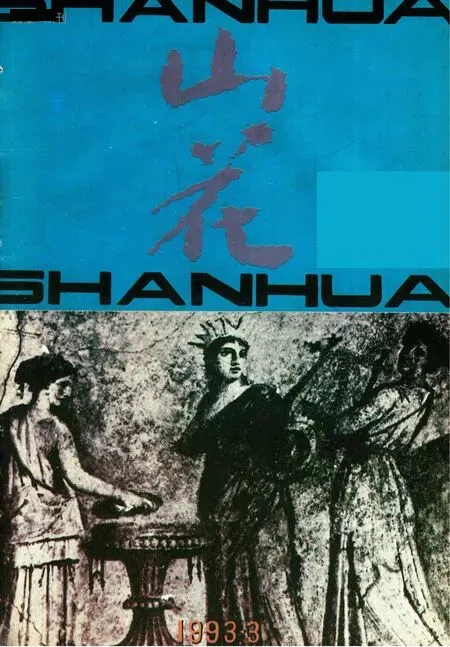幽曲四章
吴安臣
幽曲四章
吴安臣
压 迫
我在监考。我面对着无数的背,整个考场中学生的后背都对着我,我感觉潮水向我袭来。带着胁迫,我从无聊中感知到宁静的可怖。我的身体仿佛失去了一层保护,在空气里无端地沉沦,感觉在空气里撞击,思维的凝滞和开放全在空气里。一种虚空来自学生考试时写字的沙沙声。这种感觉仿佛在哪里有过,我努力回忆着。终于在思想的黑暗处绽放出一丝亮光来。
那时正读大学,一次我去参加演讲比赛,生平从没见到过那么多的脸,所有的人都满怀期待地望着我,甚至还有校园电视台记者的镜头对着我。我把那份背得滚瓜烂熟的讲稿拿在手心了,拿出后又觉得不合适,接着我把它放回兜里,但是等额头上的汗珠沁出时,我却又发现不拿讲稿我会浑身发抖,于是我又把讲稿拿出来,突然我又意识到拿着稿子上台要扣分的,虽然你没看,但是至少显示出你的底气不足,于是我又把稿子放回去。那些等着打分的评委像观看猴戏一样,把手抱起来,看我到底要干什么。我感觉手心里的汗已经泛滥了,那份讲稿稍不留意就会变成纸浆,我甚至能听到水滴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我就像欺骗所有期待的眼睛和耳朵一样,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我觉得我在犯罪。我甚至还看到负责摄像的那位记者已经把镜头对准了我,我看到摄录的红灯闪烁着,但是我居然不会开口说话了,这简直就是对他的戏弄,我看他把摄像机拿起又放下。无奈的他,我想那刻他只想冲上来揍我一顿,但是那么多的人都被我愚弄了,也不差他一个,所以我甚至也能听到他骨节响动了几下,最终他还是忍了。
我看了看他们的眼睛,只想这样开头,我太紧张了,我要爆炸了,但是我不能这样说,那样所有的人更会觉得他们受到了愚弄和伤害,也许从此就会把我当作一个非正常人来处理。我感觉自己像《围城》里的方鸿渐一样尴尬和无奈,我哆哆嗦嗦地又把讲稿从衣兜里拿出来了,惶恐地看了一眼,就一眼,我的心差不多已经跳出了嗓子眼,我感觉自己是此次演讲赛中最拙劣的选手,我不清楚自己讲了些什么,总之我看到评委的脸和我一样通红,特别是那位在场下给了我无数指导的老师,我把他的脸已经丢光了,仿佛所有的目光已经集中在他的后背上一般。当我哆嗦着把“我的演讲完了”几个字说完时,我觉得自己马上要被众人的目光解体了,我像一只仓皇的地鼠逃向座位,至于同桌的那位说了些什么我根本没心思去听,我想冲出演讲大厅,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出去了,那么我将再次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于是我像罗马竞技场上的奴隶等待我对面虎视眈眈的狮子退场一样,感觉所有的目光之箭压向我。事情过去很多年了,凡是参加过那次演讲赛的人都会记着我,于是他们在见到我时增加了一样谈资,于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活在一件往事的尴尬里。
转眼我走上了工作岗位,往事终于被一些人忘记了,或者他们已经厌倦了再去重复那些陈年旧事。但是新近的事却又以另外的形式在我的脑海里笼罩着我。
继父得了大病。以前我俩的关系很僵,但是作为人子我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来救他,临到手术签字了,我的手抖得十分厉害。村里人在继父的不断解释中认为我是一个不孝子,手术如果出现意外,那么我要负全部责任,假如继父发生意外,那么村人肯定认为我这个继子没尽力。
自从继父被推进手术室我就在外面的走廊上徘徊了,我试图用书来平静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些文字的东西,像一些无意义的符号,脑子里是继父衰弱得如风中枯草的模样。我如何减轻我的心灵负担,思考了半天我毫无办法,嘴里又苦又疼,连日的奔波把我也弄得形容枯槁,我在昆明的大街上像一具干尸一样地走动,人流在我的前后左右汹涌,声音从四面八方迫近我的耳鼓,我为什么会在这座城市里?我经常发出这样的疑问,我真的不喜欢这个地方,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两星期以来,它已经残忍得把我的口袋翻了个底儿朝天,每天几百块的医药费把我逼向绝境,拿起电话来感觉我的手伸向的是虚空,这座繁华的城市我找不到帮我的人。我像游魂一样又回到我的家乡,还是那些穷哥们帮了我,但是等我把钱真正拿到医生手里时,我新的担心又诞生了。
我在走廊外徘徊,不断地有病人从手术室被推出来,家属们迫不及待地冲向那辆手术车,夹着泪痕,夹着轻声的呼唤,我也木然机械地冲向前,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退下来,像潮汐的无意识涌动,我颓然地坐下,站起;站起,坐下。时空仿佛已经停止了,在那8个小时里我觉得这座城市已经陪着我停止了转动,我的脑中没有了一切,空气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挤压我,我退着向后,我抱着头逃遁,我眼前不断闪现血肉模糊的继父的形象,我的手又开始颤抖了。
我的恐惧像来自医院的特殊气味,我把头伸向窗外大口地呼吸一口气,但不经意间就看见了外面灰白的天空,那死气沉沉的天像大病未愈的脸,我赶紧关上窗子,拉紧衣服,靠墙根坐下,走廊里只剩我一人了,灯光已经亮了,惨黄!灯光下我觉得身影在变异,不规则地投射在地上。黄昏的来临像鬼魅一样不期然而猝不及防,我的嘴唇焦干,感觉一股一股的烟正从心底蹿上来。终于见到继父了,在手术床上的他面色蜡黄,说实话那分钟我只想说声上帝保佑,我的心仿佛走出了黑暗的甬道来到了明媚的阳光下,我和他的关系可能从没这么亲密,我俯身问他疼吗?但是医生阻止了我,他们说他的身体太虚弱了,所以手术时间长了些,比起一般的这类病人要长出好多,我想说就是这长出的几个小时,我的心灵已经走入炼狱。感谢上苍垂怜,也庆幸继父挺过来了——人生中的大苦痛,我则经历了人生中的苦痛历练。
经历一场生离死别一样我觉得自己空前坚强起来。于我来说,人生中似乎没有能超越这次苦痛的了。
人生之路漫长,也许就是在这一段又一段的苦痛压迫中我们才慢慢走向成熟,心灵之舟负载的所有折磨和疼痛都是对灵魂的洗礼,没人喜欢,但是你总会遭遇。无人能幸免。

叶永青 喜悦 布面丙烯 200×200cm 2007
假 象
我的生活充满伪饰,也许不应该这样说,因为我不是演戏的,我生活在真真切切的世界上,但是面具后我总觉得自己在欺骗自己,我呈现给别人的都是一种假象,我的一切裸露在面具里,我本真诚的人,说话办事给人的都是表里如一的印象,所以即使我偶尔在别人面前表现的不是我自己,他们也只会瞬时惊诧一番而已。
我的老同事,他们从我原先工作的地方来。我们高谈阔论,我装出在城市饱经世故、晓畅一切的样子,他们很是相信我说的。一天我们一起出去办事,因为我来城里有些时日了,于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对那些大街小巷熟悉得不得了,偏偏要找的那个地方甚为隐蔽,很不起眼,我们一伙人坐在出租车里,我坐在和司机并排的前座,作为向导我似乎要比司机更熟悉这座城市的地理一样,我领着他们转了很多圈,最后连我自己也糊涂了,转哪去了?蛛网密织的巷子,同样高耸入云的高楼,让我感觉有点眩晕了,司机有些不耐烦了,他对于我这领路的失去了耐心,虽然时间每过去一段我们总要付给他钱,但是他急躁万分,仿佛我们要赴的是火线,最终我们一伙人不得不从车里出来,阳光把我的眼睛刺得生疼,偌大的城市我随时充当的还是那个迷路孩子的角色,我尴尬地笑笑,说几天不来,这片好像增加了许多高楼。
其实谁都清楚,大楼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耸立起来的,但是这苍白的谎言总能让我虚弱地活着。他们眼里的我和真实的我完全是两个人,他们寄予我的期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多。我本就是从乡下的天空飘来的一粒稗子,不可能对于城市的肌理那么清楚。有人说女人天生没有方向感,其实我也缺乏方向感,我甚至对着徐徐西沉的太阳傻想:这太阳怎么还悬在南方就下沉了,城里的方向难道和乡下不同?原来是我迷失了方向,根本就是同一颗太阳落向同一个地方,是我的感觉发生了错位罢了,可是这些我都不敢让别人知道,知道了,别人会笑话的,一个大男人居然会犯这种错误,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于是我愈来愈会伪装,最终就愈不像我自己。
记得那天我在翠湖边上绕了很多圈,腿几乎都瘦了一圈,我从下车的位置走,按正常时间十分钟就能到我朋友那,他从接到我电话时就到门口张望,直到一小时后他才见到我,他说这一带治安好的嘛,我还以为你遭遇抢劫了,我们这你来过几回了?我说我的确迷路了!他说不会吧?来前你吃了迷魂药了?我说我眼里这样的楼太多了,每幢都是一个模子,我眼睛都看花掉了,我数着门牌找来,差点被保安抓了去,他说我像溜墙根撬锁的。他将信将疑地打量我,最后说,天啊!这种错误你都会犯,把你丢亚马逊丛林里看来你只有等死了?!我说,估计我在亚马逊活不了一个时辰,在一个中型城市我都难以生存,不要说在热带雨林了。我的神经脆弱得像焦糊的纸,经不起什么折腾的。
以前的朋友往往以为我是一个百事通,什么都会来问我,但我知道的实在有限。朋友打我电话说他要买一台电脑,在下面买贵不说,缺乏参谋,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说专家?!你封的啊,我只不过比你多用了几年电脑而已,啥时成专家了,他说甭管什么专家不专家,我就信你了,我把钱拿给你,你一定要帮我买!后来他果然把钱给了我,我也就冒充专家去帮他买了一台,总之那是品牌机,人家不是卖一天两天,里面没有什么“水分”的,但是电脑拿到家就出问题了:网速慢,桌面打开半天不显示……无数的问题出来了,怎么办?问我这“专家”啊,但是对于症状的解决,我又不在电脑跟前,只能无关痛痒的说了很多对策方法,毛病依然无法消除。朋友说我以前觉得你对电脑挺内行的,特别在城市里,对于这些不是小菜一碟,我说我不是什么狗屁专家,你硬要我买,问题出来了吧?你自己愿意舍近求远跑省城来,俩人理论半天,不欢而终。他怀疑我的能力或者眼力,我呢倍觉冤枉,在他眼里,我既然每天都对着电脑,就应该是专家学者,而事实上我只会操作,不会那些“修理”方面的东西,妻子也埋怨我。我说招谁惹谁了,出力不讨好,妻子说,哪个叫你每天装作什么都懂的样子,你给人的印象就是那种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间还研究着空气的人。天啊!这种欺骗性的印象,居然是别人给我下的结论。
有很多时候,我在思考像我这样的人在这个城市究竟还有多少,究竟什么误导了我们要在很多时候装作什么都懂的样子,其实是生活!整个社会都在召唤全知全能的人,不然什么“点子”公司不会出现,在人才招聘上,要我们精通这,精通那,其实我们究竟对于这纷繁的社会知道多少,鬼才知道!我们懂的东西局限于我们有限的认知,我们的视线里假象尤其多,我们的迷惑伴随我们漫长的一生,所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你眼睛看到的全部,还要用你智慧的心灵去判断。
这些就像我参加的一次报社招考中出现的逻辑判断题,是谬论还是正确判断,答案在内心深处。我们很希望自己生活在假象之外,但是现实就是樊笼,我们无法逃离。假象依然存在着,于是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
转 身
一转身全世界都变了,所以古人才会说,“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人生轨迹就此改道,跌入往事的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转身成了追悔,转身间爱人走远,亲人离散,紫陌红尘,红颜青丝染白霜,童稚少年成老弱,人生在转身间如饮隔世的苍凉。有时我们因不得已而转身,有时我们因错误而转身,轻轻的一个动作,微小的一个举动,我们已来到幸福的门外,再去推那扇我们转身后才发现的幸福之门,却看到那门已经生锈;那个心仪已久的女子,你用整个生命去爱的人,囿于你的羞涩,你没开口,转身离开,你发现她也是那么爱你,可是你们都选择了转身;我们挚爱的亲人在我们转身远离的时刻,被埋入时光的深处,我们无奈的手做出的是凄凉的呼救。这世界很多时候不容许我们转身,我们没有回旋的余地。
记得我小的时候顽劣异常,那时的我不知道什么是我要遵守的,什么是我应该惧怕的。我偷邻居家的桃子,趁着暗夜在高高的树上攀爬;我领着一伙我的死党拔了那可恶异常的老太婆家的荚豆;夏天到来,尽管父母一再叮嘱我不能到水塘里去,但我依然在里面驰骋纵横,不亦乐乎;最后我和村里大我几岁的二流子成了朋友,伙伴侧目,大人摇头,一时间我似乎成了人人觉得不堪的人。那个下雨的午后,我和他去村子西面的破窑烧蚕豆。这次烧蚕豆,严格意义上说,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假如那时我还为自己负责,想想将来,但是那时我没有要为自己将来负责的打算,那时尚属懵懂无知啊。
其时,我母亲带着我一人在云南,继父在河南,继父的姐夫,也就是我的大姑父在他唯一的儿子遭遇车祸后,打算把我接到昆明去接受最好的教育。因为我的这位姑父当时在云南省供销社工作,云南省供销社那时是个富得流油的单位——这自然跟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国情有关。他有这个能力给我接受最好的教育,他会把丧子之痛后的全部爱转移到我身上,甚至还准备把他的第五个女儿嫁给我。我们间是无血缘上的半点牵连的,这就好像荣华富贵一下子堆积在我面前一样。那天母亲把我在昆明要穿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折好放好,我回来就可以和大姑父上车去昆明了。但是那时我正和那个所谓的二流子大朋友忙得热火朝天,蒙蒙细雨里烧蚕豆的香味粘住了我的脚步,我想不出这世上还有什么会比烧蚕豆更有趣的。假如我转身回去了,不吃什么狗屁烧蚕豆,那么我以后也就不会遭遇一系列的人生磨难了,但这世上没有“假如”,只有事实,既定的事实,无法改变的现实。大姑父等了一下午,因为急着赶时间,他开着车走了,那一走把我人生轨迹拖得变了形。直到今天他还在说我,因为现在我们都在昆明。但我能在昆明,是我兜了很多圈子,吃了无数苦头才来到这的,如果当初跟着他来,那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地地道道的昆明人了,也许我也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市民,但这倒不是我希望的。母亲在那时不是咒我,而是“嫁祸”于烧蚕豆和那个大我很多岁的朋友,虽然这二流子朋友而今已长眠于地下。而我丝毫不怨他,我在多年以后把一切归于命运的安排,我就是多灾多难的命,像唐僧取经一样,不遭够那么多难,似乎难成正果,但想想命运之神究竟在哪谁说得清。
后来我读了高中,那时我在河南的商丘,古时称为归德府的地方。生活的艰苦不说了,生活了十多年我居然还是一个黑人户,在高考来临前我回了云南。那时和继父的关系异常紧张,家庭困难,所以按庄户人家的逻辑我应该回家砍柴拉石头挣钱娶媳妇,过平常日子,但是考虑到我自己不是那块料,文弱书生一个,我不打算做个庄稼汉。我和继父的关系开始冰冻,我去丽江打工时他写信给我,叫我去当兵,离开他了,他仍然不放过我,我感觉到窒息,人生的路该由自己选择,他为什么就要时时安排我呢!我坚决不去,连信也懒得回他,现在想想也许他的想法是对的,如果我去部队,凭着我能写点小东西,在那儿或许就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因为我从小就想当兵。小时候我在青岛看到海军时我还央求母亲给我买了一套海军服,穿起来甭提多神气了。干什么事你首先要感兴趣,兴趣可是最好的老师,但是为了和继父赌气,骨子里的那点倔强让我头也不回。再后来由于交不起学费,上了师范学院,成了自己做梦都没想到的老师,一不小心,育人六载。当老师有当老师的乐趣,现在我的学生遍布昆明各个大学,这或许也是一种欣慰,但总觉得和儿时的理想差之甚远。转身的错与对我实在说不清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那些错误的地点,不,地点也许从来没错,只是我们站立的地方错了,于是我们再来一个错误的转身,一切再也无可逆转。
记得前几天在《辽宁青年》上看到一篇文章叫《你敲门了吗》,故事说一个来自农村的、才华横溢的少年,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班里一个气质高雅、美丽脱俗、家庭背景很好的女孩,女孩也十分仰慕他的才华,俩人一直保持着那种纯洁的友谊,但是谁也不愿捅破那层窗户纸,男孩出身农村由于自卑,女孩则因为矜持。女孩在毕业前的一天告诉男孩,她家里人都出去了,暗示了男孩,男孩憋在心里的话终于有机会表达了。但是男孩按照女孩给的地址找去,按了很多次门铃,却没人来开门,于是他伤心地离开了,认为女孩只不过随口说说而已,自己怎么就当真了呢!很多年后已为人妻的女孩告诉孑然一身的他,那天是她家的门铃坏了,她忘记告诉他了,他只要敲敲门,而不是转身离去,那么心仪已久的女孩将属于他,幸福之门将不会再关闭,转身间红尘中他少了相伴的知己,也多了一位伤心的红颜。一个转身,爱人们从此南辕北辙,冥冥中似乎总有声音在喊,转过身来啊!只可惜世间多少伤心人没有回头,却只会哀叹。
来到陌生的城市后,天天疲于奔命,家的概念似乎淡了,父亲重病,回了三趟家,每次转身离开总抱着幻想,总以为他会好起来的,最后一次看到骨瘦如柴的他,我有种预感,但我没有在预感下留下陪他,他不知能否挺到我再次回去看他?已经无法言语的他做着手势,那个手势或许就是挽留,但是我为了工作离开了。那个转身带着多少残酷的意味哦,我至今无法衡量,压在心上隐隐如巨石般,弥留之际我没能在身边,入棺时我没能看看他,于是从此阴阳殊途。我无法原谅自己,每个我的心能腾出清闲的日子,我总要燃一炷心香遥祭他,弥补我曾经的转身之过,疗我内心深深的伤。
莫转身,可我们还是头也不回,甚至义无返顾;莫转身,但我们还是固执己见,甚至自我辩护;莫转身,而我们仍然勇往直前,甚至错误献身。纷繁尘世,诸般迷障,理智转身,莫在转身后嗟叹,莫在转身后呼喊,上苍耳背,听不到这些。转身是自我的选择,谨慎点,小心点,彼岸的花香自然就会飘来。

叶永青 姿势 版画 150×600cm 2007
黑 暗
我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条黑暗的甬道,我们一生都在试图从甬道中突围出去,所以我们犯了错误。所谓的错误其实就是黑暗的外在显示,有些人甚至走向了极端,比如诗人顾城。这位外表文弱白皙的天才诗人,你无法想象他会向自己的妻子举起利刃,那可是结发妻子啊,但他终究砍下去了,黑暗将他自己也送入了极端:他也死了,归入永久的黑暗中去了。人们无法理解左右这位天才诗人的“恶魔”是什么,连我这位很不爱诗的人也为此感到震惊;海子卧轨自杀了,从诗歌之神的手里接过死亡令牌后,他从我们的视线里永远消失了,在内心黑暗的驱动下,他不顾亲人的悲恸和绝望,把身体交付给冰冷的铁轨,他解脱了,后人却无法解脱,很多的人还活在他的诗里,寻找着他卧轨的答案;三毛随荷西去了,在遥远的撒哈拉,她把和荷西的爱情经营得像热情的沙漠,也许在她的生命中不会再出现另外一个荷西,抑或再找不到活着的理由,连民歌大王王洛宾也无法给他歌声之外的另一半,于是他走得匆匆而决绝。
走入极端的他们依然在黑暗里徜徉着,而我们呢,我们内心那块阳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呢?它在哪里?它在哪左右着我们?我们不清楚,黑暗不是因为夜的来临,是我们内心总有背阴的地方,我们无法告知别人,因为它在我们身后,在适当的时候它会潜入我们的内心隐蔽起来。我们宝贵的躯体总是在黑暗的包围中输给所谓永恒的灵魂,这一切人们惯常的说法是“无常”,这个无常鬼躲在冥冥中。其实冥冥就是我们内心的某个角落,无法抗衡的命运似乎永远游离在我们之外,真正的却是驻扎在心灵里,于是心理学家说我们要突破自我。其实我现在才明白,那个自我就是内心那个黑暗的角落,突破说白就是向黑暗宣战,可惜很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突破自我。

叶永青 画鸟 布面丙烯 200×150cm 2008
小的时候很怕黑,天一黑更甚,那时还没有电灯,煤油灯的光源总是覆盖不了多大的地方,而且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些长长的影子比我们的身体大出几倍,起初也许我们的怕就是那些拉长的影子造成的。加上大人爱讲鬼故事,吓唬哭闹的我们,于是我们在黑暗中噤若寒蝉。那时村西的山坡上埋了许多人,大人们就发挥各自的想象力说那些鬼会在晚上出来狂欢,和人过节一样,那时不明白鬼为什么要那么高兴,出于恐惧,也不敢问大人为什么鬼要天天出来狂欢,难道鬼认为自己和人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是一种解脱?经常有晚上出去放田水的人会碰到鬼,甚至连我舅舅都说他在村西的三观殿下见到了鬼,当时那鬼向他借火,我问鬼借火干嘛?舅舅说能干嘛,吸烟呗!哦!我似乎明白了,觉得这鬼也是个烟鬼呵!不然怎么敢跟人借火。但是我又问,不是说鬼怕火吗?舅舅的回答似是而非,你说半夜三更的,哪个人会在那荒郊野地里,而且我刚把火把凑过去,那鬼打了个唿哨,倏忽就不见了,你说那不是鬼是什么?而且人怎么能在崎岖不平的河道里跑那么快?小小的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如此迅捷,于是就姑且相信世间有鬼。
鬼是黑暗来临之后,在人们似乎进入梦乡的时候才开始活动的,这鬼界和人世间一样有好有坏,比如向舅舅借火的可以称其为无伤人恶意的鬼,而有些鬼则像世间的恶人,它会处处与人作对。
大人们在我们恐惧的基础上告诉我们,晚上,特别夜深的时候,有人叫你的名字,千万不能答应,一答应,你的魂儿就会跟鬼一起去了,鬼让你坐轿,也就是把你丢在刺蓬上;领你往墙上撞;让你往井里跳……好家伙,这些可差不多全是致人死命的举动啊,这鬼真是可恶!但是我们又对他们无可奈何,活动在黑暗里的他们有超乎人类的伟力。于是小时候自然而然地怕黑,大了以后才知道这些都是生理上的惧黑,其实我们不可能在白天把所有的事情做完,很多事情还要在夜幕降临后来做。譬如走夜路,我一个人有一次走了很长一段夜路,那段路据说有很多鬼出没,但是为了回家我还得走,最终我克服内心的恐惧走完那条路,没碰到鬼,慢慢地我发现其实外界的黑暗给我们造成的恐惧远远不抵内心的黑暗,走不出内心的黑暗,我们将永远陷在自我的泥淖中无法自拔。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的增多,那些生理上的黑暗恐惧逐渐远离了我们,困扰我们内心的黑暗却越来越多,大面积地在我们的心里延展着。
高考结束,我落榜了,我是平时师生认为的优秀生,平时的荣誉让我负载了太多的期望和责任,能考上是自己的荣耀,也是别人的安慰,考不上别人失望都在其次,无法原谅自己才是致命的。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黑暗里,我似乎感觉到黑暗已经笼罩了我的世界,我似乎能听到胡子生长的声音,几天下来我苍老了一大截。接着我只有外逃,我到那个没有几个人认识我的地方躲藏了起来,后来我发现无论我躲在哪里,我终究无法躲避我内心的黑暗,终究无法突围出去。暗夜里程海湖在晚风吹拂下,扑向岸边,发出巨大的空响,躲在工棚里的我总感觉自己被什么淹没着,想到未来的不可知,前途的不可测,人生航道中种种的艰险,我从来没感到过如此沧桑和失落,整个世界都在陷落,最后我成了孤岛,孤岛则陷在永恒的黑色海水里,漂流到哪儿都是黑暗。最终我战胜了黑暗,因为我还要用高考证实自己,最终漂流让我找到了停泊的港湾。
第二次黑暗袭来是在我进入教育岗位的次年,那年我和电视台谈妥,台里同意接收我,当时我的理想也就是当一名翻译或者记者,能进入电视台我也算夙愿得偿了。然而我们的上级领导不给签字,不能按正常调动手续意味着我就要出去打工,饯行的饭也吃了,人却没走成。一个学校闹腾得沸沸扬扬,一个小小的乡镇几乎都知道我要出去,但是最终没有出去成,那段时间总觉得自己像过街的老鼠,这种奇怪的感觉让我的工作激情几乎降至冰点,谈了多年的女朋友在这时也和我发生最为激烈的“战争”,我不是那位能一苇渡航的达摩,无法渡自己到彼岸。内心的黑暗像汹涌的海水呛得我灵魂颤抖,最后是那句“既来之,则安之”的古话救了我,人生的种种不如意似乎总能击垮我们,于是在自我的安慰与疗救下我度过了人生的第二次黑暗。
从生理上的黑暗畏惧感到心灵上的黑暗畏惧感,其实每走一步我们都在成熟,黑暗无处不在,但是最终它都要潜入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智慧双手拨开那厚重的窗帘吧,让窗外的阳光洒进来,再拿起那洁净的拂尘掸去隐匿的黑暗,我们的心一定会充满光明。
驱除黑暗似乎有史以来就是我们的大事,而今还是,将来更是,因为人类越发展,自我的障碍就越多,我们内心的黑暗也就越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