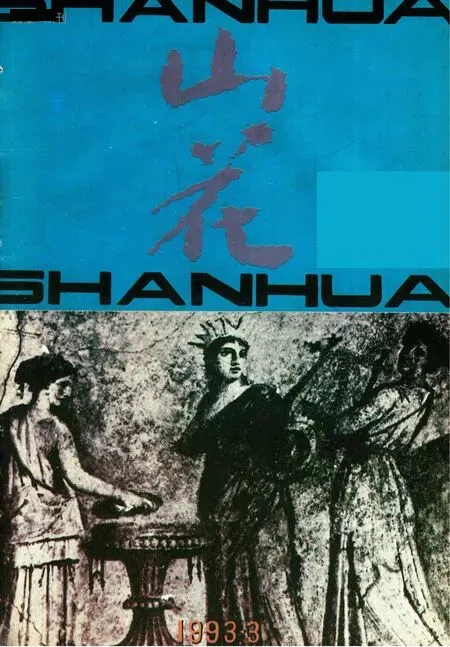知识分子:过期的死亡宣判
何同彬
知识分子:过期的死亡宣判
何同彬
1990年代开始于知识分子的所谓的“带有理性色彩的战略性退却”,虽然经过短暂的学术化修整和市场化炼狱之后,他们又以不同的身份和姿态重返“公共领域”,但一切都已不同,国家和政党意识形态作为1980年代的自由的对立物已经转化为更为潜隐的权力机制,借助于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市场法则对知识分子的物的依赖性的“培育”,它们的控制能力更加强大起来,但却在整个社会的表象上形成了一种多元和虚假“自由”的景象。从本质上讲,1980年代与1990年代并无实质的不同,前者被始终想象为一种知识分子处于中心地位的理想情境,如今愈发显得荒唐。“80年代的主题是所谓的人的解放,人从各种网罗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对自由的理解核心是解放。事实上,80年代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时代,这个抽象的、自由的、摆脱了各种束缚的人,因而也是以知识分子形象的自我理解来设计和想象的,而到了90年代,当社会从国家中部分地游离出来,以市场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世俗法则时,80年代的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就转化为社会与国家的想象性二分,而在这样一个市场社会中,社会的中心在一些思想者看来,当然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因而也形成了一场市民社会的大讨论。”[1]以上的分析与论断是一种没有多少事实依据的知识想象,这在1990年代以来的思想史语境中成为一种话语生产的惯例。1980年代是如何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呢?事实上,1980年代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只是意识形态统治策略的权益之计,并且密切关联于当时并不完善的、单一的公共空间的建构形式,而所谓的中心无非是众声喧哗的声音比较集中和热烈而已,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什么“抽象的、自由的、摆脱了各种束缚的人”。或者更为确切地说,1980年代并没有为19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和自由行动树立什么可行的策略和典范。1990年代之后的世俗法则的建立事实上深刻关联于知识分子的“战略性退却”,他们的责任感的放弃给世俗法则的建立扫清了主体反抗的障碍,所谓的中产阶级并不存在,即便存在也只是一种物质基础的身份象征,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文化建构的“中心”,也无法替代原有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功能。但199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话语的表述逻辑日渐陷入一种悖谬的语境之中,即一方面是知识分子话语的不断繁衍、更新,深刻地关涉到任何一个阶段的思想论争和学术讨论,以至于形成一种“知识分子学”的显学的地位,各种著述、研究、对话和争论层出不穷,甚至于某些学者以“知识分子研究专家”著称;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功能却日渐衰退,并在公共知识界和大众视野之中遭到广泛的质疑与诟病。这种悖谬语境的形成实际上已经动摇了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言说,甚至于应当像福柯那样反省知识分子这一虚拟的主体是否真实存在[2],或者至少应当对知识分子及其相关价值进行一个深入的反思。但是反思不能仍然通过新的话语和知识的形态来进行,而是要剥去攀附在知识分子话语之上的历史和知识内容,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话语反复中撤离,回到一个价值主体的实践行动的抉择上来,这才是1990年代至今知识分子话语失败的本质所在。
齐格蒙·鲍曼是这样来定义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一词乃是一声战斗的号召,它的声音穿透了在各种不同的专业和各种不同的文艺门类之间的森严壁垒,在它们的上空回荡着;这一词呼唤着‘知识者’(m enof k no w led g e)传统的复兴(或者,可以说,这一词唤起了对于这一传统的集体记忆),这一‘知识者’传统,体现并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这三者的统一。”[3]他在这里提供的知识分子的定义包含了这样几个重要的价值元素:战斗、集体、知识、真理、道德和审美,而且强调了知识分子跨越专业和学科的森严壁垒的特殊性。而科塞的定义则着重强调了知识分子天生的“反抗”意识:“知识分子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他们‘在一个社会内诱发、引导和塑造表达的倾向’。……知识分子是从不满足于事物的现状,从不满足于求诸陈规陋习的人。他们以更高层次的普遍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问,针对注重实际的要求,他们以‘不实际的应然’相抗衡。他们自命为理性、正义和真理这些抽象观念的专门卫士,是往往不被生意场和权力庙堂放在眼里的道德标准的忠实捍卫者。”[4]事实上,以上两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并没有超出我们对知识分子理解的范畴,也即属于被利奥塔等后现代学者质疑和宣告死亡的传统知识分子或者普遍知识分子的形象,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文化语境所试图建立或破坏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一种形象。但是,理智地看待知识分子的价值命名,我们不得不某种程度上认可后现代对这种知识分子普遍价值的主体形象的质疑,因为这里面的确矛盾重重,几乎把主体的缺陷和局限性全部抹去,留下了一个极端理想化和抽象化的价值堆积。所以,我们可以更为明确与清楚地意识到:知识分子是一个集体性称谓,一个价值共同体的命名形态。因此说,看某个个体是否是一个知识分子首先要考察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有没有这种价值共同体存在,而且这一共同体一定要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建构和价值选择起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倘若并不具备这样一个集体性的共同体,那一切关于知识分子的言说都是虚假的、毫无意义的。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话语的建构与争论并没有深刻地认识知识分子的这种集体性,尽管他们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但在他们的意识之中构成知识分子集体性的是一个虚构的、由不同时代的典范组合的知识分子的“神谱”,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想让这一话语有什么具体的指涉,只要能具备抽象的价值功能、只要能具备新的话语生产功能就足够了。所以,当我们谈论知识分子的时候,必须要认识到这种集体性称谓的价值共同体里面真正能够容纳哪些人?而且是哪些目前在语境中存在的人?自己是否能成为这样一个集体性价值的彰显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言说者?事实上,在我看来,1990年代以后一个边界泛滥化的知识分子群体没有谁能够真正面对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语境是一个本质上扼杀和对立于所谓的知识分子代表的价值的,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存在这样一个价值共同体的话,那么整个思想界应当呈现的是一个同仇敌忾的“浴血奋战”的场景。而事实上,知识分工的细化不但不再可能促使一个统一的、普遍的价值共同体的形成,反而愈来愈促使他们内部的分离、对立和相互指责,他们唯一的共同体是“体制”,一个根本上背离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价值的更强大的共同体。但我在这里并不想拣拾后现代解构知识分子话语的牙慧,因为后者在中国的盛行根本上是一种话语的破坏性快感而已。

叶永青 狂热 布面丙烯 200×150cm 2009
在“人文精神讨论”中,陈晓明和张颐武作为后学在中国的代言人,利用福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对“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进行了理论上的拆解,认为所谓的“人文精神”不过是启蒙知识者“最后的神话”[5]。陈晓明认为,对于“人文精神”这一神话而言,“没有人能对此有所怀疑,确实,这种反诘是致命的:难道人类可以没有理想而存在下去吗?没有人文精神,人类还成其为人类吗?又因为追寻‘人文理想’,而使得这种叙事,这项学术事业和相关的活动变得尤其高贵。在这种追寻中,思考者终于贴近了生命本性,进入人类生存的精神深处,这个思考着的主体甚至变成神,变成真理的天然解释者和占有者。它高大伟岸的姿态呈现于现实的思想舞台之上,它当然有权力,有资格和理由向民众示范和启蒙。谈论这样一种知识,进入这样的知识谱系,知识的意义和价值自然投射到讲述者身上。他们顺理成章被指认为或自我认为一些思想深刻的人,有责任感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民族的脊梁’和希望所在。”[6]他的质疑与嘲讽无疑是深刻且“犀利”的,但他所针对的语境也是其自身所处的语境,他自己也是这种症候的共有者,这种解构又何尝不是一种“知识谱系”,何尝不是试图投射“知识的意义和价值”于自我的知识叙事之中,何尝不是想彰显自己是一个“思想深刻的人”呢?一味推崇“人文精神”、阐释知识分子立场却缺乏任何有建设性、反抗性的行动的知识者,固然是需要奚落与嘲讽的,但传统知识分子命名中所承担的价值应该由谁来承担呢?主体的解构如果蔓延到价值和责任本身的解构上,那不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虚无主义了吗?最终,解构“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同样进入了一个繁衍虚假知识的谱系之中,并且表现出了比他们所要解构的谱系更为武断的话语想象能力和批判热度:“它与一种神学化的写作倾向相结合,以彻底否定今天的世俗日常生活为特征,变成了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宗教式的否定,变成了与肯定人的欲望和正当物质精神要求的人文主义情怀极端对立的狂躁的神学精神。它导向了一种中世纪式的对于技术发展与现代文明的否定性的表述,它显示了对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进程的恐惧与逃避的清晰。”[7]“世俗日常生活”、“宗教式”、“神学”、“人文主义情怀”、“中世纪式”、“市场化”、“全球化”等等,本身尚属需要论证和阐释的话语形态,它们的“所指”模糊而空洞,组合起来同样是一种神学精神:“市场化”、“全球化”、“世俗日常生活”真的那么值得信赖吗?如今距离以上的论断已经十几年了,“市场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真理、道德和审美的堕落由谁来负责呢?至于寄希望于世俗日常生活自身繁衍抵抗意志和价值创新就更是荒诞不经的了,1990年代以后日昌的“大众文化研究”就明显表现了对文化堕落的曲线肯定:“如果我仍关心中国文化的现实,我就不能无视大众文化,因为90年代以来,它们无疑比精英文化更为有力地参与着对中国社会的构造过程。简单的拒绝或否定它,就意味着放弃了你对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重要部分的关注。……必须把它放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来,放入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中来。所以在一段颇为痛苦的反省和重新思考之后,我开始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大众文化研究上来。”[8]如今看来,戴锦华对“人文精神”论争的这种反思性的学术转型毫无意义,大众文化研究已经开始了这么多年,它给大众文化带来了什么?大众文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逃避责任的追问,到新的话语形态中寻求价值上的虚妄的安慰并不是解决知识分子现实障碍的合适的手段,否定现实语境中的知识分子的知识谱系固然有足够的理由——它的确没有给它所应承担的价值功能带来多少进步,但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价值进步与观念建构的力量由谁来继承呢?因此,对于知识分子话语的日益的失望重又唤起了许多人对精英阶层的现实的否定与厌恶,转而再次在下层民众和传统儒家文化那里寻求精神资源:“在道德上,这种‘德’与‘仁’的精神资源,绝不能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获得,而必须在小民百姓中挖掘。我一贯认为,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的成分。他们本质上都是韩非理想中的法术之士,自以为掌握着某种国家理性,总想着获得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干预老百姓的生活。钱穆和鲁迅,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在人格和学术上都属于保守派或激进派之中的佼佼者。但钱穆对中国历史的吹嘘,如同痴人说梦;他对西方民主和中国传统不相融的判断,也早已被东亚民主化的进程所否定。而鲁迅对老百姓的冷血,更不应该在未来中华文明中有任何位置。知识分子的精神被主专制腐蚀至今,几乎无药可治。”[9]这种对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否定虽然略有偏激(譬如对鲁迅的论述就过于武断),但却很大程度上触及了知识分子问题的实质,只是寄希望于小民百姓和儒家“德”与“仁”的资源的方式并不新鲜,不过是融合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而已,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很难行得通。因为底层和大众的道德感是自发的,在我们这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之中,显然缺乏持存性和持久性,值得褒扬但不值得信赖。毕竟,真正掌握这个社会权力的人是知识者,尽管目前知识分子的道德感的确无法像他们的知识话语那么有说服力,甚至可以说,知识分子的寡廉鲜耻已经到了令人愤慨的地步,但我们仍然要信赖那些掌握知识的人,这很无奈,但却比寄希望于民众要好得多。毕竟,对黑暗时代的真理所负有的责任必须要有承担者,而这个承担者仍然是知识分子——我们权且延续这个过时的命名。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尽管当代法国哲学家利奥塔一再声称,与先前的‘近代’相关的‘解放与启蒙的宏大 叙 事 ’(g rand narrati v es of e m an c i p ation and enli g hten m ent)这类雄心壮志在后现代的时代已不再通行,但我相信上述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依然成立。根据后现代的看法,宏大叙事被具有地方特色的情境 (lo c al sit u ations) 和语言游戏(lan g u a g e g a m es)所取代:后现代的知识分子现在看重的是能力(c o mp eten c e),而不是像真理或自由这类的普遍价值。我一直认为利奥塔和他的追随者是在承认自己的怠惰无能,甚至可能是冷漠,而不是正确评估即使在后现代主义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仍然有着许许多多的机会。因为,事实上政府依然明目张胆地欺压人民,严重的司法不公依然发生,权势对于知识分子的收编与纳入依然有效地将他们消音,而知识分子偏离行规的情形依然屡见不鲜。”[10]“怠惰无能”、“冷漠”,在中国的语境中或许还要加上一个“怯懦”,应当是那些无情解构知识分子责任意识的知识者所共同拥有的现实“障碍”。解构的知识效力已经发挥了它最大的功能,在中国的语境中也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但我们所痛苦的仍然是一些道德的堕落、真理的迷失和审美的扭曲,我们所仇视的仍然是遮蔽和压抑自由、真理和道德的各种权力机制,所以,于人性而言,于知识者而言,这样一种诱惑非常强烈但并不可取:“从世界及其公共空间转到一种内在的生活中,或者,完全忽略这个世界,而去热衷于一个幻想的‘应然’世界或曾经存在过的世界。”[11]这无疑是一种浅薄的精神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索取,而忘记了所有自由的基础是“行动”,因此对于1990年代以来愈来愈热闹的关于知识分子重返“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的阐释和论述,最终因为实际“政治”行动的缺失,再一次沦为一种简单的知识和理性的无意义累积。因为,对于中国“公共空间”的建构而言,简单的知识引进与理性思考并不能撼动现实体制的顽固与僵化,对知识和理性的盲目信任、对西方时髦话语的空洞和无节制的阐释,都不可能起到建立真实的“公共空间”的政治功能,事实上不就是这样的吗?政党意识形态些许退让和改良都是以其它方面的压制为代价的。事实上,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并不是1990年代特有的境遇,我们根本就没有建构过良性的公共空间;而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再度边缘化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是边缘化的,当他们自认为不再边缘化的时候,也即他们出卖和丧失立场的时候;至于什么“后现代”理论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解构,如上所述,在中国的语境内无非是显现了主体的逃避而已,与那些空洞褒扬知识分子立场的知识者没有区别。所以,中国语境内的“公共空间”的思考和期待就如同下面的论述一样,充满话语上的矛盾和无关乎实际行动的空洞指涉:“在当前社会的语境下,知识分子应该是这样:当他对社会公共问题发表意见时,首先他是专家,他在社会某方面有一定的知识权威性,比如生态学家在生态问题上就具有权威性。……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你总是要具备若干相关的知识,这才具备对与生态相关的各种问题发言的基本资格。其他社会阶层也能发言,但他们往往是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但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个人也许与这一公共问题没有丝毫的利益关联,但他必须从公共立场出发,依据自己超越性的知识背景,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公共分子的职业道德在于,当他就公共问题发言时,不能以自己的个体或群体的利益需求,而是应该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做出自己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如果掺杂了个人利益,那仅仅是作为一个自利性的社会成员,而非超越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12]在中国,一个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和发言的资格是由谁赋予的?他发表意见的权利与媒介由谁来指认并许可?一个没有丝毫利益关联的公共立场如何表达?由谁来传达?知识自身是否能够产生“良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如何实现超越性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分析?有多少知识分子在“自私自利”面前是免疫的呢?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无意义的、缺乏现实行动的“公共空间”的学术论述本身,就是对中国脆弱的“公共领域”的伤害,人们从这些论述中窥测到的仍然是知识和历史帷幕后面的懦弱与逃避。说到底,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障碍仍然是一种最原始的障碍,只是披着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外衣而已,那就是物质欲望及其衍生物,诸如荣誉、权力等,这也是他们最为本质的政治障碍,也是意识形态得以控制他们的最基础的屏障。

叶永青 涂点彩 布面丙烯 200×150cm 2009
正如韦伯所说的:“自从禁欲主义试图重造尘世并在俗世中实现他的种种理想以来,物质财富获得了一种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未曾有过的、愈来愈大且最终变得不可抗拒的统治人类生活的力量……禁欲主义的后继者——启蒙运动——那玫瑰般的乐观情绪,似乎也在不可挽回地逝去,而职业义务的思想亦像宗教信仰的死魂灵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四处游荡。如果完成某种职业不能与最高尚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念直接相联,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假如它根本就无需使人感到是一种经济压迫力量,那么人们一般就不会做出任何努力,去为它寻找存在的根据。”[13]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而言,这种概括难道不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吗?物质的力量越来越无法抗拒,就显而易见地削弱了知识分子的价值承担的可能性和可信度,而职业义务最终被纯粹的物欲统摄,不再构成与“最高尚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念”的真实的、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不断把价值和观念历史化、知识化的方式,来抽象地、隐蔽地遮掩知识分子日渐失控的“自私自利”和屈服、怯懦。知识分子话语的不断繁衍与其价值承担功能的衰退并存的悖谬语境,就是得益于知识和历史的隐秘的、巨大的网络。因为知识化和历史化之后抽象的价值言说仍然能在卑弱的知识分子那里培育出一种“真诚”的冲动,可以让他们“自私自利”的同时保持对自身道德立场的内心的虚假认同,他们像一群演技高超的演员,让自己的虚妄、虚伪在内心培育出一种别样的高贵来:“假象如何变成真实。——演员即使在最深的痛苦中,也不会最终停止考虑他的角色给人的印象和总体戏剧效果,例如甚至在他孩子的葬礼上,他将作为他自己的观众,为他自己的痛苦及其表达哭泣。总是扮演同一角色的伪君子,最终不再是伪君子;例如神甫,他们年轻时通常有意无意地是伪君子,但是他们最终变得很自然,那时候便真正是神甫了,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或者父辈没有走得那么远,那么利用了优势的子辈也许就继承了父辈的习惯。如果一个人长期地、顽固地想要显得是某种人,那他就很难是另一种人。几乎每一个人的职业,甚至艺术家的职业,都是以伪善、以一种外部的模仿、以对有效之物的复制开始的。总是戴着一副友好表情面具的人,最终会获得一种支配权来支配友好情绪,没有这种情绪,友谊的表达就不能实现——而最终这种情绪又支配了他,他就是友好的了。”[14]我们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像那些伪君子和神甫,他们在自己的不停的表演中,即那些不停繁衍更新、缠绕往复的历史与知识的网络内变成了这个时代最为丑陋的“真实”之一,藉此他们免除了精神和灵魂的自我拷问。于是,我们宣布知识分子的死亡似乎已经是没有多少争议的了,但死亡之后的价值承担者仍然是缺席的,而知识分子的言说和知识生产仍然是源源不断,结果就是,连对知识分子的死亡判决都被历史化了,死亡了,没有谁再来承担责任了,而大家都是无辜的。1990年代以来,西方的知识场域、我们的知识场域每天都有人在诅咒知识分子的堕落,宣布它的死亡,但这些迟到的死亡判决已经毫无“沉痛感”,只是一种更加痛快的“解构”而已。

叶永青 山雨欲来 150×200cm 2009
知识分子问题真的有这么复杂吗?显然没有,它本就不该成为一个学术问题,也不应该以如今如此热烈的话语方式出现在文化的场域之内。无论我们把这个集体性的“想象的共同体”称之为知识分子,还是知识者、人文主义者、批判者,无非都是把这个符号赋予我们所认同的那些可贵的持存性价值而已。但我们不敢直接面对这些价值,不敢为此而进行实质性的反抗与斗争,于是就把它们放置到一个可以被知识和历史填充的虚假的容器——知识分子——里面。“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15]何谓“正视”?并非冷眼旁观,并非是乐此不疲的不断的话语分析与阐释,而是首先要做一个真实的、真诚的、勇敢的“人”,切实把自身的知识转化为一种付诸行动的真理冲动,无论是否被冠之以知识分子的命名,他都实现了一个持存性价值承担者的责任。我们已经到了应当从主体历史化和不断接受死亡判决的网络中挣脱的时候了,当主体的死亡都无法唤醒我们的自由意志的话,这种空洞的判决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了。
注 释:
[1]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28页。
[2]“我并不觉得知识分子谈得太多,因为对我来说他们根本不存在。但是我确实发现谈论知识分子的倒是越来越多,我对此深感不安。”[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包亚明主编,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3][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导论),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前言),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5] 张颐武:《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作家报》1995年5月6日。
[6] 陈晓明:《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上海文化》1994年第5期。
[7] 张颐武:《人文精神:一种文化冒险主义》,《光明日报》1995年7月5日。
[8] 戴锦华:《犹在镜中》,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9] 薛涌:《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南方周末》2008年1月10日。
[10]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页。
[11] [美]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12]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13]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75、176页。
[14]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杨恒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5] 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