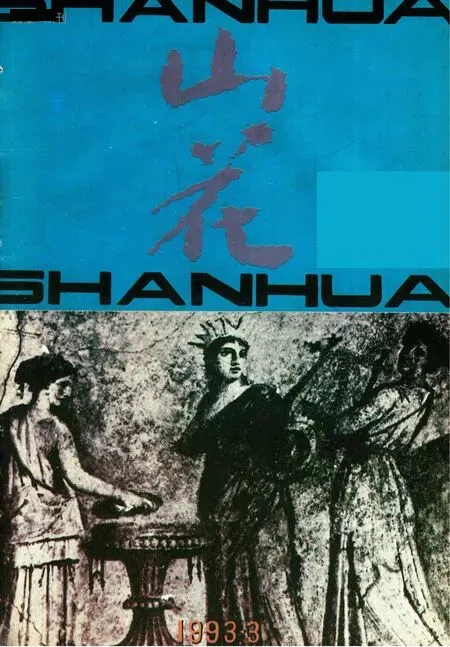传帮带
张学东
传帮带
张学东
清早下过一场暴雨,直到这阵子地上还残留着几汪银亮银亮的水。出租车的灯光从巷口猛然照射进去,那几汪寂寞的雨水仿佛受到了光的召唤,在不远处的水泥板上一晃一晃地跳闪个不停,跃跃欲试着,要从地上飘升起来的样子。
下雨的事起初折鹃红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时候她正在自己的房间里蒙头昏睡,前一天晚上陪客人出去喝酒,折腾到凌晨两三点才回来。她的酒量比起当初已经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了,她现在经常是喝完白酒喝啤酒,有时还可以再喝点干红或白兰地什么的。总之,她觉得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像一只坚硬的容器,随便什么酒都来者不惧。听说那场雨下得特别大,是入夏以来的头一场雨,后来还落了一阵指甲盖大小的冰雹,连路边刚开没几天的槐树花都被冰雹击落了,枝头看上去有些光秃秃的印象。通常,槐花开的时候,叶子还只是隐藏在枝梢上的十分细嫩的茸芽儿。
早晨的时候莎莎用手指轻轻掀开被角对她说,鹃子姐下雨了,你快起来看看,好大的雨啊!折鹃红没好气地哼了一声,翻过身又要睡去。莎莎却忽地爬到她床上一个劲摇她的头,莎莎说快起来吧鹃子姐外面下冰雹了!折鹃红真的有点恼了,眯缝着眼睛骂莎莎你是不是要死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有什么稀罕的!真是少见多怪。莎莎后来再没有喊她,折鹃红蒙在被子里依稀听见房门好像开了,从外面传来一阵丁丁冬冬的声响,接着门又被轻轻关上了。折鹃红嘴里不无怪怨地嘟囔了一句,这个小贱货,就又睡着了。
莎莎当然不是真名,莎莎的名字是莎莎自己给自己起的,鬼才知道莎莎原来叫什么名字呢。平时莎莎好像很痴迷那些当红的女歌星,有事没事总哼着那些女人唱过的什么歌,却总也把不准调的样子。莎莎刚来店里的时候多亏了折鹃红跟她搭讪。当时别人都不拿正眼看莎莎,嫌她身上有点那么个劲儿,具体是什么谁也没明说出来,好像是群体无意识地联合起来对付莎莎这个初来乍到的外地女孩。事实上,她们这里经常会有新的女孩从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过来加盟。这些女孩一般能在同一家店里做上一年以上已实属难得了,都喜欢四处打游击,所以,对新来的暗怀着生分。
那时的莎莎本来是到店里寻一个同乡姐妹的,可那个女孩半个月前就不辞而别了,没人能说清她究竟去了哪里,或者根本就离开了这座小城。莎莎扑空了。莎莎拎着两只颜色很艳的旅行包,傻傻地站在发廊里,站在那些穿着入时打扮俏丽的姐妹们中间,她的模样既单薄又拘束,还有一些土气。她的目光带着期盼和求援的味道从那些懒洋洋地深陷在沙发上的女人身上一一凝望过去。而别人的目光与此同时也在莎莎的脸和身上一划一划的,像是要掸落莎莎旅途中沾在身体上的那些汗味和风尘。不过,她们很快就不再看莎莎了,她们对莎莎不感兴趣。她们开始谈论生意上的事,谈论某个出手阔绰的老客,或者,她们通过明亮的落地玻璃门将目光转向外面的街道。这条街每天都是一样的,人车攒动,熙熙攘攘。她们的目光呈喇叭状,一般够不到很远,但还是能够看清楚街对面另外几家发廊的情况。偶尔,某个男士朝发廊这边漫步走来或在门前止住脚步,她们会像麻雀似的突然噤了声,眼巴巴观望着门外人的一举一动,抹得脆白的脸上有一种难以按捺的渴望与兴奋,就像那些超级球迷们苦心等待点球射进门去的一瞬间。
恰在那时折鹃红从外面推开玻璃门大大咧咧地走进来,莎莎立刻将最后的一线希望投向她。折鹃红进门头一件事便是对着镜子用手指轻轻捋她的头发,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她一边捋头发一边拿眼睛乜斜镜子里的那些姐妹,她很少正眼看她们。这时她发现站在地当间那个有些灰头土脸的莎莎了,折鹃红也是忽然灵机一动,她想起自己租的房子还空着一间,正缺一个伴儿呢,女孩莎莎让她眼前一亮,如果把她带回去同住,至少另一半的房租就有着落了。所以,折鹃红转身对莎莎很友善地笑了笑,她说你是刚来的吧?找人还是想在这里干。莎莎遇到救星似的慌忙扔下旅行包,笑着冲折鹃红点头。莎莎笑的时候,镜子里的其他女孩似乎都更严肃地绷着脸,这种敌意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折鹃红来的。果然,在随后的日子里,店里的女孩很明显分成两派,而莎莎始终立场坚定地站在折鹃红这边,折鹃红有什么事只要一句话,莎莎绝对俯首帖耳毫无怨言。
平日里,折鹃红总让出租车一直开到巷子的最深处去,等车停稳了她才猫一样从车里钻出来然后低着头三步两步快速拐进她住的地方。可今天车刚到巷口,她就让司机停车了。汽车立刻做了一个猛点头的动作,司机扭头看了一眼她。折鹃红把准备好的十元钱从钢筋护栏的空隙间塞过去,嘴里说不用找了,司机接了钱把整张脸转过去冲她笑着。笑容非常亲切,这在她的生活中并不多见,可她并不为此多想,双脚早已轻盈地落在地上。
从停车的地方到她的住处至少还得走500多米。有一盏路灯歪斜在很窄的巷道里,灯光昏蒙蒙的,乍一看好像根本不是灯光而是天空本来就有的那么一团暗黄。每次汽车要深入到巷子里,总要在这里耗费一些时间,90度的弯子很难拐的。遇到技术好一点的司机倒也罢了,若遇到那些笨手苯脚的二把刀,半天也折腾不进去。折鹃红就闷在车里火直往上蹿,特别是晚上没有生意做,或是摊上一个吝啬刻薄的不把她当人看待的生客,她便以牙还牙似地把火气都泼在司机的身上。她会毫不客气地骂一通,你怎么这么肉!妈的到底会不会开车!
折鹃红刚从家里出来时显然没有那么厉害,她在外面稀里糊涂一混就是好几年,她先后跟人学过洗头剪发,学过按摩捏脚敲背,她当初的愿望是将来攒够了钱自己大小也要开一间发廊,后来她发现事情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光靠手艺是挣不了几个钱的,她也慢慢体会到付出的和得到的无法相提并论。换句话说,想弄到更多的钞票,其实很简单,只要天生一张漂亮脸蛋,再加上一副看得过去的身材就齐了。那些客人一进店里就会直勾勾地瞄着你,哪怕你只是傻乎乎的模特似的立在那里,挺着一对饱满的胸脯,他们会毫不掩饰地直接点名要你。她觉得男人们压根就不是来洗头按摩的,那都是男人的幌子,说白了他们到这里就是想找个乐子的。
本地初夏的夜晚很凉快,再加上白天下过一场大雨,走在巷道里就有点凉丝丝的感觉。风悄然从身后拂过来,夹杂着淡淡的槐花的香味和夜晚特有的潮湿,折鹃红顿时觉得裸露在外面的胳臂和大腿都变硬了,皮肤猛地绷紧,而且麻肃肃地生起一层细小的颗粒,那些颗粒正在不断地从肌肤表层冒出来并逐渐变大,最终好像连成了片儿。
折鹃红不由地打了个冷战,下意识地加快脚步,将双臂交叉在胸前。她很久没有像今夜这样独自一人步行一段夜路了。刚才车开到巷口时她突然改变了主意,而且,那时她的心境特别宁静。她就想下车一个人走走。
自从跟莎莎住在一起,折鹃红出入这条巷道便有个伴了,她不再形单影只。

叶永青 香蕉 布面丙烯 140×100cm 2002
刚开始,莎莎几乎影子似地粘着她,什么时间回来睡觉,什么时间该去店里做事,只要折鹃红一个眼神或做一个手势,莎莎就义无返顾地挽起她的一只胳膊,亲亲昵昵地走在她身旁,看上去真像是一对相濡以沫的姐妹。莎莎嘴甜,一直都鹃子姐鹃子姐甜甜地叫她。当初,折鹃红带莎莎回到她的住所的那个晚上,她从莎莎的手里拿到了200元钱,这是莎莎交给她的第一个月房租。其实,这套房子每月的租金只有300块,那天折鹃红没有对莎莎说实话。折鹃红说咱们俩平摊,你就拿200块吧。她说多少莎莎二话不说就给了多少。折鹃红并不觉得心虚,不管怎么说是她收留了这个看上去有些茫然的外来女孩。折鹃红想如果不是她搭理莎莎,也许莎莎那晚会睡到车站或别的什么地方也说不上,万一碰到个把坏人也是有可能的,现在外面有多乱呢。况且,她们隔壁店里以前就出过类似的事,一个新来没几天的四川女孩瞒着老板偷偷跟客人过夜,后来就失踪了,再后来才知道尸体被剁成碎块,扔进城里的几面湖里,还是被钓鱼的当大鱼一样拽上岸的。据说那段时间,大大小小的歌厅美发店生意都很差,几乎没有哪个女孩再敢铤而走险随便出台,她们都空前地规矩起来,个个都淑女一样整天待在店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有时折鹃红也想,莎莎的确是她一手领进这个行当里来的。她以一个过来人的姿态对莎莎进行着所谓的“传—帮—带”,在这个过程里,她告诉莎莎该怎样对付那些来寻欢作乐的男人,怎样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而又不至于伤害到自己。莎莎对她的谆谆教诲自然也是言听计从,甚至就连上银行存钱,或是到邮局给老家汇款这样的事,她都一样不落教她怎么做。折鹃红说你可别把钱全都存在银行里,身边得留一点儿,万一碰到警察抓住要罚款,你总不能现跟着警察去银行取吧。莎莎第一次去银行存钱居然没留密码,她说自己脑子笨,怕到时候记不得就惨了。当时折鹃红就照着她的脑门子轻拍了一巴掌,说猪笨还会摇摇耳朵呢,你总不至于忘记自己的出生日期吧,像我用生日做密码最可靠了。
折鹃红也发现莎莎是个很会来事的女孩子,她们每天候在店里无聊地等客上门的时候,莎莎总是用一只手托着腮侧着脸坐在她旁边有说有笑的。在店里莎莎的眼里只有她折鹃红一个人。夏天,她忽然想吃个冰淇淋什么的,莎莎眨眼就替她买回来清清凉凉地递到嘴边了。莎莎不喜欢吃辣椒,可折鹃红却很迷恋吃麻辣烫,三天两头非得光顾一次,莎莎从无怨言地陪着她去。有时候,折鹃红看着莎莎辣得直伸舌头一个劲掉眼泪,连她也有点不忍心了,可莎莎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吃习惯就好了,如果连辣椒都吃不了还能做什么。事实就是这样,现在莎莎有时会自己提出来去吃那种东西。莎莎对付那些客人更是游刃有余,她年轻,活泼,爱笑,皮肤白皙,身材匀称,又懂得如何打扮自己,跟个小人精似的。每每这样看着莎莎的时候,折鹃红心里都会有种说不清楚的感受,有点自豪,又有几分失落,在她的印象里莎莎就应该是当初的那个无依无靠的莎莎,看上去有点怯懦和拘谨,有点初来乍到的恐慌,还应该有点儿可怜吧唧的孤立无援。这才是那个莎莎。
又往前紧走了一会儿,折鹃红就觉得有点喘了,她很少这样走夜路的。她的鞋跟又细又高,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她脚上穿的是一双浅粉色的水晶凉鞋,很衬脚的,这种鞋今年夏天非常时新,她先买了一双,莎莎也跟着买了一双,结果店里的几个女孩都相继穿上了这种款式的凉鞋,因为她们都喜欢露出涂得红红亮亮的脚趾。
女孩们在店里一起扎堆聊天能说得最投缘的话题,莫过于穿穿戴戴一类的事了。莎莎的个头没有折鹃红那么高,身材也没有折鹃红那么丰满,可莎莎喜欢跟她学着穿戴,好像这样做也是对折鹃红的一种变相的拥戴。折鹃红觉得自己的脚天生得好看,又白又嫩,脚趾细长,趾甲富有光泽,涂上亮晶晶的趾甲油是非常好看的。可她的脸和身上的皮肤比起莎莎来就要逊色一些。特别是莎莎的两只手长得很有女人味道,湿润,细腻,手指饱满浑圆,却又不失女性特有的骨感。这就让折鹃红对莎莎多少会生点嫉妒的。折鹃红的手很瘦,骨节突出,跟鸡爪似的。但是,有时候折鹃红想莎莎毕竟小着自己几岁呢,像莎莎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优势也正在此时,年轻就是本钱啊。有时看着莎莎在眼前小妖精似的晃来晃去,一副不知忧愁没心没肺的样子,折鹃红又打心底里替莎莎感到难受感到不舒服,这种感觉并不完全来自同病相怜,更多是源于她对莎莎这种女孩子的轻蔑。当然,这种轻蔑有时甚至也包括对她自己。在她眼里,莎莎所展示的一切优势其实都是悲凉的,庸常的,而且是肤浅的,从头到脚透着一股不谙世事的傻劲。

叶永青 姿势 160×110cm 2002
很多时候,莎莎又表现出一种不知深浅的率真,她会一股脑将自己客人的一些情况透露给折鹃红。比如某某出手很大方一次就给她多少小费;某某跟她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温柔的样子,如何热烈地亲吻她;或者,某某其实挺可怜的因为他的老婆半年都不让他碰一下。遇到这种时候,折鹃红通常会以极不屑的目光看着莎莎,她说莎莎你真是蠢得可以啊,你难道没有脑子吗?男人的这些屁话你都信!莎莎被折鹃红骂得不敢再继续讲下去,在她眼里折鹃红大抵是有一些威严的。偶尔,莎莎也要适当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她会天真地眨着眼睛说鹃子姐我觉得某某真的对我挺好的。这种话折鹃红是最听不得的,她会冷冰冰地哼着鼻子说莎莎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你要永远记住,这世上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对你好的。
陡细的鞋跟一直笃笃地敲击着地面,有一些杂沓的回声在深巷里飘荡。稍不留神脚下踩到一汪泛着亮光的黑色,溅起的水珠落在光洁的脚踝和小腿上,竟有种刺痛的冰凉。
这种情况下,折鹃红多少有点战战兢兢的感觉了,别看她平日在店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可是让她走这段夜路,就有点怯了。她想要是能跟莎莎一起走也许会好一点。而且,她们还可以说说话。一个人悄声走路总是会有些害怕的。
白天多少有些懒散,也许跟早上下雨有关系吧。折鹃红后来这样想过。反正一整天店里也没有进来一位客人,大家闷在厅里打了好几个钟头的双扣,最后摸牌摸得手指都有些僵硬了,实在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才不玩的。其实,近来的生意一直都是这样,对她们来说,这种没有生意做的日子是最难熬的。因为没有客人,有两个女孩天黑前就离开了(极有可能是到别的什么场所串台去了),那时折鹃红斜躺在厅里的沙发上,老板一副一筹莫展的样子,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又出去站在门口女特务似的四处张望着。折鹃红一直懒洋洋地躺着不动,这当间她接过两次无关紧要的电话,又很专注地查看了一遍手机里的短消息,偶尔,会被某条恶俗的短信惹得忍俊不禁,吃吃地笑出声来。后来她觉得肚子好像有点饿了,嘴里很淡,想吃点什么东西。这时,折鹃红才发现身边好像少了点什么,她起身往出走的时候终于意识到今天莎莎没有跟在她身后。她扭头往店里看了看,小姐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靠椅或沙发上,都是一副无聊透顶的懒猫样子,莎莎不在她们中间。她又冲最里面的小包间喊了两声莎莎,依旧无人回答。
折鹃红这时才回想起来早上的情景,莎莎今天好像醒得很早,还唤醒过她让她看窗外的雨呢。后来房门似乎开了又立刻关上了,有一股清凉的风湿乎乎地旋到她的床前,使她不由地打了个寒噤。折鹃红继而想到等她再次睡醒的时候天光大亮,那时莎莎已经不在房里了,好像早就出去的样子,她还留意到莎莎连被子都没有叠,胡乱卷成一团堆在床上。所以,折鹃红记得自己当时骂了句妈的这头小懒猪!等折鹃红涂脂抹粉收拾妥当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她出门前莎莎依旧没有回来,这时她发现莎莎的床头柜上躺着一束打了塑料包装纸的鲜花,有玫瑰和康乃馨什么的,当时折鹃红不无醋意和嘲讽地冲那束鲜花撇了撇嘴。这种醋意多半是来自女人内心那份特有的嫉妒,而嘲讽则是折鹃红作为一个在这种行当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大姐对莎莎这种看起来有些轻薄的女孩的小觑和藐视,同样的事情她并不是没有遇到过,可在她看来,男人的虚情假意和鲜花都是他妈的臭狗屎,她也曾有过许多幻想,也做过类似于莎莎的那种不切实际的美梦,可后来怎么样呢?她还是折鹃红,一个飘荡在外地他乡的女人,一个靠姿色混饭吃被称做小姐的女人。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她有足够的资格对莎莎这种女孩加以冷嘲热讽。
的确,莎莎自从在店里留下来之后,没过多久便开始应对自如了,加之折鹃红有力的言传身教,莎莎大抵有点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架势,有点青出于蓝又胜于蓝的苗头。莎莎的优势就在于年轻,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招招式式都领悟得很快且得要领,该怎么跟客人打情骂俏,该怎么把握分寸,该怎么给客人带去欢乐,等等。莎莎来店里伺候的第一位客人也是经折鹃红撺掇的,其实折鹃红并没有那么大公无私,非要把自己的客人生拉硬扯往别人那儿推。那次正好赶上她身上有情况,她呢又不想扫了客人的兴,就顺水推舟把莎莎推到那位客人面前了,她说这是我的小妹,不光人长得好,而且聪明伶俐,可会来事了,就让莎莎陪陪你吧。说着,她又凑到客人的耳边悄声嘀咕着,说莎莎刚从老家过来,还是个雏呢,大哥可得对人家温柔一点。客人本来欲走的样子,听她这么一说,自然满心欢喜。当然,客人也不是非要给折鹃红面子不可的,实际上他的目光一直在莎莎的身上扫来扫去的,莎莎娇娆地站在折鹃红身旁,目光似躲似闪的一阵乱颤,脸蛋儿也变得绯红起来,由不得客人不心花怒放。
那天不知为什么,折鹃红早早就离开店回住所了,照理说她该等莎莎完事后一起回来才对。她们合租的房子是一里一外的套间,莎莎住在一进门的外间,折鹃红在里面,平时折鹃红一回来就钻进里面关好房门。那天折鹃红没有关自己的房门,一个人躺在床上晕晕糊糊吸着烟,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好像丢了一件很贴身的东西,明知它丢在什么地方,可就是没有脸面和勇气去把它讨回来。
莎莎回来时已经很晚了,听见钥匙拧动门锁的声音折鹃红急忙蒙头背过身面朝里装睡了。莎莎轻轻地敲了敲她的门(这是折鹃红以前给莎莎定下的规矩,进她的房间必须先敲门),折鹃红虽然睁着眼睛,却没有吱声。莎莎说鹃子姐我回来了。折鹃红才懒懒地翻过身,打了个哈欠,然后摸索着拧开床头灯。
莎莎始终不说话,眼圈红红的,像是一路哭着跑回来的。要是莎莎还像平常那样笑嘻嘻地靠过身来黏糊她,折鹃红也许会毫不客气地挖苦她一番的,她也许会说哟!莎莎小姐可算回来了,怎么样,玩得还开心吧!可是,眼见着泪水从莎莎的眼眶里汩汩地涌出来,然后悄无声息地顺着眼角滑下来,折鹃红忽然觉得自己的鼻子也有点酸酸涩涩的,很久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她急忙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连声问你这是怎么啦莎莎,他欺负你了对不对!听话别哭,快给姐说姐一定替你出气,他到底怎么着你了?说着,早已经将莎莎亲生孩子似的揽进怀里,一边拿手摩挲莎莎的头发,一边不无愧欠地劝说都怪姐不好,我不该让你去陪他的,我就知道那家伙坏着呢。莎莎慢慢地抬起脸看着她,竟破涕笑了一下,她说鹃子姐你千万别这样说,我没事的,我知道你这都是为我好。说话的工夫,莎莎从裤兜里掏出一百块钱拿给折鹃红,莎莎说鹃子姐这是孝敬你的。折鹃红一怔,无力地松开了手,她觉得心里更不是滋味,脸上热辣辣的痛,像是被谁左右开弓连扇了无数个嘴巴,倏地勾起了她对往事的简短回忆。

叶永青 鸟的草图 布面丙烯 180×100cm 2003
那也是她自己的第一次。那时候她是多么的狼狈不堪,在客人眼里她肯定显得傻乎乎的,除了有一张年轻漂亮的脸蛋,对于男女间的事情她一窍不通,任由客人摆布,结果还没鼻子没脸地遭到一通奚落和白眼,她记得客人骂她你他妈的跟僵尸似的怎么出来混啊!所以,折鹃红没有像上一回那样从容地从莎莎手里接过钱,她甚至不敢去接触莎莎此刻的目光,而是扭过脸将莎莎的手很坚决地推了回去。她说傻瓜我咋能拿这种钱呢,这是你的辛苦钱你拿回去,只要你有心,往后记着点姐的好就行了。那晚折鹃红怎么也睡不着了,后来她就喊莎莎过来陪她说说话,再后来莎莎就在她的身边睡了。
不知是什么东西猛地从路旮旯里窜出来,在折鹃红的眼前一闪,便静静地停在路中央了。折鹃红几乎快吓蒙了,一连打了两个激灵,身体哆嗦着,好半天才缓过神来。随即,她听到喵的一声细长而尖利的叫,她这才意识到眼前不过是一只猫。
即便这样,折鹃红也没敢往前迈出半步,而是故作勇敢状地在原地快速跺了跺鞋跟。笃笃笃,声音传得很远。她试图用这种方法吓走猫。可那只猫丝毫没有被她怔住,更没有迅速逃跑的意思,猫更加神秘地打量着她,像是非要看清楚她的脸面似的,或者,根本就是在同她对峙。借着身后那团微弱的灯光,折鹃红发现那猫的眼睛绿得令人发怵,也说不清是绿色还是蓝色,总之,她完全被来自猫眼的一束冷漠而又阴郁的光芒威慑住了。

叶永青 鹤舞 150×110cm 2004
有那么一刻,折鹃红眼前忽然产生了某种幻觉,她发现蹲伏在自己面前的并不是一只猫,而是一个身着夜行服的黑衣人,一个神秘的蒙面拦截者。这种幻觉一旦在脑海里生成,折鹃红立刻感到浑身瘫软无力了,手脚变得冰凉不听使唤,心跳忙乱潦草,毫无节奏。更要命的是,她觉得自己的两只脚像粘死在地面上了,无论她怎样努力也拔不起来。情急之中,她猛地将挎在肩头的坤包摘下来,用双手紧抓住包的挎带,然后在眼前挥来舞去,嘴里发出无助又无奈的尖叫,滚开,快滚呀,你这死猫。猫似乎并不理会她的气急败坏,而是低下头在路面上饶有兴趣地嗅着什么,即而发出那种凄凉而绵长的叫声,并不时抬起头很警惕地朝她瞥一眼,像是随时做好准备冲她扑来。
这回她真的傻眼了,手臂酸软了,坤包无力地从半空中垂悬下来。
折鹃红从小就不喜欢这些猫啊狗的,尤其是猫,她总是固执地认为猫是鬼魂的化身。她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房子里,那是一个表面看起来非常斯文的男人,可后来她一想起那天的事就恶心得要吐了。那晚男人给她看过一张碟片,尽是些狗啦猪啦还有猫交媾的画面,看得她一个劲发怵,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她实在想不通是哪个无聊的家伙在拍摄这种东西,她只记得那种猫叫春时的绝望和凄惨。后来那叫声经常在她的睡梦中回荡。而此刻,她只好回过头朝身后求助般地张望了一下,除了那盏昏黄得近乎憔悴的路灯和默默蔓延开去的空巷,连个人影也没有。
等折鹃红无奈地转过头去,眼前的道路看上去又平坦了,那只路障一样的黑猫早没了踪迹。这种印象似乎更加充分地印证了她先前所产生的那种幻觉。她迟疑着,一时间竟不知该继续向前走,还是原地站着别动。她想,万一那只猫再次窜出来自己该怎么办呢。
就在折鹃红犹疑之际,一团黑影从前面的路口拐出来,摇晃着径直朝她飘来。
是个男的,歪斜着肥胖的身体,脚步蹒跚,嘴里不停唠叨着什么。近一些的时候她听出来对方正在打手机。男人经过她的身旁时不可遏止地打了个响亮的嗝。折鹃红闻到一股很浓的酒味,这种气味的男人对她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男人也注意到了她,其实他已经越过她好几步远了,可又转身摇摇晃晃地折回来,站不稳似的在她面前一阵摇摆,他的目光是那种被酒精浸泡过的猩红。接着,他冲她发出一记非常怪诞的笑,语言相当含混。怎么,不认识我吗?上次,在,在什么地方……反正咱俩一起喝过酒的,忘,了?折鹃红始终不露声色地盯着对方。男人的舌头硬得像把锅铲。她下意识地用双臂搂紧自己。这种事情经常能碰到,她们总是在跟形形色色的男人打交道,一点儿也不奇怪。所以,折鹃红当即很坚决地冲对方摇头,你认错人了。
她转身想要走开,可男人却伸手拽住了她的一只胳膊。她立刻痛得叫了起来,干什么呀你快放开我!她用力想把胳膊挣脱出来,可这样做的结果反使疼痛加剧。她强忍着痛说你再不松手我要喊人啦!男人又冲她嘿嘿一笑。她觉得他的笑跟刚才遇到的那只可恶的猫的叫声一样刺耳难听。他妈的,我不是老,虎,你,你喊个屁呀,老子有的是钱,走,陪我,玩玩。男人一边说着,伸过另一只手在折鹃红的下颌上很暧昧地捏了一下。
折鹃红乘机挣脱出来,这时她反而变得相当冷静了。这种冷静很大程度上出自对男人的深度了解和轻视。她一本正经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谁跟你去。
当她三步并作两步再次往前去的时候,听到身后的人正嘿嘿地狂笑不止,或者,在冲她恶毒地咒骂。她听得最清楚的依旧是那个很刺耳的字眼,这是人们对她最普遍的称呼,但她从来没有像此刻觉得如此亲切。在内心深处她像是在跟另一个自己较劲,又像在自言自语说服自己,鸡怎么了,那是老娘的职业。
接下来,一串闹哄哄的手机声在巷道中飘荡开来,淹没了她的所有气息。她甚至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了。
房门和灯相继打开了。
折鹃红背倚着房门闭上双眼,静了静心神,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这时,她注意到莎莎的床依旧是空的。未叠的被子蜷缩成一团,占据着那张床的一角。她走过去靠床沿边坐下来。她很少坐莎莎的床。今晚她实在有点累了,特别是两只脚,她胡乱踢掉脚上的鞋,用手轮番抚摩着脚踝。她看到那两只水晶凉鞋死耗子似的反趴在地板上,鞋跟鞋底沾满了黑色的泥浆,看上去让人十分厌嫌。
本来有一肚子话想对莎莎说的,比如那只该死的猫,再比如那个令她异常憎恶的醉鬼。女人通常喜欢跟别人分享一些可怕的经历。可是,该死的莎莎居然还没有回来。折鹃红的目光有些呆滞地落到床头柜的那束鲜花上。塑料包装纸的开口处正朝向她,有一只花朵不知什么时间脱落下来,蔫蔫地静伏在距离床头柜不远的地板上。她看了看,那是一朵绛紫色的玫瑰花。与此同时,她的目光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她注意到床脚下整齐地摆放着另外一双鞋,浅粉色的,水晶质地,细高的跟,和自己的一模一样。只是,看上去要比自己的那双洁净许多,似乎一尘不染,根本看不到黑色的泥浆。
折鹃红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来,可翻来覆去老半天就是睡不着。她只好打开床头上的台灯,想找点什么看,又觉得灯光太刺眼了,随手把灯关掉。她在黑暗中猫一样警觉地睁着双眼。她没有关自己的房门,因此,她可以清楚地听到外面忽然响起的一阵雷声,闷腾腾的,她估计很快就要下雨了。可莎莎还是没有一丝回来的迹象。她实在有点生气。不知怎地,她竟有点想家了,这个念头一旦生成,立刻就变得十分迫切难耐了。算了算,自己将近有两年没回过家。她想最近生意反正不太好,也许她可以抽空回去一趟的。
雨点开始乒乒乓乓敲打窗户。她恍惚听见房门打开了,一股又湿又冷的腥味在黑暗中弥漫开来,接着房门又轻轻扣合上了。那阵浓浓的睡意刚好爬上折鹃红的眼皮。与此同时,她的口鼻突然间被一只大手死死蒙住了,是个男人,带着酒和烟草味道,她的睡意顿时像灵魂出窍,可她已经不可能喊出一点儿声音,手脚胡乱挥踢了那么几下子,便失去了知觉。
这个可怕的雨夜过后,莎莎也在这个城市彻底消失了,连同她一起消失的,还有折鹃红这些年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那些钱分为两部分,一小部分就压在她睡觉的床垫下面,而大头则在那张银行卡上,折鹃红是在第二天上午才挣扎着醒过来的,她跑去银行一查,自己的钱早在夜里就让别人从自动取款机里提走了。
折鹃红眼前顿时一团漆黑,人就瘟鸡样瘫在银行的地板上了,一只水晶凉鞋从脚上飞窜到人群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