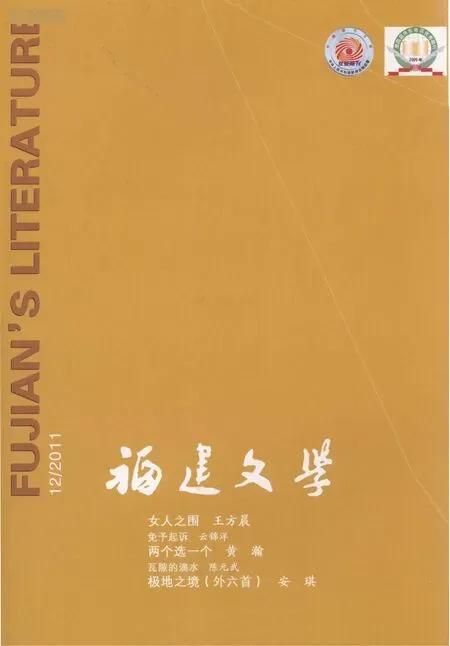别样的城
刘成章

在群贤毕至、惠风和畅的东晋兰亭之边,书圣王羲之以精美绝伦的独特书法,写下了他光彩夺目的生命体验——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这体验,抖动而放光,乘着公元353年的风云,飘越一千余年的满目沧桑,此刻正震荡在我的心里。但引发我心灵共振的,并不是大自然的亿万物种,而是北美大陆的一大人文景观——位于大湖区的一座大学城,因为它以它的新异和独特,把书圣王羲之笔下的那个“盛”字描摹得更加繁复多姿。
大湖有五,曰:必利尔湖,休伦湖,密西根湖,伊利湖,安大略湖。它们都荡漾在美加边境处,总面积等于欧洲的十多个国家。湖水清澈,湖岸多林,有数百条大小河流注入其中。不必说它的湖面有多少船帆,不必说它的上空有多少水鸟,也不必说它的周围有多少避暑胜地,单是那蜿蜒如奇妙琴弦的湖岸线,就足以令人销魂的了。不是吗?你看那边,那灿烂阳光照射的沙滩上,一个身着泳衣的少女欢快地走来,走来,而当她把她的一只赤脚刚刚踩在湖岸线上的时候,仿佛整个北美大陆都在律动作响了,一如触响了冥冥中的全部音箱。
大学城就在这里,在这水意溶溶的乐声之中。
校叫什么?密西根大学。城叫什么?安娜堡。但是,校,无墙无门融入城;城,处处化进学校中。整座密西根大学的校园就是安娜堡市,也可以说,整座安娜堡市就是密西根大学的校园。在这儿,在这座大学城里,众多雄伟建筑错落排开,钢铁、水泥、石头和玻璃的各种组合,各种结构,各种线条,各种造型,各种气势;各种墙面和门窗,各种柱体和雕花,各种走廊和栈桥,各种过渡和对比,各种想像力的极致;看一眼,那不凡的境界,仅仅看一眼那不凡的境界就把你的心给揪住了!而随着光线射角的推移,丰富的光影便在众多建筑上演绎着一幕幕变幻无穷的迷人景致,令人心醉神迷。引人驻足的还有面积高达一万多平方米的浩浩阔阔的计算机中心,它令人想起《敕勒歌》的风吹草低,而足球场的看台如月亮的环形山,环形山上足可以围坐十万多吴刚和嫦娥。
这是一座不凡的城,由它发出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时时都拨动着华尔街的敏感神经,深刻地影响着美国以至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是一座青春的城,全城居民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六岁,到处是蓬勃向上的丰沛意绪。它是全美公立大学的翘楚,15,000多门课程和近6000个研究项目任你挑选。这真是一座别样的城,宽带无线网络遍布于各个角落,十分钟一趟忙碌穿梭的校车总是免费乘坐,校车的吐出和纳入之间,教材,最新书籍,青年杂志,刚进货的时尚衣裤,杰克逊和苏珊大妈的抢手唱片,捧在帅气的男生手中,捧在如花的女生手中,清芬扑鼻。
像马克·吐温对他的作品一样,大学城已经相当好了但还要更好,所以它一刻也没有停止新的建设。住在这儿,我常帮女儿做做饭,往幼儿园送送孩子。闲来无事随意在校园里走走,坐坐,或者与同为探亲族的中国老人们聊聊天,或者只是望望周遭环境,让绿阴缝隙洒下的阳光轻抚着我多皱的脸颊,觉得均不啻是惬意的享受。徜徉于这座大学城,无异于徜徉于森林之中,到处被绿阴掩盖着。除建筑之外,余下的地方,不是高大的树木,就是草坪和绿地。你信着步儿随便向哪里走去吧,尽皆草色,草色,草色,草色上脚绿;尽皆树影,树影,树影,树影入眸青;走在这儿,你甚至感到连你的肺腑也都变得绿茵茵的了,甚至其上还开着小花落着花蝶,多么舒心!
作为一个爱书痴书的人,我来不久就到图书馆去了好多次。这里的图书馆有主馆与好多分馆,一进主馆你就沿着旋梯大迈双腿吧,只见旋梯层叠向上,光影倾泻而下,仿佛是在经历着一次最神圣的伟大洗礼。我蓦然倚栏回首,似看见许多高大的背影刚刚下楼:十九位诺贝尔奖得主,七位宇航员,一位总统,接着是讯息理论与数位电路之父,谷歌和美林的创办人,以及众多的别的领域的杰出人物,其中的华人有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台湾物理学家吴大猷,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那一串背影披着光,挟着风,隐隐绰绰,似幻似真。但我觉得我是真的看见他们的背影了,那一串气宇轩昂的背影。他们仿佛都是刚刚拿到这个学校的毕业证书。我似乎看见他们正好碰见一群刚刚入校的新生。新生们热情地围住了他们。他们朗声对新生们说:“我们以校友的名义祝福你们!愿你们在这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的学校里,发奋努力,一往直前,铸造好自己的创造精神!”
我转首向上,光影泻下,泻下。我在腾空。到了。映入眼帘的,是苍穹般的高高屋顶,天宫般豪华的阅览室景象。一缕缕装饰。一幅幅名画。一尊尊塑像。一架架书籍。一排排桌椅。一台台电脑。一张张年轻的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种肤色的脸孔。聚焦这边吧:一个放在腿边的中国制造的书包。书包旁是一双穿在脚上的也是中国制造的高筒靴子。桌上一杯咖啡。湖水样的蓝眼睛透过森林般的长睫毛,定定地望着一本打开的精装书。头发呢,她的每一根头发都是一条黄金之丝,这黄金之丝在斜射过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如果我不是亲眼所见,我绝不会相信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奇异这么悦目的头发。姑娘来自哪里?属于哪个族裔?我正这样思忖着,我的目光却又被一个又一个的我们中国的留学生们吸引过去了。一看见他(她)们我就有一种亲近感。他(她)们无愧于长江黄河无愧于我们的民族。他(她)们是当代的子路、颜回和冉耕,不,他(她)们远比衣袂飘飘的子路、颜回和冉耕们渊博上了千倍万倍万万倍。哦,我的年轻的有出息的小同胞们,我羡慕你们!羡慕你们在这知识的海洋里大口吞噬着无数营养,如一拨又一拨的进取之鱼。比起你们,我知道我不但上了年纪,而且,英文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英文,我只是一条睁眼盲鱼,我纵有极好的胃口,却什么也无法捕获。我只好到一个分馆东亚图书馆里再去看看。
东亚图书馆虽然规模小了好多,却有我心爱的仓颉造下的美丽文字,一层层一弯弯的,如中国的山,中国的水,甚至如我的生身之地我儿时欢蹦疯耍的野花飘香鸡啼犬吠之地,走近它,我如近乡情怯,心跳咚咚。我终于平静下来,踏入密密的书架之间一本本地翻,一本本地读。让人惊喜的是,我想起了陈忠实,举目一瞅,就有陈忠实的小说;我想起了阎纲,举目一瞅,就有阎纲的文学评论;而且,我居然也看见我自己的作品了!我的一些我早已无从寻觅的文革前的幼稚之作,一篇篇,也居然被收藏在这里了!那时我好不激动!哦,我生命的衍生物,我失散多年的孩子们,咱们在这浩渺大洋的彼岸,竟意外地相逢在一起了!恍惚间,我直欲伸出双手,把他们揽在怀里。看娇儿,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而我,真想从自己的衣袋里为他们掏出点什么。
不知不觉间,夕照已然燎红远山。湖里水鸟游弋,鱼来鱼往,新荷朵朵。巨大的松树枝叶垂挂下来,树下满是松塔,长着蓬松长尾巴的松鼠在那儿互相追逐。另外看见的,是脚蹬滑板飞驰而过的年轻健美的学生,还有边走边谈的老教授。而在绿地上,学生们有的身着运动衣在打橄榄球,有的懒散地躺在木制长凳上翻阅着一本什么消闲书。而还有些学生则是去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全校共有一千多个学生社团,其中汇聚着各方面的杰出人才,他们围坐在一起开会,蹙着眉头细心切磋,共同探讨人类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各种前沿问题。思想和智慧的花朵,在这儿灿然怒放。再晚的时候,萤火虫出现了,在新剪的草香袅袅的草坪上闪烁如一盏盏迷你小灯,有的学生便扑了前去。一股一股的青草香。一闪一闪的小精灵。一阵一阵的大狂喜和大欢呼。而这时候图书馆大楼上依然灯火通明,一些舍不得离去的青年助教和学生们就在楼下的小卖铺里买一点比萨饼,甜点,或者啤酒,一边吃着喝着,又一边上楼去了。这时候如果来到健身室门外,你常常可以看见有些学生一边在跑步机上跑步,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一边还在看书。因为他们明白,在这里,山外有山,云上有云,再优秀还不够优秀。因为他们知道,双脚一踏进这座大学城,你就像跳进高压锅了,你必须忍受那不断升高的气压和沸点,那远不是十倍百倍的桑拿天可以相比的。你必须咬着牙关忍受。倘问同学们感受何如?不用说,多数对母校都是爱得要死,恨得要命,爱恨交加。
这里生活着包括留学生和探亲族在内的四五千个我们中国的同胞。我们中国同胞向以大声说笑著称,但是到了这里,他们受到环境的感染,也变得低声细语了。整个大学城常常静得就像古刹一般。但是也有嘈杂之声可以抬起房屋的时候。市政府几间房原在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很不起眼,如随便建在那儿的一个饮水龙头。现在它却成了焦点所在,围着它,群情沸腾,口号声声。那里聚集了好多学生,好多抗议者,斥责政府花了一些不该花的钱,影响了教育方面的许多事情。学生们都有很强的参政议政意识,对于这样的活动,一个个不甘落后。一位站在一边的梳着马尾辫蓄着大胡须的教授赞赏地说:“我的学生真是好样的,说不定会从其中出现一个总统哩。”他说完豪爽地大笑起来。OK!他的喜悦全然发自内心,每句话都有烫人的温度。
我虽然常被乡愁所煎熬,但我还是很喜欢这里。我发现这里的每个季节都各有各的鲜明特色。
冬天是这里最为漫长的季节,而且经常下雪;难得的是只要下雪,就从不忸忸怩怩,而是豪爽旷达,痛快淋漓。往往一夜大雪,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楼顶升高三尺白,小丘加肥三尺白,钟声里也携着三尺白,整个校园,整个校园都被厚厚的白雪埋住了。只有高飞的鹰是黑的。刚辟出的道路有时就像雪谷,人们背着书包,在雪谷中呵气如云,踽踽而行。泊在停车场里的汽车,哪里还再有汽车的样子,它们都成了一个一个的又白又亮大蘑菇了。冰雪的世界让许多小动物都钻入地下进入冬眠状态,而莘莘学子的头脑这时候却特别清醒,于是他们便抓紧这一时间,猫在室内或者做一个什么缠斗似的艰辛实验,或者赶写一篇不亚于在硝烟中夺取制高点的毕业论文。到了星期天当然还是要上街的,要去超市购买粮和菜。那么首先就挖掘吧,每个人都在亿重白羽的掩埋中挖掘他自己的汽车,像挖掘一座座庞贝古城,一个个秦俑坑。而到了消雪的时候,那残雪和初步裸露出来的散发着泥土、草根和水汽混杂味道的大地,也是很有几分看头的,它就像出自哪个大师之手的一幅凝重的铜版画。
春天总是姗姗来迟。但迟来的春天总是十分诱人的。先看那草,它们很像由冬眠而醒的小动物们,一个一个张大着好奇的眼睛,钻出了地面,并且炫耀着它们鲜碧的生命之汁。再看那花,一朵一朵争着抢着开放,一朵一朵展着露着笑颜,一朵一朵摇摇曳曳喜气洋洋好不快活。一些我不知其名的猫样的小兽,春阳下,总是在这儿刨,那儿刨。它们在寻找什么呢?天知道!还有那奇奇幻幻的庄周梦中之物也一齐拥来向这世界注册报道——翻飞蝴蝶乱纷纷。而大雁们,天鹅们,更是成群结队地飞到这里,在绿地上觅食,时而咯喽咯喽,引颈高歌。它们的数量真多,走遍校园,几乎到处都有它们的由于心情快乐而显得更加高贵优雅的身影。也有大大咧咧的雁妇人和天鹅娘子,它们竟然把好大的蛋遗落在草丛中了。当然只是少数;如果谁人以点代面,对此大加奚落和调侃,那就显得与大好春光不够协调,不够厚道啰。过不了多久,往往使人们惊喜得不能自持:一伙一伙的大雁的天鹅的毛茸茸的小贝贝们都出世了,在绿地,在水中,走着,游着,跟着它们骄傲的母亲。学子们看见它们,无不投去深情的一瞥。这时候仿佛有音乐响起,音符就荡漾在小提琴的弦上,钢琴的键盘上,和圆号、木管、双簧管的绝美的袖珍隧道里,如抒情的慢板,令人感动勾人回想。夫回想起什么啦?母亲之爱乎?家乡之美乎?友情和初恋乎?梦中的欣喜和苦涩乎?都有点又都不全是也。都耐人咀嚼又都有些虚幻也。都被升华了也诗化了也。而各种肤色的男女学生们,就穿行在这瑰丽的乐声之中诗意之中。
要说真正给人以最大欢乐的,还要数从不酷热的夏天,因为每年这时候的七月这里要举行规模宏大的街头艺术节。那是全美最大的露天艺术节。其时也,这座大学城完全变了样子。随着众多卓尔不群的艺术家的纷纷赶来,随着他们搭帐篷,卸车,摆放,街道上,校园里,铺天盖地的是各种精美的艺术品——绘画,雕塑,摄影,陶瓷,玻璃制品……还有美食,还有行为艺术,还有音乐表演和舞蹈表演。平日内心深处偶尔生出一些无奈的乡愁的中国的留学生们,此刻便借机排遣心中的伤感,便在宿舍门前张灯结彩,并且请了远方的同学,聚集在一起,在观看艺术展演之余,唱唱土得掉渣的家乡民歌,聊聊这些年的诸多深刻感受,然后或烧烤,或包饺子,同时打开多年不沾的中外酒瓶,一醉方休。潜藏于他们身上的过剩的青春活力,因而获得了最完美的宣泄和释放。我曾听见过有人在众声喧腾中大声喊叫:“不亦快哉!”哦,那不是大才子金圣叹笔下的妙语吗?那当然是的。不过现在经中国留学生这么一喊,这“不亦快哉”便有了浓烈的后现代意味了。
而景色最绝最美最瑰丽的时候,应是秋天。密西根的红叶是久负盛名的。秋风一吹,满校园的高大乔木和低矮灌木,就准备着悄悄给人一个大惊喜了。而当你每天早晨起来放眼看时,都会发现它们正在用力蓄势,色阶与前一天有了明显的不同。要是你三五日忘了留意而有一刻忽而转脸时,啊!树树都是红叶,两颊被烤得似有汗珠儿冒出来了呐冒出来了!啊!深红的火!浅红的火!橙红的火!桃红的火!棕红的火!紫红的火!啊!到处都是火焰!到处都在燃烧!千万棵燃烧的树木的茎叶何其夺目何其灿烂!它们狂野得就像刚刚参加了毕业典礼的男女学生啊男女学生欢呼的打滚的男女学生!啊!千色已然迷人眼,万彩乱了地平线,茎茎是火,叶叶是焰,层层热烈层层酽,校园成了火的调色板了呐矣哉矣哉!而有些学生还不满足,还要在周末,三三两两地结伙,驾了车,到周围茫茫的枫林中去疯张。其实应该说,他们都如神话中的人物,如东方的后羿和西方的普罗米修斯,以造福人类的崇高襟怀,一个个都扑到火海里去了!待到暮色苍茫他们返回,待到他们又走进灯光明亮的自习室,待到他们又打开电脑,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的发上、衣上、鞋上,依稀还飘动着隐约可见的火苗。
美国是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国家,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很早就非常重视教育。其貌不扬而绝对伟大的林肯总统曾经签署了一项流芳千古的《莫里尔法案》,根据这一法案,联邦政府将它在各州的一部分国有土地赠与州政府,让州政府出售这些土地,然后用其收入作为开办州立大学的基金。从此美国的大学便像雨后春笋般地到处冒了出来。所以美国的大学动辄都有一百五、六十年到二百年的历史,直逼国家的历史。
我尝自问:多年以来,美国这个只有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国家,为什么却拥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世界经济生产力和百分之四十的高科技产品?又为什么拥有世界上最多、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和超过一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当我这样问着的时候,只见五大湖的风凌波而来,风撩起我的花白的头发;只见五大湖的雾倚林而来,雾凑上我的欠聪的耳朵。我知道风是在回答我雾也是在回答我,风和雾分明都是在说:
因为——
因为在美利坚这广袤无垠的美丽土地上,矗立着以那些带藤的大学和密西根等大学为标杆的许多顶尖大学,它们是一批大气磅礴厚重无比的雄伟山岳,巨石嵯峨,连嶂竞起,半腰多伸入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