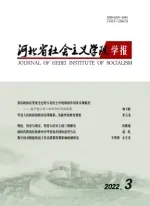从理性经济人假设看市场经济的道德缺失
孙苇杭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
从理性经济人假设看市场经济的道德缺失
孙苇杭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
理性经济人假设和资源稀缺性假设其实是一体的,我们不能把其中一个断言为真理而去证明另外一个的正确性。利益最大化不应成为必然。把理性经济人假设奉为圭臬,引发了利益冲突、人际对立和道德缺失等严重问题。当今社会经济应该开始重视道义,尝试抛弃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和做法,寻求另一种价值。
理性经济人;利益冲突;道德
近年来的金融风暴不留情面地把市场经济华丽的外表吹得凌乱,以至于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市场经济的弊端。人们反复批判道德的缺失,但是未见成效;尽管一个又一个金融监管规定出台,损人利己甚至引起经济重挫的行为却仍然有增无减。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向国会公开承认:他很震惊于市场运行的结果并开始怀疑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理性自利带来社会效用最大化”这一说法的正确性。西方经济学是否会影响人的道德情操,这个问题从李斯特至今有很多人曾经讨论、研究或者批判过,经济伦理学专注于理性道德和经济道德两方面,边际效用学派也认为人性是具有社会良心的利他主义的人性。但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当今社会经济的主流体制下还被当做一个真理,这种类似于性恶论的假设被应用到各种经济学研究和操控中,会不会对市场经济的道德产生不良影响?本文主要探讨理性经济人假设与市场经济道德缺失的联系,探讨利益最大化的普遍应用带来的问题,期望有助于现今的“经济”拾起道义,有助于社会和个人认可“最大化利益”以外的价值。
一、理性经济人是否应该成为必然
西方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和资源稀缺性假设。这两者实际上没法区分谁是谁的前提、谁在前谁在后。然而,资源稀缺性往往被当成不争的事实,于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也就随之而来——因为你拿走了,我就没的拿,所以人们要去竞争、去占有、去利益最大化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话说回来,正因为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贪婪,凡事都要利益最大化,这个世界的资源才显得那么稀缺。其实,这两个假设是互为因果的。如果我们认定资源稀缺性是事实,进而得出人们就应该成为理性经济人的结论,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研究和发展经济,那就多少有点自欺欺人的意思。
工业革命至今,尤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这个世界的产品愈加琳琅满目,丰富的卖方市场和频频出现的经济危机足以说明产能的过剩。可是,我们发现所谓的“资源”却越来越稀缺了,争夺也越来越激烈了,几乎所有个人、企业和国家都认同了这种稀缺性。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在定义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形态的时候,都要说到“物质资源极大丰富”这个前提,好像是在刻意回避资源稀缺性的问题。这让人感到未免有些遗憾,因为资源稀缺性被当做一个不可撼动的真理,于是理性经济人就成了“合理”的产物,除非资源不再稀缺,否则理性经济人假设就顺理成章。
如果从各种社会现状来看,资源稀缺性和理性自利假设似乎是那么地真实可靠。果真如此吗?很可能只是因为今日理性经济人假设如此深入人心,被应用得如此之广,以至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假说固化成了事实。为了看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溯一下“文明时代”以前的社会状态。根据《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讲,在野蛮时代初期“家户经济是共产制的,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1],而市场经济宣扬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1]。所以恩格斯相信摩尔根的说法:“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他们相信“理性自利”依然不是真理,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需要“在更高级形式上复活”[1]。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理性自利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属性,也不能担负使社会良好发展的责任。
理性经济人假设还涉及到人的本性问题。虽然亚当·斯密一直在讲人的“自利性”,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认真地提到“相互同情的愉快”、“对正义、悔恨的感觉”、“对赞扬和值得赞扬的喜爱”、“对责备和该受责备的畏惧”,提到善的思想道德和感情给人们带来的愉悦[2]。可事实是他的“理性经济人”说法使很多人受到唯利是图的精神的激励,并认为那就是效率的源泉。
有学者通过对桑塔费学派所进行的“最后通牒”等博弈的讨论得到这样的观点:利他者之间更容易达成合作,如果合作剩余足够大,就能弥补利他者损失的进化优势,而一个完全自私的人类族群却由于无法建立稳定的合作秩序,最终会趋于灭亡[3]。另有学者指出,李斯特及其后继者(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和克尼斯等)猛烈抨击忽视了精神、道德因素以及利他主义动机等的作用的经济人假定的单纯利己主义,最终“拓展了‘经济人’假设的内涵”[4]。前者证明了利他主义和合作的真实存在及其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后者指出了狭义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不足,说明“人都是理性自利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非但不是真实可靠的必然现实,更不是利于经济研究和发展的良好选择。
我们看到了理性经济人的片面,看出了它不能反映真实的完整的人。但是,理性经济人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像宗教一样的事物,既使人们承认其中有说不清楚的地方,但还是要死心塌地地维护它,把它应用于我们的经济中。如果有一天这个系统维系起来变得困难,就对它稍加修饰和调整,给纯粹的理性经济人挂一些饰品、穿几件衣服,但是不改变它逐利的本质——就好像把一具简单的人体骨骼模型加上其他的血管模型、内脏模型,甚至连接得精巧细密。但这终究无法改变一个事实:这个模型永远不会是一个活人,因为没有血液中的各种组分,没有生物电,也没有思想。
二、利益最大化引发对立和冲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做出的大。”[5]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支柱之一,这个观点被人们深信不疑,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非但无害反而有利。这个观点当然有它的道理,从今日产品的丰富可以看出,理性自利带来的高效率的结果是确有其事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这样的机制下利益冲突也会成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在人人都自私自利的社会,必然导致急功近利和贪婪、纷争与对立。
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原因很简单,因为资本家都理所当然地自认为(也被认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他们需要考虑的出发点绝对不是社会的需求,而是利益二字。因而马克思说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对缺乏的商品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可同时又有商品生产过剩,这之间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生产的驱动方式有关,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这势必会导致两个问题——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争夺以及人们对所需的商品的争夺。前者表现为企业的竞争,后者表现为为了获取可供交换的价值储藏(主要是货币)而进行的拼杀。
那么现在社会到底在经受着多大程度的利益冲突呢?从中国的情况来讲,虽然我们看到肩负“按社会需要而生产”的使命的计划经济是不太成功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膜拜式的接受也是很有问题的。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人们相互间产生一定的敌意,二是占有优势的人不断地贪婪地攫取,引起人们对他们的仇视。如果这些敌意和仇视还不够把所有无辜的人都卷入其中的话,那么“市场化”的推广会逐渐地使穷人和富人对立起来,各个利益集团对立起来,个人和社会对立起来,人的内心和行为也对立起来,因此冲突也就多起来。
如果人们完全认可了理性自利的说法,那么就可以到处奉行:不必顾及道义,因为自利是合理的;不必对弱者怀有仁慈之心,因为全怪弱者自己无能。“弱者无能”这个巧妙的托词实际上演变成了一种市场经济中的伪道德,即:我尊重你公平竞争的权利,但是你争不过别人,这就不怪我了。发展到后来,如果谁不随波逐流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谁就连基本的利益也可能保不住了。由现在的企业之间激烈甚至不太正当的竞争,由一些为了以低成本牟取利益、打压对手而不择手段的诸如毒奶粉等现象,由令人瞠目的高基尼系数和所谓“社会再分配”的“不公平”,由其他损人利己的行为,我们可以惊叹于现在社会的利益冲突。
危害还不止于此。利益最大化引发的利益冲突和人们的过分的竞争影响了社会和谐,而且由于冲突带来的往往是补偿性的争夺,人们进一步地被禁锢在了纷争之中。利益最大化动机逐渐蚕食着人们的仁慈,因为仁慈的代价变得太大了,人们感到“负担不起”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样一来,仁慈就被“权衡取舍”掉了。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唯一能使任何行为具有美德品质的动机”,“美德存在于仁慈之中,这是一个被人类天性的许多表面现象所证实的观点”。[2]但是,由于仁慈之心已经被一些人所遗弃,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另一个严重问题——道德的缺失和扭曲。
三、市场经济下伪道德、道义缺失和出路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讲到“努力把权利所许可的同利益所要求的结合起来,使正义与功利二者不致有所分歧”[6]。他后面还提到,正义的法则如果只被正直的人遵守,而其他人不用遵守,就会出现“正义的法则就只不过造成了坏人的幸福和正直的人的不幸而已”的情况。因此“需要有约定和法律来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并使正义能符合于它的目的”[6]。似乎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下面有这样一种思路:“正义”需要靠法律来维持,而人们对功利的本能需求则在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下得到合理控制。这当然有道理,而且现代文明社会正是这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同一章里卢梭的另外一句话也值得深思:“毫无疑义,存在着一种完全出自理性的普遍正义。”这种完全出于理性的普遍正义应该体现于法律中,但是不能被法律所替代。
在今日来看,市场经济体系中法律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正义,但是如果因为有了法律,就失去心中的“普遍正义”,仅仅在法律框架下去“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想着,“反正我依法行事,已经是正义的,我只需要去满足功利的需求就无可厚非”,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就有沦丧的危险。之前已经提到过人们对亚当·斯密的“理性自利带来社会效用”的观点的盲目相信,这种信服也被一些人拿来作为道德的粉饰,即自己的行为能够给社会“带来好处”。而人们的理性自利是否真的能在长远上给社会的经济带来好处,也值得思考。恩格斯说过:“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1]可见一些人理性自利的结果是盲目的规律,盲目的规律带来的不只是“无心的贡献”,更有周期性的金融危机这样的巨大的破坏作用。毫不顾及道义地自利的同时宣称对社会作出了贡献,这根本就是文过饰非。
市场经济下盛行这样的一种伪道德:极力表现对其他人所关心的“正义”的关注——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破坏其他人追求利益的权利。虽然看上去很正确,但这种“道德”本质上是冷漠的,它只是美化利益冲突,并不能消减利益冲突。这与把“程序公平”作为正义的全部,是一样的道理。亚当·斯密说:“对损人者的动机表示赞同,对受难者的愤恨就不会有一点同情”[2]。如果人们都接受理性经济人假设,那么在规则下实质上损害他人的动机(最大化自身利益)就被广泛的赞同了,那些市场经济中的受难者能够得到的就绝对不是同情。如此一来,社会道德就无从谈起。
普遍正义的缺失和市场经济下自觉或不自觉产生的伪道德,正在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健康。在这个问题上,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应用难辞其咎。它扭曲了人们内心的是非标准,使人们无暇关注利益和规则以外的重要的东西。
在著名的巴林银行倒闭案中,无赖交易员里森在受到法律的制裁时曾说过,有一群人本来可以揭穿并阻止我的把戏,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我不知道他们的疏忽与犯罪级的疏忽之间界限何在,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对我负有什么责任。但是如果是在任何其他一家银行,我是不会有机会开始这项犯罪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段话里面根本没有里森对自己弃道义于不顾之行为的悔过和反思,有的只是对他人没有监督好自己的责备。由此,人们更加关注的不是利益最大化动机有没有错误,而是在无力地指责“道德缺失”,并强烈要求监督和内部控制的完善。这种舍本逐末的反应说明了一个问题:面对市场经济的道德问题,当下社会很少去反思理性自利的假设是不是引发问题的元凶。
有学者通过探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伦理盲点指出,有几百年历史的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局限性,所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给整个社会和自然带来的外部性成本也急剧上升,迫使我们进行经济伦理的建设。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巨大代价、重视经济伦理自然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如何建立经济伦理,该学者能够提出的办法仍然是“外在强有力的约束机制”[7]。然而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方法——打破现有市场下的伪道德,并且用道义替代单纯的理性自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认识到道德情操在人性中的地位,换言之,重新获得对人性中的善良和道义的正确的认知。正如另一位学者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最终走向对道德情感的强调,实现道德向自由情感的回归,使道德建设同人类心灵的秩序和谐统一”[8]。
利益无论最大化到何种程度,都不会是人们真正需要的价值的全部,何况理性经济人假设中的那个“利益”只不过是自身的利益。不能只从良心、社会和谐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道德缺失,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经济学研究的构架、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应用。有朝一日这些基本问题清晰地凸现出来并得到批判纠正,我们才有希望从经济怪圈和道德困境里脱身。
[1](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王京安.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及其批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6).
[4]徐传谌,张万成.“经济人”假设的发展[J].当代经济研究,2004.(2).
[5](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
[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7]张忠,曹树青.论经济人假设的伦理盲点[J].前沿,2005.(1).
[8]李建华.从道德理性走向道德情感——近代西方道德情感理论述评 [J].中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0.6(1).
B82-053
A
1009-6981(2011)03-0073-04
2011-04-29
孙苇杭(1992-),就读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郭清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