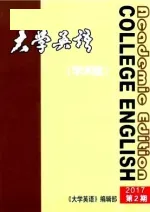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施笃姆研究综述
汤 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北京100191)
引 言
特奥多尔·施笃姆 (Theodor Storm,1817-1888)是德国文学史上诗意现实主义时期(Poetischer Realismus,1840-1890)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和诗歌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在我国,他被公认为“五四”以来最受欢迎和最富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 。
本文将笔者尽可能搜集到的近三十年来施笃姆研究的相关文献整合起来,力图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施笃姆研究现状有一个整体和尽可能全面的把握。本文分为四节,第一节是对诗意现实主义及诗人施笃姆的介绍,包括施笃姆研究者对于诗意现实主义的理解及诗人施笃姆的定位;第二节是对施笃姆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及影响的研究,包括施笃姆研究者所记录的《茵梦湖》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第三节是对施笃姆作品的分析,在这一节笔者整理了施笃姆研究者对其诗歌的研究、对其小说特点的研究、部分文本分析,并附上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缺漏和错误;第四节是结论,笔者大致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施笃姆研究的发展轨迹,并提出了对未来施笃姆研究的展望。
1.诗意现实主义及诗人施笃姆
特奥多尔·施笃姆在德国文学史上被公认为诗意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刘颖在2007年发表的论文《诗与情:施笃姆小说中的诗意追求》中较准确地概述了德国诗意现实主义的特点:“诗意现实主义(1840-1890)是德国文学史上介于浪漫派和自然主义之间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时期。诗意现实主义作家把直接的、感性的、源于内心经历的创作视为理想创作,沉湎于过去,避免对社会和政治冲突与危机作极端的描写,而致力于从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中挖掘诗意的因素和瞬间。虽然诗意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多数回避了时代和社会的重大题材,但在局部上却不都缺乏反映现实的深度。作家在写作艺术方面刻意求工、精雕细琢,因此作品富有巨大的表现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1]任卫东在2008年的论文《现实主义时期两位风格迥异的德语诗人》又概括出现实主义诗人的创作特点和目的:“……他们的诗歌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和读者感到赏心悦目,让人们感受到音律、节奏和情绪的美。……现实主义诗歌所展现的,是自我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及自我的感受。诗歌中虽然表现出自我在社会中的孤独以及世界的物化和异化,但是作者最终追求的是宁静和情绪的升华,而不是矛盾的激化。”[2]
施笃姆的小说在读者之中影响深远,但施笃姆本人却认为自己的诗歌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他曾表示:“我的小说是从我的抒情诗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因此,国内研究者在接触施笃姆初期的一个研究焦点是对施笃姆的定位。早期研究者郁达夫曾说:“与其称他作小说家,还不如称他作诗人的好”,这确定了为施笃姆定位的基调,后来的研究者则多由此出发,结合其作品中的诗意元素论述其“诗人”身份的合理性。对于施笃姆作品中各种诗意元素的收集,也是研究者们乐意进行的一项工作:如小说人物形象不是纯粹的形象,而更接近诗化形象;小说中叙事成分比一般小说的为少,而更注重描写(前期作品中更为突出);“创造意境和气氛”是施笃姆小说最主要的创作特色之一,其景物描写是为营造意境服务的,等等。杨武能与张世君还分别在1986年的 《施笃姆的诗意小说及其在中国之影响和1993年的 《诗意小说<茵梦湖>》中研究了施笃姆小说之所以充满诗意的原因[3][4]。因此,虽然施笃姆的小说在读者之中影响深远,但总的来说,施笃姆仍被我国研究者定位为一位“诗人”。
2.对施笃姆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及影响的研究
2.1 《茵梦湖》译介研究
《茵梦湖》的译介工作始于五四运动之期,从钱君胥最初试译时全文采用中国旧平话体小说到后来层出不穷的译本,《茵梦湖》的译介可谓枝繁叶茂。单是小说的题目就曾出现过 《隐媚湖》(之盎译,1916年)、《茵梦湖》(郭沫若与钱君胥合译本,1921年)、《意门湖》(唐性天译本,1922 年)、《漪溟湖》(朱偰,1927 年)、《青春》(梁玉春,1940 年)、《蜂湖》(巴金 ,1943年)等不同版本。杨武能和卫茂平详细记录了各译本之间的差异、诸位译者对施笃姆作品的评价及小说最终定名为《茵梦湖》的全过程。其中卫茂平论述了《漪溟湖》与《茵梦湖》相对于其他译名的优胜之处,最终分析指出“茵梦湖”的最终胜出是浪漫主义追求的胜出。
马君玉曾重译《茵梦湖》并于2007年在《译林》上发表《新译<茵梦湖>有感》,强调翻译要在“充分读通原著,理解词句所表达的确切意思”的前提下进行[5]。不过由于译者尽力替读者揣测作者的意图而造成了译文与原文在字面上出入较大、对应性不强。此外还有钱定平在《千里追寻<茵梦湖>》(1999)中用具体的例子指出杨武能《茵梦湖》译本的错译、翻译欠妥和语句不通的问题。
2.2 《茵梦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在向中国读者介绍施笃姆的工作中,郁达夫属于垦荒者之一。刘久明和龙全明在其合著的论文《郁达夫与施笃姆》(2002)中总结了二者作品的相似点[6]。郁达夫创作后期的力作 《迟桂花》与施笃姆的作品《迟玫瑰》的多处相似更体现了后者对前者在创作上的影响。部分研究者分析认为,《茵梦湖》之所以激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共鸣是因为19世纪的德国社会与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都处于新旧社会制度交替的过渡期,新旧道德观的冲突所涉及的家庭伦理问题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年轻人,尤其影响了他们在爱情和婚姻上的自由追求。刘久明和龙全明还指出,两位诗人的作品虽然富于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但却都只局限于作家接触到的一小部分现实而回避了重大的社会政治题材,使得作品在整体上缺乏宽广的生活视野和恢弘的艺术气度[6]。关于这一点,杨武能提出过反对观点,认为这显然受“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教条及“题材决定论”的影响而得出的结论,如果以此为依据草率判定施笃姆不够深刻、不够经典,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地,正是这些恋爱、婚姻、家庭题材才能更好地展现社会变迁、反映时代风貌[3]。
除郁达夫的《迟桂花》外,周全平的中篇小说《林中》(1925)诞生于“五四”时期,小说的主题、情节、表现手法、篇章结构甚至小标题和许多细节都与《茵梦湖》十分相似,被认为是《茵梦湖》的仿作;卢隐的《象牙戒指》也被认为是参照《茵梦湖》完成的一部成功作品。此外,巴金《春天里的秋天》(1932)与萧乾的《梦之谷》(1938)都把《茵梦湖》当做范本。这表明施笃姆的作品已经具体而直接地影响了部分中国作家的创作。
3.对施笃姆作品的研究
施笃姆作品主要分为小说和诗歌两大类,本节将对两种文类的研究分别加以论述。
3.1 对施笃姆诗歌的研究
在我国对施笃姆作品的研究中,小说研究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诗歌研究则相对较少,目前有任卫东、赵红平在其研究成果中涉及了施笃姆诗歌的特点研究。
任卫东将现实主义诗人施笃姆与迈耶及二者迥异的诗风加以对比,认为“施笃姆强调的是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对他来说,语言和感受在音乐性下统一起来,这就是诗歌的根本特点。……因此,作为诗人的施托姆更加靠进浪漫。他的诗歌基本上是浪漫的民歌风格,强调音乐性,有意识地接近民歌。”[2]此外,任卫东还指出,在施托姆的诗歌创作中,爱情、自然、四季和晚年的死亡是绝对的主题[2];施笃姆的诗歌强调的是简朴,但是他的诗歌所产生的力量却是同时代诗人无人能及的;他描写的自然风景诗歌常常带有明显的故乡痕迹;其早年的爱情诗丝毫没有哀伤的情绪(这与他早年的中篇小说完全不同)。赵红平则通过 《试论施笃姆小说的主要创作特色》(1984)一文更为细致地从形式分析(Formanalyse)角度出发,指出施笃姆在诗歌押韵中用得最多的是毗连韵(aa bb)、交错韵(ab ab)和连环韵(ab ba)[7]。
3.2 对施笃姆小说特点的研究
国内研究者往往根据作品的风格变迁将施笃姆的小说创作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认为其前期创作以《茵梦湖》为代表,注重创造意境而缺少连贯的情节和激烈的矛盾冲突,《玛尔特和她的钟》、《一片绿叶》、《迟蔷薇》等作品属于此列;后期创作以《白马骑士》为代表,重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富有戏剧性,《双影人》、《她来自大洋彼岸》、《淹死的人》等则属此列。也有研究者在这两个阶段中加入了一个过渡阶段,将《在华丽的庄园里》、《在大学里》、《燕语》和《木偶戏子波莱》等作品划入其中。在实际分析中,研究者多从内容和形式两个角度对施笃姆小说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
3.2.1 内容分析
首先,浓郁的家乡特色是施笃姆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作者在作品中曾多次以不同形式展现家乡胡苏姆的景致及风俗,这已是被众多研究者公认的施氏创作特点之一。施笃姆作品中的远足、舞蹈、滑冰、木偶戏、集市、婚庆等场景及一些细腻的景物描写,无一不是其家乡风貌的再现。
其次,施笃姆小说大都带有悲剧色彩,这一特点也被一些研究者所关注。邵思婵1988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题为 《施笃姆悲剧命运小说的艺术特色》的论文,将施笃姆小说称为“悲剧命运小说”,认为小说主人公苦闷绝望的情绪反映出了作者彷徨迷茫的精神状态,作品中屈从于现状的人物则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8]。
第三,施笃姆小说中往往以象征(或暗喻)作为主要的修辞手法。如《茵梦湖》中的白色睡莲、《淹死的人》中的画像、《双影人》中的枯井等意象在都小说中反复出现,既作为线索贯穿全篇,又暗示着情节发展的方向。
第四,在小说中穿插诗歌是施笃姆所特有的一种手法。在《茵梦湖》中,作者共用了四首诗歌,另外,在《在大学里》、《林中角隅》、《淹死的人》中,施笃姆都运用了诗歌。此外,施笃姆文本灵巧的构词也使得其作品简练的语言中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第五,施笃姆擅长对女性和儿童的描写。按照王秉习在《初探施托姆笔下诸多女性》(2009)一文中的划分,施笃姆笔下的女性形象总地来说被分为了具有悲剧命运的女性和有美好生活前景的女性两类[9]。在前一类女性身上寄托了施笃姆对人性的良好愿望,后一类女性身上则体现了施笃姆的人道主义关怀。另外,施笃姆又是一个描写儿童的出色作家。邵思婵和赵红平都强调了《茵梦湖》中对儿童的生动描写,笔者认为此外《双影人》中的儿童刻画也是十分成功的[7][8]。
3.2.2 形式分析
首先,框形结构是施笃姆小说结构的一个明显特征,即小说的中心故事是由小说中的人物回忆出来,或者由人物听到、读到的。框形结构有助于将读者的视线引到叙述的中心事件上去,使得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得以淋漓地展现。赵红平进一步指出,在框形结构的研究中应将施笃姆小说划分为历史性小说和现实问题小说[7]。其中历史性小说的框形结构起到了今昔对比的作用,而以现实问题为题材的框形小说(作者列举了《木偶戏子保罗》和《双影人》)则可另归一类:框内叙述主人公值得同情的遭遇,框外的内容则常常寄予着作者乌托邦式的理想,如受难者的女儿们和中产阶级缔结了姻缘而摆脱了苦难。赵红平强调“这种结局在现实中并不多见,因而失去了真实感和深刻典型的社会意义,多少有削弱作品批判力量的作用”。
其次,施笃姆在小说布局上详略得当。在情节安排上,他的故事看似不符合事实的逻辑,却合乎情感的逻辑,读者在阅读时会觉得情节安排正符合自己的感情需要。在人物描写上,小说次要人物少,出场次数有限,作者着墨也不多,这些人物既不喧宾夺主,又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如《茵梦湖》中伊丽莎白的母亲。
3.3 文本分析中的缺漏及错误
在笔者收集到的近30篇论文中,部分篇目存在着一些不恰当的观点,也有一些错误。如赵红平提出施笃姆描绘自然景色 “实际上却在用赞美大自然魅力的方法否定宗教的威力,表达自己反对宗教迷信的思想”[7];周柳波认为“施笃姆在莱茵哈德身上,寄托了至善至美的人格理想,莱茵哈德具有一种内倾性的悲剧美,具有宗教情怀——放不下的心肠和自我牺牲精神”[10],这样的观点则显得有些主观,缺乏有力的依据。从语言上来讲,赵红平将“scharfe Augen”(锐利的目光)、“helles Lachen”(爽朗的笑声)和“kalte Blicke”(冰冷的眼光)视作通感修辞[7],则是不够了解德语习惯用法的表现,且论文中引用的德文有多处大小写的混乱和拼写错误,这不能不算是论文中的缺憾。
4.结 论
施笃姆的作品《茵梦湖》最早在“五四”期间被译介到中国,被当时的青年人解读为批判旧道德束缚的文学作品,得以广泛传播。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文本解读模式仍然影响着一些研究者,一些文本分析中会出现一些政治性或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的评论。随着施笃姆更多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一方面译作日趋完善,且同部译作的不同版本也能形成对照;另一方面研究者基于对施笃姆作品更全面的了解也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新的研究方法如性别研究、社会学研究被应用于文本分析,新的研究角度如美学角度、形式分析等也将施笃姆作品的文本分析引向了更广阔的方向。
[1]刘颖.诗与情:施笃姆小说中的诗意追求 [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第6期。
[2]任卫东.现实主义时期两位风格迥异的德语诗人[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第19卷,第2期,15-19页。
[3]杨武能.施笃姆的诗意小说及其在中国之影响 [J].外国文学研究,1986,第4期。
[4]张世君.诗意小说《茵梦湖》[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3,第1期。
[5]马君玉.新译《茵梦湖》有感 [J].译林,2007,第4期,215-218页。
[6]刘久明,龙全明.郁达夫与施笃姆 [J].江汉论坛,2002年8月。
[7]赵红平.试论施笃姆小说的主要创作特色[J].国外文学,1984,第1期。
[8]邵思婵.施笃姆悲剧命运小说的艺术特色[J].外国文学研究,1988,第1期。
[9]王秉习.初探施托姆笔下诸多女性 [J].青年文学家,2009,第24期。
[10]周柳波.凄怆的爱情挽歌,完美的人格理想——浅析《茵梦湖》[J].柳州师专学报,1995年6月,第10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