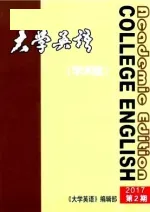死亡之美:论爱伦·坡与海子诗歌里的死亡观念
张君茹 郑 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191)
引 言
叔本华说过:“没有死亡问题,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1]P118同样,存在于诗歌之中的死亡意识也为诗歌带来了长久的活力,使诗歌更切近生命的本质,使之进入人文和生命终极关怀的最高层次。笔者认为死亡不仅仅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是伤感的代名词,更是一种生命的延伸。当今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晦暗不明的舞台上,我们只是茫然地将生命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而死亡意识的迸发不再允许我们沉溺于以往的自以为是的假想中,为浑浑噩噩的众生敲响了反省的钟声,对生命的最终意义进行追问,追求人生的真谛。而谈到死亡意识,就不能不提及埃德加·爱伦·坡和海子这两位伟大的诗人,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两人的作品中蕴含的死亡哲学来分析他们的诗歌所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特色。
一、埃德加·爱伦·坡的死亡观念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一生致力于探索死亡的真谛,死亡之美在他创作的众多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读者也可从中领悟到诗人对生的渴望,对爱的追求。诗人认为死亡是自然超脱的,极力追求死亡之美的境界,他复杂痛苦的人生经历令其体会到死是一种“善”,甚至是“解脱人类痛苦的最彻底的方式”[2]P84。也就是说,“‘死’是一种美,一种‘超凡之美’!”[2]P87坡关于诗歌题材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最富有诗意的忧郁话题”则是“死亡与美的紧密结合。”[3]P12
爱伦·坡极度崇尚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他强调美的再现是诗的主题,而死亡之美更是美的极致,坡诗歌中亘古不变的主题即时美人之死。他的诗歌里总会出现一位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性,但都有诅咒般的宿命,注定走向死亡。诗人会有这种极端诗意是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爱伦·坡觉得现实如此残酷而丑恶,在死亡之美中找寻生命的意义。在他的诗中美丽与死亡总是如影随形,幸福与恐惧也是交替出现。爱伦·坡将死亡、忧郁以其独有的形式表达出来。《致海伦》、《乌鸦》、《安娜贝尔丽》、《尤娜路姆》等抒情诗都表达了对所爱之人的死亡无以言表的悲痛和绝望。
二、海子的死亡观念
海子原名査海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诗人的重要代表。他的主要诗作强调的也是死亡的悲剧气息,与坡诗歌中死亡的悲剧美学色彩不同。海子生前好友、著名诗人西川说:“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对于我们,海子是一个天才,而对于他自己,则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4]P72读者可以从中明显感触到,海子的带有强烈的悲剧美,孤独美。现实中海子的大部分诗歌里都弥漫着一种浓重的死亡气息,他对死亡有一种强烈的感知力。对诗人而言,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只是抛弃了束缚灵魂和思想的肉体,却带来更自由的精神冒险,所以,海子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投身到死亡的大海中去,完成他无比凄美和壮烈的人生写作。
三、坡诗歌中的死亡主旨
在死亡主题的时代影响下,坡更加倾向于从死亡、幻觉和重生中追寻诗意,执着的追求死亡之美。
《乌鸦》是坡的代表作之一,全诗一百零八行,描写了一位美丽女性的生命逝去。乌鸦是死亡和不幸的象征,坡在诗中运用这一意象,传达出男子失去爱人的痛苦。同时也表达了男子在“愉悦的悲哀”中得到快感,而且“这种快感因主人公的过度感伤而更显美妙”。[5]P214《乌鸦》的总基调是悲痛而压抑的,弥漫着浓浓的哀思愁绪。每一段结尾不断重复的“永不复生”,提示读者生命永不再回来。男主人公因此而极度悲伤不能自已,几近崩溃,同时也令他体会到悲伤和美共存的双重享受。诗中写道:“每一面紫色的窗帘都发出悲伤而又不定的沙沙声,那声音使我震颤—从未有过的恐怖布满全身……”[5]P230紫色本身是一种冷色,烘托出气氛的阴郁和色彩的恐怖。爱伦·坡在他的诗歌中大量地铺陈死亡场景,构建死亡意象。但同时他的诗歌意境又能带给读者美的享受,鼓励人们探索生命的真谛,追求生命的美好,这种死亡之美是是脱胎换骨的、超现实的美,是净化人心灵的美。
爱伦·坡关注的不是个体的生命极限,而是大美与大爱。对死亡之美的通透描述令读者感悟到内心的恐惧,在震撼中升华自己的内心情感。在坡看来,死亡将灵魂带出繁华的物质世界,通往空灵纯净的内心世界,所以,他说人人都“向往死亡”。爱伦·坡痛苦的人生经历令他极度痛恨这个万恶的现实世界,挣扎却毫无出路,诗人只能渴望着在死亡中解脱自己,摆脱肉体的束缚,升入最纯洁最美好的境界中。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只好努力营造出死亡之美的意境,塑造死亡之美的主题,为自己也为读者描绘出一个超越现实的,无限美丽的,充盈着自由的灵魂王国。另一方面,爱伦·坡把“死亡”当作“新生”。他的内心永远处于尖锐的矛盾状态:永远追求,永远失望。而死亡即时这种矛盾与对立的统一,他用死亡的力量对抗现实的冷酷。透过他对死亡的悲观恐怖的描写,对现实世界的鄙视与抛弃,读者可以洞见到诗人对美好人生的憧憬和对不朽灵魂的追求,对纯洁、永恒事物的向往,这正是爱伦·坡的死亡哲学的真谛。
四、海子诗歌中的死亡主旨
海子对死亡的态度与坡颇为相似,尽管对读者来说是另类的。死亡对于诗人不再是恐惧和痛苦,而是自然和自由的超脱,是恬然和淡定的抉择。他于1987年写下这样的诗句:“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2]P15反映了海子对死亡已经不再害怕和恐惧。在他看来,既然尸体并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死亡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当他最终躺到山海关的一段铁轨上时,仰望蓝天,他可能想到的是升入天堂时的静谧与安详,当火车轮滚滚而来碾断他躯体的那一刹那,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剧痛,他也许会在心底大喊:“你变成尸体了,而我——解放了!”[2]P20
海子在许多诗中都谈及死亡,在其三首名为《死亡之诗》的“之一”中写道:“漆黑的夜里有一种笑声笑断我/坟墓的木板/你可知道。这是一片埋葬老虎的土地/……一只埋葬老虎的木板/被一种笑声笑断两截。”[2]P37这首“歌特式”、意象明确的小诗颇有另一番寓意:“笑断两截”与海子自己在山海关被火车轮碾轧成“两截”是多么惊人地吻合!可见海子在此时已预见到自己的死亡方式。在“之二”中有这样的句子:“请在麦地之中/清理好我的骨头/如一束芦花的骨头/把他装在箱子里带回/我所能看见的/纯净的少女,河流上的少女/请把手伸到麦地之中/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凌乱的骨头/放入一个小木柜。”[2]P58海子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如画、凄美景象,如同一副令常人惊悚的死亡之后的卷轴,麦地、骨头、芦花、箱子、河流、少女、麦子,种种意象的叠加,使死人的“骨头”和棺材(“箱子”)不再是令人惊恐恶心的死亡的象征,相反,骨头好似象牙般的宝物,须由“纯净的少女,河流上的少女”带回家,并且要将其整理好“放入一个小木柜”中。我们读到这里一点也感觉不到死亡的悲伤,因为这实在是一幅太过凄美的图画。海子对死亡的极度迷恋与渴望有时是令读者不寒而栗的,却总能用充满诗意的描述带给我们想象的空间。
海子曾说过“生是需要理由的。”这是他留给世人最值得回味的警世良言,有了他这句话,读者会时常问自己:“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也许我们就因此而不去浪费生命,也不会再害怕死亡;“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的海子也许会在某个春天复活,他并没有消失在读者的视野中,只是暂时迷失了。而海子的复活将带给这片大地一派欣欣向荣,成为读者心中不死精神的永恒存在。生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就应该慷慨赴死,这正是海子死亡意识的核心内涵。
结束语
儒家思想在中国沉淀了几千年,这种历史厚重感决定了国人更关注怎样处世做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现世意义,西方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形而上的、唯美的有一定的思考。海子在他的诗中时时刻刻透露出对死亡的思考与推敲,颠覆了读者对国人这种固有的框架模式,海子的死亡之美表达出人类追求生命的本质意义的努力,这点与坡一脉相通。通过分析比较两者对死亡的思考有助于引发人们对当下贫乏的精神世界的反思。反思死亡即是对生存的沉思。只有当每个人都意识到生存危机是普遍存在的,人类的内在潜力才会充分发挥,生命的光芒才会更加耀眼,才会带来整个民族的振兴,因而不能忘却诗人所眷顾的死亡之美。
[1]叔本华.叔本华论文集 [M].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
[2]查海生.海子诗集 [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6。
[3]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西川.死亡后记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5]爱伦·坡爱伦·坡精品集 [M].曹明伦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