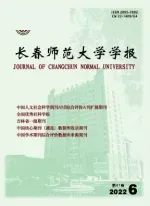从认知语用推理维度审视言语交际中的语境思维
李 爽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江苏无锡 214153)
语境在认知语言学中主要指语用者通过经验把具体的语境内在化和认知化后,存在于语用者自身的语用知识。语言除了字面意思外还包含交际意义,听话人需要根据认知语境进行认知语用推理,即:语言传出者在传出语言交际意义前,已根据语言接受者可能的认知语境,进行了逆向的认知语用推理。下面我们对《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这篇文学作品中的时空交错进行分析,以此解读语用推理对语言超载信息的理解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认知语用推理机制:用语用推理解读语言接触中的深层思维
语言是人类形成和表达思想的手段;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能动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思维与语言虽然是两种机制,却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根据英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格赖斯的语用推理模式,交际者传递某一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接受者明白他的意图,语用学的中心任务就是解释这些刻意的交际意图是如何被推导出来的。语用推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它包括各种语境信息的搜寻和激活、一次或多次的推理过程以及结论的验证等。其实,人们之所以能在信息不完备的前提下进行推理并获得合理的认识,就是因为利用了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这种以默认前提或常识为基础的推理,一般是自动的、无意识的、无需刻意作出努力的思维过程,从而使人们在瞬间作出判断和推理成为可能。人们交际的目的不是寻求最大关联,而是寻求最佳关联,即受话人以最小的信息处理努力获得足够的、最佳的语境效果。在这一明示——推理的认知过程中,关联理论为语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理论框架。
本文重点分析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特征,即关联理论这一语用学理论主要研究信息交际的推理过程,尤其注重语言交际的话语解释原则。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篇章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语篇建构过程和语言信息处理行为,从而更好地指导阅读理解实践。本文在概述关联理论核心内容的基础上,以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下文简称《玫瑰花》)为范本,从叙事学的角度,着重分析这篇小说在叙事中时间与空间刻意交错与互补的特征,以及这一特征对于表现小说主题的特殊意义,并由此从时空维度来分析关联理论与语篇分析的关系,论证语篇分析是一个读者和作者交流的过程,语篇分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作者所表达的话外意图 (交际意义);语篇分析的实质是推理,是一个读者利用自己的百科知识、逻辑知识与词汇知识对新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语篇分析是一个读者与作者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所依赖的语境是一个动态的并且是相互作用的心理构建,并以此来探讨如何通过语境来寻找关联、进行语用推理来正确理解语言,进而增强局部连贯和整体连贯的意识,深化将语篇连贯理论和方法渗透到阅读与写作教学中去的思想内涵。
二、背景知识的激活与连贯性的保持:用最佳关联解读叙事时空的交错与互补
1.以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交错解读语用推理是语言交际的核心
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把交际看作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人类活动,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认知过程。明示是对说话人而言的,指的是说话人明确地向听话人表示意图的一种行为;推理是对听话人而言的,指的是听话人通过明示手段所提供的信息推断出说话人的意图。语言交际活动涉及两种意图: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也就是说,说话人说话时不仅表明他有某种传递信息的意图,更要表明他有传递这种信息的意图。
因此,交际过程不仅仅是单纯的编码—解码过程,还是对话语和语境信息的动态推理过程。推理是获取隐含意义的主要方式,它根据语言手段或非语言语境获取有关话语内容的逻辑结论。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听话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设才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一方面,形成假设的过程是人们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依赖语境因素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语境必须结合交际事件的社交因素。在任何一部叙事作品中必然会涉及两种时间,即故事的时间与叙事的时间 (文本的时间)。传统小说中,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基本呈重合状态,事件的排列犹如串好的糖葫芦,清晰而有序,即使偶有插叙和倒序也不影响直线而下的顺利阅读。想用和故事实际发生的时间来描述叙事文本的时间跨度是很难做到的,任何人都无法回避这一客观限制,然而《玫瑰花》却用短短的几千字就展现了爱米丽小姐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小说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开头采用了法国学者热奈特提出的“时间倒错”的手法,直接概述爱米丽小姐的葬礼,然后又将目光推回“1894年某日”镇长沙多里斯上校豁免了爱米丽的一切税款。但是后来“思想开放的”第二代镇长和参议员因对这项安排不满而打算登门访问。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在沙多里斯和第二代镇长就任之间的时距上采用了省略的手法,其叙事时间为零。这中间究竟隔了多少年,爱米丽小姐发生了哪些事还无从得知。但当参议员们正式访问爱米丽家时,却插入了一句“自从八年或者十年前她停止开授瓷器绘画课以来,谁也没有从这大门出入过。”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参议员的拜访应是在开授瓷器彩绘课之后,即“八年或十年前”这段本该在前的故事时间被穿插进了作品的叙事时间。与之相同的还有第二部分中当镇上的人们处理完爱米丽家的“异昧”事件后,出现了一个“内倒序”,即以镇上人们的视角转入了对爱米丽父亲生前与死时爱米丽境况的回忆。这种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相互交杂的情形不仅在每个单独的部分中频频亮相,而且在每部分间的衔接上也被巧妙地加以利用了。如第二部分开头就并未紧扣第一部分末尾展开叙述,而是猛然将镜头拉回了30年前。读者所期待的叙事时间被中断而又回到了往昔的故事时间。诸如此类的插入式回忆与正常的故事逻辑不断冲击碰撞,迫使我们以跳跃的眼光和非直线型的思维参与揉和到作品中。虽然小说里的时间“线条不是笔直的,而是依据一定的思路将看似不相关的东西串起来”的“一种主观认知和感情的产物”,但人类需要意义,而意义取决于连贯性,并且时常产生于某种一连串同质成分组成的完整无缺的线条之中,所以无论先后以及出现的东西多么杂乱无章,人们都会试图在其中找出某种秩序,在秩序中发现各自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认知脚本的激活不仅依赖于话语中的语词,更为重要的是依赖于语境假设的确立,依赖于交际者的认知语境。
2.以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互补解读语境关联是话语理解的理据
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这个过程是靠明示推理来进行的,并受关联原则的支配。在交际的过程中,每个交际行为都传递有最佳关联的假设,即说话者总是通过话语提供具有最佳关联的假设,话语理解则是一个通过处理话语找出最佳关联解释的推理过程。波兰美学家罗曼·英伽登在谈对文学作品的认识的时候曾提出“不定点”的概念。“不定点”正好符合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即言语交际涉及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对话语信息的处理:说话者通过明示交际行为,为听话者理解话语提供一定的相关信息和认知语境,让听话者获取某种信息;而听话者对话语的理解,是经对方的明示信息激活有关的认知语境,而努力寻找关联,并进行推理以明白对方的交际意图,从而获得语境效果。而正如本文刚才的分析,因为叙事与故事时间的杂糅似乎造成了时间的中断和情节的流失,但作家设置的若干个“不定点”并未成为悬而未决的无头公案,而是在某一小节的叙述中再次展开,不着痕迹地互相补充说明,填补了空白。如第一部分中爱米丽开授瓷器绘画课一事虽一语带过,但到第四节中又出现了对同一事件的更为详细的描述,使我们对女主人公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开授瓷器绘画课是爱米丽孤寂封闭的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关于爱米丽故事的重要一幕,虽然故事的帷幕在第四节中才正式拉开,但这也恰是对开头部分零叙事时间的照应和补充。比较明显的例子还有第二部分开头略微点到爱米丽的心上人抛弃了她,但下文却将这颇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信息抛到了九霄云外,铺开了对“异味”事件的叙述。而当我们尚沉浸在这一片“异味”的迷雾中时,作者在第三部分却又回到了几乎被人们忽略的“心上人”身上。至此,这一消息性联结因素才向我们揭开神秘的面纱。于是,荷默·伯隆这个新的人物浮上水面,又牵连出新的关系和事件。由此,在福克纳那里,“葫芦串”的主轴已经断裂,甚至还横生出许多“枝节”。而这一个个滚落的“糖葫芦”已成为散在的存在,需要我们的大脑重新赋予其秩序,这种看似混沌一片的布局却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和思索。所以小说中的一些事件以不同面貌较高频率地重复出现不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在实际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为了准确理解话语标记语的制约性,我们就很有必要依据一些语言手段解码话语信息,积极寻找关联,以达到推断语篇内容的目的。
3.以时间与空间的互补解读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所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是语用推理
篇章分析是对语篇的理解,它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需要读者通过从文字中获取信息并进行加工而获得有效信息。在这个过程中,读者根据最佳关联的原则把分散于篇章中的各种信息整合与联系起来,经过必要的判断、推理,寻求话语与语境的最佳关联,在认知语境的作用下取得话语的交际意义。也就是说,通过语用推理建构一个篇章的意义是读者与篇章不断进行交际活动的结果。读者把新知识和旧知识联系起来,在对词汇意义的解码的过程中,实现对篇章的全面理解。可见语篇分析的实质是一个判断、推理、归纳、总结的过程,是读者根据最佳关联的原则在认知语境的作用下通过推理取得话语的交际意义的过程。在交际时,双方的认知语境要形成互明,说话者要根据他对听话者认知语境作出的假设,选择合适的语言形式。
《玫瑰花》中不乏对“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的出色运用。对于小镇上的人来说,时间从其对爱米丽一家有记忆起直到她去世始终是自然地向前推进的。“我们”看到爱米丽小姐逐渐“发胖”,“头发越变越灰”,唯一服侍她的黑人“头发变白了”,“背也驼了”;然而与时间的洪流格格不入且顽强对抗的因素依旧“岿然独存”。对于爱米丽小姐来说,时间已然凝固和冻结。70多年来,她几乎完全封闭于那间“19世纪70年代风格”的房子里。在这“光线阴暗”,“空气阴湿而又不透气”,包着笨重家具的皮套子“已经坼裂”的空间里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小房间,荷默·伯隆的尸体在那儿躺了40余年。爱米丽用砒霜将他毒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每晚都与这具尸体同床共眠。这幢大木屋就是一种特殊的时间形式,是“过去”插于“现在”之中的象征。爱米丽身上那似乎因停滞而失去了的时间正是在这一屋子中找到了存在的证据。
小说的五个部分中,时序来回颠倒,故事悬念迭出,时间被割裂又被重新拼贴得天衣无缝。福克纳正是要通过这种叙事时间的跳跃性来迫使读者注意叙述时间本身,而以“房子”意象为代表的空间也是与时间融合在一起的,它标识着爱米丽生前的时间与回忆。这些被割裂分散的信息单位巧妙地互相关联,有机地构成一个艺术整体,每一个单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本身,而且也在于它与其它单位的联系。由于本文挣脱了以往因受“西方主导传统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假定”而将叙事“视为因果相接的一串事件”的束缚,所以读者必须在与整体的联系中去理解每一个单位。
语境是保证交际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使交际灵活的重要手段。说话人可以利用语境因素成功表达思想,受话人可以结合语境因素对话语进行分析,推导出言外之意,在语境中学习语言是使学生获得言语交际能力的重要要求。如果我们能够在阅读理解教学中较好地运用语用预设与认知语境,一定能够帮助学生挖掘出话语的深层含义,从而有助于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本文通过实例论证了语用推理、认知语境在阅读理解推理中是一种主动的“猜测—证实”的过程,一种心理语言的揣摩过程,一种 (作者与读者)“相互交流的过程”。这一认知过程体现在阅读理解中即为对文章和段落要义的理解、具体信息的搜索、上下文中词义的推测、作者态度或意图的推断。
[1]罗钢.叙事学导论[M].3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32.
[2][美]H·R·斯通贝克选·序.[M]//《世界文学》编辑部.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00.
[3]刘灿,贺荟中.西方心理语言学中回指推理的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10(4).
[4]翟雯婷.关联理论对语用推理机制的阐释[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3).
[5]张斌峰,张毅龙.意思表示解释的语用学透视——语用推理的维度[J].前沿,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