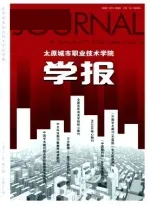文学作品翻译之中翻译人内心偏差
魏春枝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漯河 462000)
文学作品翻译之中翻译人内心偏差
魏春枝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漯河 462000)
翻译所出现的内心活动是非常复杂的,涵盖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就有意识来讲,翻译人常常会深受外在因素的作用与内在因素的约束;不过由潜意识角度来审视,此种作用与约束却显得非常含糊不清。文章由文学作品翻译视角进一步探讨了翻译人潜在思想意识之因素对于译文真实性所导致的非正面作用,且探讨了翻译人在译文表达上一些偏差的原因。
文学作品翻译;心理
翻译乃是各种文化与语言相互间开展信息传输与交流沟通时所应用的一种方式。此种方式,它自身应该有二种主要功能:就是文化间相互交流以及信息传输。对于不是文学翻译来说,能实现此二种主要功能就算是满足了翻译基本要求。不过对文学作品翻译来讲,只满足此功用是不行的。由于文学作品乃艺术之精华,展现的是作者的社会认知、内心情感和其创作风格。所以对于翻译文学作品来讲,展现原著的意蕴就显得特别重要。
翻译乃是某种理解和认识的过程,就理解此环节,一些翻译人就会不由自主地被那些觉察不出的内心活动等因素影响,进而出现判断失误,理解差错。就像社会心理语言学指出的“接纳意识”所讲的那样,受用人在接纳相关作品之中,依照自身的人生价值观、审美观念、自身经历、生活氛围、个人嗜好等对文学作品有不一样的认知与想象。并且翻译人还要深受外在条件的作用与约束,比如对翻译作品社会效益之注重以及对于翻译作品读者渴望视野之关注等。
所有作者在文学创作的时侯,其文学创作都源自其自身的生活实践,也就是说,是源自其对自己现实生活之体会。文学创作乃是为了迎合人的一种渴望和需要,且此种渴望和需要又是经过人内部的素养和外部氛围的偶合而导致的。翻译乃是某种逻辑思维之过程,其注重不用主观意识去了解与探究目标。可实际上,翻译人会往往不由自主地被那些人的内心活动所影响,让其翻译的作品和原著在好多地方有偏差。在人的内心活动上,布什就提出过“事实兴趣”概念。也就是说,人们会有或者被激发出的某种极强的愿望:渴望人们喜欢或者欣赏的人能够成功,不喜欢的人被打击,也可以说,人们渴望见到或担心见到人物的品格有转变。此种人的内心活动常常导致翻译人远离了原著里的人物,是翻译人所喜爱的人物根据其主观希望的方向推进,展现在翻译方面翻译人或许会对有的内容描写的少,有的却夸大内容,进而削弱了所翻译作品的真实性。下面我们来分析鲁迅小说《阿Q正传》结尾部分的翻译: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好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了一趟。
As for the responses ofthe event in Weizhuang,there were no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it.Undoubtedly,they all said Ah Q was so unfortunate,and having been shot was the proof of his unfortunates;ifnot,howcould he have been shot?
人们都知道,鲁迅对该作品的真实创作目的是主要通过创设阿Q此愚昧无知的小说人物来批判那个年代的愚昧无知,进而暗示辛亥革命的不成功就是其革命不彻底以及没能深入人民大众基层。作品的结尾部分所描绘的未庄人与城里人对于主人公死亡的各种不同反应,就是作品的核心所在。可是对阿Q此人物角色,若对我国的近现代历史不清楚,以及对于作者真实创作目的不清楚的话,就不能准确把握,自然而然地认为阿Q傻乎乎、有趣,进而对其有种同情怜悯。原著里面的“坏”这个词,在翻译中被翻译成“unfortunate”。此种翻译对原著中所蕴含的嘲讽意味被削弱,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于原著文学实质的掌控。而有的译作之中,仅仅是把它翻译成“bad”,此翻译简单明了、正确地表达了原著主旨。因此,人之内心活动肯定会在翻译之中展现。不过,人的内心活动和他性格、教育、氛围等有很紧密联系,还和人的生活阅历有联系。人们所说翻译就是翻译人和原著作者内心沟通交流之过程,翻译常常需要翻译人忠实地翻译原著,可在具体翻译之中,人的阅历在这里面也有相当影响。翻译人在阅读原著的时侯,若其曾有和文学著作中的人物相近或相同之经历,则其在翻译之中就会加入其自身的情感。
翻译有三难:是否能做到信达雅。雅指的是文体与艺术风格之问题。在翻译过程中,其涉及到的常常是翻译人怎样重现原著的的艺术风格。由人的心理学视角审视,所形成的文风是思维定势之范围。所有翻译人,在其具体翻译过程中大都多多少少有自身的翻译风格。有的注重高雅,有的注重朴素,有的注重整体效果,有的注重神似,而有的注重形似等。可是整个事物全是绝对和相对之统一,若人们一直是过分注重某个方面,则译文的真实性也很难确保。黑格尔是这样描绘“作风”的:“由于作风仅仅是众多艺术家特别的,因此也是偶然之特征,它的这些特征并不全部是主题自身和它的理想的展现所需要的,恰恰是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之中逐渐展现出来的。……如果艺术家具有作风,就好比是捡到了某种很坏的东西,由于艺术家拥有了作风,其也就仅仅是在放任其自身的纯粹的狭隘的过于主观之摆布。”翻译人怎样来认知翻译之中介实质且在翻译过程中准确恰当处理好其自身的翻译风格以及原创者的独特文风。有专家曾经如此来评论一个翻译人对作品《红与黑》结尾言语之中“die”的翻译,此位翻译人员居然将其翻译成为“魂归离恨天”。法语里对死亡的词语表现不比汉语的表达差,可是原著里面仅仅只用了一词“die”,可是翻译者又为什么将其翻译得如此复杂化。“魂归离恨天”就是原作者让“死”这个词汇中所暗含的让人们去领悟的意思,翻译人将它翻译出来,此行为对该作品的作者以及阅读译文的人们来讲都是很不公平的。首先,就文学作品来讲,其需要激发起人们的想象思维,而不是使想象思维去停滞,其激发起的想象思维愈发形象活泼、愈发宽泛广阔,就愈发证明其大获成功。优秀作家的文学作品常常能让人们应用想象去弥补这里面的虚线。其次,就作者自身来讲,其需要有内敛之权利,这能够让其文学作品拥有弦外之音。所以,就翻译自身来讲,翻译人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需要力争规避让自身的翻译风格僵硬死板。
众所周知,在社会心理学层面,有一重要概念:光环效应。光环效应就是单个人在社会知觉之中,把知觉目标的一种印象不作任何的分析拓展到别的方面中去。比如“情人眼中出西施”这乃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光环效应。此种现象在对知觉之印象的逐步形成之中很显著地展现为单个人的主观臆断,此种单个人的主观臆断,在印象的形成之中极具宽泛化、扩展与定势之功效,就是人们常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种心理现象展现在翻译方面会致使翻译人对以后词义的关注度降低,每当首次印象形成以后,就不太关注余下的描汇性词汇的意思;或是对词语意思的大打折扣、忽视,乃至变化。在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每当原作家对作品中的人物描汇,让翻译人产生最开始的印象以后,则翻译人就很轻易将以后描汇的忽视。我们不妨看看看鲁迅名著《阿Q正传》中“阿Q又很自尊”一句话是这样翻译的:阿Q又很自尊“Ah Qalsohad a high sense of self-respect.”实际上,此时的自尊乃是阿Q自我感觉良好的意思,这就是一嘲讽的运用,相对合理的翻译应该是“had a high opinion ofhimself”,不过若阿Q给翻译者的首次印象只是“争强好胜、懦弱无能、爱捅娄子”的话,“自尊”被翻译为“self-respect”这也能让人理解了。很明显,此种翻译远离了原著,且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人们对译文作品的误读。
然后,我们由翻译文化心理学角度来探讨翻译人其偏差。翻译学的目的论指出,其实翻译就属于人类行为研究,人们的相互交往受情境的约束,可是情境又深植在文化习惯之中。所以,翻译肯定会受到译出语与译入语文化之约束,有些专家还认为,翻译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文化上的交流。人们由文化角度来探讨翻译,出现有两种倾向:第一是由译出语和译入语两种文化在历史积淀之中出现的文化中心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出角度研究两种语言在表现方法与思维方法的不同;第二是以列斐卫尔和思耐特为代表,二人注重文化回归。此种方向的研究和由原作品与翻译作品读者视角出发的翻译研究截然相反。文化当作一个社会的共同物来讲,单个人的内心层面肯定会有文化之印记,就是人对某事物、事情以及人物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也肯定会和他所处的文化有紧密关联。此点在翻译上展现为:社会状况、历史事实、文化都在影响着翻译人的取舍,翻译人的取舍不是其自身的一时兴起,而是深深受社会文化的左右。诚然,文化心理涵盖的方面非常多,限于篇幅,论文基本上由文化价值不同与文化态度不同两个层次来探究左右译文准确度之要素。
文化的价值观主要展现在哲学与道德观念,乃是做出取舍与处理冲突之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常常经过耳濡目染之作用给此文化中的所有人员来灌输好和差、对和错、正和反等标准,让其懂得该批判什么、赞扬什么。就东西方文化里关于幸福的各自价值观来讲,在我国,很多人认为趋乐避苦不是属于人之天性,且还将追求享乐当作是不道德、不高尚的。此种倾向在宋朝明朝的时候演绎到顶峰,最终形成了一点不在乎人之正常感知,仅仅注重“压抑自己”、“克制”的禁欲主义。人之幸福就是人类修身养性的附属品。因此,人们就往往深陷贪欲和理智、实际生活欢愉的诱惑和心中道德观念的碰撞之中,这肯定会形成忽视实际物质要素的构建和享受,注重压制自己与精神需求之传统。和我国比较,欧洲,特别是发展到近现代社会的欧洲,众多思想家们为了和中世纪盛行欧洲的禁欲主义想抗争,将肉体之幸福提高到实际生活之重要的内容,因此常常忽略精神对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极具享乐哲学之色彩注重实际生活幸福,更多突显人之情感和谐与对物质的满足。东西方的此种对于幸福的价值观的差异肯定会表现在翻译方面。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相互间简单的相互交换,不过不能说只要精通了这两门语言就可以做好翻译工作,由于翻译不但是涵盖语言学,也涵盖心理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从哲学角度上来讲,所有事物全是矛盾的普遍和特殊性的融合,翻译人在翻译之中要做的不但是处理好两种语言表面意义上的众多问题,并且还得认知与处理好克己之问题,这里面还包含上面所提到的众多诱发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翻译人在某个地方的偏差会影响所翻译作品的读者对作品中人物角色形象的更深的了解和整体的掌控,进而不能确保整部翻译作品的质量,也就不可能实现“准确”此翻译最基本要求。
[1]张成柱.文学翻译中的情感移植[J].中国翻译,1994,(21): 28.
[2]王元化.黑格尔[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3]马文驹.当代心理学手册[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4]廖七一.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H059
A
1673-0046(2011)07-018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