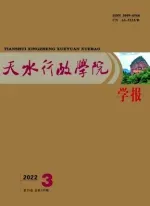评析科恩民主的心理条件论
刘军伟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评析科恩民主的心理条件论
刘军伟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民主是人类理想的社会生活模式。健康的民主生活离不开行为主体健康的心理素质。在科恩所阐发的民主的心理条件中,“对现存民主制度的现实主义态度”、“对领导人持批判态度”、“相信错误难免”、“愿意妥协”、“能容忍”和“有信心”等充满睿智的唯物辩证思想,无疑对我们今天的民主生活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主;心理条件;科恩
当代美国哲学家卡尔·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从性质、前提、手段、条件来解说民主,又按逻辑为民主辩护、辩白。他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1]。这种体制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选举制或议会制,民主本身需要前提和条件,才能成熟和有效,才是真正的民主。他说可能有教条主义的民主主义者,但不可能有民主主义的教条,或者反过来说,虽然民主就其本质而言是反教条的。民主的核心是选择,并不带有任何先验的价值标准,但这种选择确是平等的人之间解决问题、维护利益、实现社会效率与公平的最适宜方式。
一、心理条件是民主运行的最基本条件
在《论民主》一书中,科恩对民主的心理条件作了入情入理的剖析,读来发人深思。他将民主的心理条件或心理素质理解为:社会成员实行民主时必须具有的性格特点和思想习惯。它们在于各个公民的内心,但就其实用意义来说,重点还是外在的性格特点,即可以视之为气质上的、行为上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的心理条件也就是促使许多社会成员按自治所要求的方式去行动的习惯与态度。
他甚至断言,在“民主的所有条件中,心理条件是最基本的”。“民主的其他条件主要取决于此”,比如说法制条件——保护参与权,尤其是言论自由权与公开批评政府权,也同样如此,如果绝大多数成员在气质上不善于克制自己的行动,符合这种保护的需要,法制条件必然难以发展或被滥用。尽管气质方面的条件基本不会体现在法律以及相关文件或者机构之中,但是终究要以其为支撑。法院与立法机关的行为、对宪法的尊重、报纸的编排,归根到底都取决于公民的特性。“民主的机器是由其成员风格来润滑的”[2]。民主的心理条件象其他条件一样,是在不同程度上来实现的,其实现的程度愈不能令人满意时,则民主的实现也将在同样程度上令人难以满意。
二、民主的心理条件的主要方面
对于民主的心理条件,科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1.对现存的民主制度的现实态度
这种态度要求人们对现存的任何民主制度既不求全,也不失望,而要能在这二者之间找寻到一个平衡点。要彻底抛弃那种理想主义的空洞论调,尽善尽美当然更好,可谁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人类组织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完美的不具体,具体的不完美,世上没有绝对,只有相对。科恩认为,一味追求至善至美,就会排斥较为现实而合理的民主制度,或“听任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而导致民主的毁灭”。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公民一旦听任基于理想主义的不满情绪的日益积累,终将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如是,自治的激情消失,监督的责任就会放弃。“选民或群众如果不能提出现实的要求,或者向许诺可以立即创造出奇迹的人喝彩时,自由便走向民主的反面。须知,幻灭会长期构成对民主体制的威胁。”[3]这就是说,民主理想主义是民主之大障碍。科恩说得好,民主正是基于并非绝无瑕疵的人与制度之上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完善倒是件好事,因为任何瑕疵均可成为关注的对象,有瑕疵才会激发人们去寻求改善的办法。
抱有现实主义态度的人会承认:“社会问题不会有一了百了的解决方法,调整与改进人类制度将继续不断,永无尽期。”既然社会变革永不会一劳永逸,那么“如果实行民主,公民必须心甘情愿地生活在并不完善的政府之下”[4]。当然,这种现实主义不是那种满足现状、无所作为的庸人态度,而是在求全与失望两端寻得一种“中庸之道”,即“永不满意但绝不失望”,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定能满怀信心地积极参与民主生活,为民主建设而竭尽心力。
2.对领导人持批判态度
在真正的民主社会里,官与民关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相互信任和相互忠诚的关系。但成功的民主却要在“信任之中搀合一些批判精神”。因为即使领导人有高度的智慧和良好的愿望,但只要他还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凡人,那就无法避免出错,这是其一;其二,领导人作为部分民权的代行者,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又是极为复杂和繁重的,难度大,后果也大,兼之并非所有领导者个人时时处处都能排除私欲的干扰,这使他们比一般百姓更易犯错误,出错后的危害也更大。为避免犯大错,为能迅速挽回损失,领导者的决定和行为必须由公民经常加以评论乃至尖锐地批评。应当看到,科恩坚持对领导者持批判态度的观点理论根据明显地带有西方传统的自然主义人性论的痕迹。不过,性恶论的一个积极的成果是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各项监督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为此,作为普通公民就应具备为公益而勇于质疑的勇气与能力;作为“公务员”更应有接受任何批评质难的大度胸襟,把公众的批评视为做好工作的必要“监察器”。为了使这种批评产生积极的效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必须具备强烈的集体责任感、无私的精神品质以及较高的批评艺术。
3.“相信错误难免”的观念
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意识到“人人不免出错”,否则就没有必要实行民主。“在这个世界上,无需更多的经验即可认识到:即使在重大问题上以及在自己深信不疑的意见方面,人是多么容易出错。”[5]所以科恩认为,在没有听取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意见之前不应对任何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相信错误难免”被科恩视为民主国家的公民所应具备的气质中最根本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我们认为任何人或任何团体绝对正确,那么就只有把管理一切事务的权力交给他(或他们)才合乎推理。可如果我们否认了这种绝对明智,就会要求和鼓励一切有关的人都参与决策。
科恩没有详析具备这一心理素质的意义,其实,公民树立“相信错误难免”的观念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它有利于激发公民参政、议政和决政的热情。因为如上所述,既然谁也不能保证绝对明智与正确,那么,为确保能有尽量科学的决策,就需要“群策群力”,形成集体的智慧,这虽然也还难免出错,但它毕竟使错误降低到了最低的限度。第二,它为新闻自由,尤其是为新闻实行公开性原则提供了哲学依据。由于谁都可能出错,故单一的信息来源——不论是政府内的还是政府外的——都可能使公民偏听偏信。要获得客观的全面的信息就必须有多渠道的信息来源,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在辩论和验证中分辨是非。如果新闻界连对立的报道与意见都听不到,所有渠道仅提供一种看法,那么,公民参政、议政的兴趣就会大减。第三,作为个人就有可能主动而谦虚地去听取他人的意见,避免了自以为是和固执己见,同时还有助于克服家长制作风。第四,有助于克服盲目崇拜和迷信心理,培养独立思考、勇于提出不同见解的习惯和能力。第五,民主社会中的成员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尤其是领导者乃至领袖人物,就易于给以应有的理解与宽容,进而有助于缓减和避免个体与群体组织(包括政府和社会)、群众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与对立。
总之,“相信错误难免”既不是要将真理性的东西抛掉,也不是鼓励犯错误,而是对现实的人和事要有一个现实主义的和一分为二的认识态度。它对民主生活的根本意义在于,它使民主的生活成为必要与可能,为人们树立追求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4.愿意妥协
民主国家的公民须乐于以妥协办法解决他们的分歧。“民主的所有条件之中,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而有关各方若不愿妥协,即无达成妥协的可能。”[6]
在任何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要用大家都完全满意的办法来解决,那是很少有此可能的。在自治社会中,制定出冲突各方虽不完全满意但至少都能忍受的办法便成为社会成员的任务。如果问题少,由他们直接制定,如果问题多,则通过代表间接制定。权衡冲突各方的争议,从而形成政策、制定法律的过程便是妥协的过程,妥协是民主程序的核心。同时,“妥协的达成也依赖于各方的积极参与、平等协商与同意”,因此,“就其实质价值来看,妥协与人民的同意这一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是相一致的。”[7]
人类社会有许多共同的目标与理想,其中之一就是政治生活的和谐稳定。政治妥协作为化解冲突、解决矛盾的有效机制越来越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政治生活追求的价值目标。政治妥协是在当今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解决矛盾、化解分歧最经济的一种方法。作为一种理性选择,政治妥协是一种政治智慧,是妥协、让步、宽容与和解的艺术,政治的奥秘之一就是妥协。政治妥协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政治实践中不但有利于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维持在一种合理状态,增加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也有利于政治各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5.学会容忍
宽容要求我们接受他人,“甚至当我们很不赞同他们的做法时也要允许他们实践”,因而,宽容“包含着一种中间态度,此种态度处于完全接受与坚决反对之间。”[8]
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在三个层次上有意识地容忍逐渐加大的困难:第一层次的容忍是要能容忍不守成规。不守成规并非尽是消极的破坏性行为,事实上,“人类社会许多重要的进步都是大胆地违反成规的结果。很可能这些行为都曾使人惊怪或厌恶”[9]。在民主生活中,这种不守成规更多地是指想象力、独特的个性和各种各样的见解。这些品质对民主生活深度的增加会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相反,“如果公民不倾向于容忍不守成规,参与管理可能是广泛的,但必然是表面化的。如果大家想的和做的都一样,全面而有深度的参与根本是不可能的”[10]。19世纪英国思想家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曾这样阐述不守成规的巨大意义:在充满性格力量的时代与地方,也一直充满着离经叛道。而且一个社会中所见到的不守常规,是与它所有的创造能力、思维活力以及道义上的勇气成正比的。第二层次的容忍是能够容忍别人直接反对自己的信念与原则。民主社会是自由的社会,每个人都可能拥有不同的生活信念和原则,对由此而产生的分歧要能泰然处之。第三层次的容忍是能容忍他人怀有恶意的或出于愚蠢的反对,对此的忍耐不是屈服,更不是姑息养奸,而是一种基于理解、博爱和博大的胸襟而具有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高尚品质,也是一种做人的风度。
6.要有信心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曾这样写到:“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非个别地,可能超过最少数精华的质量。”[11]通过社会的思考与辩论而产生的集体的意见,毕竟比圣君贤相的个别见解要全面、明智和完善些。科恩对自信力在民主生活中的重要性作了较为深刻的告诫性的分析:“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相信他们的集体能力能管理自己。如果社会成员相互轻视,视为不足依赖,把自己这伙人视为乌合之众,这个社会就是没有志气的社会。缺乏信心尤其是在危急时期,公民就会寻求外在的权威为他们作出他们不能或不愿作出的。”这里的自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对自己的自信,二是个人对社会的信心。如果个人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值得认真地考虑,他必然不会在决策过程中起任何作用。他自然要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于个别卓越的领导者身上,这不仅意味着放弃了自己参与自治的权力,也意味着推卸了自己应为社会所履行的义务和责任。这种个性特征是专制时代的人格范型,与民主社会的公民特色是格格不入的。
三、对科恩的民主心理条件论的评价
总之,只有全体或大多数公民都相信自己均能对共同问题的解决作出某种贡献,才足以对付民主的繁重义务,才会营造出生机勃勃而富有实效的民主生活。
科恩关于民主的心理诸素质的阐发,闪烁着显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火花,如“相信错误难免”、对现实民主的现实主义态度以及要有信心等都体现了对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辩证思维:“对领导人的批判态度”以及反对对现存制度求全责备的观点表现出鲜明的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
当然,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其思想的局限性也是显见的,主要表现有二:其一,他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是“光辉”的思想,但他又借反对将经济因素视为民主的“唯一条件”而在事实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基本观点,甚至不屑一顾地将这一思想斥之为“经济主义”。这势必抹杀不同社会形态下民主的质的区别,流于抽象民主论,从而无以把握和揭示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的阶级实质,把民主问题仅局限于枝节。
其二,科恩虽然承认民主需要多种条件(这里不乏系统论的观点),可他却独断地认为,唯有心理条件才是最重要的,“民主的其他条件主要取决于此”。其唯心主义和超阶级论昭然若揭。注重民主的心理素质的研究本是件极具价值意义的事,但无限夸大心理条件的作用,就使他在民主心理条件方面的许多颇为深邃的思想被其心理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所窒息。当然,倘若我们能剔除这些唯心主义的抽象民主论的糟粕,而仅就民主心理素质的诸要素内容来看,对我们的民主理论研究和实际的民主生活还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2][4][5][8][9]卡尔·科恩.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民主的再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龙太江.论政治妥协——以价值为中心的分析[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
[7]托马斯·斯坎伦.宽容之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0]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Abstrat:Democracy is human’s ideal life stile.Healthy democratic life can’t separent from subject’s healthy psychologicalquality.In th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ofdemocracy that introduced by Cohen,“the realism attitude to the existing democratic system”、“the criticalattitude to the leaders”、“believing error is inevitable”、“willing to compromise”、“being able to tolerate”、“being confident”are fullofwise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s thought,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oday’sdemocratic life’s running.
On Cohen’s View on Democratic PsychologicalCondition
LIU Jun-wei
(SchoolofPublic Affair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democracy;psychological conditions;Cohen
D093.712
A
1009-6566(2011)01-0041-04
2010-09-27
刘军伟(1985—),男,陕西武功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