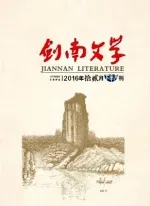论《后汉书·列女传》——儒家正统女性观确立以来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规训
范存芳
中国传媒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024
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撰写的《后汉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引女性群体入类传的正史作品,其名称、体例和格式虽然是沿袭汉代刘向的《列女传》,但能在一部极具严肃意义的纪传体史书中为女性开辟关照视域和活动场域,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其创制之功仍然是极大的,后世的正史作品大体也承袭了范晔的书写传统,二十四史中就有十三部作品收有《列女传》1。自兹以往,女性开始集体地出现在史册的特定场所,成为我国古代正统社会里男性书写的一道独特风景。那么,在史的视野笼罩之下,就《后汉书·列女传》而言,其展现的又是一种怎样的女性观及女性生存结构呢?本文正是试图从汉代以来社会政治、思想形态的发展和变迁入手,通过对刘向《列女传》和《后汉书·列女传》文本的对比分析来考察这个问题。
一、两部《列女传》的成书背景及汉代儒家正统女性观的确立
女性群体的被观照,本质上即昭示了其姿态上的卑弱性以及进入父权制社会以后,男性在话语权上对于女性的掌控。范晔以性别作为其书写的分类标准,本身也显示了一种思想形态上的高姿态和间离性。《后汉书》列传八十,《列女传》居第七十四,与《宦官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等并置于列传的末尾,且仅居于“华—夷”分野观念背景下的《东夷列传》之前,可见,女性群体的入史,自其发端便是以一种被边缘化和被卑弱化的历史命运开始的。东汉的班昭在其女教作品《七诫》中亦阐明女性当以“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卧之床下,弄之瓦砖”的斋告礼仪表明,女性生理上与生俱来的柔弱特性被仪式化地加以体认,并引申到两性关系和社会制度层面,形成了从身体到心理再到社会属性的卑弱化过程。班昭进一步将这种“卑弱”明确为“主下人”的从属地位,并细则化、标准化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可见中国古代礼教和女教机制对于女性的规训过程。同样,历代《列女传》的写作也是出于此种规训意图。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
《后汉书·列女传》传序:
“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量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兴以後,综成其事,述为列女篇。如马、邓、梁后别见前纪,梁嫕、李姬各附家传,若斯之类,并不兼书。馀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两部《列女传》的作者均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其政治功利取向和现实价值指向,但无论是刘向所说的“兴国显家”、佐“王教”、“戒天子”,还是范晔所谓的“助国君之政”、“隆家人之道”、“弘清淳之风”、“量明白之节”,其首要之道还是对于女性自身进行教导和规训,使之在个人基本素质上达到礼教的要求,有别于“赵、卫之属”而无“逾礼制”。这是根本前提,也是两部《列女传》中“列女”入传的基本标准。
刘向及范晔《列女传》的出现和书写范式,正是汉代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形态以来,以礼教为中心的儒家女性观的映射。西汉武帝时,经学家董仲舒依阴阳五行之说而区分性别属性,确立“天—阳—男—尊、地—阴—女—卑(夫—阳、妇—阴)”的哲学思想体系,以此为基础,又建构起一套完整的以夫妇、父子、君臣之尊卑关系为网络的国家权力机制。“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班昭将女性的卑弱确定为“主下人”的从属关系和日常实践,董仲舒则从根源上为这种伦理实践寻找名位和依据。“阴”“无所独行”的卑弱和“阳”与生俱来的阳刚决定了男女之间的伦常秩序是依附和被依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与“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的仪式相对应,这也是一种由自然生理而社会伦理的象征性关系的架构。在这种象征性关系笼罩下,女性的屈服就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天经地义的,男性话语因而呈现出本体性的侵略态势。由官方组织、刘向负责整理和编撰的《白虎通义》是一部具有法典意义的儒家经典著作,它统一了两汉以来诸种儒家观点,同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通过进一步规范“男尊女卑”的儒家伦理秩序而确立起了父权制社会的绝对权威。“男女者,何谓也?男者,任也,任功业也。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在家从父母,即嫁从夫,夫没从子也”;“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夫虽有恶,不得去也。故礼郊特牲日:‘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因此,在以阴阳五行为象征秩序的父权制社会里,妇女是被排除在外的,她们被赶进了家庭,躲进了男性的背后,在社会主流之外挥散着她们“阴”的本质。不唯如此,宗法制基础上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中,“家”无疑是“国”的一个缩影,是象征性社会秩序的一个缩影,因而“家”的父权性同样具有基础性的决定意义,夫妇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开始。《诗大序》称《关雎》为“后妃之德”,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可见“经夫妇” 是“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前提。以毛说为是,则《诗三百》以《关雎》开篇,正有张本溯源的用意。董仲舒和《白虎通义》在建构国家权力秩序的理论实践中,将性别的尊卑等次和夫妇的伦理关系置于其立论之本,同样也是这种用意。
由此,我们知道,女性既是排除于象征性社会秩序之外的,同时又是内在于象征性社会秩序之中的一种游离的所在。儒家父权制社会的建立以规范男女伦常为基础,将女性置于其秩序的最根基,但又永远是沉默的,这种沉默是因“阴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的天然依附性而带来的失语,是父权制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对于母权的去势,同时也是父权不断承续和蔓延自身的方式。如果对比刘向《列女传》和《后汉书·列女传》,我们不难发现,自两汉儒家正统女性观确立以来,男性书写对于女性的想象和规训策略。
二、《后汉书·列女传》的书写变异及由此展现的观念形态
刘向《列女传》以行为道德为标准,将上古以来至西汉的女性分为七种类别,即“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其中前六种类别是正面意义上的,后一种类别是负面意义上的。《后汉书·列女传》没有明确的分类,然其选择女性入传的标准大体亦是以刘向《列女传》为范本的,且其传序言“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可见也是以某一种道德品行为准则的。详加区分,就能见出二者在传主群类选择上的偏废。
1、母亲类形象群体的消退
刘向《列女传》中单列“母仪”群类,而且将其置于七大群类之首,不唯如此,在其他六类女性群体中,母亲形象所占的比列也相当之大。“母仪”者,顾名思义,乃天下母性之仪表,仪则天下之典范。《母仪传》中的17位女性,既有帝王将相之母,如姜螈、简狄、“周室三母”等,也有平民庶士之母,如孟轲母、芒慈母等,但无论是哪一种身份地位的女性,其共同特点都是“广于德教”。她们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宽广的胸襟气度,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善于相夫教子,“胎养子孙,以渐教化”,如契母简狄的“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启母涂山氏的“明教训而致其化”;孟母三迁的“善以渐化”、“处子择艺,使从大伦”;魏芒慈母的“慈惠仁义,扶养假子”……可以说,正是此类自身道德高尚同时又懂得“广于德教” 的母亲群体培养了历代明君贤相,圣人君子,成就他们开疆扩土、治国平天下的崇伟功德。在这里,女性因为性别上的本质和优势而得以体认其价值,也由此获得了一种崇高的光环,甚至表现出一种“阳”所不具备的“阴”的优越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阴”对于“阳”的凌驾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常常是父权的延续和接管者)。 刘向对于母亲类形象群体的书写,尽管依旧是将其置于作为“父权”结构之代表的帝王将相、圣人君子的背后,将她们的价值实现依附在这些人价值实现的基础之上,但却客观上肯定了女性的独特价值和独立人格,也提高了其地位(不仅仅是从“孝”的立场而言的)。
与之相形,《后汉书·列女传》中,“母仪”类女性形象群体却消退了,而“贤明”类女性形象群体和“节义”类女性形象群体得以突出。《后汉书·列女传》共列叙了十七位东汉时期的特出女性(如果加上附传中的曹丰生和马芝,则为十九人),涉及母亲形象的仅一人(汉中程文矩妻,字穆姜),且完全可以将其划归“贤明”类女性形象群中,然而可入于“贤明”、“节义”类的女性数量却高达十余位,几乎占据全部入传女性的三分之二。同样,在《晋书·列女传》三十三位入传女性中,“母仪”类也仅一人,“贤明”和“贞顺”类却高达十八人。“母仪” 指涉的对象主要是母亲群类,而“贤明”、“节义”“贞顺”指涉的对象却主要是妻子群类。“母亲”从书写的顶端消退,取而代之的“妻子”再不具备那种凌驾于父权之上的光环和优越性,只能是从属于“阳”的“无所独行”的附属者,于是,以三纲五常为基本伦理规范的儒家统治秩序又复归其父权的绝对权威性和操控性。
2、“节义”类形象群体的突出和变异
《后汉书·列女传》的传主类型中,最具有人格光彩和悲剧意味的当属“节义”和“才辨”两类。前者承袭了刘向的传统,后者斯为新变。“节义”类女性群体在《后汉书·列女传》中所占的比列相当之大,十七位女性里有七位可划归其中,她们分别是:周郁妻,庞母、许升妻、孝女曹娥、皇甫规妻、盛道妻、孝女叔先雄。刘向《节义传》中的女性多是以深明大义、为公义舍私利乃至勇于“杀身成仁”的形象出现的。如《楚成郑督》、《楚昭越姬》、《盖将之妻》中,三位女性为了家国大义、君臣之节而以死劝谏其夫君;《鲁孝义保》、《鲁义姑姊》、《梁节姑姊》中,三位女性在生命危难之时“明不私己”、大义灭亲,毅然舍弃自己的亲骨肉以保全别人之子;《邰阳友娣》、《京师节女》里,两位性则在孝与义不能两全的困境下凌然赴死,舍命求全……总之,《节义传》中的女性都具有全义守节的侠义精神。当义和节遭受侵犯,或者与孝道、仁道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女性则表现出至刚至烈的舍命精神。相比之下,《后汉书·列女传》中的“节义”型女性群体却发生了很大变异,七位节义女性中,只有周郁妻(因妇道和孝道的冲突而自杀)和皇甫规妻(因誓死捍卫家国大义和人格尊严而被诛)是刘向《节义传》中所出现过的类型,其他五位女性的节义之举则全体现于“殉父”、“殉夫”的行为举措之上——或者手刃父亲、夫君仇人(庞母、许升妻),或者追随父亲沉江而死(孝女曹娥、孝女叔先雄),或者代夫君受刑狱之灾(盛道妻)。
可以看出,刘向《节义传》中多节义之母,她们的义举在于深明大义,舍己子以保他人之子,而《后汉书·列女传》中多节义之女,他们的义举在于至孝至贞,舍性命以守护父亲、夫君的尊严。死亡在这些节义女子的身上不仅体现着人格上的至刚至烈和行为上的悲壮之美,更体现着父权制社会中女儿对于父亲/妻子对于丈夫的单向度奉献和无条件牺牲。“女儿们,作为封建社会和儒教体系永远的异乡人和流浪者,没有资格进入契约仪式,没有资格得到父亲的收养。她们属于内宅,也必然嫁入别人的家庭。她们受制于作为父权延伸物的母权;她们被要求具备绝对的孝行和对家庭的服从;即使出嫁后,由于姓氏也还依然对娘家负有义务……”。“绝对的孝行和对家庭的服从”最直接而彻底的表现形式便是死亡。表面上,死亡以其崇高性和悲剧性突出了“孝行”和“义举”,实际上是加强了“孝行”和“义举”背后所体现的父权、夫权的绝对合理性和无可动摇性,只是《节义传》中的节义之母体现的更为隐蔽,而《后汉书·列女传》中的节义之女表现的更为明显罢了。
3、才辩型女性群体的内部冲突及班昭《女诫》所展示的女性自我规训
承袭刘向《列女传》中“辩通”类女性群体的写作传统,《后汉书·列女传》也收录了三位这种类别的女性,同时附传中的曹丰生和马芝也属于此类别。区别的是:《辩通传》中的女性以能“辩”著称,以“微喻”解难,伶牙俐齿而又智识过人,常常是逞着口舌之“辩”得以进退从容,替自己及他人(常常是“父”、“君”——国君、夫君和儿子)消灾解惑。《后汉书·列女传》中的才辩型女性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不唯有“辩”才,更在于有文才,班昭和蔡文姬均因为文学上的才华而为当世所推重,《后汉书·列女传》亦不惜篇幅和笔墨收录她们的传世作品。这自然是汉代立经学博士以降各儒学世家的家学渊源熏陶出来的女子——马伦和马芝的父亲马融、班昭的父亲班彪和哥哥班固、蔡文姬父亲蔡邕都是汉代大儒,虽然都出身高贵家教良好,然而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个性气质却迥然相异。
班昭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她的存在体现着封建制父权制社会对于女性合乎理想的规训效果。“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这是班昭在其女教著作《女诫》中提出的女性道德规范。作为“三纲五常”的儒家礼教传统浸熏出来的女性,她自己即深合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是儒教体系和父权制社会秩序的建构者们成功训导出来的优秀女性代表。作为代表——具有榜样力量和训诫资格——她因而得以从家庭深处走出来,进入象征性的父权制社会秩序中,和男性一起缔结“契约仪式”,训导包括她自身在内的封建社会的女性们。班昭与父权社会所达成的共谋,正显示了传统女性在父权和夫权凌越下的无条件顺从和自我抹杀,同时也可谓是一种自我保全策略。“最明显的表现,首先自然就是对权威的顺从态度,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迟疑。所有别的出路都被堵死,除了跟随父亲的脚步以及更古老的先祖的足迹”;“父权的巩固使得那些具有文化素养的上层妇女思考生活的新策略,她用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女儿辈如何在既定的生活空间中适应生存,在不利的环境中以谦德忍道在丈夫中站稳脚跟。”显然,班昭不仅在夫家站稳了脚跟,也在父权制封建社会秩序中站稳了脚跟——不仅得以接续并完成父兄未竟的修史事业,且被汉和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
与班昭形成对比冲突的是另两名才辩型女子——马伦和蔡文姬。马伦富于辩才,学识渊博,机智犀利,面对丈夫的诘难表现得不卑不亢,从容应对且气势凌人,与班昭所训导的“卑弱第一”格格不入。班昭强调“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显然,马伦之夫既无能力“御妇”,马伦也不贤于“事夫”,二人是断不合于班昭所谓的“夫妇之道”的,然《后汉书·列女传》却谓“隗既宠贵当时,伦亦有名于世”,可见马伦之见重于当世,乃在于其才辩而并不涉及妇道。如果说马伦对夫权构成的挑战是言语与威仪层面的,那么蔡文姬则是伦理层面的。“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蔡文姬有过两次婚姻,又被胡人虏获为妻而生下二子,于伦常不合,但因“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依旧为当时和后世所推重。
班昭和马伦、蔡文姬两类才辩型女性的内部冲突,隐现的其实是汉代以来儒家官方正统思想与民间遗风习俗之间的矛盾,以及范晔自己对于女性审美观照的兼容开放性。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并在孝武帝的支持下开始在大一统帝国内实行。自此以往,儒家思想渐成汉代官方正统思想,作为封建国家进行思想钳制和秩序建构的工具,然而思想的转变、观念的普及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向来具有一定的延时性与滞后性,加之已经深入在民间、社会生活中,并且伴随着应用性的遗风习俗的普泛性和顽固性,它们时刻冲突和阻碍着新思想形态的流布与接受。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即使身处这种附属性,被如此专制的儒教道德所压制,双边血亲关系的遗留和简单泛化交换的中介形式(要求迎娶母舅的女儿)还是继续授予了女人一定的自由,使其得以继续逃脱父权的完全压制。”所以,在以封建礼教为基础的儒家女性观甫一成形的两汉社会,女性的实际生存空间也还是比制度形态所规划的要空阔和富余。刘向谓其作《列女传》的初衷“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可见当时皇宫风气尚且如此,何况民间乡野呢?刘向作为“独尊儒术”不遗余力的践履者,自然无法容忍此种风气,“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将宗法制国家的兴亡与女性的“贤贞”和“孽嬖”联系起来,而天子自身的作为和责任被隐去,正是刘向作为一个儒者在维护汉朝统治基础时对于女性的驾驭策略——试图将女性从儒家象征性社会秩序中驱逐出去,将她们安放在家庭和闺房之中,以此来稳定两性关系的地位,并确保封建血缘宗法制统治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相比刘向,处于刘宋时代的范晔则显现出大得多的宽容和气度。如上文我们分析的那样,班昭与马伦、蔡文姬两类气质不同、道德迥异的女性均被收归《后汉书·列女传》,足以见出他在女性审美观照上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这自然是魏晋以来“越名教以任自然”的社会风气使然——正统的儒家思想形态受到上层文人士大夫的挑战,老庄式的追求个性自由的文化人格得到广泛推崇,流为一时的任诞习气——范晔自身正是受此种习气熏养而成长起来的,他“博学多通,善谈名理”,也继承了魏晋名士放达的行事方式和任情任性的作风:为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守灵时以挽歌助酒;嫡母去世时拖延奔丧,并携妻小随行;始终不肯为宋文帝弹琴等行为(见《宋书·范晔传》)都显示出范晔个性的傲岸不羁和风流狂放。作为儒家思想结构基础的儒家礼教受到质疑,自然也会波及女性观层面,以及对于女性的审美观照层面,因而马伦对于丈夫的抵触和反驳不再完全被认为是有违夫妇之道的,蔡文姬一嫁再嫁的伦理瑕疵也不遮盖其文学才华上的大光异彩。这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们以一种难得一见的胸襟和气度包容了女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女性依然只是被观赏的,依然没有从家庭走入封建父权制社会的秩序结构中。马伦也好,蔡文姬也好,都是封建父权秩序内部的书写,都是文人士大夫的附庸风雅。“借助儒教对封建社会的保护,似乎有两个障碍建立起来了:一个是卧室的门帘,另一个是一般意义上书写。一个女人无法同时跨越这两个障碍:要门她走出卧室门帘,母凭子贵;要么可以进入象征性社会秩序(作为诗人、舞者和歌者),但只能伫立在卧室门帘之后。”
总之,作为封建儒家父权制社会统治机构中的一员,范晔对于女性尽管持开放的审美观照,但永远也不可能没有限度,不可能放弃儒家正统礼教对于女性的规训。这个时代女性们虽然获得了更大的生存和活动空间,也以更加多姿多彩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眼界中,但父权和夫权是她们永远也逃不开的宿命,正如闺闱是她们永远的归宿。
【注释】
1.这十三部作品分别是《后汉书》、《晋书》、《魏书》、《北史》、《隋书》、新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
[1] (刘宋)范晔撰.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2] (汉)班固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汉)董仲舒撰,凌曙注.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汉)班固撰,陈立、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5]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中国妇女[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6] 杜芳琴.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本土化探索[J].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