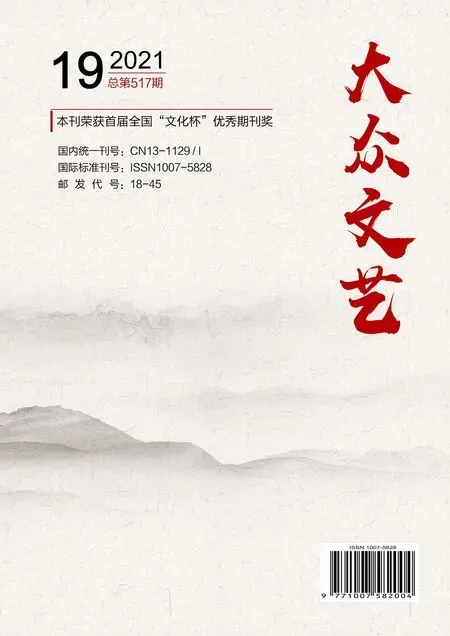隐逸文化中“自由”要素的消极性
武根柱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目前对隐逸文化的研究性文献内容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对隐逸文化本体的论述,二是隐逸文化的历史个案研究。这两个层面中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对“自由”要素有侧重不同的部分论述。
在隐逸文化本体的论述文献中,一方面集中在它的定义、成因、类型、要素、流变等意义论证范畴,另一方面是细分的概念论证如时代特征、区域特征、历史研究考证、中西比较、要素特征、道德融合等。其中对“自由”要素都只是概念提及和精神世界的积极意义表达,对这一要素对现实生存的消极性探究专论尚属空白。
在对隐逸文化的个案研究中,主要研究其在社会领域的文化显像,主要范围有文艺作品,如诗、词曲、电影、电视、还有历史人物、社会经济等古今文化中隐逸文化特征的体现。
在对各类著作及论文中,由于没有对“自由”要素专题论证,依据片段提及,综合相关信息,已有文论中对“自由”的阐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对“自由”特征的阐释,即心灵自由、行为自由、人格自由,把个体从各种世俗束缚中解脱出来;二是求“自由”的原因“道所赋予”“困境解脱之路”“问道”;三是对“自由”途径引导即“自我实现”。四是对“自由”结果描述即“表面贫困或死亡,但本质是归道”。
在对“自由”阐述的方式上有本体解释、文本阐释、个案注解,即就“自由”的理论解释自由、用片段解释全面、用只有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才能产生或适用的理论来解释广义的不分条件的自由。在对隐逸文化中“自由”要素的引述中,没有在客观的、辩证的、全面的、科学的立场中分析论证,缺少历史观和实事求是态度,没能揭示隐逸文化“自由”要素的现实本性。
第一部分:“自由”隐逸追求倾向源于弱势士人的自我保全思想。
一、用“道所赋予”解释隐逸自由是一种拜神教式的学说,是精英士人向大众“神道设教”的途径
隐逸之士是先秦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知识群体,主要集中在儒道两家。隐逸思想是先秦社会思想的一种取向,历经西汉酝酿期、魏晋南北朝逐渐成熟期、中唐以后的衰变三大发展阶段。士人之隐是相对于入仕为官的一种社会行为,儒家的“隐”是追求“待时而出”,是追求入仕过程中的挫折历程,而道家老庄树立的“自由逍遥”则是学派确立的一种核心学说。
集中了隐逸自由思想精粹的儒道两家撷取了先秦时期人类智慧之果,由于先秦时期的社会思想可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在神道设教的大纛下发展变化[1],“道”的传播,正是依靠“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孔子、老子、庄子等圣人,把“道”推到了“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2]的“神道”境界,使“道”为天下民众慑服。《庄子》把逍遥的人生态度推到了极致,王凯在《逍遥游——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中论述:从哲学和美学上讲,庄子的逍遥之游排除了目的性和功利性追求,是超越时空、超越现实的自由精神状态。尤其是“游”与“逍遥”相联结,使“逍遥游”更加突出了作为自由的主题,也更带有“游戏”的意味。[3]而且“逍遥游”的过程就是“体道”“闻道”“与天为徒”的过程。[4]无论是孔子之“道”还是老庄之“道”,追求的自由都是以“道”为依托的学说体系,而“道”之神玄莫测只能使隐逸文化追求的“自由”成为空中楼阁,这种“自由”也是一种虚无的冥想,对于人生现实和社会文明发展只能是一种消解。王凯博士在他《逍遥游——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中对庄子学说的“自由”境界论述为:“逍遥游”是体道之游,道是无,体道的心灵也应是无,道是静寂的,体道的心灵也应该是宁静的。从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通过虚无化的否定达到心灵的净化,构成“逍遥游”的逻辑开端和内在动力。人在现实的人世活动中,离不开各种欲望的驱使,也无法摆脱各种名利等外物的困扰,此乃是“有累”,“有待”,故人是不自由的。只有“无累”、“无待”,也能做到自然无力,从而进入“逍遥游”的自由境界,成为真正的逍遥者。[5]“隐逸自由”是精英思想家们的一种门派学说,这种“自由”来源虚无的“道”,它的本身也是一种虚无。
二、士人隐逸求自由生存是春秋战国先秦时期的一种社会思潮,是当时社会结构由氏族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迈进的转型期,士人生存危机情况下一种消极的必然选择
晁福林教授在他的《先秦社会思想研究》中指出:先秦社会历史的巨大转型,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一是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一是由氏族时代向编户齐民时代的过渡。[6]而春秋战国时代就是“由氏族时代向编户齐民时代的过渡”的社会巨大转型期。这个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尤其是庄子生存的战国时代更是一个昏暗的时代:以兼地夺城为务,以攻伐为贤的“新道德”,建立的是强权的“新秩序”,“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7]”战国时代生命沦为统治者巧取豪夺的工具,道德沦为冠冕堂皇的形式,人们的生存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人的本性遭到了可怕的扭曲。[8]士人特有的特征使他们必须归属于某一特定的势力团体,而无休止的争伐掠杀使士人也时无定主,生死无常。孔子的“无道则隐”的思想更使生死一线间的士人产生用隐逸来求自由之身的行为。庄子更是继承发扬老子“道无”的精神,在时代乱世中总结升华“自由”的巅峰诉求“逍遥游”,以隐逸出世来追求“真正的自由”,而这种对后世士人影响至深的用隐逸求的“自由”的生存方式,只能是一种“审美生存”,只能在精神世界里实现,在现实生存环境中只是一种消极的虚无。庄子把人与世界间的复杂关系简单约化为理想的审美关系,并且用隐逸自由“逍遥游”等审美的方式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知识理论问题,这种方式是对现实世界的远离,无法实现现世的生存自由。
前苏联美学家列•斯托洛维奇解释了审美价值与其它价值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无论物质——实践价值和认识价值,还是道德价值和社会政治价值,其存在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互相影响的。根据我们的意见,审美价值处在所有价值相互渗透的中心。第一,这种状态表明,审美因素能够参与到一切形式的人类活动中,因此审美价值能够处在其他形式的价值中。第二,这表明审美价值本身的综合本质,这种本质包括各种多样的社会——人的关系,具有各种意义的综合。”[9]庄子总结强调的用隐逸来实现的自由自在“逍遥游”的审美生存,但那种审美生存的本质,却与他们追求的“自由生存”的初衷相反。审美生存只能是士人们与复杂无常世道无法抗争的一种无奈的消极的应对方式,是士人们在那个时代中求得自我麻醉的必然选择。
三、儒道精英士人对隐逸“自由”的价值取向
隐士主要集中在儒家、道家,其它学派如墨家、法家、纵横家、农家中也偶有出现。儒道两家对隐逸自由追求的审美价值取向是我们认识隐逸文化中“自由”思想本质的载体。
1.儒家隐逸之士虽然把道德品格看得比功名利禄更为重要,但自始至终却斩不断从政入仕的情结
《论语•微子》篇所载子路的言论,能明确表达儒家对隐士的基本态度。他在文中说道:“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儒家思想将入仕与隐逸的差异看作是“大伦”(即本质的伦理原则)和小善的不同,并且坚持不能用小善影响大伦。儒家强调提出的“大伦”是长幼之节,君臣之义,而用隐居的方式自洁其身则是与之矛盾的。孔子对隐士的行为虽然理解,更有感慨说“道不行乘桴于海”[10],但自始至终他也没有走上隐逸之路,且与鲁君与权卿季氏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因而孟子说他是“三日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更是充分肯定从政入仕对于士人的重要,他称“士人失位也,犹如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11]。孟子认为士人入仕为官才是最有本分的事,就象农夫种地一样。子路更是直言隐士们不顾“长幼之节”,“君臣之义”,“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称隐士们的作法是“不仕无义”。但孔子又言道:“天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儒家的隐逸观点充分显示是一种“天无道”时的被动行为,隐逸的自由只是一种“待时入仕”中的一段调养,并非主动脱离人世的“真隐”。
2.道家精英隐者著书立说参与社会和学说中审美生存的悖反
道家隐逸追求人格的独立自由。庄子本人把魏国的相位视为“腐鼠”(《庄子•秋水》),把凡人争相追逐官位的行为视为“舐痔”(《庄子•列御寇》),庄子和其后学推崇的人物大多和庄子一样清高,在《让王》篇中列子是个典型例子。列子在饥饿的困境中拒不接受国君的赠粟,唯一原因是国君知晓自己的途径是靠客言,因为“人之言”而赠粟,表示自己的独立人格并不为国君所知,列子感到自己的独立人格受损,所以拒绝接受赠粟。
道家隐逸内容在于实现精神自由。《逍遥游》中寄托着精神自由形象的许由、肩吾、连叔、接舆等都是寓言中人的描述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 而年谷熟”(《逍遥游》)。他所设定的人完全超越了现实社会生活之上,只求在无边无际的精神领域行逍遥游,这就是他宣扬的理想的隐士。
道家隐逸是一种自由的审美生存,诉求一种与世隔绝的真自由。但精英道家隐者一方面极度宣扬审美生存,另一方面著书立说参与社会思想干与,与百家争鸣。《老子》、《庄子》、《列子》这些著作本身就说明来自老子、庄子、列御寇等道家隐者的大家,并非真正的隐匿,而是借总结动荡社会中弱势士人的生存方向独树学说宗派,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参与社会,拯救无数遭遇险境回天无力的无助士人的灵魂,让这些士人在饱受苦难身家难保的危险境遇中能有不断的来自内心的精神麻醉。他们的这种言行本质的悖反向我们揭示了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呢?正是这种言行悖反向我们展示道家隐逸自由思想是一种生存的无奈,一种对“无道”社会的无力抗争,是对弱境士人的安慰剂,是一种神教式的庇护,是乱世中士人精神的避难所。
第二部分:以隐逸求“自由”不具有普遍社会意义。
一、用隐逸来追求自由只能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是对自由生存的悖反
自先秦隐逸风气开始之后,各朝封建士人在历史激流中不断延伸着隐逸文化的脉线,不断演绎着这个特殊阶层的沉浮史诗,但数目庞大的各代隐者,却都经历着不同的悲凉境况。他们用非实践性的、强调个体行为的自由审美生存方式来处理人的现实社会生存,让个体的士人从社会属性的人根本无法摆脱的社会实践中脱离出来。这从本源上决定了脱离尘世的“隐逸自由”士人必定在社会人的生存世界中无法生存,且在“士人”的原本身份影响下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冲突与干扰,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
包兆会博士对庄子生存论中追求隐逸自由做了很好的论述:“过于强调意识的作用,以及流露出回到前主体的无意识状态的设想,虽回避了认识论中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模式,但他所提倡的‘混沌’和‘冥合为一’不是主体占有客体的过程(肉身和知性参与其中)后而最终形成超越主客关系的一种后主体的主客融合,这种主客融合更多的是一种空疏的形而上学玄想,因为它把生活世界关在形而上学的门外,以不靠外术、反己体认、扫相证体、自明自了的内心直觉来把握本体。”[12]隐逸自由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玄想”,士人在改朝换代或复杂社会实践中采取的隐逸行为根本无法得到自由生存,而是对自由生存的悖反。
在《让王》篇中所塑造的最早的著名隐士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他们为了“义”而隐居首阳山,以“隐”来维护自己的身心自由,但最后却饿死于山中。他们在处理矛盾时采取行为时的主导精神“天道”,司马迁就曾发出“是邪非邪”[13]的强烈质疑。这两位以天下为己任,有博大胸怀的圣贤之士,用极端的归隐式生存求的的“自由”就是生命的消失,肉体物质已消逝,由头脑产生的精神享受更是烟消云散、无法存在。魏晋时期著名隐士嵇康的死同样是对于隐逸自由行为的极端注解,“嵇康之死,不仅属于其个人更属于那个时代,是时代的牺牲品。”[14]唐代诗人孟浩然隐逸生活同样是一种无法实现的自由追求:佟培基在《孟浩然诗集笺注》中说“纵观他的诗篇,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生都加在出仕与退隐的矛盾痛苦之中。”[15]
隐逸之士人无法从隐逸中获得自由,有的只是生存的困苦和无序的烦扰,更有甚者是成为封建义理的牺牲。
二、士人隐退只适于相对特殊时期的特殊个体
中国隐逸文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成因特殊。后来众多士人在与当时并不相同或不相似的环境中采用了隐逸,用“隐”来追求一时的自由,结果却是对生存自由的否定。
士作为一个知识阶层,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思想精英,具有相对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智慧,他们承载着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作用,历代统治者都深知这一阶层的价值。
战国时期政治制度正处于由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向封建官僚政治转变的过程,列国争雄,一方面争伐使部分士人无依无靠走向无奈之隐;另一方面也为士人的进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们可以在各诸侯国间流动,完全没有必要非在一处等待获取功名利禄的机会,天下之大,任士周游,如果没有生死之诀,根本没有必要用隐逸方式来获得只存在于精神层面的某种自由。至于秦之后历代王朝,封建官僚的选拔及流动走上制度化和系统化,士人们更可利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在人世间自由生存。被后世隐者奉为至尊的“逍遥游”完全自由之境,那只存在于精神幻想层面,是虚拟的世界。“老子做史官,庄子为漆园吏,没有身家性命之虞,也没有多少无聊的应酬,在这种闲散的职位上同样可以追求其适性理想。”[16]老子庄子提出个体无限自由理想的大家,也是在“史官”与“漆园吏”的现世环境中提出令后学不精者陷入“隐逸自由”消极困顿境界的道家学说的。隐退世界之后追求个体自由只是道家的一种虚幻冥想,如果“没有身家性命之虞”士人们完全都可以象老子、庄子一样为社会发展尽一份力,且可在工作之余实现精神“逍遥游”,著书立说,传世立传。
第三部分:隐逸文化中的“自由”是士人客观存在的自我消解。
一、隐逸文化中的“自由”是对士人知识阶层的本质取缔
士阶层既不同于官僚又区别于庶人,他们拥有的知识和才华、文才和武略是士子们唯一的资本和凭藉。士人对知识才华的掌握是文明社会生存能力的一种获得方式,也只有凭借文才武略为社会服务,参与社会实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士”。
隐逸文化中的“自由”是面对与世隔绝的孤立个体,只重视个体自由,离开社会群体抽象地谈论人的自由,不把人放置于社会现实环境中。马克思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7],这句话充分显示个体自由的最终获得必须依靠集体的依托。隐逸之后的个体的“士”,不仅无法实现自由,而且放弃了自我资本的社会服务,在本质上他已不是作为“士”来存在了。隐士如果不入世,“士”的身份随之丧失,以“隐士”自居,是徒有虚名。
二、隐逸文化中的“自由”是一种审美诉求,无限泛化的“自由”,已与“隐逸”无关
儒家隐者的“待时”观点认为,暂时的隐退是为了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而非为了获取极端个人的自由,这类隐逸行为客观来说是一种解决矛盾冲突时的“退让”,是矛盾一方克制另一方的一种解决方式。由于“退让”的表面现象类似于“隐逸”,因此人们把“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儒家“退让”称为隐。在这个观点上,肖玉峰已有定论:“在中国隐逸史上,受官本位文化及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儒家隐士要远远多于道家隐士,但道家隐士却又往往被视为隐士之正宗而备受推崇,因而社会影响更大。”[18]“不正宗”的儒家隐士“远远多于”正宗的道家隐士,正说明“退让”比“隐逸”更能让人获取更多自由生存的空间。儒家参透了道家隐逸自由只能在精神世界里实现,他们在行为上极力“求仕”,而“无道则隐”的暂时退让,工作之余则任意在精神领域放松自由。《南史•齐宗师传》记载道衡阳王萧钧对孔珪说:“身处朱门而情感江海,形入紫闼而意在青云。”他认为“亦官亦隐才是人生的最佳选择。谢眺、王维、白居易等人都曾采用过这种方法,这样做虽然有留恋功名,贪图禄位之嫌,但他们不愿介入险恶的政治,不愿与黑暗官场沆瀣一气,不能不说是独立人格的表现,更何况有些人在任职期间还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19]
岳国文在对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的研究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正是庄子把隐士这种特立独行的极端处世态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对它做了整合提炼,成为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能享用,都能受益的普遍的生存方式,把这种与世隔绝的、矛盾的人生观,转化成于人的现实存在密切联系的,可以操作,可以利用的方式,扩大了隐的范围(由知识分子到所有人),矫正了隐的方式(由身隐到心隐)。”[20]在文中指出的是庄子为了使纯精神的审美生存理想进入普通人的认识层面,把隐士的身隐转移到心隐,这样就取消了隐士的实体存在;把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称得上的“隐”扩大到了“所有的人”,也就取消了“隐”的概念。所有的人都“隐”,那隐是对于谁存在呢?平民百姓不参与仕事,何来“隐退”?泛化了的“隐”已经走出了士人生存的空间。
结语
隐逸文化中的“自由”产生于先秦广大士人危机生存环境之中,是先秦时代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经精英思想家总结、代言并流传渗透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消极文化倾向。它在客观上对社会集体存在产生抵触,是一种个体对社会实践的逃避,它追求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存在的虚幻自由。不但对个人存在没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社会文明发展也起着消极的消解作用。对“自由”要素消极性的全面理解,对客观认识隐逸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1]晁福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7).
[2]《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
[3]王凯.逍遥游: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7-28).
[4] 王凯.逍遥游: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8).
[5] 王凯.逍遥游: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44).
[6] 晁福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
[7]时晓丽.庄子审美生存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7).
[8] 时晓丽.庄子审美生存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8).
[9](苏)列•斯托洛维奇著,凌继晓译,审美价值的本质[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1-6.
[10]《论语•公治长》.
[11]《孟子•滕文公》下.
[12]包兆会.庄子生存论美学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5.
[13]《史记•伯夷列传》.
[14]张骏.魏晋隐逸文化与嵇康之死[J]四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5):80.
[15]李迎新.论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无奈之隐,[N]2009,(4):27.
[16]尚玉峰.隐士的定义,名称及分类[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87.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2页.
[18]肖玉峰.隐士的定义、名称及分类[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88.
[19]李善奎.古代隐逸的文化思考[J]济宁师专学报,2001,(1):15.
[20]岳国文.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9,(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