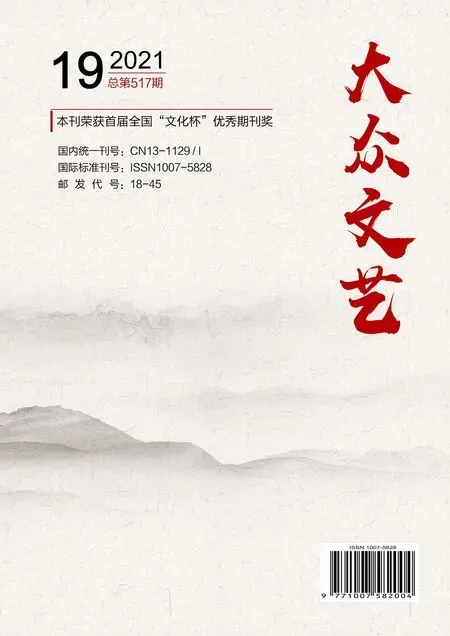自我引导与他人引导—— 西方自画像的现代阐释
郭晓冰 (安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河南安阳 455000)
一、视觉系统概念
视觉是人类感官的中心环节,是造物主赐予人类的一份高贵礼物。人类通过观看来获取外部世界,认识外部事物,观看、分析、判断和识别逐渐形成了一套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系统。就像索绪尔说的,我们是通过创造出一个词汇的系统才创造出词汇的意义。我们同样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有通过创造观看的系统才能创造出视觉文化。依据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把人的感官分为距离性的感官(如视觉和听觉)和非距离性的感官(如触觉、味觉和嗅觉),并认为前者是一种认知性的高级感官,后者是一种欲望性的低级感官,进一步证明视觉的独一无二性。另外在我们人类的日常和哲学话语中,常常会运用视觉隐喻来表意那种具有启示意义和真理意义的认识。尤其是在西方的认知中,无论是对真理之源头的阐述,还是对认知对象和认知过程的表述,视觉性的隐喻范式比比皆是,因此也就形成了—种视觉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体系,一种可被称为“视觉中心主义” (Ocularcentrism)的传统”。1并且,在这一传统中,建立了一套以视觉性为标准的认知范式和一种价值秩序,建构了一套以主体认知到社会控制的一系列文化规制的运作准则,形成了一种“视觉引导”。
二、引导概念
“引导”这个词语是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书中对历史的三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中提到的,即“传统引导”“自我引导”“他人引导”这样三种。里斯曼在文章中提到,什么引导着人们的行动,社会中的人们又是怎样被引导的。2
我想把“引导”引入自画像的解读中,自画像引导人们观看什么,人们又是怎么被引导观看的。自画像本身引导我们看的不应该是简简单单画像本身,它想引导我们去看,画家本身正在看的事物,他希望观看者能够像他这样去看,一方面画家引导人们像自画像中人物形象一样,另一方面就是引导人们像自画像中的人一样观察自画像所关心的事物。我将从“引向他人”和“引向自我”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
(案例分析)
1.引向他人
丢勒一生执着于自画像,我们在丢勒的自画像中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一种神性。锥形的形象,完美的卷发,匀称的脸,放在胸前的手充满高贵,包括小指轻微弯曲的暗示,合乎高贵的血统,显示了威严和不朽的坚定。丢勒将自己的形象与基督复合起来,远非是自我崇拜,而是在暗示将自己奉献给上帝,以自我消解(殉道)的方式实现救赎。(上帝化作人的肉体,并以基督的殉难承担起人类的罪恶——“道成肉身”。)我们看到丢勒在创造这幅自画像的时候带有一种神的确定性,首先画家有种身份的确认,殉道者,然后画家的目的很确定(这里不是简单的画画这个事情),就是我要自我的消解实现救赎,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画家想把我们引向另另一地方(天堂),画家在这里充当了媒介的作用,人们站在这幅自画像强观看,就像站在了一扇通向天堂的门,画家正在引导我们的信仰。
委拉斯凯兹的《宫娥》是一幅非独立式自画像的典范(一种有场景自画像)。画家这样描绘自己:他站在画室中一块大画布前,他可能就是在画这幅画,也可能是在画国王菲利普四世和王后。这两人的肖像在远处墙上的镜子中反射出来。年幼的公主玛格丽特和她的两个宫女,她喜欢的侏儒以及一条大狗出现在前景。中间的是一个神职人员(有的书上说的是穿着寡妇服的妇女)和一个男性护卫;在后面,一个绅士出现在明亮的大道中。画中所有的人物都确认了王室的存在。他们之中同样高贵的是委拉斯凯兹,与他的君主面对面。3画家想把我们引向君主社会的生存状态。一方面画家本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员,服务君主。他同样希望观者可以像他一样去效忠君主。在这幅自画像中,画家一方面在炫耀我可以和君主这样面对面的,画面中的同时存在和在做画过程中的面对面;另一方面这里的画家已经不像丢勒那个年代以救赎式的方面去引导他人,而是以一种夸耀的方式在引导人,把人们引向一种欲念(升官发财)。
在维米尔《绘画的寓意》这幅作品中,画家背对着观者,穿着“历史性”的衣服(好似勃艮第服装)。他正在努力做画,一个站在他前面的模特带着月桂花冠,手持喇叭和一本书,她是克利俄,代表缪斯女神。后面墙上的联省地图(荷兰家庭日趋大众化的墙壁装饰)也暗示了历史。观者处在这些情节发生的空间之外,拉起的帘子提供了视觉上的通道。一些艺术史学家认为,左边不可见的窗口透射的光线照亮了模特和画布,这一场景暗示了艺术的启迪之光。4这幅画中我们仅仅看到了画家的背部,但我们还是把他作为自画像来讨论。在这幅画中,画家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为需要的人而画(画商或是赞助人)。画家穿着流行的服装,墙上挂着流行的装饰,另外就是流行的女性形象,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符合需要者的口味而强调的。画家把自己塑造成了引导社会流行文化的人,自己处在社会最前沿,前沿文化的使者,指引人们的流行时尚。
在“引向他人”的自画像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他人”,一方面就是引向自画像本人,画面中呈现的图像,另一方面是要引向目的的“他人”,要把我们引向那里。更深层就是,我们在被引导的必然结果就是屈服于我们被“引向的他人”的脚下。我们屈于上帝的脚下,我们屈于君主的脚下,我们屈于画商的脚下,我们屈于流行文化的脚下。
2.引向自我
自我回归,人们真正地开始了解自我,一种真实性,因为写实性的绘画总是在虚幻的空间下进行呈现。现在的画家已经开始运用各种手法来彰显自己,自画像本身的逻辑就是,在画家把自画像画完的那个时刻,画家的灵魂已经释放,画家只剩下了皮囊,画家已经宣布死亡,自画像中只剩下了人类的同感,画家留下了整个人类的自画像,画家消融在了这幅自画像中,画家希望通过自我的救赎来回归自我,也是希望人类的救赎来回归人类本身。
凡•高将他所有的理想和苦痛全部转化为他的自画像艺术,艺术对于他是全部意义上的生命的结论。他不断地画自画像,他的自画像是透视其心灵的一扇窗一一敏感、脆弱、坚毅、矛盾。
纵观凡•高的一生,不难理解他的自画像上镌刻着孤独的印痕。成熟期四十多张自画像绝大多数是胸像,没有一张全身像,这也能揭示出艺术家的孤独的内心和渴望与他人交往的心情。因为艺术史上没有哪一位艺术家如此接近、审视自己以及真实地描画自己。数量之多,目光之坚定绝无仅有,使描绘本身首次变成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行为。绘画本身的真实存在一一纯粹的外表,纯粹的视觉性,纯粹的形式一一开始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个性的画家描绘了共性的图画,我们社会上的人类自画像本该的面容,非常真实的描绘了人类的孤寂和不能被别人所理解姿态,画家希望人类审视自己来救赎自己。
对蒙克(1863-1944)来说,绘画是他人生解脱愁苦的工具,自画像是他人生自我心理与情感的外化。
因此,他在很多自画像中对自己进行探讨,似乎想使生命的时间在一瞬间停住。在一系列的自画像中,他总是表现出对自我精神与心灵世界的忧虑。
在《站在钟与床铺之间的自画像》中,表达出画家对死亡的忧虑,蒙克从幼年起就面对病魔的威胁和恐惧,为一无所有而焦虑不安。因此感到需要描绘的不是现实的美丽和平静,而是个人备受折磨的内心世界。钟和床,这两件东西都是象征死亡的,床的后面隐约显示出另一个房间,在他身后的墙上则挂满了反映他一生的艺术作品——它叙述了他一生中漫长的创作路程,其中有痛楚、愤怒、忧愁、欢乐,当然还有爱情,有生也有死。正如画家自己的陈述:什么是艺术?艺术是痛苦和快乐的产物,但艺术主要来自痛苦。(引自《大师自画像》第126页)。人类具有自我审疼的观念,画家希望通过审视自己的疼,来救赎自己,但他更希望人类审视自己的疼来救赎人类自己。只有自己“疼”过才会想起自己,才会感受自己的真实存在,自我回归的本体才会实实在在。因为人类最害怕失去,只有存在才会有希望,“疼”召唤回了我们。
“引向自我”的终极方向就是回归自我,自画像中的人现在的指向已经是我社会中所有人的共同自画像,已经不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引向他人”那种个性化的自画像,这种个性化的自画像有种高高在上的隐喻,它是引导我们的媒介,我们屈于这样的引导。而在“引向自我”的自画像中,个性化其实是失效的,画家意在描画整个社会中人的肖像画,自画像最后呈现出来也就是整个人类自画像,他在审视整个社会,审视是什么把我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三、小结
对于自画像的画语分析与解读,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有形式主义分析法、图象学分析法,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分析发及精神分析学方法和新马克思主义分析法。其实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引导”来观看这些图画,“引导”构造出不一样的“我们”。
本文将自画像划分为“引向他人”和“引向自我”,是一种社会学的概念。我想强调的是画面的被引导性我们,“引向他人”体现了一种屈从感,“引向自我”则体现整一性,这种自画像具有了一种社会指向性,画面所呈现是一种我们共有的情绪,我就在画面中。
画家的社会关心度已经被提到很凸显的位置,画家的社会责任感,也许就是我们当代艺术应该首先具有的一种能力。艺术家处在社会的前沿,扮演着先锋角色,他们将继续引导我们,同时他们的社会责任将越来越重。
注释:
1.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页.
2.[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8页.
3.[美]弗雷德•S•克莱纳等编著.《加德纳世界艺术史》.诸迪.周青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746页.
4.[美]弗雷德•S•克莱纳等编著.《加德纳世界艺术史》.诸迪.周青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763页.
[1]海德•米奈.《艺术史的历史》.李建群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2]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理论导读》.杨竹山 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弗雷德•S•克莱纳等编著.《加德纳世界艺术史》.诸迪 周青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