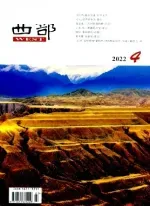第七感觉的魅力
(哈萨克斯坦)穆和塔尔·夏汗诺夫
哈依夏·塔巴热克 译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整个二十世纪以及二十一世纪的伟大作家,他本人就是一个精彩的世界,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已经被译成一百七十七种文字。尽管在世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家,但是,他从没有骄横高傲,从不失去真主赐予的谦逊性格,从不给自己男子汉的高大形象抹黑。
在苏联政权极盛时期,民族文学曾经出现了五位伟大的作家,依年龄大小来排列,年长的是哈依森·库里耶夫,然后是穆斯泰依·卡里木、达维德·库古蒂诺夫、热苏勒·哈木扎托夫,最年轻的是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他们五个人是朋友,他们说:“我们五个人犹如一只手不可分离的五个指头。”命运使我成为这五位伟大作家的兄弟,这是我的幸福。尤其是我与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之间,结下了比亲人还要亲的兄弟情谊,这是一种基于第七感觉的特殊的友谊。
2008年2月23日,我因病第二次入院治疗,我没有告诉任何亲友。那天夜里12点,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从保加利亚打来的。他说:“我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就想给你打电话,身体怎么样?”这是什么呢?难道是神奇的第七感觉吗?
2008年6月10日,我在阿拉木图住院治疗。当然,我每天都给德国纽伦堡挂电话,向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妻子玛利娅姆和他们的儿子叶斯达尔询问钦吉斯兄的病情。五六天前我就买好了飞机票,准备去探望他,但主治医生说我的心脏病不允许我做长途旅行,不给我准假,所以一直没能成行。那一天,我的弟弟胡迪亚尔·毕拉力、侄儿热万、儿媳古丽娜尔来到了病房,我起身迎接了他们。就在我重新坐回病床的一刹那,那张病床却鬼使神差地从中间断成了两半儿。这张曾经承受了比我还重的病号的床怎么就在那一刻突然散了架?又过了一会儿,手机急促地响了起来,噩耗传来了——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兄去世了。这究竟是偶然事件,还是一种预示?我至今都没有想明白。
2007年,我俩曾经一同参加一次会议。期间,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曾经对我说:“穆和塔尔弟,最近,我将咱俩多年前合著的那本书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了一遍。我之前不知道人们为什么碰到我的时候就会频频提起这本书,后来才知道原来咱俩在这本书中不仅仅谈到了个人的命运,而且还谈到了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随时代潮流发生了巨变的社会,还有民族、历史、爱情、男子汉的职责,以及民族的未来。作为情同手足的兄弟,我们是植根于人类智慧的精神挚友。也就是说,我们围绕共同的主题展开的倾心交谈,散发出了异常耀眼的光芒。我想,没有读过这本著作的人,不可能对我俩做出公正的评价。”
在比什凯克,国家降半旗来悼念这位伟大的作家。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一样,世界各国政府和各地的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悼念活动。我与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亲人们一起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精神恍惚,悲痛万分。这支几乎没有尽头的送葬队伍又被出现在道路两边垂泪悼念的人们簇拥着。当送葬的人们来到了中央广场停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位苍老的俄罗斯老太太手中拿着艾特玛托夫的一本著作,她老人家泪流满面,大声对我说:“愿真主赐予您健康的身体,您是艾特玛托夫还活着的精神挚友,所以请接纳我诚挚的劝慰!节哀顺变吧!”前一天,在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家中,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胡尔曼别克·巴基耶夫也曾经对我说过同样的话语。顿时,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当送葬的队伍开始向先祖之墓行进的时候,有一位憔悴不堪的年轻人来到了我的身边,并伸出了手。
“大哥,我是从阿拉木图赶来的,是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的大学生。我虽然只在电视上见到过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是,我读完了他的所有作品,有的作品甚至读了两三遍,他是我最敬重、挚爱的作家。我从电视上知道今天要为他送葬,便乘坐公共汽车赶来了。”
“这说明您忠诚于人类的精神财富。”我悄悄地回答。
“在今天这个悲痛欲绝的日子里,请您签名,确实有点儿唐突。”他说着拿出了用报纸包着的书——《世纪之交谈话录》。“从我入学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背诵您的诗歌。而在这本书中,您与艾特玛托夫关于精神、思想方面的谈话,能一路指引着我向前,所以我完全接受了它。”
后来,我前往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德国医院接受心脏病治疗。在此期间,我又回想起了这些事情。十二年之后,我与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一样,又将我们合著的作品《世纪之交谈话录》读了一遍。读到关于1937年艾特玛托夫的父亲托热胡勒被诬陷为“人民公敌”而遭逮捕,受尽折磨的经历,以及艾特玛托夫与布布萨拉·别依切纳李耶娃之间真挚的爱情的时候,我流下了难抑的泪水。最神奇的是,钦吉斯·艾特马托夫在搜集整理这些素材时忧郁悲伤的精神状态,以及无数次含着泪水的情形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刻,我惊呼道:“真主啊,原来我已经成了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活着的记忆啊!”在写作这本书期间,我们不知有过多少次倾心交谈,精神会晤,产生过多少次矛盾冲突,之后又被对方据理说服,达成一致。在确定书名时,我们迟迟无法做出决定,最后,经过反复协商推敲,我们共同确定了书名。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为了历史。
两人合作写一本书是很难的事情。在写作这本书中的一章——“戏剧《回忆苏格拉底之夜》”时,我们为内容与形式,为许多棘手的问题进行了许多次的交谈,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多少辛劳的白昼啊。啊,那些使人备感亲切的日子!
去年,我曾经与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两人商谈修改书中的一章——即“权力与精神财富在帝王将相命运中的体现”。但是,无情的时间没有使我们如愿,现在我又不能独自一人去修改这部分内容,只好作罢。由于这本书与钦吉斯·艾特玛托夫这个名字息息相关,所以,现在它只能以独特的魅力,也以缺憾再版。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涉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重大问题,其中最为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中所讲述的有关曼库尔特酷刑的故事,即让正常人变成白痴的故事。他讲述了一个被实施了曼库尔特酷刑,完全不认自己的母亲,完全摒弃了精神思维的白痴的悲惨故事……即便钦吉斯·艾特玛托夫除了这部长篇小说之外什么也没有写,我们也会因此为他修建一座纪念碑。
现在,无论那些怀着恻隐之心的人怎么努力,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第二生命,即永恒的艺术生命已经开始了。所以,我想用2008年5月14日在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葬礼上曾经朗诵过的一首诗来结束序言。这首诗的题目是《两个钦吉斯 以及曼库尔特灾难》:
两个钦吉斯都从这健忘的世界逝去,
为民族为时代留下两串独特的脚印。
他们都用智慧用胆识而熊熊地燃烧,
他们一个用剑一个用精神闻名遐迩。
他们都征服了广袤地域和千百万人,
他们都留在吉尔吉斯大地记忆之中。
他们一个是用暴力攀登荣誉的顶峰
竟使半个地球哀鸿遍野的成吉思汗。
另一个则是挥动精神与尊严的翅膀,
用人类的智慧尊严去反抗抨击暴力,
唤起了每一个人心中的善良之火种,
成为了当代玛纳斯的男子汉钦吉斯!
……
谁说您已经逝去,我的钦吉斯兄长,
您的每部著作都是不可复制的丰碑,
可以在那第七感觉的高峰燃起光亮。
我是一个可怜无助的人,除您之外,
我没有挚爱的朋友更没有一个兄长。
您的离去使我的心灵再次受到重创,
但是您依然连接着两个伟大的民族。
您是第二个玛纳斯啊像他一般贤明,
您每天每日每时每刻啊都在用精神,
医治着无数的曼库尔特心灵的伤痛。
您已经与那大自然母亲浑然成一体,
从此您是比阿拉套雄伟的青格斯山!
2008年9月于阿拉木图
注:在吉尔吉斯语中,“钦吉斯”和“成吉思”是意思和读音完全相同的词。也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一座山峦——青格斯的称谓。只是在翻译时用了完全不同的几个字。所以,穆和塔尔·夏汗诺夫说有两个“钦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