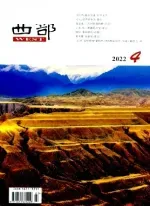最后的炮弹
热合木江·沃塔尔拜 著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译
不知道在你们村子那边的风,刮起来是什么样的?反正,在我们马木尔村这边,风不刮,草是不会动的。要我告诉你为什么吗?好,那你听着。听村里人讲,我们村的贾孜勒大叔临死前的两天,邻家大嫂曾诅咒过他,说:“该死的贾孜勒,上帝总是护着你,死神也总是宠着你。你太得宠啦。你,吝啬鬼,当心你小命不长。”因为那些天,大嫂家的小公驼总是不断骚扰贾孜勒家的小母驼,贾孜勒大叔一气之下,就把一勺滚烫的开水浇到了那个小公驼的屁股上,那小公驼受了惊吓,喷着白沫落荒而逃。那副极其无奈的样子,显然也是在诅咒他不得好死的。
我们村里还有人说,就在贾孜勒死前的一天黄昏,他家的牲口归圈,把村里什么人家的小羔也带进了他的圈子里,而他竟没有给人家小羔的主人说一声,害得人家到处找。这样,那家刚过门的小媳妇就向人抱怨:“贾孜勒大哥家门坎邪哩。进他家,都怕沾上邪气。”
说怪也怪,命短、邪门之类的话,好像真的让村里的女人们说中了。就在那个五月阳光和煦的一天下午,贾孜勒大叔被一颗炸弹炸死了。而这事儿,就发生在他们家院子里,发生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后的第四十个初夏。二次大战,最后一颗炸弹!令人瞠目!我们马木尔村——里海东岸胡沙拉克草原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村落,女人们的咒语竟是如此灵验!是的,也许,我们应该好好讲讲这个故事,就从邻家的大嫂的诅咒说起,那家小媳妇的话以后再慢慢说……
那是四十年前,贾孜勒大叔还很年轻的时候,任小学老师。胡沙拉克小学,只有四个班,他任小学老师。那是秋末的一天,他大清早,顶着寒风去学校,工作结束,天擦黑时,路过邻家乌尔达坎老汉家,进去坐了一会儿,就风风火火地回了家。要把一件可悲的事情告诉他的媳妇。
走进院子里,他就向妻子喊:“阿丽玛,嗨,阿丽玛。天哪,邻居家发生的事,你听说了吗?或者,你听说了,一直瞒着我?”但小屋黑着,无人应答。他就又喊:“阿丽玛!你哑了吗?”还是无人应答,贾孜勒就愣了片刻,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对自己说:“这女人,每天都在门口瞎忙,今天是怎么了嘛……”这样想着,他气鼓鼓地往里屋走,倏然瞥见媳妇就蜷缩在外屋的角落里,且有抽泣声在黑暗里响,就站住了。
贾孜勒说:“哦,哦,照这么着,你是听说了的。”但是,贾孜勒还是想对妻子说,自己刚去过邻居乌尔达坎大叔家,发现乌尔达坎大叔和老伴古丽贾米拉蜷缩成一团,以为他们接到儿子努尔哈力的阵亡通知书……贾孜勒正想说话,就见妻子阿丽玛站起来,走到案边,怅然地点亮了灯,然后,忧郁地看着丈夫。
贾孜勒说:“你也听说啦?努尔哈力的媳妇哈娣玛,昨天晚上,跟那个叫名穆哈麦狄的老狗跑啦。乌尔达坎老爹的小儿子哈斯哈力要去追,被老人制止了……老人怕小孩子出意外。”
阿丽玛听着贾孜勒的话,越发显得忧郁。邻家小伙努尔哈力好像就在她眼前。他是个高个子的帅男孩儿,右额角上有一颗美男痣。阿丽玛知道这孩子总是对他那个痣乐此不疲,他平日里也总是面带笑容。阿丽玛记得,有一次努尔哈力从怀里掏出一块红花的小手帕,笑着对她说:“阿丽什卡嫂嫂,瞧,这是小弟从哈尼西根镇上带来的小礼物,笑纳笑纳。”阿丽玛真的就笑纳了那块绢子。然后小伙又说,求嫂嫂帮他物色个漂亮的姑娘,阿丽娅也就真的给他物色了一个漂亮的小媳妇。谁料想,那可伶可俐的小伙子努尔哈力,与嫂嫂阿丽玛连玩笑带撒娇娶来的小媳妇,竟会在一夜之间,跟一个老鬼私奔。而努尔哈力那时却在前线浴血奋战。这使得阿丽玛感到自己无地自容,那感觉,就好像小青年努尔哈力明天就会拖着伤残的身体从前线回来,面对空空的香屋,一筹莫展。如果他质问:“阿玛什卡嫂嫂,你怎么会给我介绍这么个花心的女子?”那她该如何回答是好!可怜的孩子,是个多么善良的青年,总是面带微笑。阿丽玛这边心潮汹涌时,小屋门又响了。努尔哈力的两个妹妹努尔哈妮姆和茹扎推门进来,然后,三人相拥,哭作一团。贾孜勒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是呀,遇到这样大的事,搁谁家都不容易呀。但是,待三个女人哭完了,静下来了,努尔哈妮姆说起了另一件事,竟让贾孜勒吓出一身冷汗。
努尔哈妮姆说:“大哥,我们来找你们,本是有要事转告的。邮差达……乌……克拜叔叔……问,我贾孜勒大哥的征兵通知书已发出多日了……您这边怎么还没有回音?”
这叫个前山火正旺,后山又起火。眼前发生的事,贾孜勒还没有来得及和媳妇好好商量商量,突又冒出个征兵的事儿,而且偏偏征的是他自己,他心中就有了点大难临头的感觉。
贾孜勒脸色有些苍白,仔细想,竟想不起来那征兵通知书的事,就看看妻子阿丽玛,问:“是不是你把那东西藏起来了?”他女人就红肿着一双眼睛,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颤颤巍巍地递给男人。那张纸不过两指宽,像寺里的主持随手写下的咒文,沉甸甸地落在贾孜勒手上。
贾孜勒就轻声念起来:“贾孜勒……贾布……哈力耶夫,你已经被征兵入伍,务请于七月……”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额头上也沁出了一层冷汗。他感到两腿发软,眼前也有些眩晕,他就势扶住了屋中央的那根顶梁柱。
他在那里站了良久才转过身对女人说:“阿丽玛,我们完啦……明摆着,这是去送死。”女人就喃喃地说:“也许……你不会被派到前线去,而是留在后方,写写画画……”这话,着实发自阿丽玛的内心。在她眼里,她的丈夫是个秀才,而秀才是不能大材小用的。但贾孜勒却狠狠地向空中翻了一下白眼,说:“见他娘写写画画的鬼去!”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最知道自己肚里有多少墨水。他——一个小小的小学老师,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水平,能把小学一年级的课拿下来,对他来讲,已经是积了大德。再别说去年,他为了跟他唯一的同事争某个词尾的“S”音,露了马脚,丢大了人,他为此感到十分后悔。他后悔那个该死的词,“S”的尾音,同样可以发“N”的,为什么他就一定要跟同事争个面红耳赤。而这事儿,竟也闹得胡沙拉克的几十户人家,有好一阵子茶饭不思,那些家长深怕如此教书先生,误了孩子的前程怎么办?孩子们交给他这号人,了得?结果,离胡沙拉克百十里远的哈尼西根镇上就来了一位真正的教书先生,把他和那个同事几乎是捆绑在一起,扎扎实实地集训了足足一周,又是听课,又是考试,又是验收,让大家都看到了,才算了结此事。事情算是过去了,但从那以后,两个教书先生在我们村同龄的女人那里,却成了永远开心的料。女人们说同事的尾巴带“N”,他贾孜勒的尾巴带“S”。每每遇到尴尬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逃之夭夭。而此时此刻,这一切,好像已经不重要了。这要命的通知书,来了竟然已经有三个月啦。贾孜勒不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天夜里,贾孜勒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的媳妇阿丽玛,也跟着那个穆哈麦狄跑了。他在后边追他们,气喘吁吁。他在喊,可怎么也喊不出声。眼看就要追上了,竟突然发现穆哈麦狄穿着一身纳粹的军官服,拿着德国大枪,准备向他射击,而阿丽玛却了无踪影,站在穆哈麦狄身边的人却成了努尔哈力的媳妇哈提玛。哈提玛对他说什么,她说,大哥,她说别的什么话,但他一概听不懂。他心想,哈提玛讲的一定是德语,她可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女子。但那个德国军官穆哈麦狄却说:“贾孜勒,我要要你的命哩。你要再向前一步,我就要要你的小命哩!趁你还活着,留下你的遗言。”于是,他就苦苦求饶说:“放了我,我这里有礼,有礼……”俗话说,梦是狐狸拉在野地里的屎。可贾孜勒后来曾一直责怪自己,在那夜的梦里,他怎么就那么没有原则,追那一对姘头不说,最后,为了活一个小命,竟逃到胡沙拉克东边那条满是野兔的沟去了呢。也难怪那天夜里,他睡姿实在不好,一个趴着睡觉的人,美梦又能好到哪里去呢?结果,肯定是要被恶梦惊醒的。
第二天清晨,贾孜勒从惊梦中醒来,发现妻子阿丽玛起床了,不在身边。就下意识地想,也许她去挤牛奶了,就翻了一个身,继续躺下。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对妻子有些粗暴,心里就有些愧疚,而那个可悲的梦,却好像还没有完。他有些怆然:“是啊,战争期间,兵慌马乱,谁跟谁讲客气?”他这样想着,目光投向窗外正在亮起的天光。当年,父亲曾被人当作“财主老爷”盯上了那点家产,和一些同样被当作“财主老爷”的人一道赶到了胡沙拉克这个地方。父亲是个神算。被抓之前,就算到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连夜亲自将儿子送到奥尔达的大舅家里去。临回去时,父亲说:“亲爱的孩子,你上无兄长,下无兄弟,而你爹我也是独生子。你爹本指望借家里的那几头牲口发点家财,好养你长大,可没有想到它们竟成了爹头上的套锁。爹现在已经是一匹没有铁掌的马,走哪儿哪儿打滑。但是,亲爱的孩子,人说,谋事在天!但,谋事不成,也怪不得天命。现在,爹只求咱爷儿俩仍有个好路数,等将来有一天爹接你回家。在爹来之前,你一定要好好在大舅家里。”父亲一定是不想让儿子看出他内心的脆弱,说了很多伤感的话,却没有掉一滴眼泪,然后,他一去不返。现在想来,父亲是个心很硬的人哩。贾孜勒三岁,母亲就因出天花丧命,后来父亲又送走了他。按说,再苦的日子,他也应该和父亲在一起。事实上,没有父亲和母亲,让他在恐惧中长大,以至于后来的他胆小如鼠。更可悲的是,他和阿丽玛结婚四年,一直没有孩子,这是最让他感到痛心的事儿,寒着他的心,酸着他的肋。相比之下,他的朋友明德哈力比他可是幸运得多了,虽然人家当兵上了前线,可身后留下四个孩子。只要顺天意,将来,朋友明德哈力至少有四顶小帐续香火!贾孜勒一想到这些,更是感到十分宿命。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谁都比他贾孜勒活得强,就连同样去了前线的萨布尔也有一个独生子。贾孜勒清楚地记得萨布尔的父亲纳基麦丁说过的一句话:“多子多福,死一个,还有活着的,而独子死了,就绝后了。”为此,萨布尔的父亲特地给他唯一的孙子选了一匹最好的马,还在那马头顶上挂了一束鹰羽避邪。老爷子日夜守候着他唯一的孙子,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而他——贾孜勒就要上前线去了。天下的子弹何曾长过眼睛?谁敢担保枪林弹雨里,他这个独生子能平平安安……贾孜勒越想,心里越觉得发凉。他就“腾”地坐起来,那感觉,好像被窝里钻进了蝎子。然后,他就马马虎虎穿上了衣服,出了卧室,洗了脸,走进厨房里,开始与妻子一起用早餐。只是,他的脸色依然很难看。
贾孜勒用眼角看了看妻子,喝着早茶,说:“阿丽玛,去年冬天,那个叫地娃子的想了个啥法子,逃过征兵通知书来着?”阿丽玛被他这一问,问糊涂了。明摆着,他是明知故问,因为他最清楚地娃子的那档子事了。阿丽玛就瞪大了眼睛:“你忘啦?那天,他去哈尼西根镇应征前,光着脚板在门外冻了一夜?一夜呀,寒冬腊月的,把十根脚趾都冻掉了啊!人家前线才不要一个没有脚趾头的人!可他对人说,脚趾头是他去找骆驼的时候冻掉的。那征兵队长气得直摇头,后来,就把他废了。现在,人家在村里,人不是,鬼不是,就那么混着,那日子也够他受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嘛!”阿丽玛说话的时候,贾孜勒的眼睛一直盯着女人看。他发现,女人的脸也是冷着的。
自那天起,贾孜勒就一直心灰意冷。可偏偏只要他一出门,他就总是碰上那些平日里瞧不上他的人,好像人家都知道了他心里的那点小九九。
一天,他妻子阿丽玛突然冲进屋来,说:“贾孜勒,不好啦,好像是征兵的人来啦,三四个,还有那个军医——我萨维特大哥!他们去了布开什家。听说,布开什也接到征兵通知书哩。我早些时候听哈力大叔说,他们要来,说来,还真的就来了。”贾孜勒一听脸就变了,越发变得黑了。
贾孜勒说:“好啦,好啦,别再说啦!”
说完,他就出了屋门,径直向屋后的小羊圈里去,闹得女人一头雾水。
一会儿功夫,贾孜勒就端了一盆鲜血,从羊圈那边回到屋里。阿丽玛发现那盆里的血还冒着热气。
女人就瞪大了眼睛:“你疯啦?”
贾孜勒说:“快,拉铺,在火墙旁。”
铺很快被拉好,贾孜勒躺下,那盆热血已经凉了一些,贾孜勒就喝了两口。那血粘在他的脸上和嘴角上,甚至有一滴,还慢慢滑到他的下巴上。贾孜勒就向女人警告说:“你敢走漏半个字,我就……”他停了停,好像意识到自己说得过了,又说,“算了,我自己会对付他们。”
胡沙拉克不过几户人家,外边又是大冬天,那些征兵的人没转几家,就转到了贾孜勒家。先进门的是农庄主席达吾列特。农庄主席像往常那样,进门时说着话,但前半句贾孜勒没有听清,只听得后一句话是俄语:“同志……贾孜勒·贾布哈力耶夫,你还好吗?”
农庄主席的话还没说完,另一个身着军服的俄罗斯人就抢了话头,用一口地道的哈萨克语说:“好样的,主席同志,我看……这位朋友身体好像不好。你们看见了吗?他躺在床上。”达吾列特主席看了一眼站在身边的阿丽玛,继续操着俄语:“不不,哈!不会的,没瞧见这里有一个健壮的女人嘛!”话的意思是说:一个男人,守着一个健康的女人,怎么可能有病呢?弦外之音,不言自明。
军官惊奇地问了一句:“哈!这血是怎么回事?”
农庄主席的眼睛这才落在那半盆血上。那血已经凝固,又稠又黑。主席就吓出一身冷汗:
“亲爱的贾孜勒兄,昨天不是还见你满地乱跑的吗?你这得的是啥病哟?”
(3)建筑质量差:土坯建筑、彩钢房、荒废失修的破败建筑等,根据村民需求和意愿原地重建,确定需要原地重建的住宅建筑数量。
贾孜勒就一副痛苦状,吃力地抬起头,咳嗽了两声,说:“主席,你知道……我肺上有结核。今天……来血了。”他说着话的时候,竟也有两块鲜血从他的嘴角上流出来,稀稀拉拉地掉在那个盆子里。这情景,让一直默不作声地站在一边的军医萨维特差点笑出声来。贾孜勒这边,还以为自己表演得不错,结果,军医萨维特就一声不响,慢慢走过来,让他张开了嘴。然后,在地上捡起一根草,从盆里的淤血里蘸了一点,对农庄主席和军官笑说:“好啦,明天,会有结果的。我们还是走吧。”说着,转身出去,那些人就跟着军医萨维特鱼贯而出。客人一走,贾孜勒媳妇这边就哭上了:“你这可怜虫!你这里做的又是哪门子傻事?咱们刚混出一点人样儿……这下好啦,过去,你爹是‘财主老爷’,这回儿,你又成了‘逃兵’。你活得还不累呀你?上前线,穿那身皮又能怎么了啊?只要不是殓衣,你能活着回来,不就行了吗?我说你呀……呜……呜……”
贾孜勒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切怎么就这样荒唐地发生了。他感到十分慌乱,一气之下,又向女人大声喊道:“哈,你这狠心的婆娘,你是想让我穿殓衣呀。我就知道,你这娘们想的就是让我自己往死神嘴里跳。知道吗?死神的嘴喷着火!”
“国家大难临头,你那小命比谁更值钱?你以为自己是谁?”
这句话如天赐利剑,突然间就刺在了贾孜勒的七寸上。而这女子,平日里与他同生同死,几乎没有给过他冷脸,但就这么一下,她把他逼到了绝路上。是的,他这条小命比谁人更值钱?那些在前线死掉的人,不也义无反顾地去找死神了吗?而他,想保住小命,结果弄巧成拙,人还没有死,就已经穿上了殓衣,在这里半死不活。
照此说来,贾孜勒是作茧自缚,自讨没趣,明天,他刚才做的一切,将大白于天下。那个大眼睛的军医萨维特将把羊血的化验单拿来,放在他眼前,放在世人面前,那样的话,他的脸往哪放哟?谁肯替他求情,替他解释?如果他说,这只是跟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谁又会相信天下有这鬼话?军令如山倒,岂能儿戏哟?况且,那俄罗斯军官又不是他贾孜勒的大舅,就是贾孜勒对他说,我家就我一根独苗,人家肯听吗?就是听了,人家又肯放过你贾孜勒吗?他一定会说,见你的希特勒鬼去吧!像你这样的人必须死在德国前线。贾孜勒这样想着想着,越想越觉得迷乱,以致他想尽快逃离这个世界,逃得越远越好。这样,他就扔掉了被子,慢慢坐了起来,怅然走到屋中央。
贾孜勒心情十分沮丧。结婚四年,他的女人没有下过一仔儿……穆哈麦地,那条老狗……偷走了努尔哈力的小媳妇!贾孜勒这样胡思乱想着,他只感太憋气,太憋气了。阿丽玛还在屋里,坐在炉灶边上抽泣,而炉膛里的火已经快要熄灭。他在妻子面前站了一会儿,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看不出是在恨女人,还是在同情女人,然后,“咣”地甩了门出去。屋里突然一下像死了一样,过了好一会儿,阿丽玛不见贾孜勒回来,突然想起了什么,冲出门,果然看见丈夫骑着那匹枣红马,向野地的黑暗里走去,那马背还驮着被他亲手宰掉的黑羔。她明白了什么,想喊他,可是一点勇气也没有。他们已经无脸见人。
从那天起,贾孜勒就成了一名临阵脱逃的逃兵。这是寒冬腊月,寒风已经刮了四天,而这个深山老林里的洞穴,竟也已经成了他的家。这个家就在诺盖拜峡谷中,隐蔽而宁静,与世隔绝。他已经有很长时间躲在里边,偶尔出去,从雪堆下拣来些红柳。那些红柳,烟熏火燎,既经不得烧,又容易暴露目标。他曾用那只黑羔肉做诱饵,打来的猎物最后的肉也已经吃完。此刻,他就像一条躲在狼窝里的狗。贾孜勒过去曾听打猎的人说,狼窝冬暧夏凉。见他妈的鬼去!这洞分明是一座坟坑,四壁白霜,躲在洞里,他不但感觉不到温暖,而且只能把自己裹在大衣里,动也不动。直到肚子饿极了,屁股坐疼了,他才升点火,烤几块肉,以使自己感觉到一点温饱。而此刻,他索性连吃的都没有了。可悲的是,日子越是这样,这个饥饿的人越是满脑子胡思乱想。他总是想到有人在议论自己:“他爹当过财主老爷,儿子又成了逃犯。当年,我们就说过应该把他老子和儿子一起流放掉,可是没人听的。”还有人说:“狼崽,狼崽,狼之崽子,永远在荒山野林里。这下好啦,是你自己撞到人家枪口上,给人当活把子打,那就开会斗死你。”还有人说:“胡沙拉克人出名了,这里出了逃犯哩!”
是的,在胡沙拉克那个小小的山村里,贾孜勒不用猜也知道,男人们一定会这样讥笑他。男人们尚且如此,女人们那边更是有话讲了。她们会笑说,贾孜勒带着个死羔出逃,连坐骑都不肯跟他走,自己找回了家门,他是没有脸回来的。一个老鼠害一锅汤,一粒羊粪坏一袋油,最要命是,他害得老婆都出不了家门,整天把自己关在黑暗的小屋,也不跟人说话哩,怪可怜的。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那女人哪还有脸见人哩。
每每想到这些,贾孜勒就生气了。此刻又是这样。他半蹲着身子,从洞壁上拿下猎枪,向洞外瞄准,仿佛那里有他想射死的靶子。阳光正从高空洒下,映着洞口松软的雪,那光又明又亮,他的眼睛感到了些许的刺痛,他就出了洞。大概是有好几天没有出来的缘故,他的眼睛真的是有点难以适应这明亮的阳光了。他站了一会儿,努力让眼睛适应些。自躲到这个洞子以来,他还是第一次拿枪出洞。是的,拿枪,是为了充饥。他不敢走远,只是在洞口站了一会儿,希望有一只野兔出现,然而,四周就像死了一样,什么动静也没有。他的脚步就开始在雪地里本能地向前进。走着走着,他突然感到有些怆然,已经有四个月了,自己竟没有跟人说过话。这种时候,他才明白,一个人,能跟人说上几句话,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说也邪,正这么想着,远处果然就有黑影晃动了。那黑影动一下,又静一下。人?还是兽?是人,又能是谁?若是人,一定是来找他或抓他的吗?若是野兽,那敢情好,他的肚子正愁没有吃的。这样一想,贾孜勒就决定大胆向前走,逼近那黑影。不用怕!最坏也是个人。毕竟人心是肉长的,给人说说自己的遭遇,让人听听他一个人目前所处的困境,也难说,人家就一定不会感动得涕泪横流。不用怕!最坏也是个人,大不了,小命会给人五花大绑,大不了,自己会苦苦哀求,大不了,自己的脑袋就出现在人家的枪洞里,或者,被倒挂在炭火上,那他也认了!这样想着,贾孜勒就加快了步子,但走近了,他的眼睛也瞪大啦。原来,那竟是一头老鹿!这老东西,骨瘦如柴,肋巴条一根一根裹在皮下。它独行荒野之中,显然是鹿群里,两雄争斗的惨败者。可怜的东西,正用蹄子刨地上的雪,好像那里有鲜美的青草,但,只有天知道,它吃到了什么。贾孜勒本想一枪解决了这老东西,可看着它那副可怜相,又动了恻隐之心。事实上,连贾孜勒自己都没有搞明白,他放弃打死老鹿的念头,是怕枪声给自己引来灭顶之灾。于是,他决定追。这老东西,有几分气力跑得过他?
可是,真正可怕的事,竟也在此时发生了——贾孜勒听到有人说话:“啊哈!原来,是你这个蠢货!”
贾孜勒差点背过气去。他下意识地端起了枪。他看见,眼前的这个人不是军人,而是当年的逃兵地娃子,那个没有脚趾头的地娃子。地娃子戴着一顶滑稽的皮帽,坐在一匹母骆驼背上,两只脚像两个大铁锤子一样挂在母骆驼的两肋上。是的,毫无疑问,眼前的这个人正是那个把自己的脚趾头冻掉的地娃子。也不知,这银色的雪地,晃得他睁不开眼,还是眼前的贾孜勒让他有那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反正,贾孜勒看见的是地娃子一张可笑的脸。过了好一会儿,两个人竟同时骂道:“你这个蠢货!”
也难怪,在贾孜勒的眼里,他从来就不曾看得起过这个地娃子。
地娃子又呆了一小会儿,看看贾孜勒黑洞洞的枪口,怪吓人,欲掉转骆驼走开,说:“祝贺你!我想,你盯这头死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吧。可怜啊,一个逃犯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呀,可怜虫……”
贾孜勒突然就大喊了一声:“站住!狗崽子!你还有脸骂我是逃犯?你才是,是你!是你!是你!”
地娃子勒住骆驼,歪歪地坐在驼背上,冷笑:“唉,说你是个可怜虫呢!可怜虫,你给我听好喽,你见过哪家逃犯像我这样混在人堆里?逃犯、逃犯,野地逃窜,说的就是你这种人。你说我是逃兵?对!不假!我是为了五个可怜的孩子才当逃兵的。我有个完整的家。而你呢?有人牵挂吗?你以为你家里那匹不产崽的五岁雌马——那个婆姨,缺了你,就会饿死,没人要?……你还不知道吧,你的朋友明德哈力的阵亡通知书上周刚来。他是死了,但他的女人和四个孩子,不也照常活着吗?他老婆顶多不过像死了驼羔的母驼。”
一听说明德哈力死了,贾孜勒吓出了一身冷汗,几乎惊叫道:“死啦?”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明德哈力可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像一对小马一样。
他愣愣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不知如何是好,等他反应过来,地娃子和他的骆驼,已经消失在东边的小林子里。
贾孜勒突然愤怒起来,冲着地娃子消失的背影大喊:“站住——你给我站住!”他想对地娃子说:你个狗地娃子,去告农庄主席好啦!就说我在沟里的地洞里,让他们来抓我,然后,再让他们把我送到地狱里去。我认啦,我什么都认啦!只是,别让村里人看见我这般模样就行啦——
是的,可怜的贾孜勒本来有很多话要对地娃子说,但是,他独自一个人站在野地里的时候,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见他身子向后倒下,躺倒在雪地里,然后泪水溢满了眼眶。那些话,就窝在他的肚子里:“我认啦……什么都认啦……来抓我……你们来抓我好啦……”
有意思的是,第二天,村里的哈比警长果然带着三名警察来,从那个洞里,像捉狐狸一样,把贾孜勒抓走了。那叫抓得个痛快!不费吹灰之力。
话又要回到先前去了。
就在贾孜勒大叔临死前的那个下午,做小宗教课的当儿,听过邻家大嫂的诅咒后,贾孜勒气鼓鼓地回到了家。他生气是有道理的。那都是过去四十年的事了,陈谷子烂芝麻,还让这个缺了胳脯的女人翻出来,当新话说。他贾孜勒再怎么不好,和她老公乌尔丹也是同一年的“狗崽”嘛——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儿去。平日里,人前人后,他和这个女人好歹“大姐长,兄弟短”的,给人手足情长的印象,怎么一旦有事儿,就忘了年龄,开始翻脸了呢?这哪有一点做长辈的尊严?
事实上,事情好像本来就是这样。当年,她丈夫乌尔丹从前线平安回了家,让这个可怜女人尝到了夫妻重逢的喜悦,她比那些死了丈夫的女人真是不知幸福到哪里去了。但是,有意思的是,丈夫平安回家,竟也成了这残臂的女人在他面前显摆的资本。她当然应该在他面前显摆的。贾孜勒依然清楚地记得,战争结束开庆功会的前一天,他看见乌尔丹挂着一身的军功章,光彩夺目地从家门出来,准备去会场。贾孜勒就下意识地说:“恭喜你了!”
乌尔丹也回敬说:“谢谢你,兄弟,有人让我们到小学校去集合,我们应该共同庆祝胜利……走吧兄弟,一起走。”
乌尔丹说话的时候,脸上挂着笑容,但这笑容却让贾孜勒感到十分心虚。那笑容里,好像有几分讥讽,又好像什么都没有。他仔细地品味了一会儿,一时琢磨不出什么,索性低了头,无声地绕开了。尽管后来贾孜勒不无自慰地想:嗨,同龄人之间嘛,话多一句,少一句,只当玩笑,说过就完,何必当真?可这心里还是落下个小九九。想来想去,乌尔丹的话,乌尔丹的笑,总是有点讥讽的感觉。
好说歹说,四十年都已经过去了,可邻家大嫂今天说的那番话,听起来依然像他丈夫当年说的话那样刺耳。也许,这得怪多事的孤老婆子达丽佳特。那天,达丽佳特一大早就来敲贾孜勒家的门,说:“我家大侄子哈劳江从城里来看我啦!他在城里搞研究,我的可爱的小宝贝。昨天他一来就说,大姨妈,您知道二战时候,咱们这个村子,多少是燃过点战火的。我想找几个老人聊一聊那段历史,一个一个拜访他们。他说那些老人都是活历史,千金不换哩。我说,哦!我的天赐的小宝贝,你做的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何必一个个去拜访他们,我要杀一只羊,把他们都请咱家来,我要把你介绍给他们,你将得到他们的祝福,然后,你就跟他们好好聊。我侄儿说,这事儿很重要,好像跟他研究的什么课题有关。听到了吗?我们是他的课题,课题哩。哦,我的小宝贝,他真是个宝贝,好宝贝!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一定要来,午前。”老太太说着,往门外走,去请别人。她走的时候,还骂自己的腰:“哦,我这不争气的老寒腰……”
老太太走了,门关上了,阿丽玛揉着面,不以为然地看了一眼贾孜勒,说:“依我看哪,那些城里人都疯了,看什么都觉得新鲜,这村子有什么课题好讲的。”
中午的时候,贾孜勒夫妇便按约定去了老太太达丽佳特家。他们进屋时,发现已经来了不少人,坐了满满一屋子。看上去,大家都很快乐,唧唧咕咕说着话。达丽佳特老太太的大侄子满屋子忙着。他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儿,个子不高,脸很白净,额头很宽,很智慧的样子。贾孜勒一看见他,就想起这孩子小时候的样子,虽然记不太清楚,但依然有印象。现在,他身板抽条了,个子见长了,人也变得很有学养的样子,着实令贾孜勒心里感到几分舒坦。贾孜勒就暗自祷告了几句,为孩子求个平安,远离晦言。
一道茶喝过之后,年轻的哈劳江发了话,说:“我大姨妈说,她已经把我的愿望告诉诸位长辈了……那我就直说了。是这样……我在查阅有关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资料时,发现西哈萨克斯坦奥尔达、贾尼别克及沿海几个县的铁路,曾遭受过法西斯战机的轰炸。我想知道,你们中……有谁亲眼看见过轰炸?”
就听达依尔老人说:“好孩子,想问,就多问呗。”显然,老人已经准备好了发言,“不过,依我看,在座的这些人,除了个别的,可能没有几个人经历过敌人的轰炸。因为,这些人,大多是战后才从胡沙拉克那边搬过来的。那个时候,我自己在白俄罗斯前线打仗,这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我看我说不好。”老人停了一下,用胳膊肘指了一下什么人:“问问那个杜尚拜老爷子,也许,他能说上一点儿。”大家就一下把脸都转向了杜尚拜。然而,结果让大家都有些失望,因为,那老爷子并没有讲出什么新鲜事儿,讲的全是众所周知的老话。
老爷子说:“远方的战鼓,我们这里听得见的。一天来了敌人的轰炸机,炸了马依尔地方,有三四间民房倒了,五六个人死了。十几天后,敌人的飞机又来了。村里人吓得冲出屋子,四下里乱跑。就见一架飞机飞过,两颗炸弹落下,一个开了花,另一个啥声音也没有!”
哈劳江看着手中的一份什么资料,听着老人的话。看得出,老人说的这些,他已经耳熟能详,但无论他再怎么变着花样启发他,想从老爷子那里问出点儿新东西,最终的结果,还是令他彻底失望了。
无奈之下,哈劳江只好说:“那么,参加过战争的老前辈们,你们是否……可以告诉我,你们去过的前线发生的事,还有……你们的支队长的名字,战友的名字什么的?”
这话应该是问得恰到好处。这些年过半百的上过前线的老人们,谁肚子里没有留着几则关于青春的故事。就见他们有的摸着山羊胡子,有的翕动着没牙的下巴,作沉思状,然后,就有小故事断断续续地从老人们的记忆里涌出来,一点一点落在哈劳江的笔下。
故事一直在讲,老人们一个一个排着队讲,直到肉锅下灶,汤香四溢,老人们也洗过了手,准备上席用餐的时候,轮到了贾孜勒这里。贾孜勒就多少有些不自在了,遮遮掩掩地说:“还是……让大家先用餐,用餐吧!”可是,年轻的哈劳江那边一点推让的意思都没有,坚持让他讲。
就听贾孜勒说了一句人们常感慨的老话:“战争给我带来的灾难还少吗?”他停了一下,听听周围没有多少反应,就又说,“那时候,我们去海上打鱼,支援前线,一点也不比战场轻松。”
年轻人兴奋起来,说:“贾爷爷,快快讲,这可是一个新鲜话题呀。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贾孜勒说:“里海就在我们村旁。我们出海打渔,夏天、冬天……”
贾孜勒正说得起劲儿,同龄人阿布勒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挥了一下断臂,满脸怒色地警告道:“唉,老兄,别忘啦,人的嘴能把话说歪,眼睛能把事儿看扁哩。悠着点儿,别让人家年轻人写歪了字,坏了事。有种,为啥不讲实话嘛!哪怕,讲讲你被送到哈巴罗夫斯克那边的事。你这蠢货!”
贾孜勒一时间怔住了,尴尬地停了一下,支支吾吾地说:“1942年……我们去了哈巴罗夫斯克,我们牵制日本人,一直到战争结束……这些,年轻人,你读过书,都知道的……”
阿丽玛坐在丈夫身边,再也沉不住气了,对那青年说:“孩子,求你别再追问你大爷了……因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你大爷犯过事儿……”毕竟,这孩子见过世面,有心智的,一听大妈话里有话,也就不再追问什么了。但是,大家在老太太家的这顿午餐,却也因此吃得几分冷清了。
午饭过后,贾孜勒携夫人悻悻地回到家中,进了院子,发现他们的小儿子蹲在院子里,无所事事地在戳地上的一个洞。贾孜勒一见孩子这副无事可做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问:“唉,多多!”这是他给小儿子的昵称,儿子真名叫阿德力,“你哥他们来信了吗?我在问你读书的哥哥,还有当兵的哥哥,有信来吗?”
儿子回答说:“没有。还没!”
贾孜勒说:“那些个崽子,全他妈没有良心。我这一辈子根本不指望他们上学念书,将来给我树碑立传。都两个多月了,一个都不见音,也不见信,敢情,我得向星星月亮求问他们的平安喽。”
今天在老太太家吃饭,吃得窝囊,贾孜勒心里着实不痛快,跟儿子说过话,蹭蹭地穿过院子,往屋里走。就听小儿子多多说:“爸,刚才有条大灰蛇钻进这个洞里去了。我看见的,好像是两个脑袋的蛇,又灰又长。”
贾孜勒就没有好气地说:“那还不快打死它。你想让它把咱家人咬死,像去年被蛇咬的朱玛哈孜?你好看热闹?”
儿子却说:“爸,这个洞,好像是个直洞哩,我放了盐,它不出来,我又从茶炉那边拿了沥青灌进去,它还是不出来。我想,它是不肯出来了。”
贾孜勒想起了什么,追问:“你倒沥青倒得多吗?”
儿子回答说:“小半罐子哩。”
贾孜勒就说:“拿火柴来!我们把火柴扔进洞里去蛇就会被烧死,然后,我们在洞口压上红砖头。”儿子就转身跑进屋子里去拿火柴。儿子跑去的时候,贾孜勒想起自己口袋里还有几根火柴,掏出三根,点燃,扔进那洞里去,嘴里还骂了一声:“见你的鬼去!烧死你,这条蛇!”
可就在那一刹那,可怕的爆炸发生了。随着猛烈的爆炸声,贾孜勒家的院子被掀了个底朝天。爆炸过后,村里男女老少,像潮水一样涌向贾孜勒家。村里人都被吓呆啦,不知所措,唯有杜尚拜老人还保持着几分清醒,一再警告大家不要靠近,赶快卧倒,或者疏散。但是,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在说着什么。女人孩子的哭喊声响成一片。有人看到,贾孜勒的一条腿和一只胳膊被炸飞了,剩下的身子,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他人好像还有半口气。而他们家的房顶也被掀掉了一半儿。那以后,镇上来了车,又来了人马,然后,村里人终于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是那蛇带出了那颗曾经没有爆炸的炸弹——就是1942年落下的那两颗炸弹中没有爆炸的那一颗!人们听到了贾孜勒的小儿子阿德力的哭声,那孩子说:“都怪我呀,爸爸,没有对你说实话……我看出爸爸心里好像有气,就撒谎说,往蛇洞里倒了小半罐子沥青……事实上,我倒了三罐子呀。我可怜的爸爸。”
贾孜勒就要死了,有人扶着他的血淋淋的头,听他说:“我没有什么遗憾啦……再见了……你们。”然后,他的下巴动了动,人就永远地走了,把这个世界所有的烦恼都留给了村里的人。有趣的是,就在他死去之后,他残缺的身体慢慢舒展开来,布满鲜血的嘴角上,还挂上了一丝冷笑。好像这个世界什么也不曾发生,好像一生时光不过五日而已,好像他身后什么话也没有留下。他死得平静而平凡。如果你以为,他临死前的那一刻,还因为同龄人阿布勒的讥笑,心里窝着老大的不痛快,那你就错了,因为,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什么遗憾啦!”
贾孜勒留下的这最后一句话,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颇令村里人回味:他的意思,也许在说,比起那些个曾经死在前线的人,我贾孜勒毕竟有过几天天伦之乐;或者是在说,你们把我的那点事,当成了眼睛里的疣子,这下该舒服了;或者是说,天命难违,无论我是对的,还是错的,反正我做了,我之前的耻辱已经被上帝洗清了。再见了,你们!
其实,不管人们怎么议论贾孜勒最后的话,事实上,最令人揪心和难忘的话,还是贾孜勒的女人阿丽玛哭送丈夫时说的话:“可怜的贾孜勒,为了躲避四年的战争,你背了四十年的耻辱。现在,总算可以解脱了呀,可怜的贾孜勒!”
他的小儿子阿德力说:“我可怜的父亲!”
贾孜勒家出事那天,昨天还讥讽贾孜勒是“上帝护着你,死神宠你”的邻家大嫂,去荒地拣干牛粪,傍晚回到家来,看见贾家大院满目疮痍,一个巨大的弹坑张着血喷大口,又听说了发生的惨事,就嚎啕大哭:“哦,天啊——你抢走了我的小猎隼——我的小兄弟——”
更有意思的是,这事发生之后,村里人好像变得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当年,哈丽大妈的男人去了前线,没有回来。听村里人说,贾孜勒死后,老太太每天都面西而望,满脸忧伤。有那么一段时间,吓得村里的少妇们不敢对做工晚归的丈夫给冷脸。当然,仅仅一段时间而已。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年轻的哈劳江终于在本子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距斯大林格勒以东一百三十五公里的一个小村里,二战留下的最后一颗炸弹爆炸了……
还记得先前贾孜勒的兄弟媳妇说过什么吗?她说:现在,做人媳妇最好小心点,进人家门得先看看人家门坎高不高,地邪不邪。说的也是,如今,这“地邪不邪”的话,真的需要好好想想,谁知道谁家的院里藏着啥?谁人的心里窝着什么事?不好说,真的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