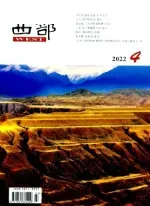我没撒谎(上)
文/邹厚龙
一
多年以后,王大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那团熊熊的火焰还在燃烧,烤得他的心肉焦痛,险些烧掉了他的下半辈子。
那是一九九八年初春的一天,王大树从村子的东墩口钻进了那辆开往恩施市的班车。偏僻的花桥场很少有车子跑,每天仅一辆长途汽车从村子东面穿过,那台班车破旧不堪,车厢里乘客挤成堆。五短身材、一脸络腮胡子的司机在驾驶室气吼吼地骂人:“他妈的!不要挤了!”
旅客们不理他,继续拼命往上爬,他们必须赶上车,不然脚可要受罪了。王大树也一样,他必须搭上这趟车走,他已经不想在村子里多呆一分一秒。凭着一身好力气,他挤上了车,努力插进了人缝中。后车门“啪”的一声关上了,随即响起一声惨叫:“妈呀,我的脚夹着了!”络腮胡子不耐烦地把车门重新开关了一遍,准备发车,但车子出了毛病,趴在公路上一动不动了。络腮胡子骂骂咧咧地拿起工具,跳下车,钻到车子肚皮下去了。
这功夫,王大树把留恋的目光射出车窗,最后看了一眼他从没离开过的村庄,目光扫过那些陈旧的瓦房、泛绿的禾田和坡上洁白的羊群,最终落到在小河边的大柳树下,那里有一个穿红衬衫的姑娘在洗衣裳。
他的心陡然变得难受。
年轻的姑娘叫田翠翠。她的模样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甜美迷人,在村子里是数一数二的漂亮,而且还是那么精明灵动。几乎整个花桥场的年轻小伙子没有不想爱她的,可全是白日做梦。漂亮就是女孩子的资本,田翠翠的心气高得很,似乎还没有谁能打动她的芳心。
老实说,可怜的王大树深深地爱上了田翠翠。虽然他算不上什么出彩的人物,只是个会手艺的小木匠,但凭他的英武相貌和憨实的品格,也似乎渐渐博得了田翠翠的喜爱。
可是,当他充满爱情的心底刚刚油生出一线希望的当口,却遭受了致命的一击。
前天晚上,他乘着暮色下河挑水,竟惊诧地看到田翠翠跟一个叫李生铁的家伙坐在小河边聊天,看样子十分亲密。要说那小子长相平平,却脑瓜子灵敏,能说会道,还能耍耍笔杆子,在市报的边角上发表过几篇有趣的小新闻呢,算是村民们公认的有出息的后生。前不久,他刚刚加入了党组织,光荣地成为村里唯一的青年共产党员。当时,王大树虽然对这个情敌十分恼恨,也是毫无办法,他一颗火热的心彻底冰凉了。
经过一个通宵痛苦的思虑,他决计出门打工。甚至可以说,他是为爱情而出走的。
方才,怏怏不乐的他来赶车的路上,恰巧碰到田翠翠拎着一篮衣物下河,她好奇地问他是上哪儿去。“唉,到远处去!”王大树哀愁地说,拿目光深情地凝望着她。他是多么希望从她嘴里溜出一句挽留的话,但是很使他失望,田翠翠只对他说的远方感兴趣,一个劲地钻牛角尖。王大树伤心地转身离去。
胳腮胡子还在车子底下敲敲打打。田翠翠淘好了衣服,从水边直起来了,像一面鲜艳的红旗。她的目光投过来了,不经意地瞅着死甲壳虫子似的班车。王大树一直在呆呆地凝视着她,并想极力与她对视一眼,但田翠翠的目光很散漫,她好像在好奇地欣赏着狗一样翻趴在车下的司机呢。
又过了好一会,司机才跳上车来,启动引擎,车子像头老黄牛似地深喘几口气,终于跑动起来,眨眼间便把村子甩远了。王大树张望着窗外,视野所掠过的地方,路边成排的树木长了脚似地迎面冲来,又飞快地后退,一些集镇、农田、小河和山包像影子似的一晃而过,一个陌生而奇妙的世界在他的眼前呈现着、变幻着、晃动着。可这一切他都无心欣赏。他的手紧紧抓在货架的拦杆上,在车子的摇晃中站着打起瞌睡来。
不知走了多远,一阵惊乍声震醒了王大树。他抬起头,惊呆了!司机台里陡然窜起的一团火焰映红了他的眼睛,大事不好!车头起火了!车轮子同时停住不动了,那司机想赶紧打开车厢门,但电路早烧毁,车门闭得死死的了。司机显然吓破了胆,不顾一切地跳出了驾驶室,撒腿便跑,隔老远了才回头甩下一句话:“我去报警求救!”转眼便不见了踪影。这截路段叫磙子山,前面不远处的一块指示牌上标得清楚,距这里最近的周贺家坪镇起码有五里。
车头前的火势已经越烧越旺,吐着浓烟迅速横窜,烈焰向后厢卷来。车厢内像被捣的蜂窝,乱作一团。有人去脚踹车门,但车门纹丝不动;有人拼命用柔软的拳头去砸车窗,但厚厚的有机玻璃显得坚不可摧;有人想从驾驶仓逃生,中间却隔有一道钢筋做的栅栏。旅客们开始绝望了,女人和孩子急得哭嚎起来。
这当儿,王大树也好生焦急,难道就呆在车厢里等着烧死吗?
着急中,他想起了随身携带的那把做木活用的斧头,于是赶忙从货架上的蛇皮袋子里把它扯出来,抡起来大喝一声:“闪开!”众人当即给镇住了,瞅了一眼他手上明晃晃的斧头,自动让开路,只见他手起斧落,一斧子砸过去,哗啦一下,车窗便穿了个大窟窿,“好!”有人高兴地叫起来,可窟窿小了,几个脑袋同时挤上去,便把洞口堵死了,一个也出不去,王大树又抡起了斧子,众人抱着脑袋全俯下身去,王大树发疯似地砰砰一通乱砸,眨眼间所有的车窗玻璃都变成了碎渣。没有什么比逃生的欲望更为迫切了,所有人便混乱不堪地从窗洞鱼贯而出,往外钻、往外跳、往外飞,有人甚至是大头朝下猛栽了下去。
王大树最后一个跳出车厢,却见一个年经的母亲尖叫着扑上来:“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王大树一听,便明白了究竟,转身又一次钻进了燃烧的车厢。在呛人的乌烟里,他循着一阵奄奄一息的啼哭声,把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从车尾的旮旯里抓起来,一个后滚翻跳出了车窗。
随即一声巨响,汽车爆炸了,旋转的轮胎、冒烟的油箱和长翅的车骨冒着火焰飞上了天空。
当王大树回过神来,才发现那个搂着孩子的女子“扑通”一声跪在了他的脚下,“救命恩人啦!”她流着泪连连磕头,随后像栽篱笆似地又跪下了一大排人,“这是干嘛呢?”眼前的悲壮轮到他不好意思了,他一个个将旅客们拉直,并提着那斧子幽默地说:“要谢就谢它吧!”旅客们都笑了,他也笑了,心中油生的一丝自豪让他忘掉了身上的烫伤,他的手臂上有好大一块烫破了皮,还起了几大个水泡,在火辣辣地疼哩,但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
客运公司很快派人来救援了,将所有受惊的旅客都送走了。英雄王大树当然受到了特别的礼待,他被公司领导用一辆漂亮的小车径直送进城里的医院。所幸烧伤势不重,只是浅度烧伤,医生给他只做了简单的包扎。
当然啦,客运公司的苟经理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桌酒菜压惊,一大桌人频频向他敬酒。
“英雄啊!敬酒!”
“干杯,义士!”
赞扬声不绝于耳,王大树虽然受了伤,吊着一只膀子,但还是来者不拒,大口大口地喝酒。他的酒量大得很,从不喝醉,他变得满脸通红是被那些赞扬声说醉的。一个铲大地的农民,一个使斧子的小木匠,一下子变得如此受人尊敬,能不高兴吗!
酒兴酣处,苟经理偏着头问:“同志,你为我们公司帮了大忙,我们该怎么谢你呢?”
“不用!”王大树说。他不过在一场意外的事故中抡了几斧子,就受了人家这么高的礼仪,已足够了,还好意思提别的啥要求。
王大树的耿直让苟经理更为钦佩,苟经理说:“我们起码要写一封感谢信寄回你老家去,有机会还要到你家乡去送锦旗!”
王大树激动得满面通红,还有点不好意思,心里可像灌了蜜似地甜润,嘴上却直叨着“不用不用”。
苟经理说:“一定得去,你等着吧,不出三五天就去!”
二
第二天一早,王大树便搭上了回家的客车。因为膀子被烧伤,他不得不暂时改变去恩施市打工的计划。
当他出现在家门口时,老爹王山坡疑惑了,问儿子:“你这是咋的呀?怎么这副模样回了呢?”儿子要出门去打工,也正中他的心思。王大树一晃二十多岁了,一直窝在村墩里,连对象也没找上,难道要像旱地里的草枯活下去么?眼下社会渐渐开放了,让他出去闯闯也好。再说,他已把自己祖传的木匠手艺全教给了儿子,俗话讲饿不死的手艺人,相信他能在外谋生。说起手艺,可能是遗传,王大树念小学时,算术常吃鸭蛋,但他偷偷用爹的凿子、刨子做的木手枪跟真的没两样,曾吓坏过民兵连长。上中学时,他学做的木滑车轮子比考分上的零光蛋更多更圆。王山坡看到儿子读书无用,只好教他木匠手艺。王大树一学就会,不几年,功夫就到家了,甚至比老子都更精了。他会在床架上雕龙,在梳妆台上刻凤,连衣柜的脚也会做上十种形状。山湾里穷,做木器讲不起高级,手艺再好也难赚钱。王大树就借口说想出去闯闯,听说城里人做家具讲究的是古色古香。王老汉正猜想儿子这回出去可能会干点正经事,给自己增光呢。可仅隔夜的功夫,他竟狼狈不堪地回来了。
面对爹惊讶的目光,王大树镇静地挨着他坐下来,神色骄傲地讲起他昨天在失火的车上救出五十五条人命的事来。听着听着,王老汉眉眼舒坦开了,高兴了,这太合他的味口啦。王老汉当即唤王大树的娘:“拿酒来!”
王大树的娘兴冲冲地拎来一壶酒,一碟花生米。看到这爷儿俩聊得开心,她也乐着,又进厨房去炒下酒菜。
王老汉拿起一个二两的杯子往小桌上一摆,满满地酌上:“儿子,来,把这个酒喝啦!”
当时王大树惊讶极了。在村墩子里,老子给儿子敬酒,那是倒翻天的事呀,那太了不得啦。王大树激动极了,端起酒杯“咕咚”一声,喝了个一滴不剩。
王老汉又给儿子斟上了第二杯,问;“你做了那件事回来的当儿,他们是怎么给你说的呢?”
王大树得意地摇晃着脑袋说:“爹,你等着瞧,他们三五天就给我写信来,马上还要派人到乡政府来,送锦旗哩。”
王老汉笑出满脸的褶子来,夸道:“儿子,有种!”
地处深山野地的花桥场向来民风淳朴,一向崇尚古道热肠的英雄壮士。王老汉年轻的时候也称得上一条好汉,满腔义气。想当年,那庚子年的盛夏,他曾从翻滚的花桥河洪水中救出三条人命,换得了个英雄的美名。到过年过节的当儿,那些被他捞起的人总拎着烟酒来谢他哩。救了三条人命,他就受到了满村子人的崇敬,他觉得一辈子挺荣耀的了。现如今,儿子竟大火中救出五十五条人命,硬是超过了多少倍哇,真了得!
他给儿子又酌了一杯。
不知不觉,王大树与老爸喝了好几巡,便有微微的醉意,于是想去沿村墩转上一圈。他走在五月的村道上,他从没发现眼前的景象这么惬意,身边成片的苞谷禾闪烁着翡翠般的绿光,一股股清香像风一样浓郁。头顶上,那一颗晒人的烈日也显得格外明亮。他感到精神分外爽。
远远地,望见村民高瘸子的经销店门前挤着一大群人,坐着不少男男女女,有说有笑,十分热闹。更让人眼睛一亮的是,他瞅见可爱的田翠翠也在那儿,她清朗悦耳的声音隔老远都听得人心痒。
王大树故意挺直了腰板,大步走了过去。
大伙儿都愣愣地看着他,见他的膀子上缠着一块绷带。
“王大树,你不是出远门打工去了吗?怎么还在村墩上晃悠呢?”一个人说。
“王大树,你这手是咋的了?活像一个在战场上光荣负伤的大英雄呢!”另一个说。
众人哄地笑了。
王大树没有笑:“呔,这话多半说对了。”他把扎绷带的手举得老高说,“这回我可干了件大好事!”他的伤口吸引了所有好奇的目光。接着,他把那辆跑恩施的破班车如何失火,他又如何奋勇救出五十五条人命的事儿从头到尾地讲述起来。大伙儿都兴趣盎然地看着他讲,好像在听一个有经验的艺人在演精彩的说书似的。
王大树讲的时候,眼光却时不时地飞落在田翠翠的身上,观察着她的表情。她偏着脑袋专心致志地听着,十分入神。时而有人小声咕哝、啧啧有声,她便叫一声“别打岔,听他说”,他看到她的脸色渐渐涨红,眼光也渐渐变得柔情多了。于是,王大树更上劲了,讲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讲到高潮时,田翠翠禁不住发出一声动人的喝彩声:“好啊,王大树,你太棒啦!”
有人跟着鼓起掌来。
“哼,这事儿是真的吗?王大树,我看你八成是白日吹牛!”人群里的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突然打断他。
王大树住了嘴,不知所措地看着质疑他的那个人。他就是李生铁。人群立马像蜂窝似地嗡嗡作声,发起议论。是呀,他王大树一个人救了五十五人,这怎么可能呢?这王大树啥时学会扯谎了呢……有人开始摆脑袋,眼睛里放出嘲弄的目光。
“这个大伙儿放心好了,”王大树定了定神说,“过不了三五天,人家那边要给我写感谢信来,还要来人送锦旗哩,不信等着瞧吧!”
“这么说来,八成是真有这等事了,这王大树也不是个爱吹牛的小子,是个老实的小青年。了不得啊,小村子里出大英雄啦。”于是,大家一窝蜂围住了他,吵嚷着问一些他没讲到的稀奇古怪的细节,弄得王大树心里有点发烦。这当儿,只有田翠翠奋力拨开一条人缝,心疼地抚摸了一下他的手臂,脉脉含情地问了一句让他入心入肺的话:“伤得严重吗?疼不疼?”
“不碍事。不用几天就好了。”王大树坚强地说,抬头环顾了一眼,瞅见那李生铁垂头丧气地悄悄地溜走了,他头一次品尝到了得意的滋味。
接下来的几天,大伙儿看到,吊着膀子的王大树成天满村墩地晃悠,而且田翠翠也形影不离地跟在他身边。每碰到一个人,不管是男女老少,王大树都会神采飞扬地把他的英勇事迹再讲一遍。每当这功夫,田翠翠就会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仿佛为他感到骄傲。那一双美丽的眼睛灼灼闪亮,弥漫出无限地爱慕。
“他俩好像搞上对象了?”
“英雄与美人,蛮合适嘛。”
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他们。
每当这时,王大树心里便喜滋滋的,不好意思地回头瞅一眼身边的田翠翠。他从田翠翠那大胆热烈的目光里读出了爱情,内心感到分外激动,一次冒着胆子的鲁莽行为,竟赢得了姑娘的芳心,这是他始料不及的。而在田翠翠的心目中,王大树再也不是一个普通俗气的村民,他陡然变得高大起来,成了个见义勇为的英雄。她想爱的就是这样的硬汉子,村子里再没一个男人比他伟大、崇高。每当她站到他身边,看到别人对王大树的夸耀,她也会激动得满脸通红,感到十分光荣。
傍晚,他们相约来到小河边,沿着波光粼粼的河边漫步,继续兴奋地聊着。“大树,想好了没?”田翠翠陡然问,“隔天儿,那边送锦旗的人真来了,你该咋说呢?”
“这个……我还没想好呢。”王大树急得直搓手。他平时口舌笨,不会怎么说话。
“若是上面的领导也来了,报社、电视台的记者也来了,你又咋说呢?”田翠翠又问。
“咋说呢?”王大树更猴急了,求她道,“你是一张鹦鹉嘴,快告诉我啦。”
“我也没见过大世面,咱俩商量商量才好。”田翠翠说。
他俩蹲在河水边,有说有笑地合计起来。
“王大树,你要大出风头了,”最后,田翠翠忍不住轻轻抱着王大树受伤的手臂说,“乡领导肯定要在会上表扬你,市报、县电视台也要宣传你,这回你做成大名人啦!”
“嘿嘿!”王大树得意地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