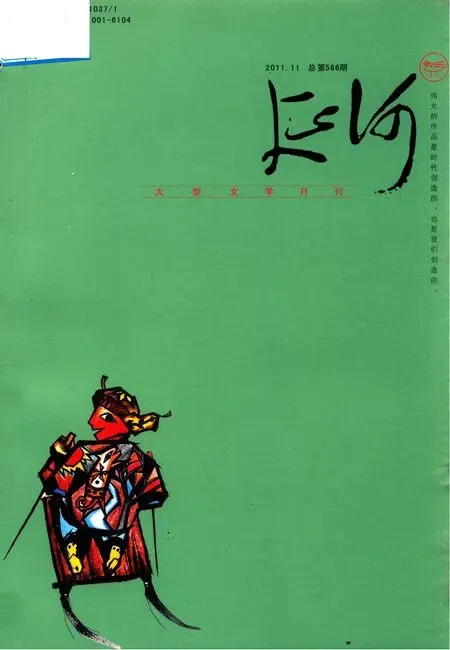奥斯特的叙事遁形术
包慧怡

保罗·奥斯特 著 包慧怡 译 《隐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保罗•奥斯特的第十五部小说《隐者》有一种表面的轻盈:更加生脆、洗练、从容的文字,更清晰的叙事框架,更多可读性——太好读,以至于你会疑心它不够好。这种具有欺骗性的轻浅正是冷静自律的结果。《隐者》不是那种可以令人掩卷时长舒一口气的作品,也绝不是一部精致版的《罗生门》。它是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长蛇,你找不到圆环的起点;它那漩涡状的叙事有一个安宁的台风眼,所谓“隐者”,恰恰栖居在这看不见的中央。
一如奥斯特的其他几本小说,《隐者》书中有书,故事里套着故事。故事的核心部分是由三个叙事者相继讲述完毕的:《春》中的亚当•沃克(第一人称),《夏》中的亚当•沃克(第二人称),《秋》中的吉姆•弗里曼(第三人称,由吉姆根据此时已去世的亚当留下的手稿改写而成),《冬》中的——不,没有《冬》,冬是隐形的,只有冬的寒意长存于冰冷单调、永无休止的击锤声中——第四部分中的塞西尔•朱恩(第三人称)。其中《春》、《夏》、《秋》合起来便构成了亚当没能写完的回忆录《1967》,那些随亡者逝去的秘密则由塞西尔在日记中补充完整。或许应该在“亚当”、“吉姆”、“塞西尔”上打引号?第四部分伊始,吉姆就告诉我们,《1967》中所有的人名和地名都已经过了篡改。随着故事的不断展开,我们脚下自诩为真实的台阶被一级一级抽空,我们对每一个叙事者的信任也逐一瓦解,直到我们被抛入一扇反转之门,一座迂回的镜宫——究竟谁是真正的隐者:那个不是亚当的亚当?不是波恩的波恩?不是吉姆的吉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假名替代、蒸发、成为幽灵,实相化作影像,场景化作蜃景,人人都是说谎者,人人都是勾引家,人人都躲藏在一个故事/一本书的面具之下,奥斯特似乎在不无反讽地暗示着,惟有在阴影幢幢之地才可能稍稍接近真实。

蒋子龙 著 《农民帝国》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本书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背景,以郭家店的发展变化为蓝本,以郭存先的经历为线索,细腻而深刻地描写了一群农民起伏变化的生活,入木三分地剖析了金钱、欲望、权力对人性的冲击。一代枭雄,从农民到农民帝国之巅到阶下囚,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大起大落和灵魂蜕变?作家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中,带给人们的是强烈的情感碰撞和无尽的思索。也使作品在一如既往的硬朗中,又添几分沧桑与深厚。
和奥斯特前几年的某些小说不同,结构上的匠心并未使《隐者》显得文胜质,书中人物也并非用来试验作者种种认识论立场的乐高玩具,而是真正倾注了作者的感情,真正与作者情同此心——《隐者》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是如此,连波恩也不例外。事实上,亚当在写作《夏》时遇到的“作家阻塞症”很可能是奥斯特本人再熟悉不过的,而通过尝试吉姆“改变人称”的建议,亚当和奥斯特拯救了各自的写作。
“通常,被阻塞的情形来源于作者思考中的一个缺陷——也就是说,他不完全理解自己想要说的东西,或者,说得委婉些,他对主题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式……用第一人称来写自己时,我压抑了自己,使自己成为隐形人,因此就无法找到所要寻找的东西。我需要把我从我自己身上分开,后退一步,在我和我的主题(也就是我自己)之间雕刻出一块空间,于是我回到第二部分的开端,开始以第三人称书写。”在这一意义上,《隐者》又是一本关于小说写作的元小说,和这一文类中的许多作品不同,《隐者》读来毫无学究气,那些把它归为智性小说的评论家其实低看了它,《隐者》首先是通过血肉匀停的故事打动我们的,正如奥斯特永远首先是个说故事的能手。
“隐者”——直译为“看不见的事物”——究竟是什么?奥斯特没有采用粗俗的点题法,而是将一幅闪光的地图剪碎,看似漫不经心地抛掷在叙事的湍流中。开篇不久,亚当如此描述波恩的脸:“一张寻常的面孔,一张在任何人群里都会隐形的面孔”;给吉姆的一封信中,亚当称奥克兰和伯克利的族裔居住区里的黑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是“看不见的人”;吉姆在从旧金山到纽约的飞机上回想着1967年的糟糕日子,感到“一个看不见的美国在我下方的黑暗中沉睡着”;最后,当塞西尔逃离孤岛奎利亚上波恩的大本营“月亮山”,她听见了金属与石头冷酷而浮夸的合奏——“每把都以自己的节奏运动,每把都被锁在自己的韵律中”——却看不见声音的来源,即便在一切水落石出之后,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将永远起落于塞西尔的颅中,永远叮叮当当地敲凿着石头。

郭文斌 著 《农历》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小说以“小说节日史”的方式呈现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潜流,展示中华民族民间化的经典传统,经典化的民间传统,堪称清明上河图式的长篇。作者花费12年心血,写成这部以农历为名的长篇小说,其中包含的不仅是作者对中国古老习俗和文化的理解和阐释,更是作者对人心世道的深切关怀。该书三十万字,以十五个传统节日为纲,从元宵开始,到上九结束,记述了一整个季节的循环。
而看不见的远不止这些。亚当在《夏》中对与姐姐格温的不伦之恋的回忆和格温本人的回忆完全对不上号,两人都声称自己道出了真相——也许的确如此。我们的记忆是个惯于擅自筛选的黑洞,我们无从了解它运作的机理——为何保存这些,屏蔽那些,又自动改写那些——它却使我们成了无动机的撒谎者,并且各自问心无愧。这个尘世的万花筒啊,不要轻易摇晃它,别把眼睛迫切对上那许诺了确定性的窥孔。
假设亚当在《夏》中写出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奥斯特仍通过亚当的写作活动对自己和所有小说写作者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该如何书写生命中重要的故人——同时又不书写他们?该如何诉说一个秘密,但秘密还是秘密?那些最初促使我们提笔写下故事的人,那些如今早已淡出我们生命的鬼魅,只要他们尚在同一个世界上呼吸着,我们又怎可能避免遭到误解,我们的作品怎可能不被看作单方面对真相的修正、对共同经验的重新阐释、自我辩解、个人潜意识的外化?我自己从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它们像一挂湿漉漉的蛛网,缠住写作者的心智,令我瞻前顾后,踯躅难行。而奥斯特通过书中之书《1967》提供了一种苦涩的慰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写下就是暴露自己,写下,然后被指认——这就是小说家的命运。每个人都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说故事的人对此无能为力。
反过来,对著书者身份的竞争——对讲述者、大写的“我”字的竞争——也一直是贯穿于奥斯特作品中的重要主题,比如《密室中的旅行》里的茫然先生、范肖、特劳斯(Trause,Auster的镜像?),比如《隐者》里的亚当和吉姆,波恩和塞西尔,当然,还有奥斯特本人。写作意味着主体性,而成为书中人物就是被客体化,被阉割,被没收存在权,因为在书页阖上的刹那,你就被迫噤声。
回应这一主题的作品可以回溯到乔斯坦•贾德《纸牌的秘密》、博尔赫斯《莎士比亚的记忆》、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在镜子背面的世界里,史上最帅的怪叔叔、萝莉控、摄影师、数学家、伪童书作者卡罗尔让红骑士和爱丽丝争夺做梦者的身份,因为做梦意味着存在,而被梦见者将随着梦者的醒来不可避免地销声匿迹。当波恩要求塞西尔以小说的形式代写他的自传,塞西尔的回答是:“我为什么会对帮别人写书感兴趣呢?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不过,谁知道呢,也许被关入白纸也并不那么糟糕,至少那儿存在一种表面的确定性,词语本身绝非隐者,而言辞之树常青。一如奥斯特所写:“作为另一种意识的臆造之物,我们将比创造我们的意识有着更久远的生命力。”

刘庆邦 著 《遍地月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小说写文革时期的农村生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普通人的戕害:少年黄金种出身于地主家庭,父母遭受批斗死去,金种与弟弟银种和叔叔黄鹤图生活在一起。他们生活在屈辱之中,随时都会被村干部、贫下中农欺侮。金种先后追求村里的两个姑娘,但是由于出身不好,到头来只是一场梦幻。换亲、逼婚、假扮夫妻,被毁灭的爱情、被扭曲的人生。爱情毁灭了,人生扭曲了,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隐者》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将吕柯弗隆的《卡珊德拉》从古希腊语译成法语的塞西尔。这篇晦涩的长诗也曾出现在奥斯特的处女作、半自传体的《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中:每隔一百年左右,神秘的罗伊斯顿男爵会在某人身上附体,把这首写于公元前三百年的古希腊长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一如卡珊德拉疯狂的预言永远没人相信,吕柯弗隆疯狂的作品也永远没人阅读,“于是这是项无用的任务:写一本永远合着的书”。罗伊斯顿男爵的幽灵在《隐者》中附身于一个孱弱、神经质、落落寡合的天才少女,塞西尔身上有种奇特的悲剧性,她平庸的结局比亚当的更令我难过。吉姆如此评价晚年的塞西尔:“尽管她在狭窄的学术研究领域是个成功者,她一定明白她为自己选择了怎样一种奇怪的生活:禁闭在图书馆和地窖的小房间里,埋头于逝者的手稿,一种在无声的尘埃之领域里度过的职业生涯。”永远在一盏孤灯下翻阅古卷的现代隐士,这正是奥斯特长于刻画的那类人。虽然生活在此世,他们的心智更贴近中世纪修院的缮写室。
一如奥斯特笔下所有那些沉默的译者——无论是《幻影书》中翻译夏多布里昂《墓后回忆录》的齐默,还是《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和中靠翻译维生的A,或是《隐者》中翻译普罗旺斯诗人贝特朗•德•波恩的亚当。作为抵御或者维护孤独的工具,翻译是一项将我们拉近地面的活动,一种谨小慎微、耐心而谦卑地把握世界的方式,能够赋予我们可贵的安心。
《隐者》是我翻译的第一本奥斯特小说,也是我最享受其翻译过程的一本小说。充盈于全书中叙事的暗面、意象的环形山、可能性的滑动门虽然赋予了《隐者》更加轻捷的结构,呈现在其中的却是一个变重了的奥斯特,一个和以往不一样的奥斯特。但愿读到这里的人们会如我一样地喜欢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