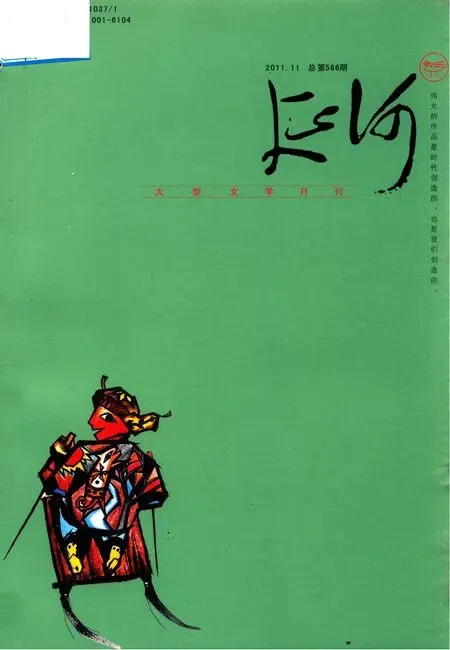贴着人物游弋:《古炉》的语言艺术
刘秀丽
贾平凹的《古炉》甫一出场,就在评论界受到欢迎,这当然与作品文革叙事的主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古炉》主题的探讨、解析与臆测一时成为文学评论的热点。然而,对文革的回忆与叙事并不算少,《古炉》的独特在于它既没有宏大叙事的野心,也没有义愤填膺的偏激,作者只是选取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乡村,截取了文革酝酿和发轫期的一年半时间,建立起叙述的时空坐标系,不疾不徐地展示文革在中国底层社会的燃起。正如这本书的推介所言:“作者用真实的生活细节和浑然一体的陕西风情,将中国基层‘文革’的历史轨迹展示在读者面前。”《古炉》的精彩之处不在文革轨迹,而在充满陕西风情的艺术世界中,在古炉村,在那群命运急促变换的乡民身上,在山坡上几百年的老白树上,在河里昂嗤鱼的叫声中。
《古炉》延续了贾平凹一贯的语言风格,流畅而简洁,阅读起来非常舒适,仿佛一叶扁舟滑过平静的湖水,又如指尖穿过女子的秀发,没有阻隔,没有牵扯,流利顺滑。这种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不是少年的轻快和跳脱,而是中年成熟的开合有度,作品不是随着作者的驾驭,而是随着人物命运的发展逶迤前行,它让读者忘记作者的存在,而仅是关注作品本身,关注作品中的人物,这样的语言像沈从文所强调的,是“贴着人物写”。《古炉》贴着人物写,不仅表现在人物的话语特别是对话符合特定身份,表现在人物的心理描写行动描写等贴切准确,而且表现在根据人物确定环境描写的乡土与神秘两种气质。
一
语言作为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独特存在,是展示人内部世界的窗口。语言的迂回与直白,浅近与深邃,生动与干涩,华丽与素朴,往往体现说话者品格、性格与气质的不同,一种语言就是一种人。《古炉》中的人物多集中生活在同一个小村子,人物语言有相似性,贾平凹试图寻找每一个人物语言之间的细微的差别,从而展示语言背后人的差异。善人和婆同为村子里善良而神秘的长者,同样是对人的劝说,善人和婆说出来的话迥然不同。“善人说,人落在苦海里,要是没有会游泳的去救,自己很难出来,因此我救人不仅救命还要救性。救人的命是一时的,还在因果里,救人的性是永远的,一救万古,永断循环。人性被救,如出苦海,如登彼岸,就不再坠落了。”这是讲道的方式,是一个接受过教育、领悟了大道的人才可能有的语言,他讲的道理狗尿苔这样的孩子常常听不懂。婆不会这种方式,她也说不出来,婆的话是粗糙的,质朴的,是古炉村人人懂得的。
人物的对话,由于存在着交锋和碰撞,更能够体现对话双方每一个个体的特殊性。倘若要体现人物的性格差异,就让具有类似身份的人物对话,在相似性中寻找那一点不同,这样,就像被显微镜放大了一样,“不同”就显得十分突出。狗尿苔和牛铃都是孤儿,年龄相仿,是一对好伙伴,一窝老鼠不嫌臊,就算有时候闹矛盾生气了,二人也还是彼此惦着对方,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呢?狗尿苔和牛铃提死老鼠被天布媳妇骂了,树棍儿也被拿走了,二人很生气,“狗尿苔说:她拿了你的棍儿。让蛇钻进她家院子里咬她去。牛铃说:钻进她裤裆里咬她。”都是说气话让蛇去咬天布媳妇,可是牛铃就凶狠得多,他的话让人一下子想起古时妲己的做法,不由背冒冷汗。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口中,一个没有父母而是被古炉村的大人们调教出来的孩子口中,古炉村的性与情也就可见一斑了。牛铃身上体现出的使强用狠、咬牙切齿,与霸槽身上的那一股蛮力与狠绝如出一辙,和古炉村人分成两派发生械斗的残忍又有多少差别呢?谁能断言,在古炉这个村子里泡大的牛铃不会成为第二个叶霸槽?与之相对,狗尿苔身上沿袭了古炉的另一种风气,自婆一脉传承下来的善良与隐忍之风,这种风气在善人身上有,在婆身上有,在杏开身上有,在戴花身上有,就连霸槽和天布的身上也偶尔流露出来。使强用狠是一面,是显露的,一触即发的,却也是非常态的,短暂的,善良隐忍是另一面,是隐蔽的,慢火烘焙的,却是常态的,恒久的,是古炉村的希望和底蕴。这是孩子,再来看古炉村大人们的一段对话:扬麦要乞风,让狗尿苔当圣童,“场边的麻子黑说:他当不了圣童么,出身不好能当圣童?!田芽说:你见过天下雨有没有把四类分子的自留地空过?”一人仅一句话,呈现出古炉村显与隐的两种品格。田芽的一句话是古炉村底子里的善良隐身的体现,麻子黑的一句话中则折射出对一个孩子的不宽容、不接纳,将这句话做为他后来性格与行为的铺垫来看,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他能够投毒杀人越狱,能够直接在人肉上别毛主席像章,能够成立一个人的刺刀见红造反队等等行为了。

李樯摄影作品·北方风景系列 青海鸟岛 2006年
二
通过人物的语言特别是对话,《古炉》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秉性,而这两种秉性都是古炉村自有的性格与品质,是古炉村民的性格与品质。除了人物语言,在心理描写、行动描写等各种人物描写手法上,《古炉》也试图贴着人物来写,让小说的语言跟着人物走,符合人物的特定身份。
小说写到霸槽消失了一段时间再回村子里,没有人理会它,只有支书一个人心情大好,“开了院门,等着霸槽来。他把墙上挂着的烟叶串取下来,拆开,一叶一叶铺在水桶旁的湿地上阴软,然后抽去烟筋,用剪刀铰成细丝,还喷上酒,滴了香油,窝在烟匣里。”这样的动作和细节,符合一个十几年掌管整个村庄命运的村支书形象,读者能够想象老支书意满自得的模样,能感受他驯服霸槽的踌躇满志,甚至能够联想到他必得先清清嗓子再开始训斥,训斥的语气必定是痛心疾首与语重心长相掺杂,高潮的时候会把烟袋敲在桌子上。
小说中另一处写到在大环锅里煮太岁肉丁,香气弥漫,“这种香味谁也没有闻过,像是槐花香,又像是板栗香,还像是新麦面馍才出笼的香,说是哪一类香好像都不对,是一种花的板栗的麦面馍和青草的,雨后田野里翻出的土,麦草集下那些甲虫,甚至还有擦黑做饭时站在巷道里那种烟的呛味,这些东西混在一起,说不清成了什么,就是只觉得奇异的香。”长期处于不温不饱的状态,古炉村民们自然对吃特别敏感,槐花、板栗、新麦面馍,他们的联想只能和基本的吃食有关,和他们的村庄有关。要是作者写他们能够联想到玫瑰花,联想到别的什么山珍海味,那自然失了真实,会引起读者的质疑。
小说中写到婆看见人家屋檐下的冰锥往下落,“她几次站在那儿想:这些冰锥是从天上刺下来的,它悬在各家墙头的瓦棱上,像她在县城经过监狱时那些棚栏门口的铁棍,铁棍上都是矛子一样的尖”。这是非常精细而准确的比喻,最要紧的是“她在县城经过监狱”,若没有这几个字的交代,而直接写“像监狱棚栏门口的铁棍”,就会让人怀疑一个农村老太太怎么会知道监狱门口什么样?只是几个字,增加了真实感,读者对作者和作品就增加了一份信赖。
当然,《古炉》在对人物的描写上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有些笔墨还不够精细。小说的一开篇狗尿苔说闻到怪气味儿,婆怀疑他是不是鼻子烂了,“狗尿苔的鼻尖被掀起来,鼻腔里都好,婆擦了一把鼻涕,揩在鞋底上。”前文并没有明写或者暗示狗尿苔有鼻涕,掀起鼻尖的动作也不会产生鼻涕,那为什么婆要做这个动作?是作者主观上意图通过将鼻涕揩在鞋底上的动作展示彼一时代农民的形象!毋庸置疑,那个时代甚至今天仍有许多农民保持这样的习惯,这个动作也确实能够生动鲜活地展示婆这个人物形象的农民身份。可是,一类人物可以有一类动作,他却不一定非要做这样的动作。毫无必要的动作,做了反而画蛇添足,人工的痕迹太明显,文章就显得矫情!文中另一处,狗尿苔被买磁货的人称为“特色”,他很生气不理人家,转过身“却看到霸槽重新坐在小木屋门口的钉鞋凳子上,戴着墨镜,样子像个熊猫。”这是谁的视角呢?狗尿苔吗?他知道熊猫什么样吗?从下文看,狗尿苔除了对村子里的人情世故知道一些,其他知识都懵懂得厉害,他知道熊猫的可能性不大。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隐藏在狗尿苔背后的作者现身了,代替了人物的视角。
在评论当代作家叙事伦理的时候,谢有顺先生认为“中国当代活跃着太多‘知道’的作家,他们对于自己笔下的现实和人世,‘知道’该赞颂还是该诅咒;他们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也‘知道’该为他庆幸还是悲哀。其实这样的知道,不过是以作者自己单一的想法,代替现实和人物本身丰富的感受而已。他同时赞赏贾平凹是一个不怕不“知道”的作家。确实,贾平凹之前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废都》,都更好地将作者隐匿起来,让人物自己说话、自己行动、自己思考、自己选择,但在《古炉》中,贾平凹时不时走到了“知道”太多的路径上去。孙郁在谈到贾平凹后期作品时,认为它们“都有一点‘做’的感觉,不像散文那么自如。”“就作品的影响力而言,忘我的时候往往很好,自我意识多了,反不及先前了。”小说固然要经营,有技巧,但要不留痕迹,藏巧于天然之中,要贴着人物自由游弋,而不是牵着人物拽他走。在这部小说里,可以看到贾平凹忘记作者、随着作品中人物自然走笔的努力,不过当他偶尔想在作品中卖巧的时候,反而弄巧成拙,失却了那一份笔调的流畅与自然。
三
环境是人物生存的土壤,环境描写是否成功,关键就看这个环境是否适合作品中的人物生存,把人物安放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否具备合理性。《古炉》塑造的是一批生活在小乡村里的农民,因此,就需要营造一个适合农民生活的环境,这个环境要能够安置农民的身体与心灵,它应该是乡土的,既要符合六十年代农村经济水平,也要符合陕西一地特殊的人情风貌。作品中,这个具体的环境就是古炉村,贾平凹赋予了他的古炉村两种气质:乡土和神秘。
对比《废都》所营造的环境,能够更好地理解《古炉》环境描写的乡土性。在《废都》的男性人物形象中,四大闲人都是文化人;女性人物形象中,大部分都是具备一定文化修养的,如牛月清、景雪荫,文化层次不高的女人们如唐婉儿和柳月对文化界持仰视的态度,她们把庄之蝶当成精神偶像来崇拜,当成心目中的文化符号。综上,《废都》是知识分子之书,写的是知识分子的颓废,小说人物生活的环境西京自然应充盈着文化氛围,不管是夜晚城墙的埙声还是老头子的歌谣,整个西京流淌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沧桑,那是文化余韵失落、精神世界坍塌之下的废都的苍凉。而《古炉》呢?古炉村中最有文化的也只是中学生,大部分村民要么不识字,要么不识几个字,上过小学的水皮都能算是古炉村的文化人,古炉村人多没见过大世面,常年在古炉一村生活,顶多去个县城。刻画这样的人物形象,人物生活的环境古炉村当然和西京不同,《古炉》的语言感觉和《废都》也是迥异的。
看看作品中的人名:狗尿苔,牛铃,天布,霸槽,杏开,田芽,灶火,护院,面鱼儿,秃子金,单看这些人物的名字,既有来自乡野的村味儿,符合农民起名字的质朴与随意,又夹杂着陕西一地独特的风物在其中。看看一年半以来古炉村都干了些什么:春天耕种秋天收获,夏天除虫冬天夹柿子,就是分成两派大打出手,磨子也还是带着大家去地里干活,生病了要吃簸箕虫,被马蜂咬了要糊鼻涕,农闲了在家里铰花花。这是实实在在的农民的生活,在“革命”的变态情形之外,这些拉拉杂杂的琐事才是一个村庄生存的常态。这就是古炉村人生活的地方。
古炉村人看天气:“太阳虽然还在天上,却是一点屁红的颜色,嘴里哈出的热还是一团一团白气,每个嘴都哈了,白气就腾腾起来,人像揭开了锅盖的一甑耙包谷面馍馍,或者,是牛尾巴一乍,扑塌下来的几疙瘩牛屎。”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断然看不出太阳是“屁红”的颜色,断然想不到冬天嘴里哈出来白气的人脸像包谷面馍馍,甚至像牛屎,就算想到了,也鲜有这样表达。古炉村人说话:“秃子金说:今冬州河里的红鱼少得多了。他的话没人接,落在地上就没了。”说的话也会落在地上没了,这当然只能是乡土世界的表达,是都市文化经验者所不擅长的。城市的语言更接近所谓的“文明”化,儒雅化,贾平凹不喜欢这些。“他似乎越来越远离士大夫的儒雅的一面,不放过那些黑色与龌龊的存在,而且对此还津津乐道。”(孙郁:《汪曾祺和贾平凹》)这样,他用自己看起来粗糙的甚至是鄙俗的话语模式,建构了与这种语言气质相同的乡土世界。
对于乡土描写而言,乡土性不仅是某一个词语,某一个人名或者地名。它可能体现在细节处,“从日常细节之中发现各种因素的冲突、搏斗和相互制约”,从而“真正地描绘出历史演变的细致纹理”,但绝不完全如此。它还应该是通篇文章所营造的一种整体感觉,是一种强大的气场,像一团雾气一样和作品融为一体。贾平凹在《古炉》中所营造的乡土环境便不仅仅是在细节处,他已经形成了自己乡土描写的风格和气场,当乡土描写越来越成为贾平凹作品的一种格调时,他的语言和他所描写的内容也形成了同一种风格——乡土化的语言。这正如爱德华•萨丕尔所言:“最伟大的(不如说最叫人满意的)文学家,莎士比亚和海涅们,下意识的懂得如何把深藏的直觉剪裁得适合日常语言的本地格调。”(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
神秘性是贾平凹环境描写的另一语言特色。樊星在《当代陕西作家与神秘主义文化》一文中较为详尽地梳理过贾平凹多部作品的神秘主义脉络,《古炉》可谓贾平凹作品神秘主义脉络上又一条喷张的血脉。
《古炉》中,神秘性首先体现在“有情”上,鸟木虫鱼是有情的,古炉村的一切生物都是有情的。霸槽打了杏开一巴掌,狗尿苔自己很生气,“他同时听见夜地里所有的东西,蒿草,土堰,土堰上爬出来的蚯蚓,河里的水,石头,昂嗤鱼,以及在远处逃窜的一只野兔正跑着站住了,回过头,全都在愤怒地声讨着霸槽。”最有意思的一段,姓朱的说姓叶的是六畜,给霸槽、秃子金他们按狗鸡猫蛤蟆长虫来定位,结果“村里的猪狗鸡猫都不愿意了,猪便不再吃食,鸡不下蛋,狗不护家撵猫,牛在牛棚里成夜叫。”古炉村是个有情的世界:人无情,物有情。
古炉村有几个神秘的人物:狗尿苔、婆和善人。狗尿苔相貌奇特,能够听懂动物的语言,后来他发现自己还能够听懂植物说话,甚至听见风雨说话;狗尿苔的鼻子能闻到奇怪的味道,他一闻到怪味,古炉村就会有灾难。婆会绞花花,用树叶、用纸、用布等各种材料,婆懂得各种红白喜事的来龙去脉,甚至还能看个小病小灾,婆是古炉村的长者。善人则是古炉村的智者。善人博学、善良,内心强大,重要的是他会说病,不管是身体上的病还是心理上的病,善人都能够找到病源,开出方子,善人为了山顶一棵几百年的老白树被砍而自杀了:善人的一生都是个传奇。
古炉是一个现实的村庄,但又掺杂着许多神秘的力量,现实的世界在一般村民眼皮底下展开,神秘的世界在村庄、在狗尿苔的眼皮底下展开,村民的世界与村庄的世界不同,有现实古炉村才得以存在,有神秘古炉村才显得独一无二,二者交融着构成了真实、立体的古炉村。有了这样神秘而乡土的古炉村,才能够生养一方百姓,形成《古炉》里异化与常态的村民。能够营造这样的村落,是因为贾平凹的文学视野不“光局限于人的视角”,他还“从佛的角度、从道的角度、从兽的角度、从神鬼的角度等等来看现实生活”,用多维视角看待生活,生活成了万花筒,更加丰富和多彩。(贾平凹:《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而文学作品指向一个神秘的精神所在,才不会干瘪无味,才能够丰富、有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