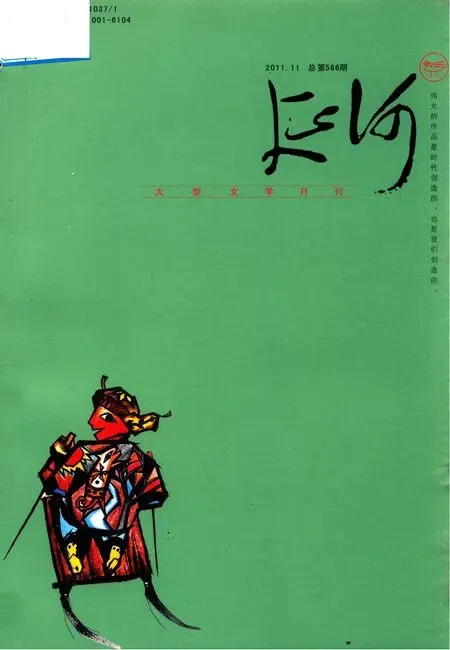父亲影像:蛰伏在旧片上
赵钧海
一
没有赶上父亲出殡,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瑟缩在腊月的飘着飞雪的大漠小屋里,我头脑嗡嗡嘤嘤鸣响着,满眼泪翳。我用拇指在手机上摁出了内心最悲戚的文字,传向四千公里外已回到父亲身边的妻子和女儿。那篇追念文字是由女儿代我陈述的,她哽咽的声音通过冥冥天穹又传回我耳边。它是我的心音,也传导了与我一样的悲悯、绝望以及天崩地裂般的凄冷。
如今,站在没有父亲身影的家里,我觉得一切都虚假和惶悚。呆立着,我恍惚又觉得,父亲似乎还在,肯定就蹒跚在为我买早餐的路上——那是一种被称为“果子”的油饼;或者就守蹲在楼下炉灶旁煮稀饭,用手轻轻搅着饭勺;或者正用火钳往炉膛里添加蜂窝煤,炉膛里升腾着暗红的火焰。
这种意象纠缠着我,啃噬着我的灵魂,使我无法安宁。母亲一边哭泣一边叙说着父亲临终的细节,我感觉那就像一部遥远的天书,冥冥地挂在萧索的天上,闪着冷寂的光,不能亲近,不能交流。
二
坐在老旧沙发上,我翻出了父亲遗存的照片——那些被称为遗像的东西。它们被父亲用报纸包裹在一个隐秘的空间里。它们是一叠伴随我出生、学步、启蒙的照片,它们隐匿着我五十年的幸福与欢悦,也隐匿着我肉体生长与灵魂洗练的微妙过程。年代久远,它们斑驳而黄旧。我熟识它们的一切。只需轻轻一弹,它们就会还原那些曾经的色彩,漂溢出那些缱绻的亲和之音。小时候,我经常盯着照片遐想,企图发现藏匿在影像背后的清新与私密。

李樯摄影作品·北方风景系列 陕西定边 2000年
最早的一张已十分黄旧,背后标有“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字样,是三寸黑白照,也是拍摄于照相馆的正规照片。站在照片里的青年军人眉清目秀,肤色细润,脸颊泛着柔和的肉质光泽,自信,青春。我想,它可能是用当年的修相技术在底片上加工后洗印的,不然不会那么清晰那么层次递渐,反差适中。青年军人身着老式棉军服,侧身而立,双腿呈微叉状,显示着男子汉的威严与顶天立地。军人最英武的一面被摄影师表现得淋漓尽致——那老式棉帽上的“八一”五星和左前胸“中国人民解放军”标牌,都炫示着那个年代边防军人的潜在自豪。我想,也可能它是一幅临时而为的照片,因为青年军人穿的是一身旧军装,那肥大宽松的棉衣上,有无数横竖交织的褶纹,并且极深,尤其那膝关节拐弯处,更是交错纵横,如若没有脚上锃亮的黑皮鞋映衬,就无法辨认出是一位军人,倒像个地道的农民。是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解放军大多都来源于农民,他们都是从烟雾弥漫的战场的尸体中长起来的农民军人。他们用拿锄把的手掀翻了蒋家王朝的病体。
照片上的军人不是我父亲,他应该是父亲的亲密战友。我想。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是他与父亲分别的日子。他转业了,退伍了,复员了,也可能调走了,总之,他留下这张三寸全身像。他把他自认为生命中最得意的形象留给了父亲,希望父亲铭记他。
父亲显然做到了。除了日期,父亲还用钢笔写下“摄于伊犁惠远古城”的字迹。这是父亲刻意记下的,它潜伏着深邃又多重的意味。惠远,那是一个在大清王朝乾隆年代就设置有军队的边陲重镇。父亲在那个叫惠远的地方镇守边关十六年之久。清王朝时,惠远曾经是著名的西域首府,设有正一品高官——伊犁将军。它一七六三年兴建于伊犁河北岸,是乾隆亲赐的地名,取大清皇帝恩德惠及远方之意。林则徐和左宗棠就曾被惠及到这里。小时候看赵丹演的电影《林则徐》,结尾时林则徐凛然地走向西方。父亲说,林则徐就到我们惠远来了。我惊讶地问,林则徐住哪栋房子。父亲说,在东街。我就偷偷去找过几次,试图找到林则徐的只鳞片爪。我很徒劳。父亲在苍凉邈远的惠远十六年当中,从机枪手、炮兵班长、排长、连长一直干到营长,直至一九六五年离开。我清晰地铭记着那些依旧灵动的岁月,它像天幕一样印刻在了我幼稚的虚怀之间。
这个站立的惠远军人,我并不认识。一九五二年还没有我。我设想着他与父亲一同站岗的细节。父亲那时已经是排长了,不过父亲扛机枪摆弄子弹的经验却来自这个清秀的老战士,他曾教给父亲一些动枪的细节。在惠远那个天寒地冻的早晨,他们出操了,老战士说,带上手套,不然钢壳就会粘掉手指的肉皮。老战士说得很随意,却充满真情。我想,这个老战士也许姓章,也许姓欧阳,也许姓郗。总之他成了一个谜。从黄旧的相纸与退了色的笔迹分析,他与父亲有一种刻骨铭记的关系。也许就是他救过父亲的命。父亲曾说,解放兰州战役中,在祁连山的某个断崖上,父亲的腿曾被子弹打过两个窟窿,是一个姓郗的战友背他下的山。也许他就是那个姓郗的老战士。
三
父亲也有一张那个年代的青年免冠照。二十郎当岁的父亲样子挺可爱,阳光,帅气,浓黑的头发像焗过油一般。当然,那时父亲不可能焗油。——父亲的头发在他七十六岁时仍然是全黑的,它让我很蹊跷。我在四十二岁那年鬓角就开始变白,我非常窝火,我不知道我的头发为什么没有随父亲。父亲的浓眉呈大刀状,眼窝有些微微凹陷,刚毅,智慧,英俊。我小时候看父亲这张照片,脑海里总会冒出一个“英俊”概念——父亲多英俊啊,我会这样自言自语。那时我八九岁,知道一个叫王杰的解放军战士、一个叫刘英俊的解放军战士和一个叫门合的解放军教导员。部队大院的孩子知道最多的当然是部队的事。王杰身扑炸药包救民兵牺牲了,刘英俊拦惊马救孩子被炮车压住牺牲了,门合为保护群众也扑到炸药包上牺牲了。我被他们的事迹撼动着,也时刻想为人民献身。我这点高远又傻气的想法,隐藏在心底许多年。我认为刘英俊的形象洒脱英俊,与他的名字和英俊的外表很吻合。而王杰就没有那么英俊,虽然他也是英雄和榜样。门合没见过照片,不好评价。——这又是我一个无知童孩不洁的想法和低级审美观。但我觉得父亲很英俊,他一点不比刘英俊差。父亲只要站在一群军人中间,我总能第一眼认出他,他不仅高大魁伟勇武,而且英俊。那时我经常会长时间地看父亲的照片。父亲在合影集体里,炫亮,夺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韵和气度。
写有“一九六三年八月”落款的照片也是父亲的笔记。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他的所有文化都是十八岁参军后在部队学的。那时父亲在野战军第六纵队的第一线,参加了西府陇东战役,后来跟随彭德怀司令员参加了扶郿战役,歼灭了胡宗南部,又攻打了兰州。父亲常说,部队是个大火炉,是熔炼人的地方。那一年,父亲的军衔是大尉。——看到照片,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当年的样子。那是一帧七人照。父亲在前排坐着,表情定格在抿嘴即将大笑的一瞬间。那个瞬间定格了父亲许多内涵。英俊、硬朗、活力、健康、磊落。夏日正午的树荫下,一位军报记者在采访父亲的模范连,父亲作为一名炮兵连长,带队伍很有一套。记者认为还需要一张连队首长的集体照。这个七人照片上,另有两人与父亲的表情一摸一样,也定格在同样的抿嘴表情上。我猜想,他们和父亲一样,是被军报记者逗乐了,但并没有笑出声来。他们也同样充满阳光,充满爽朗。他们俩军衔分别是上尉和中尉。当年我甚至能叫出他们的姓名,但现在一点想不起来了。照片上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七人中有五人的军帽色泽已退成了白色。那是伊犁盆地夏日酷暑暴晒的结果。父亲的军帽当然是最白的那一顶。因为父亲常年带战士在野外训练,摸爬滚打,上哨卡,种地,甚至长途拉练。那时父亲常常不由自主地哼一支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歌曲。父亲认为毒烈的太阳只能烤白鹅黄的军装,却烤不白他健壮而透红的皮肤。白色军帽意味着父亲是一位勇武且吃苦在前的典范连长。
四
“分别留念”的照片最多最抢眼。它们一张张叠加着,被留存在了纸包深处。其实那一瞬间,它可能就阐释了它的主人将永远不会再出现再见面的现实。那是一份痛苦永别的留念。他们都是父亲的战友或士兵。他们来了,他们又走了,只留下了身影,只留下了回忆。他们是陕西人,山东人,甘肃人,河南人……他们或许是从最贫瘠的黄土坡梁走来,或许是从沂蒙山区的沟壑里走来,或许是从华北平原的小村庄走来的。他们服役,扛枪打仗,也学文化学做人,并且成长了。但他们又该走了。他们就是古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践行者。
一九六五年的照片居多。这一年父亲调出来原来的部队,被安排去组建一个新的炮兵单位。今天我无法揣测父亲当年的心态——新的环境将如何面对,又如何适应?但父亲服从了组织,只身一人调到了完全陌生的新兵营。于是,战友们就纷纷给他送照片。他们是一起摸爬滚打过多年的战友。
照片背面的文字都十分简练。主题直奔主人心境,虽然字体字迹各不相同,但真挚,怀旧,温馨。——“送给老首长赵副营长留念”“送给敬爱的首长分别留念”,“送给亲爱的副营长留念”,落款分别是“你的战友陈恢白”、“你的战友黄锡安”、“战友王应栋”、“战友闫明义”、“战友康炳南”。
留念,留念,分别留念。留念就是留下念想。这个念想可能今生今世就只是念想了。从此天各一方,再不相见。以当年的交通条件,父亲的新兵营距离老兵营一千多公里,分别几乎就是永别。军旅生涯就这样冷酷,你必须在变幻和不确定中适应这种人生的变数。父亲说,我适应新环境能力很强,请首长放心。看着照片,我恍惚又听到了父亲极富磁性的声音。父亲的嗓音洪亮、清脆、磁性。我认为我的长相不像父亲,但我的嗓音却酷似父亲。这是我最骄傲和自恋的资本。很多次打电话,总有女士说,你的嗓音很磁性,很有男人魅力。有一位美女作家曾说,你的声音太男性了,我很想见见你什么样?然而,当我们真的见面后,她却没有提此事,好像早就忘在脑后了。我挺失望。不过,我为有父亲这个特别遗传而庆幸。
父亲的声音会传导得很远。我曾多次在数百米之外就分辨出父亲的咳嗽声。我对母亲说,爸爸今天要回家。母亲愕然地看着我,以为我在说胡话。果然,十分钟后,父亲就进门了,带回一股热气腾腾的暖意。那时父亲通常住连队,很少回家。他每晚要查房,查岗,甚至给战士掖被角,盖大衣。虽然我家也在营区内,但父亲最多两周回一次家,而且夜里很晚很晚才回来。那时没有双休日,也没有长假。自我记事起,父亲就很少在家吃饭,一日三餐都在连队。
五
一九六八年是奇特的一年。这一年父亲经历了两件大事。那同样是两张极有分量的集体照。父亲后来常常会端着小酒杯回味那一年的往事。父亲啧啧地喝着酒,利落地夹菜,利落地送到嘴里,然后就有很响亮的抽筷子尾声,让人觉得他的饭很香。我曾许多次屏息静气观察父亲的这个举动,企图效仿一下,但总也没有那种愉快的尾声。父亲即便是吃最家常的萝卜白菜,也会如此这般地让人羡慕。
第一件事是父亲见到了毛泽东。那一年我十岁,清晰地记得父亲回家的兴奋与欢悦。父亲说着在北京的感受,如一个童孩。父亲说,毛主席魁伟高大,精神抖擞,脸上放着神采。父亲还说,林彪就没有那样的气度,不过他打仗还行。父亲说这话时就吃着土豆丝,味道很香的样子。我们——母亲、我、大弟、小弟就很崇拜地盯着父亲的嘴。那一年,“文革”进入了白热化程度,也是最波澜壮阔和汹涌澎湃的一年。林彪别有用心地推崇着“万寿无疆”的把戏,形成了一种山呼海啸的气势和模式。我在纪录片上经常看到那种沸腾场面。我激动万分。后来父亲又数次给母亲和我复述过北京细节,也多次重复过一句话:主席真是一个伟大的人。我知道,父亲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父亲从来不表扬人,包括对上级首长,也不阿谀奉承。那一年是父亲作为部队团以上干部代表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的。从北京回来后,全师受接见代表在乌鲁木齐“八楼”合影留念。“文革”期间,“八楼”是新疆第一高楼,也曾经有许多年,它一直占领着新疆楼房的最高点。那是一幢庄重威严又令人敬仰之楼。歌手刀郎后来唱过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叫《二00二年的第一场雪》,里面提到了“八楼”,如今它叫昆仑宾馆。虽然,如今它早已被林立的高楼所湮没,但威严依旧。后来,我几乎年年来这里开会,我不叫它昆仑宾馆,仍然习惯叫它八楼。
父亲站在第三排靠右的位置上。在百名军官队伍里,父亲很醒目,很英武。我一眼就能找到他的身影,也一眼就能看懂他的内心世界。虽然照片上也有许多我熟知的军官,他们大多是我同学的父亲,但我总觉得只有父亲光鲜,俊朗,骁勇。草绿的军装笔挺着,帽徽闪着熠熠的亮光,它们衬托出的是父亲独特而别有一番滋味的风韵。父亲头顶是一幅抢眼的横幅,写着黑体白色美术字——“最最幸福的时刻,我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1968年8月11日16时”——多年后,我偶然翻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典》一书,“文革”军史大事记一章里说: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解放军六地区陆海空三军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全体人员。大典上还说,这一年,毛泽东分别接见过三次军队干部,总人数超过五万。我想,毛泽东这一年太辛苦,日理万机不说,还三次接见几万干部。我十分羡慕和敬仰每一个在天安门广场热泪盈眶的人。父亲见到了毛主席,就像我也见到了一样,十岁的我感觉很得意很幸福很傲慢。毛主席不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我为有这样一个光荣的父亲血液沸涌了很久。
父亲从北京带回了我终生难忘的两个记忆。一是北京特产“茯苓夹饼”,二是北京故宫紫禁城。茯苓夹饼是一种薄纸一样的食品,中间夹有一种深褐色甜软食物,很特异,很好吃。那是一种可食的“纸”。我品尝它奇怪的“外衣”,也记住了它的奇妙的名字。长大后我只要到北京,就会购买这种可清火、可明目、可明智的食品。二OO六年冬天,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会后抽两天回河北看望父亲,还专门买了几盒茯苓夹饼。
我说:爸,我们第一次见到它,就是您一九六八年带回新疆的。父亲笑着说,是啊,三十八年过去喽,现在我传给你啦。我说:您曾经说,这物件能通气,活血,理气,明智,是好东西。父亲说,是吗?我真的说过吗?我说,是,不过现在包装好看了,可味道不如从前好吃了。父亲拿了一片茯苓夹饼,品吃了一会儿,才说,对,好像味道不如从前了。
听父亲说故宫,对于我这个视野仅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圹埌之地的孩子来说,简直就像听天书。父亲一边吃着苞谷面发糕,一边对母亲和我说,故宫里很大,一天也走不完,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有乾清宫、坤宁宫、储秀宫,是过去皇帝、皇后和妃子们居住的地方。我无知而惊讶地问父亲,什么是妃子?父亲停顿了一下,说,就是皇帝的小老婆。我似懂非懂,老婆就是老婆,难道还有大小之分吗?不过我没有打断父亲对天堂的描述,我只是在自己心中营造了一个奢华皇宫里烟雨缥缈的故事。我想,这辈子我也要去故宫看看,看了我就知道是多大的房子,需要一天还走不完?也就知道什么是小老婆了。父亲还告诉我们一个细节——故宫是从天安门城楼的大门进入的,我惊奇无比。——天安门不是毛主席接见人民群众的地方吗?怎么是古代皇帝的宫门呢?天安门这个辉煌而崇高的地方,是祖国心脏中的心脏,如一片虹霓,高高悬挂在我的心头。毛主席就站在城楼上挥手指方向。可我没想到,它居然是过去昏庸腐败帝王的家门。我悲哀了很久。——这就是我这个洪荒、封闭年代孩子的可悲之处。这个可悲的疑问曾经潜伏我心底许多年,如同一个死结。
一九六八年,父亲的另一件大事,也是让我自豪一生的大事,这一大事载入了父亲彪炳史册的经历,也是我对父亲仰慕和折服的另一个精神亮点。这一年父亲受命到一个叫精河的天山北坡农牧业县“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父亲“军管”了精河。父亲准确的职务是精河县革委会主任。那一年父亲三十八岁。现在想来,他太年轻了,也太稚嫩了。妻子说,我印象电影电视剧里的革委会主任都是那种很坏很狡诈的人。我说,那是他们瞎胡扯,那时还有很多忍辱负重的好干部。县革委会主任相当于县长。那照片是一张九人集体照,是当年革委会班子成员的集体照。
隆冬时节,父亲与其他革委会成员身穿五花八门的皮大衣、棉衣,头戴棉帽子,也分别是那种栽绒的、狗皮的、羊毛的。只有父亲一人是戴领章帽徽的军人。父亲身穿棉军服,整洁,威武,从容,洒脱。我以为父亲真正洒脱的标志就是棉军帽。那是一种羊皮制作的棕色皮帽,羊绒蜷曲着,呈现出温暖柔顺的样子,很像一个保暖的小火炉。这种棉军帽,我曾经戴过多年。我们野战部队军人子弟在小学时就开始享用这种特殊用品了。那时天山北坡的冬天异常寒冷,大院里的孩子们都会使用父亲们积压节省下来的棉军帽、棉手套和大头鞋。那时这种福利也是我们唯一可以享用的优厚待遇。年年冬天,我们数十个孩子们就穿戴着它们,玩打仗,打尜尜,滑冰,或者去红柳梭梭林里打柴禾,套野兔。那时野战部队的物品是地方老百姓最羡慕的高档奢侈品。我曾经偷偷用一双军用皮手套换过一个爬犁和一只野兔。我始终未敢把实情真相告诉父母,那也是我迄今为止犯过的最大错误。爬犁和野兔都拿回家了。我和两个弟弟坐爬犁在雪野上奔跑撒欢,然后就吃母亲做的野兔肉,那野兔肉与鸡肉同煮,味道十分鲜美。至今我仍然能回味起当年我饕餮野兔肉的情景。
那时,北疆冬天的积雪很厚,雪没膝盖是常有的事。用爬犁滑雪就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父亲的大皮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显得很松垮,动不动就遮挡住双眼的视线,我于是就有一个上推帽子的习惯动作。那动作后来多年不改,戴单帽子也会不由自主地做。不过,我没有不适的感觉,我觉得我的棉帽子很合适。那时小孩们还会互相攀比帽子质量的好坏,说谁的羊绒顺溜,光滑,谁的羊绒龌龊,肮脏。滑雪滑热了,我们就摘下棉帽子,于是就有一股热腾腾的水汽氤氲地在我们头顶升起,如一个烟囱,白晃晃的阳光射洒在雾气上,如一条升腾的白霭在头顶漂移,很是艳美。
那个冬天,父亲就一直在那个叫精河的县城忙碌着,春节也没有回家。虽然我家距离父亲的县城仅仅一百多公里,但父亲就像进入了痴迷状态一般,忙碌着,总是说在组织“两派”群众大联合;总是说在访贫问苦;总是说在安排知青到村里插队落户;总是说在修一条叫南干渠的引水大渠。
寒冷的十二月八日,精河县城广场聚集了数万群众,父亲的忙碌有了成效。精河县开始欢庆“两派”群众实现大联合——“革委会”正式成立了。父亲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那时,“革委会”均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而成。它取代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县委和县人委的职权——那是由“文革”的“动乱”走向好转的重要一天。现在看来,它可能还藏匿着诸多的瑕疵和可悲可叹之处,但它却带有那个时代的不可磨灭的光点。父亲夜以继日工作的回报是——头发莫名地脱落。当我在十个月之后见到父亲时,他的头顶居然秃了。他变成了另外一个父亲。一缕缕头发在清晨的枕边呈现窝巢状,如废弃的鸟巢。父亲爽朗地说。父亲说着就用手捋梳着头发笑笑又说,哈哈,这一年掉的头发盛过过去十年的总和。父亲后来就不笑了,一边嚼着苞谷面发糕,一边深有感触地说:农村苦啊,老百姓苦啊,有的老百姓家里所有物品也就值五块钱,甚至还不到五块。父亲说着,表情就有些酸楚,让我感到那酸楚既无奈又力不从心。那酸楚也勾引出我的眼泪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着转。我默默组构着那个老百姓家里的样子,很恐惧。我想,新社会了,五星红旗下,怎么还会有这样贫困苦难的老乡呢?父亲那酸楚无奈的神情让我铭记了四十年。我知道,我肯定还会再铭记下去,直到我的肉体消亡。
照片上,身穿棉军装的父亲有些雄心勃勃。他是革委会集体中个头最高最魁梧的一个。紧挨父亲站立的是一位少数民族,方脸,高颧骨,黝黑,粗壮。另一个年轻人,在灰黑色照片中脸部显得过于白净,并且消瘦,与实际年龄很不匹配。还有一个中年妇女,略显土气,但敦实,质朴。
六
犹豫了很久,我终于下决心将照片装进了我的背包。我看了一下母亲。母亲没有反对,母亲似乎希望我拿走更多的照片回新疆。
辗转数载之后,我奇迹般在精河县找到了一位当年与父亲共过事的干部,他已经是一位耄耋老者。观察了我很久,他才蠕动着褶纹稠密的嘴唇说,像,还挺像赵主任,只是皮肤比赵主任要白一些。我说,我的肤色随我母亲。
老者指着照片说,你父亲左边站的是蒙古族副主任巴德曼,右边的年轻人是群众组织代表副主任陈清甫,那女的叫邱忠和。我惊讶于这位白发老者的记忆力。他如脱口秀一般,快捷准确地说出了他们的姓名。
老照片没了。它们像一个断带,隔断了以后的岁月。我觉得蹊跷,问母亲,母亲说,后来你爸去黑山头带人施工,到九工区施工,都没有留下照片。那时候,施工也都是保密的,你爸没有带回一张照片。母亲红肿着双眼,不住地用手擦眼泪,我发现母亲苍老了许多,皱纹也更加浓密了。我知道,这是父亲离世,母亲心力憔悴的结果。我不再问母亲。
父亲转业回河北后的照片就基本是我探亲时拍照的了,那都是些彩照。第一次使用彩色胶片是一九八三年,我用海鸥120双镜头反光相机,在石徳铁路线的铁道上为父母拍了两人合影。我很稀罕铁路,那时我所居住的准噶尔戈壁小城还没有铁路。父亲笑呵呵的,很知足的样子,比在新疆时瘦了但很健康。照片现在看来有些灰雾蒙蒙,色彩还原得也不够真实。冀中平原的阳光似乎缺少准噶尔戈壁大漠的通透与旷远。因为是彩色的,我没有把它们划归老照片。
只有年轻英武的父亲还长留在我的胸间,定格在那些老旧照片上。仿佛,父亲的肉体依然存活着,在冰凉通透的阳光下,迈着那种坚定的步履,并且老远就能听到他那响亮而磁性的声音。父亲永远呼吸着那些年轻而清新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