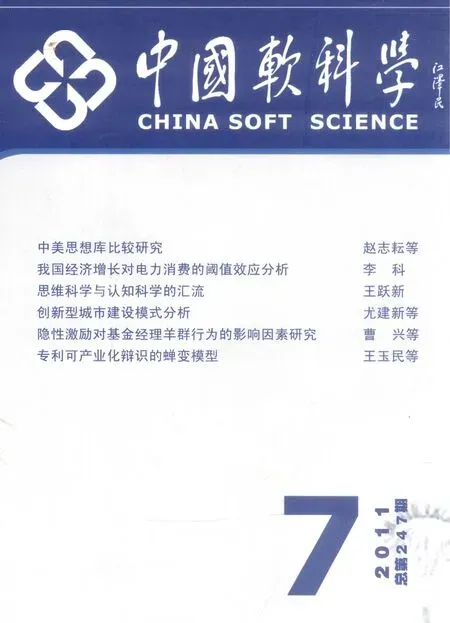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与部门工资差距问题:基于中国微观家计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余向华,陈雪娟,孙蚌珠
(1.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37;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3.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从一种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向分散的市场化模式的渐进式转型。转型中首当其冲的是部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先后经历了两次意义重大的战略调整。一次是1992年十四大确立的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由此非国有部门作为经济主体的地位合法性得到确认;另一次是1997年十五大所强调的“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抓好大的,放活小的”,由此在随后几年里,大量国有企业或者转变为股份制、或合并,或被卖给私人,或破产。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制结构不断演变,由改革前单一的国有和二国有(集体所有)部门,逐渐分化演变形成了包括国有部门、城镇集体部门、私营部门、外商投资部门等多种所有制部门并存的混合结构。
随着这种部门所有制结构的大变动,就业的所有制结构也随着发生急剧变化,由原来集中于国有部门向着非国有部门逐渐转移,最终非国有部门吸纳了大部分的劳动力就业。由于不同所有制部门所处制度和经济环境不同,就业体制和工资决定机制都不同,导致劳动者收人结构方面出现差异。在所有制就业格局变动的同时,中国所有制工资总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演变格局及其特征,如图1和图2所示,可以发现,就平均工资水平变动来看,改革初期,民营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平均而言最高,国有部门次之,集体部门最低。这一点的直观解释可以从中国经济改革启动的增量改革特点来说明,在原有体制基本不动的情况下,通过引入民营等其他增量体制启动了改革,所以,民营部门作为最早接触市场的主体,也最早享受了市场化所带来的利益,并且一直引领着国有和集体部门的改革,体现出了市场化的利益增进作用。对此,只要看一下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所经历的所谓“下海”潮就可见一斑:正是这些民营部门利益的吸引,中国在这段时期不断上演着各种国有和集体部门职工纷纷跳出铁饭碗进入各种非公有部门就业,谓之“下海”。
随着改革的全面和深入推进,在1996年左右,民营部门作为改革先行者的优势开始逐渐消失,而国有部门进入市场后,凭借其国有体制所掌握的资源优势,逐渐迎头赶上并在2003年左右开始超越了民营部门的收入水平,并逐渐拉开差距。在这个过程中,就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国有和集体部门的就业人数占比下降,而民营部门的占比则显著上升,并超越国有部门成为最大的吸纳劳动力的部门①关于这一点,本可通过具体统计数据来说明,但由于有关《统计年鉴》中这一方面的数据缺陷非常大,总就业人数和各分部的就业人数之和相差非常大,所以直接用这种数据来说明问题意义不大。。这一方面说明通过这种非国有化非集体化,使得最初改革发展的利益确实向更多的群体开放。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此时推动这种非国有化非集体化的力量已不再是二者的工资差距,而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下岗”。

图1 不同所有制部门平均工资变动趋势 单位:元

图2 不同所有制部门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变动趋势 单位:%

图3 不同所有制部门平均工资比例变动趋势
从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来看(见图2),在1993年前,工资增长最快的是民营部门,年均增长率达到10.86%左右,其次是国有部门,增长率为6.07%;1997年左右,国有部门的平均工资年增长速度开始成为最高;2004年到现在,三个部门的工资增长率开始进入高位平稳状态,国有部门达12.6%,民营部门则为10.63%。
工资增长速度的差异,使不同部门之间工资的相对差距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见图3)。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的相对工资有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两个部门的工资比在1993年之前,民营部门工资水平及其增长率都高于国有,到1993年左右,两者工资差距达到最大,相对工资降到最低点0.71,随后,由于国有部门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其他非国有部门,国有/其他的工资比率开始上升,2003年,两个部门工资水平基本相等,随后国有部门超过其他部门,2008年二者的工资比变为1.09。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的所有制结构变迁中,国有部门的就业经历了由下海到下岗的转变,而相对工资水平则经历了折价到溢价的转变。考虑到不同时期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的流动所呈现的不同特点,或主动的下海或被动的下岗,便会给我们分析所有制部门性质对工资差异的影响带来困难。本文的分析首先需要撇除这种选择性对于结果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理论界很早就试图定量化分析和解释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工资差距问题。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很丰富,美国的Smith早在1977年就对本国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之间存在的工资差异进行了探讨[1]。Blanchflower和 Borland等较早测度了主要国家的国有部门工资溢价程度[2-3]。关于转型经济体中两个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问题的文献也逐渐增多,不过,由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的差异,不同国家的部门工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溢价或折价特点,从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对于国有部门工资折价问题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Rutkowski认为在由中央集权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私有部门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日益关注,工资结构也将发生巨大变化,国有部门工资将出现折价现象[4]。对此,Adamchik和Bedi对波兰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转型使得具有工资优势的是私有部门,吸引了具有大学学历的雇员,尤其是男性,而女性考虑到一些无形的工作特征,如社会声望、工作安全性和稳定性以及非工资福利因素,更倾向于选择公有部门[5]。政府在平衡两部门收入水平过程中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提高公有部门雇员工资使政府面临巨大财政压力,而忽视工资差别则又引发雇员不满会降低工作效率。为此,文章提出削减公有部门雇佣人数,同时提高高素质雇员的工资水平来解决这个两难抉择。Lokshin and Jovanovic对南斯拉夫的研究,考察了国有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就业选择和工资差异,他们扩展了标准的Switching模型,校正了部门劳动力的自选择问题,发现南斯拉夫国有部门存在工资折价且这种工资折价还将逐步提高,这种折价随教育程度反向变动;这使得国有部门的吸引力降低[6]。
对于国有部门的工资溢价问题,Lindauer and Sabot对坦桑尼亚的研究发现,坦桑尼亚公有部门的平均工资比私有部门要高出51%,在这些总工资差别中,73%可以由劳动者个人特征差异解释,而这其中又有85%可以由公有部门平均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白领雇员的相对集中来解释。不过,在剔除了员工禀赋差异的影响之后,公有部门的工资仍比私有部门高出14%[7]。换言之,同质劳动力在公有部门的工资明显高出私有部门的市场工资水平。印度公共部门相对于私人部门的溢价程度在各国之中最高,Elena Glinskaya and Michael Lokshin,利用了一系列校正自选择偏差的方法,发现印度公共部门比私人正式部门的工资高62%到102%,相对于非正式部门高164%到259%[8]。非洲国家吉布提的 Paloma Anós Casero and Ganesh Seshan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校正了自选择偏差,发现公共部门的工资溢价与个体特征和人力资本禀赋无关,进入公共部门的多为男性,并且部门有代际传递性[9]。
尽管,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城市日益加大的收人不平等的潜在原因之一,但由于早期相关数据比较匮乏,中国有关部门工资差异问题的计量分析起步较晚[10]。已有的文献根据分析的视角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分析部门工资溢价对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赵耀辉最早对部门间工资差异问题进行了研究[11],此后的代表性文献可参见李荻等[12]。另一类分析不同部门的工资决定方程,代表性文献可参见邢春冰,通过分组回归,来考察不同部门中各因素对于工资的不同影响[13-14]。还有一类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工资差异分解,定量化部门因素对于工资差异的影响。现有文献通常是用Oaxaca分解,将工资差异分解为生产率因素和非生产率因素,其中非生产率因素用来度量溢价程度。代 表 性 文 献 可 参 见 王 美 艳[15],陈 弋、Sylvie Démurger 和 Martin Fournier[16]和 张 车 伟,薛 欣欣[17]。在计量方法上,他们设法修正了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多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别对两个部门的工资方程进行回归,也有用Switching模型的。
本文分析的视角与第三类文献相似。陈弋[16]等的研究分析的是1995年市场化改革初期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工资差异,认为“纯所有制差别和工作小时差别”是工资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张车伟、薛欣欣[17]利用“2005家庭动态与财富代际流动抽样调查”微观数据,考察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异和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特别利用分位数回归,进一步对工资差异的条件分布状况进行解析。本文的主旨虽然也是识别所有制性质对于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的影响,但在模型选择上与以上文献有所不同。本文是在考虑国有部门进入的决定问题的基础上来分析部门工资的决定问题,设计了一个两阶段Treatment-effects模型,从而校正了自选择偏差所带来的回归结果的不一致性,并得出了部门差距的一个估计值及其在所有制变迁中的一个变动趋势。本文使用的数据与邢春冰[14]一样都是CHNS数据,用这个数据库来做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它是面板数据,各年度所选取的是同一样本。但与其不同的是,2008年与本文研究直接相关的教育、收入子库数据经过重要净化,特别是个体收入部分根据地区和年份的购买力进行了平减。
三、基本模型
首先,本文采用的工资方程为基本的Mincer方程,利用这个方程,通过总体样本和部门分组样本的OLS估计,可得出不考虑自选择问题时各变量对工资收入的影响。

其中,下标i指第i个样本InYi为对数化的小时工资,Si为表示部门性质是国有还是非国有(包括民营和其他)的0-1虚拟变量。因素向量Xi中各分量的选择,本文从CHNS数据的特点出发,选取了教育年限、工作经验、性别、年龄、职业、地区、户口等变量。
不过,仅利用上述方程进行简单回归,存在样本非随机产生的问题,因为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工资的溢价或者折价情况,将直接影响那些进入国有部门者的人力资本状况。而且国有部门较为集中的城市地区国有部门的就业机会也较多,这都使得通过简单分组获得的样本本身是经过了选择之后的,而并非随机的。这种样本非随机产生的问题的存在,使得如果只是简单地用分组的子样本去估计各变量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的话,将会产生系统性偏差,难以得到部门性质对工资的边际效应的一致估计,因此必须考虑这种偏差对于工资决定的影响。这种样本选择偏差,可根据样本是否随机指派(Random Assignment)与样本是否遗漏(Sample Attrition)两种情况,分为自选择偏差(非随机且无样本遗漏)与截断样本(Truncated Samples)和样本遗漏(Censored Samples)的差异①参见Greene对于样本选择偏差及其校正方法的介绍[18]。。
若存在截断样本,则只能单独观察国有部门或非国有部门的样本,此时可用Switching模型来校正。邢春冰在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时,区分不同所有制来进行分组回归(从而存在样本截断),为校正不同所有制的样本选择性偏差,使用了这种模型[14]。该文关注的焦点是不同变量在不同所有制部门当中对于工资的不同效应,所有制并未作为一个变量出现,因而未得出所有制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
若不存在截断样本,能同时观察到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样本,则可用Treatment-effects模型来校正这种自选择偏差。由于本文旨在考察部门性质造成的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问题,因而需要同时观察比较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样本。故本文基于该模型,引入一个部门选择方程,来刻画不同个体进入国有部门的概率对工资的影响。这与Switching模型所隐含的假设有所不同,前者将部门性质的影响分散到不同自变量当中,而Treatment-effects模型则仅通过部门性质这个变量来区分由部门性质造成的工资差异,即假设个体进入国有部门,各变量的工资效应会有一个向上或者向下的平移,这个平移即为部门性质的边际效应(溢价或者折价)。综合上述考虑,本文采用Treatment-effects模型来校正自选择偏差。
Treatment-effects模型中,除了包含(1)式的Mincer方程外,还包括部门选择变量Si的决定方程:

由于自选择问题,这里的ξi和(1)式的Ui可能相关,服从均值为零的二元正态分布,两者的协方差矩阵如下:

对于Si这一内生的部门性质虚拟变量0,则进入国有部门,此时Si=1;Zi是决定是否进入国有部门的各种外生因素组成的向量,本文的实证模型在考虑了数据限制之后,选择了影响个体进入国有部门的背景因素,包括教育程度和年龄以及“是否城市”。
利用Greene将前述的二元正态分布转换为一元正态分布的方法,可以得到求解工资方程与选择方程的误差项的相关系数ρ的标准方法:

这里,atanhρ为ρ的反双曲正切函数值。再定义λ=ρ×σ为机会比率系数,作为对自选择偏差的估计值,λ的标准差为:

其中,D为λ相对于atanhρ和lnσ的雅各比矩阵,用于检查相关系数ρ。模型的零假设为两误差项不相关,即ρ=0,不存在自选择问题;若相关,则系数β的OLS估计值有偏。具体来说,若存在潜在变量同时影响工资方程和选择方程,两误差项呈负相关,即ρ<0,则直接用β的OLS估计值会低估部门性质对工资决定的影响;反之,两误差项呈正相关,即ρ>0,则直接用β的OLS估计值会高估部门性质对工资决定的影响①因为若ρ<0,则λ<0,此时简单的OLS估计值会低估β,从而低估部门性质对工资决定的直接影响;反之亦然。。
以上模型,在实证分析时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Heckman-Maddala-Lee两阶段估计法,又称Heckit法,它首先利用(2)式的Probit模型估计出自选择偏差的估计值,即机会比率系数λ,然后,将机会比率系数代入(1)式中,再以OLS估计得到无偏的系数估计值。另一种方法是Maddala基于极大似然估计原理提出的MLE方法。两种方法比较而言,两阶段法操作简单也易于理解,但由于主方程和选择方程中涉及相同变量,可能产生共线性问题引起结果的不稳健,MLE法可以避免共线性问题,但可能存在估计值不收敛的问题,同时,样本数据量较大时运算的效率也不高。由于MLE可能不收敛且我们的样本容量较大,因此,我们采用两阶段估计的方法,同时,为了避免共线性,所以如上所示,我们在选择方程式(2)中加入了主方程中所没有的外生性的识别变量(即Zi中的虚拟变量“是否城市”),由此可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共线性及其影响[19]。
此时,结合(1)式、(2)式和(7)式可知,考虑自选择偏差校正时,虚拟变量S前的系数β只是在分别考虑了两组各自的内生截断(选择偏误)的影响后,组特征差异对工资因变量的影响之一部分。部门性质所决定的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总的工资差异(即部门性质导致的工资折价或者溢价)的期望值为:

其中,β为回归的系数值,Ψ是Greene转换后的一元标准正态分布密度函数,Φ是对应的正态分布函数。由该式可以看出,考虑偏差校正之后,部门性质导致的工资差距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在工资决定上的直接影响,即系数β,另一是影响个体的进入概率从而影响工资,这体现在后面的机会比率系数项上。
四、数据
本文采用STATA进行计量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该调查是美国北卡罗来那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会合作的微观家户调查,它取得了 1989、1991、1993、1997、2000、2004和 2006年中国农村与城市中 3000多个家庭户中个人工资、人力资本以及其他反映注:农村户口为0,城镇户口为1.女性为0,男性为1.居住地非城市为0,城市为1.一般职业为0,技术职业1,管理职业2.家庭背景的数据,我们择取了后面5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本文关注的变量为对数化小时工资、教育年限、性别结构、工作经验①本文以年龄为基础,构造了工作经验变量,构造方法与传统做法保持了一致,为年龄-7-正规教育年限。、户口、职业等。表1和表2为数据描述,其中表1为各年度的总体样本情况。表2为各年度分组的样本情况。

表1 不同年份的总体描述性统计

表2 不同年份的分组描述性统计
从总体样本的时间变动趋势来看,工资水平、教育呈逐年递增趋势,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呈逐年递减趋势,其他变量保持了随时间变化的稳定性。从分组样本来看②这里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仅列出了可完整反映趋势的1993、2000和2006年。,不同部门在这些变量的取值上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进入国有部门的人群平均教育年限一直高于非国有部门,1993年二者教育年限比为7.32∶9.35(相当于初中:高中),到2006年为9.52∶13.09(相当于高中:大学)。国有部门的男性占比,经历了一个从较低到较高的演变过程,1993年二者比例为0.67∶0.58,到2006年为0.59∶0.63。从职业构成来看,国有部门的技术岗和管理岗比例一直高于非国有部门。1993年二者结构指标的比例为 1.34∶1.77,到 2006年为1.49∶2.22。从部门所处区划层级来看,城市的国有部门所占比例一直高于50%,非国有部门所占比例较低,但也随时间逐年增长。而两者的对数化小时工资水平,则呈现出起伏状态。1993年,国有部门的工资水平远低于非国有部门,到2000年时,二者接近,到2006年时,国有部门的工资水平已高于非国有部门。总之,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两者的样本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五、计量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模型和数据,回归得到附表1。
(一)不考虑自选择偏差校正的简单回归结果
如果不考虑自选择偏差问题,也就是直接利用(1)式进行回归,有关结果见附表1的左栏。根据逐年对年度样本进行的回归可以发现:
1.部门所有制性质对工资的影响:在不对样本分组的情况下,除2000年外,部门性质虚拟变量S前的回归系数多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部门性质对于部门工资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但不同年份该系数的方向有所变化,先为负后逐渐转正,这反映了部门的国有性对于工资决定中先是导致折价后是导致溢价的总体事实。
2.其他主要特征变量对工资的的影响:工作经验、年龄、性别、户口、省份、正规教育年限的回归结果,均与预期结论大致相符,具体来说:工作经验越长、正规教育年限越长,工资水平相应就要显著地高;城镇户口比之农村户口,男性比之女性,工资有显著提高;职业岗位的影响也很显著,管理岗和技术岗可带来显著的工资提升。以上回归结果说明模型与基本特征事实是相符的。
(二)考虑自选择偏差校正之后的结果
有关计量结果见附表1的右栏。逐年对年度样本进行的回归发现:
1.自选择偏差的存在性问题
估计结果显示,机会比率系数均不为0,且除2000年和2004年之外,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就拒绝了前述的无相关性假设,表明国有部门的进入确实存在较显著的自选择现象,这也验证了本文模型中考虑自选择偏差校正的必要性。2000年和2004年自选择现象不显著,表明这两个考察期中,进入两个部门的样本不存在系统性区别,此时,部门之间的竞争比较充分,个体因所进入部门的不同而形成的工资差异不显著。
2.关于国有部门的进入决定问题
自选择偏差的存在,源于进入国有部门的就业者存在某种系统性。而附表中有关部门选择方程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决定进入国有部门的各因素的系数均为正且非常显著,这正好验证了上述关于进入的系统性假设。其中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教育程度越高,进入国有部门的概率越大,这表明国有部门通过提高进入人员的教育程度要求,来达到设置进入门槛的作用,而且越到改革后面,这种门槛被提得越高。其背后的直观事实就是,随着所有制改革的深入,国有部门逐渐只保留在少数重要领域,由此进入这样的部门就越艰难,需要更高的学历才可能叩开其大门,加上人事改革导致的国有部门下岗分流潮中教育程度较低的被更多地下岗分流出去,这样也抬高了国有部门在岗人员的平均教育程度;此外,由于国有部门主要聚集在城市,故而城市人显然更容易进入国有部门,不过其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此外,由于国有部门的人员更替率较低,新进入者较少,国有部门人员的平均年龄自然要高于非国有部门。
3.校正之后的部门性质影响与工资差距问题
有关结果见附表右栏。可以发现,除教育年限与部门性质变量之外,其他因素的回归系数大小及其显著性虽然有所变动,但变动不大。而教育年限的系数由原来的显著为正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经过校正之后,单纯的教育年限多寡可能不对工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教育的作用主要是提高进入国有部门的概率来敲开国有部门的大门。
更重要的是部门性质变量的有关结果。为便于比较,我们将附表中校正后的有关数据摘取出来列在下表3中。首先可以看到,各机会比率系数均为负值且除2000和2004年外均显著,为负的原因显然是ρ<0,即ξi和Ui负相关,这意味着进入概率越高,则由于竞争加强会导致整个部门的工资下降;故校正之后各年度的β均大于简单OLS回归的系数,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这种偏差校正,直接用上面的基于简单OLS法得出的系数来作为部门性质对部门工资水平的影响系数,得到的结果是有偏的。由表3可见,在经过校正之后发现,在各年度部门性质变量的系数均变为了正值,且除1997年和2000年外都是很显著,这说明,经过校正后,部门的国有性质本身对于工资收入一直都具有正的从而是溢价性的影响,而不再是校正之前的先折价后溢价。如(7)式所示,考虑偏差校正之后部门性质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还包括对进入概率从而机会比率系数的影响。前面已指出,各机会比率系数均为负值表明进入概率越高导致了整个部门的工资下降,从而部分抵消了国有部门的溢价性,改革初期之所以出现国有部门工资低于非国有部门,其原因主要在于就业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部门偏重。由表3可见,作为两方面影响的综合结果,总的差异还是表现出先折价后溢价。

表3 国有部门的工资溢价或折价情况
六、结论与建议
上面的统计与计量分析都表明,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存在工资差异,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中,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工资水平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国有部门工资经历了由折价向溢价的转变,这种特点及其转换的背后体现的正是中国改革的阶段性。转换之拐点大约为2000年左右,这也是使得该年度的β值最接近0而且不显著的原因。不过,从本文分析结果来看,如果去除自选择的影响,国有部门属性本身一直表现出提高工资的作用(校正后β在各年均为正数),说明进入国有部门并成为公家人在各个时期都有其收益上的激励。而之所以不同时期在总体上表现为折价与溢价的变动,主要源于就业结构变迁及其所引发的部门进入难易程度的转变。
1992年前,整体经济已经历了一段半市场化的改革,作为非国有部门主力的民营部门,因为率先进入市场获得市场化改革红利,而在就业结构中占据主力军的国有部门则总体上处于“大一统”但“老大难”的困境中,所以平均而言,1993年非国有部门工资水平高于作为改革对象的国有部门,由此形成的利益落差,也恰好形成了非国有化改革的内在动力,这是国有部门工资总体上存在折价的内在根源,这种总折价从对数化小时工资水平上看在1993达到考察期最高值0.577。
正是国有部门亟待改革的困境,使得中国1992年走出了围绕计划与市场的长期争论,明确提出了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由此,加大非国有化力度以推进总体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得以全面展开,大量就业主动或被动地由传统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这使得非国有部门在总体规模壮大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了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其所面临的经营和就业方面的竞争加剧,作为改革先行者的红利缩小,故而其工资上涨速度受到挤压;而国有部门则在就业和社会保障责任大幅度转移出去的背景下,压力有所减轻,工资水平上涨幅度提高,所以总体的折价开始减小。而1997年左右,开始强调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抓大放小”之国企改革使国有部门逐渐退出了竞争性的行业(这种退出,不仅是产权和经营上的退出,也是社会就业和保障等传统社会责任上的大幅退出),所保留的大部分是关系国家命脉的行业,并且多数是行政保护下的垄断式运营;加之1998年开始实施对作为国有部门主力之国企的“三年脱困政策”,更是使国有部门得到直接的大规模体制性帮助,比如核销呆坏账、债转股、优惠贷款等等。这些体制性优势,加上国有部门传统上形成的资本、资产和技术等方面的规模优势等,为国有经济的利益从而工资快速增长提供了源泉,并且,鉴于国有部门运作主要是以非市场化方式进行,存在天然的体制性屏障,就使得这种工资快速增长速度可以依靠体制性的进入门槛,阻止非国有部门就业大规模转移过来进行竞争拉平,由此,国有部门的工资总体折价继续减小并在2000年之后开始实现逆转,在2004年左右溢价达到最大的0.146。
综上可见,所有制结构变迁中国有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差距的变化,经历了由折价到溢价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有很强的政策和体制相关性,因此解决由这种工资差距所引发的一些问题,也就同样需要从有关政策和体制入手。而本文的研究为解决部门工资差异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我们认为,政府在考量部门工资差异问题时,应当重视导致个体在进入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体制性机会不平等问题,因为这比之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为此,从短期看,在对有关高收入的国有垄断部门进行改革和收入规制的同时,也应该着力于提高整个国有部门就业岗位对整个社会的开放度,使其体制性机会所带来的收益在开放竞争中逐渐拉平。
[1]Smith,Sharon P.Government Wage Differential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77,(4):248-271.
[2]Blanchflower,D.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Trade Unions in the OECD[R].CEP Discussion Papers,No.310,1996.
[3]Borland J,Hirschberg J.and Lye J.Earnings of 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 Sector Employees in Australia:Is There a Difference?[J].Economic Record,The Economic Society of Australia,1998,(74):36-53.
[4]Rutkowski,Jan.High Skills Pay Off:The Changing Wage Structure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 in Poland[J].Economics of Transition,1996,4(1):89-112.
[5]Vera A.Adamchik and Arjun S.Bedi.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ectors:Evidence from an Economy in Transition[J].Labour Economics,2000,(7):203-224.
[6]Michael M.Lokshin and Branko Jovanovic.Wage Differentials and State-Private Sector Employment Choic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R].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23,May 2006.
[7]Lindauer D L,Sabot R H.The Public-Private Wage Differential in a Poor Urban Economy[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3,12(3):137-157.
[8]Elena Glinskaya and Michael Lokshin.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India[R].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574,April 2005.
[9]Paloma Anós Casero and Ganesh Seshan.Public-Private Sector Wage Differentials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Djibouti[R].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23,May 2006.
[10]Knight,John and Song Lina.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1,53(2):123-154.
[11]Zhao,Yaohui.Earnings Differentials between State and Non-State Enterprises in Urban China[J].Pacific Economic Review,2002,(7):181-197.
[12]李荻,张俊森,赵耀辉.中国城镇就业所有制结构的演变:1988-2000年[J].经济学(季刊),2005,(10增刊):23-44.
[13]刑春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考察[J].经济研究,2005,(6):16-26.
[14]邢春冰.经济转型与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工资决定——从“下海”到“下岗[J]. 管理世界,2007,(6):23-37.
[15]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5):11-18.
[16]陈弋,Sylvie Démurger,Martin Fournier. 中国企业的工资差异和所有制结构[J].世界经济文汇,2005,(6):11-31.
[17]张车伟,薛欣欣.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贡献[J]. 经济研究,2008,(4):15-25.
[18]Green W H.Econometric Analysis[M].Prentice-Hall,Inc.,2000.
[19]Maddala G S.Limited Dependent and Qualitative Variables in Econometric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