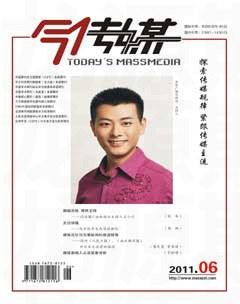电视娱乐节目的伦理反思
周少四
摘要:本文从伦理学的视角剖析了当前国内电视娱乐节目在社会责任、人文精神、创新能力和价值导向上的缺失,并提出了加强社会责任、人文关怀和审美品位等三点媒介自律和伦理纠偏的建议。
关键词:电视娱乐节目;伦理;纠偏
中图分类号:G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6-0084-02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起源于1990年3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综艺大观》。其后,电视娱乐节目经历了晚会、游戏、竞猜、真人秀等几个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各省级卫视的娱乐节目轮番登场,尤其是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一炮走红,真正掀起了一股娱乐狂潮,宣告了全民娱乐时代的到来。学术界对于电视娱乐节目历来有两种继而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娱乐是电视的基本功能,甚至是电视的最高境界。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电视娱乐节目能有效地缓解人们的紧张感和焦躁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电视为人们构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极力迎合人们的情感需要,以虚幻的快乐与满足让人们逃避现实的生活压力,具有诱惑性与欺骗性。而电视娱乐节目的低俗无聊则暗合了“人性之恶”,因此有人高呼“关上电视,打开书本!”,两种观点的是非曲直我们暂且不表,而电视娱乐节目在狂躁纷扰中的伦理失范已然成为学术界和广大电视观众议论的焦点。
一、电视娱乐节目伦理失范的表现
笔者以“电视娱乐节目”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共查到999篇文章(检索日期为2011年5月9日)。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以批判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当前电视娱乐节目所表现出来的低俗浮躁、同质模仿等问题进行鞭挞批评的。从传媒伦理的角度而言,当前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问题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缺位
随着卫星电视的迅速发展和数字电视的全面普及,电视媒介对人们生活的渗透、干预与影响也越来越大,人们对电视媒介的依赖性也与日俱增。作为社会公器,电视媒介肩负着舆论监督、协调社会、教育大众的责任,有义务为受众提供有益的信息,使受众理性地认识社会,辨别是非。但是,不少电视娱乐节目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并没有自觉地履行其应有的社会职能,甚至出现职业道德失范的现象。
为了吸收足够多的眼球关注,迎合观众口味,抢占受众市场,电视娱乐节目经常炒作偶像绯闻,窥探明星隐私,甚至渲染暴力和色情信息,助长了不良社会风气,造成极坏社会影响。有调查研究表明,电视的这类信息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道德发展,甚至会让他们模仿学坏。
舆论监督是大众传媒的一项基本职能,关注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是传媒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而如今的一些电视娱乐节目以刺激公众兴趣作为传播信息选择的标尺,对社会深层问题和严肃话题缺乏应有的关注,传播内容琐碎、肤浅、感性甚而庸俗,“躲避崇高”、放弃责任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电视娱乐节目总是对明星们的八卦绯闻津津乐道,电视新闻往往对偶像们的时尚生活连篇累牍,但是对事关国计民生的真正的大事却视而不见,集体失语,尤其缺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
(二)审美品位和人文关怀缺失
这是一个被业界称为“快乐升级”、被学者称为“娱乐至死”的年代,以“超女”为代表的诸多电视娱乐模式此消彼长,打乱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惯常理解,降低了人们的审美品位和艺术追求。电视台在收视率的指挥棒下,刻意迎合某些观众的低俗需求,放大和突出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非理性、非价值、非逻辑的一面,无视道德规范的制约,以纯粹动物性的感官刺激取代人性的审美情趣和健康的精神享受,使文化传播中的道德性、价值性、终极关怀等内涵不断被削弱,导致感性能力畸形增强而理性能力日趋萎缩。“美”从理想精神的高峰跌到了世俗生活的享乐之中,沦落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快乐生活享受,精神崇高的美感转移为身体快意的享受。随着崇高被消解,经典被解构,由传媒主导的大众文化占据了传统精英文化的领地,导致大众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转变:由追求唯美、典雅、崇高,转向了追求怪异、丑陋、缺陷甚至恶俗,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审丑”倾向。
(三)节目个性和创新能力缺乏
节目个性是电视娱乐节目的生存法宝之一,而刻意模仿、同质竞争是国内电视娱乐节目遭人诟病最多的地方。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走红之后,全国各省级卫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一批电视选秀节目,而其节目内容、游戏规则甚至主持风格都与前者如出一辙。到2006年,在全国播出的大大小小的选秀节目达100余家。电视选秀节目迅速进入一个短兵相接的胶着状态。同样地,2010年,在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和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红遍全国之后,东方卫视的《百里挑一》、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安徽卫视的《周日我最大——缘来是你》、山东卫视的《爱情来敲门》如法炮制。无论是当年风靡一时的全民选秀运动,还是时下的电视相亲擂台战,这样的“一窝蜂”现象大大降低了电视传播的综合效益,使得观众在经历了最初的新鲜体验后,迅速出现审美疲劳和节目选择权的变相流失,导致节目周期大大缩短。
(四)价值导向和教育功能缺漏
近几年来,此起彼伏的电视选秀热潮至少从三个方面对大众进行了误导:一是对“一夜成名”的鼓励与渲染,二是对粉丝的狂热追捧行为予以赞赏并推波助澜,三是尽力为受众提供缺乏思想深度的轻松愉悦感,蕴育了享乐主义的社会风气。通过电视媒介的信息传播,人们能领略到影视歌星、体育明星、政界名人和商界骄子的风采。但对于这些明星,大众传媒习惯于挖掘的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衣食偏好等信息,特别是他们的恩怨情仇、个人隐私等内容,而不是他们的奋斗经历和坚强意志。在电视媒介的暗示与引导下,受众只注意到这些明星们风流倜傥的行为方式和一掷千金的生活习惯,并把这些表面的光鲜当成追求的目标。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不再把劳动与创造当作一种追求,而是把自我实现简单地等同于自我满足。
二、对电视娱乐节目伦理纠偏的建议
对于国内电视娱乐节目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症结,批评剖析、望闻问切者多,但对于如何走出困境,开展伦理纠偏,开出药方者少。对此,笔者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在传播自由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社会责任
传媒的自由主义理论是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而逐步发展的,它对资产阶级最终取得革命成果有着重要的功绩,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它只重视传播者的权利,却忽视了接受者的权利,强调了新闻自由而没有考虑到自由滥用的问题。因而,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哈钦斯委员会)提出的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逐渐受到推崇。该理论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和公众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和义务。如今,在西方发达国家,许多新闻媒体在追求新闻时效性的同时,正在有意识地改变传统新闻的操作模式。这是西方国家新闻工作者在经过一段曲折而漫长的新闻自由探索后,对新闻价值理念重新思考的结果。可是在中国,有些新闻工作者在强调新闻自由的同时,却忽略了新闻自由所包含的社会责任,遗忘了新闻自由的边界。有些电视娱乐节目为了吸引受众“眼球”,追求轰动效应,在新闻自由旗号的掩护下,不断利用所掌握的新闻资源反复炒作某些病态的、非理性的极端事件,不仅对当事人造成了二次伤害,而且浪费了媒介资源、污染了媒介环境。
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的哲学基础可以追溯到康德的道德义务论,而它在当代社会的实践应用便是对社会责任和公平正义的突出强调。正如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所说:“对社会的责任是伦理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并且由于有了社会责任理论,媒体对社会的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1]传播自由与社会责任总是共处于现代社会的所有传播体系中。在有着“文以载道”传统的中国,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代,电视娱乐节目应在传播自由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社会责任。
(二)在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文关怀
在传媒市场化的今天,绝大部分电视媒介机构都是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电视台及电视节目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压力之下,开始了市场化改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收视率是广告投放、企业赞助的价值尺度,而这又是传媒生存与发展的命脉。在这样的生存逻辑之下,电视媒介极力迎合受众口味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从整体上来看,受众的文化素养有限,知识水平不高,他们倾向于接受表层的、刺激的、感性的信息,对于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比较淡漠,但对明星轶事、花边新闻却饶有兴趣。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其源头可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其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在当代中国,如何处理经济效益与人文精神,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两难选择。从人类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而言,电视媒介决不能唯利是图,将人文弃之。作为在现代社会有着重要影响力的电视媒介及其从业者,理应高扬人文主义旗帜,“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而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在娱乐本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审美品位
娱乐是人的内在需要,也是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甚至是传媒各种功能中最显露、最有力的功能。在当今社会,娱乐文化与大众传播相得益彰,以至于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娱乐,传媒如何形成自己“无形的文化权力”?娱乐可以说是当今大众传播的“中枢神经”。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经过长期的生存重压和泛政治、泛道德文化的压抑之后,作为一种矫枉过正的反弹,对于物质财富有着如饥似渴的追求,对于感性释放有着歇斯底里的诉求。另一方面,伴随着信息全球化、媒介大众化、信息市场化浪潮的影响,西方的传媒娱乐化浪潮对我国的传媒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有的人只看重经济利益与物质享受,过度追求感官刺激与奢侈消费,缺乏崇高理想与理性精神。全社会的过度娱乐化导致大众传媒正在逐渐丧失其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及文化认识功能。正如美国学者波兹曼所说:“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形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
电视媒介不仅是社会公器,也是现代社会一种大众化的娱乐工具,应加强媒介自律,增强社会责任,提升受众品位,提高审美趣味,构建中国电视和谐融洽、品位高雅的“绿色娱乐”。
参考文献:
[1] (美)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著.张晓辉等译.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M].华夏出版社,2000.
[2]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