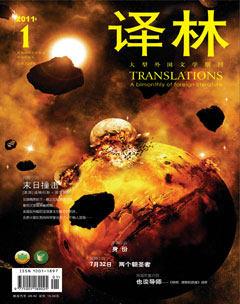理想与现实之间
朱 丽
薇拉•凯瑟是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小说生动地刻画了美国西部大草原的女性拓荒者形象,代表作《啊,拓荒者》和《我的安东尼亚》充分地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瓦格纳音乐会》与《花园小屋》是她早期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两位女主人公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安排,但作品中所表现的主题却惊人地相似:颇具音乐天赋的两位女人,为了现实的生活,不得已放弃了音乐梦想,一位在艰苦而又琐碎的生活中蹉跎岁月,另一位在奢华却又乏味的光阴中浪费着青春。在小说的结尾,读者能真切感受到两位女主人公为最终屈从于现实、远离梦想而发出的深深叹息。
《花园小屋》(以下简称《花》)中的女主人公卡罗琳自幼生长在一个充满艺术氛围却十分贫寒的家庭,生活的困顿让她从小就担起养家的重任。残酷的现实使她拒绝进一步深造,而是把音乐天赋用在了开课授徒,赚钱糊口上。生活的磨难造就了她冷静的头脑,在婚姻问题上,她顺应现实,嫁给四十岁的华尔街金融巨头,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雷蒙• 戴斯盖莱舒唤醒了卡罗琳沉睡已久的音乐梦想,雷蒙住过的花园小屋,承载着卡罗琳的欢乐、梦想和憧憬。雷蒙走后,卡罗琳的丈夫要拆除这座小屋,代之以避暑别墅。在一个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夜晚,卡罗琳再次来到了小屋,异样的情愫油然而升,被压抑的情感使她暗自感伤。暴雨骤降,在半梦半醒之间,卡罗琳终于重回现实。她答应了丈夫要拆除小屋的要求,其平静的态度令丈夫十分惊讶。
《瓦格纳音乐会》(以下简称《瓦》)中的主人公乔治亚娜婶婶原是波士顿音乐学校的一名教员,为了狂热的爱情,她和情人私奔到内布拉斯加边疆地区。三十年漫长而孤寂的拓荒生涯使她备尝人生的艰辛,三十年来她所拥有的唯一乐器是定居十五年后丈夫为她买的一架小风琴;她听到的唯一音乐是礼拜仪式上唱的福音圣歌;她见过的唯一歌手是流落到她农场上的一个飘泊不定的牛仔。三十年里她没有走出过她那座农场方圆五十英里的范围。为了爱情而放弃音乐梦想的乔治亚娜婶婶做出了奉献和牺牲。因为有要务处理,乔治亚娜婶婶回到了她阔别已久的故乡——繁华的东部城市波士顿,曾经在内布拉斯加备受婶婶照顾的“我”接待了她,并准备陪她听一场瓦格纳的音乐会。没想到从进入音乐厅起,婶婶就不再那么消极、迟钝了,美妙的旋律打破了她三十年的沉寂,她的情感也随之跌宕起伏。坐在“我”身边的不再是一个劳作在田间地头和围着锅台转的农妇,而是一位被音乐带进了幸福岛屿的听众。音乐会结束后,婶婶却不肯起身。然而,现实生活已经为她和音乐梦想之间竖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这两篇小说在创作主题上非常相似,都反映了女主人公为了现实生活而放弃梦想的痛苦与无奈。《花》中的卡罗琳是位实利主义者,悲惨的现实让她拒绝耽于幻想。为了生计,青春年少的她“压抑了自己作钢琴即兴表演的情趣,把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嗜好统统勾销,使她的生活降低到一套干巴乏味的程式,和时钟的机件那样千篇一律。”薇拉•凯瑟著,《花园小屋》, 薛鸿时译,载朱虹主编《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171。只为艺术而活着的父亲和哥哥使她不敢心存梦想,只为爱情而活的母亲使她不敢对爱情有所奢求。嫁给华尔街金融巨头后,她第一次停下来歇了口气。丈夫的金钱、地位、能力等实质性的东西让她确信,自己是彻底安全了。诚然,一个生活在重压之下的女孩,通过婚姻获得解脱,对她来说,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主要指对音乐的追求),似乎是最明智的选择。作为有同情心的读者至此为之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毕竟,与那些不堪生活之苦而走向堕落的女孩子相比,卡罗琳的这种结局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她的命运有了质的转变。
《瓦》中“我”的婶婶则与卡罗琳的生活经历截然相反。乔治亚娜婶婶曾在波士顿音乐学院当过教师,她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与当时一无所能、游手好闲的小伙子私奔到了西部边远地区,由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妇。从安逸到困苦,生活的巨大落差并没有压垮这位柔弱的女子,她没有半句怨言,很快地适应了角色的转变。她所表现出来的勤劳、善良、淳朴、忍耐给年幼的“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正是婶婶对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培养,才成就了现在的“我”,使“我”能够离开这片蛮荒之地,走向文明之都。婶婶执着于爱情,不惜放弃了她的音乐梦想,可这也成了她多年来心口的痛。她很少跟“我”谈起音乐,我知道其中的缘由。有一次我在旧风琴上弹奏从她的音乐书中找到的旧乐谱,她颤抖地说:“克拉克,别那么入迷,要不,你也许会失去它的。”言语中流露出自己远离音乐梦想的辛酸与痛楚。
小说中两位女主人公因为人生的追求不同,放弃梦想的原因也完全不同。卡罗琳为荣华富贵放弃了梦想,生活由贫穷走向富足;乔治亚娜婶婶为爱情放弃了梦想,生活由安逸走向困苦。然而梦想在她们生活中出现的轨迹却是相同的,都经历了由现实到梦想再到现实的过程。在她们的生命中,心底的梦想始终未曾泯灭。复苏的音乐梦想曾一度照亮了她们灰暗的心灵,但心灵之光转瞬即逝。现实生活是梦想的桎梏,无法摆脱的桎梏。乔治亚娜婶婶已在西部生活了三十年,青春和热情早已消失殆尽,当音乐会奏出的第一个旋律打破了三十年的沉寂,沉睡在心底多年的激情被音乐唤醒,犹如枯木逢春的她泣不成声,“这么说,那个如此创巨痛深而又无止境地忍受苦难的灵魂并不曾真的死去。只不过从表面看它枯萎了,像某种奇特的苔藓,它可以在满是尘埃的岩石上呆上半个世纪,但是一旦把它放回水中,它就立刻又变得绿茵茵的了。”梦想已经折翼,生活却还要继续。《花》中雷蒙的到来,不仅重新燃起了卡罗琳的音乐之梦,更掀起了一向以冷静务实而著称的卡罗琳情感上的波澜。夏日夜晚的暴风骤雨似乎宣泄着她内心的挣扎和困惑。虽然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安稳富足的生活,可她并未得到真正的幸福。心底的梦想像个囚犯一样被她自己严密地禁锢在心里。这是怎样的精神煎熬和痛苦!即使是这样,与她以前的困窘生活相比,她也宁愿压抑心底的声音,坚守住这得之不易看似幸福的生活。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哀。答应了丈夫拆除花园中的小屋,也就喻示着她又从梦想中重回现实。
两篇小说中,作者都从第三人称的角度,讲述了两位女性的亲身经历。这与作者对女性的态度不无关系。作为一名女作家,她深刻体会到,在当时的父权社会中,妇女的“他者地位”决定了她们是没有话语权的,不敢也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女权主义运动还没有形成规模,作者不敢贸然突破传统的叙述角度,以第一人称直接描述和表明女主人公的委屈和痛苦,而只能用一种较为委婉含蓄的方式,通过非常了解女主人公的他人之口,代替描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这样,一来可以避免引起男性甚至是部分女性的反感和打压,二来可以博得人们对女性的关注和同情,让女性的声音用当时社会能接受的方式来发出。通过第三人称叙述者客观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女主人公的内心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读者的心也随着她的情绪在波动,从沉睡三十年的心灵被音乐渐渐唤醒,到被压抑已久的激情喷薄而出,直到她从梦境中醒来,不愿面对现实的万般无奈,一种同情和怜惜升腾在我们心中。
小说都采用倒叙的手法,对环境和人物的内心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描写,主人公的现实生活与理想穿插在一起,形成鲜明对比,衬托出她们内心的彷徨、痛苦、挣扎、无奈,使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诗意的梦想与现实间的距离,以及内心的巨大落差。《瓦》中的音乐会现场对人们服装的描写:“只看见无数的女背心色彩缤纷,各式各样的衣服——柔软的,结实的,光滑的,透明的等等——微光闪烁。红、紫红、粉、蓝、丁香紫、深紫、淡褐、玫瑰红、黄、乳白、白,总之,印象派画家在一片阳光明媚的风景中所能发现的一切色彩,这里是应有尽有。”这些和婶婶那身怪里怪气的服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音乐会中,“我”一边观察着婶婶的反应,一边不知不觉回忆起过去童年时生活过的蛮荒之地:“草原上那没上漆的高高的房子,黑水塘,裸露的木房四周的泥土围墙,低矮的小树,厨房前老是晾着洗碟布,东边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西边是一直伸向落日的牲畜栅栏。”五彩缤纷的服装象征着都市人生活的丰富多彩,更加衬托出婶婶三十年来生活过的西部村庄的生活的单调和凄凉,如果不是为了爱情,这些绚丽原本是属于她的!过去的回忆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在发达的、文化气息浓郁的东部城市和发展中的、偏僻闭塞的西部乡村之间形成了一系列反差强烈、震撼人心的对比。”叶英:“真实的生活 真实的艺术——读威拉•凯瑟的《一场瓦格纳作品音乐会》”,载《名作欣赏》, 1997, (4)。原刊中文章名即如此。三十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都浓缩在这短短的一场音乐会中了,婶婶的精神追求早已湮没在那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了。失去的太多太多,永远也找不回来了。《花》中开篇就生动地描绘了卡罗琳现在的惬意生活:“从小屋的窗子里望出去,那钢青色的海湾,缀着点点白帆,清晰地映入眼帘。左边的花园和右边的果园从来没有像这样春意盎然,并且已经迸发出繁茂的鲜花,似乎在迎合卡罗琳的心愿。”而她当初的生活:“从童年起,她就憎恶那种屈辱而没有着落的生活,这里有三寸不烂之舌和一文不名的钱袋,有诗意的理想和悲惨的现实,有纸玫瑰装饰着的怠惰和贫困。”正是在今昔的对比中,卡罗琳才会强迫自己恢复理性,放弃所谓的梦想,因为对她来说,那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珍惜眼前得之不易的富足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她输不起。
两篇小说都采用了象征的手法。花园中的小屋不再单纯是一种景致,而代表着女性追求自由的梦想和意欲走出男权传统樊篱的向往。故事结尾小屋的拆除,反映出女主人公作为边缘人、附属物对自我的压抑和最终因屈从于现实、被迫放弃梦想而产生的深深的无奈。朱丽:“女性与自然的言说——《花园小屋》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第6期。暴风雨平息以后,卡罗琳又恢复了理智和平静。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小屋与别墅,孰轻孰重,她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她的回答让丈夫很意外,他原以为她会痴情一些,而卡罗琳则回答道,她睡了一夜,想法改变了。说完夫妻俩大笑起来。看似轻松的一句话,深藏着卡罗琳多么复杂的思想斗争和情感挣扎。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她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情感,保持理智,守住眼前的“幸福”。而另一篇小说中的音乐会则象征着婶婶沉睡多年的音乐梦想,音乐厅和农场分别具有不同的寓意。它们一个是那么丰富多彩,一个是那么单调沉闷。从表面上讲,它们代表了东部和西部两个不同的物质世界;从深层而言,它们象征都市人和拓荒者两种相异的精神天地。音乐声中两个画面的交替出现,似在无声地诉说西部世界的荒凉,似在无声地倾吐拓荒者的寂寞。音乐声中两个画面的相映相衬,给人如梦似幻、恍若隔世的感觉,让人分不清到底哪里是虚幻,哪里是现实。音乐厅和农场这两个现实世界的鲜明对照使她的失落感更加强烈,使她的痛苦更加难以忍受。“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使女性为了生存必得取悦于男性,并因之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价值取向内化为自
己的行为准则,安于男人指派给她们的地位,不去争取自由。”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4。两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梦想夭折的原因在于她们在生活中没有主体意识,只是把自己当成了一种附属物,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她们只是成千上万个为家庭所禁锢的妇女中的一两个而已,作为父权制社会的牺牲品,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两位如此有音乐天赋的女人除了服从命运的安排,甘于做家中的“天使”,别无选择,她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冲破现实的束缚,追求理想和自由,因为这样的举动在别人眼里是离经叛道的。 在父权制社会中,许多妇女的天赋就这样被扼杀了,诗意的理想在沉重的现实面前无异于海市蜃楼,在现实面前,梦想只能成为压抑在心底的囚徒,无论怎样挣扎,怎样抗争,最终都要为强大的现实所打败。作为女权主义作家,在这两篇小说中,薇拉•凯瑟对两位女主人公赋予了深深的同情,通过她们的命运和故事对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进行了较为隐晦但不失深刻的批判和控诉。
(本文为2009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嬗变”(2009FWX017)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
(朱丽: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邮编:46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