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逝去的文明
燕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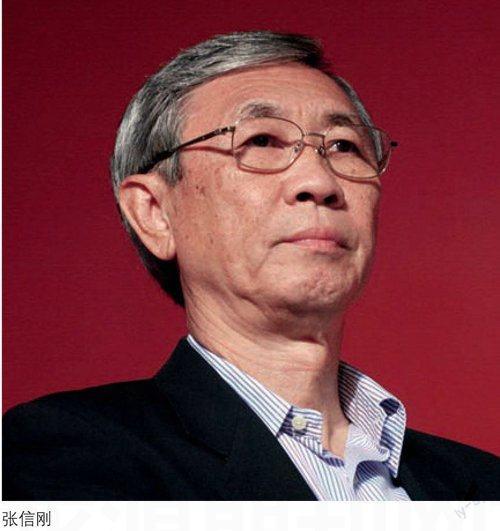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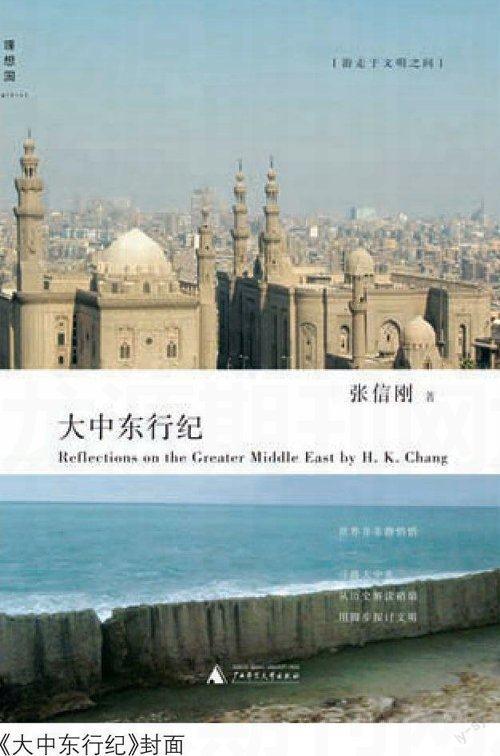
“他突破了专业化日趋严重的学术界:科学—人文,行政—教研,专家—通才,乃至古今中西之争的藩篱。他是一位有人文气质和博雅见识的教育领袖。他以横跨东西的视野向我们展现了客观认识和同情了解异质文化的学养和洞见。”著名学者杜维明如是盛赞的正是张信刚教授。
张信刚出生于一个西医世家,其父为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在父亲与劳榦、董作宾、李济等历史学家的雅集中耳濡目染,他萌生了对历史、地理的最初兴趣。1962年,22岁的张信刚在台湾大学拿下土木工程学学士学位,其后两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结构工程学硕士学位,1969年获美国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博士学位。
于纽约州立大学、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先后执教20余年后,张信刚1990年回港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创院院长,4年后再度赴美,担任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1996年,张信刚受邀担任香港城市大学(下称“城大”)校长,其后不久,连续成立英语中心、中国文化中心、跨文化研究中心和创意媒体学院;1997年夏秋之际,开始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张信刚随想曲”的周播节目。
1998年,张信刚将张隆溪、郑培凯两位学养深厚的中生代学者延揽至城大,与他们一拍即合,于同年10月开始在校长官邸举办每月一次的“城市文化沙龙”,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的张太太周敏民成为沙龙得力的女主人。十年间,白先勇、汤一介、张灏、叶嘉莹、李欧梵等文化名流成为沙龙座上宾。2004年冬,张信刚偕夫人亲赴土耳其,促成两年后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Orhan Pamuk(奥尔罕·帕慕克)在香港的首次公开演讲。
凡此种种,让这位生物医学工程专家有了“人文校长”的美誉。2007年,张信刚卸去城大校长一职,但仍住在学校附近。退休后,他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以及土耳其海峡大学讲授人文通识课程,其中担任北大“叶氏鲁迅讲座教授”。
近日,张信刚将2010年在香港《信报》上的专栏“游走于文明之间”结集、修订,出版了《大中东行纪》一书——他将传统中东地区以及地理、历史、文化上与中东难以分割的周边国家(如利比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格鲁吉亚等)纳入一体叙述,提出“摆在他们面前的两个现实问题是:政治如何民主化?国家应否世俗化?”
在张信刚看来,“在‘大中东31个国家中,实际上只有伊朗、埃及和土耳其这三个国家有可能成为他国模仿的对象。恰巧,这三个国家各有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传统,也各有其吸引力和影响范围”,“‘大中东地区哪个伊斯兰国家能够涌现大批‘独立判断的学者,在大众接受的教法范围内找到一条可行的现代化途径,哪个国家就会成为‘大中东伊斯兰国家未来发展的模式。而这一途径最简单的表述方式与中国‘五四时期所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很接近,那就是:‘伊斯兰+民主+科学”。
历史感
《新民周刊》:您的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2000年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是因为胸外高频压缩法(“人工心肺机”),那历史、地理方面的造诣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呢?
张信刚:我爷爷是医生,父亲是台湾大学医学院的教授。父亲是很好的外科医生,但是他可能会成为更好的历史学教授。他在台湾大学医学院做外科大夫的时候,家里来的客人都是一些文史学科的教授,同事们也愿意跟外科大夫来往,因为谁都会生病嘛。劳榦、董作宾、李济等先生都是我父亲的朋友,我从小耳濡目染,在家里听他们论道,我有时候倒茶,有时候挤在旁边听。小学三年级,爸爸给我一本“世界名人传”,俾斯麦这些都在里面。小学三年级当然不会清楚地知道阿波罗是怎么回事,可是对欧洲文明比较有兴趣。所以,开始求知,特别是求历史、地理、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知识。这绝对跟我父亲的影响有关,我父亲对这些有兴趣,所以他老约见这方面的专家。我从小听他们讲这些,所以对历史和地理蛮有兴趣。
我受了社会影响,1958年报考了台湾大学工学院,那时它的录取分数比历史系高得多,我考上了,之后就念了土木工程系。念工学院很难的,但很自豪,因为那时大家认为你在台湾大学工学院,所以是好学生。在这时代,也算吧。后来我就到美国去拿奖学金,念博士,博士之后,因为我不想工作只为赚钱,就决定在大学教书,因为我从来不觉得赚钱是我人生最大的问题。获取知识是我很大的乐趣和目标。
《新民周刊》:这两三年我采访一些港台人士尤其是像您这样有过台湾生活经验的师长,有的一追溯起自己的家族史就特别宏大,几乎可以把中国近代历史串起来,似乎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那些显赫名字都与他们祖上的历史有关。比如我采访的台湾乐评人和作家马世芳,他的祖父马廷英先生就是当年从大陆去的台湾,是台大地质系的创始人,其祖母回大陆后又嫁给了民主人士章乃器。
张信刚:不是都这样,200万人去了台湾,哪能个个都载入史册。但是200万人,因为度过了中国近代史中间最显著的一页,就是1949年前后的内战,或者1937年的抗日战争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这段时间,去台湾的人家里面,直接有人参与到这些活动的比例,比内地没有搬家的人高得多。
也有很多去台湾的是一般老百姓,我爸爸就是普通的医生,他会日文,是在东北念的南满医科大学。我爷爷也是念的南满,也会日文,台湾以前是日本人统治,医学院完全由日本人建立,医学院上课说日文,所以我爸爸就去了台湾,但没有特别显赫的地位。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像宋子文的后代,卧虎藏龙,多得很。宋子文后代中的一些人在纽约,现在仍然过着很好的生活,但是他不告诉你,你都不知道。
异域文化
《新民周刊》:一直以来,知识分子谈论异域文明观感的这种文本特别多,您去“大中东”地区这些国家之前不太熟悉它们,还是去之前就从文本上有一些了解了?
张信刚:最早的是1963年去的,有些国家是1980年代去的,好多地方是2000年之后去的。叙利亚是去年(2010年)10月才去的,我去的时候还问会不会出乱子,人家说不会。我回到香港,有人要组团去,问我会不会出乱子,我说2011年4月之前去大概不会出乱子,因为我去了半年之内没出事。让我说中了,他们4月不肯去,5月去就不行了。
文本准备还是做了一些的,光是带着好奇心去一个地方,也会有很大收获,但是先做一点功课的话,去的时候会收获更多。我不是徐霞客,但毕竟直接的接触还是重要的,我经常选择自己包一辆车,司机兼任导游。我们有些旅游团,去了国外还特意拉到一个中国餐馆吃饭,我在格鲁吉亚看到有一个专门去中國馆吃的中国团,去了格鲁吉亚还吃中餐,等于没有接触到那边的文化。
《新民周刊》:中国与印度的比较近些年来在国内很热,上海双年展2010年年底还举行过高规格的“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您也与印度一些重要知识分子有过交流,我很想知道你们交流的成果。
张信刚:印度当然是历史很悠久的,但是跟中国很不同,中国的汉族处于绝对优势。儒、释、道三个加起来的某一种综合,肯定在90%以上的中国人里面产生作用,没有一个完全一点都不受到道家或者佛家影响的人。
印度的官方语言有十四五种,15%的人口是穆斯林或锡克教徒,85%的人口属于所谓的印度教。其实没有一个专门的印度教,“印度教”这个名词是西方人为他们做的归纳。他们自己叫这个神那个神,加起来几万个神。他们两百年来受英国的影响,学者们对西方的了解比我们多很多。
他们上层和下层之间的距离相当大,能造卫星和航空母舰。我们老是看到他们建筑破旧,马路很脏,火车一撞就死好几百人;每年一个节日的时候要到恒河里面洗浴,一冲又淹死好几十人。其实,印度的明白人非常明白,印度人到美国去,表现一点不比中国人差,全世界大公司的CEO不少是印度人,不是中国人(据媒体报道:标准普尔500强公司中,印度人担任高管的人数只排在美国之后。2009年《财富》500强的CEO中,来自印度的有13人,来自中国大陆的只有2人——采访者注)。因为印度人的语言能力特别是驾驭英语的能力超过中国人,中国人再怎么说不是从小学的英语,而且印度语其实是印欧语系,跟英文的构思、时态比较接近,复数、单数都有的,他只需要记住英语的规则,而英语的规则比印度语的规则简单得多。中国人说英文往往容易搞错了,时态前后不一致,因为我们的语言里没有这种时态。
有人甚至说,印度第三大外销产品就是CEO。有人把美国的硅谷说成IC,本意是集成电路,这里I就是India,C就是China,在硅谷,印度人跟中国人一样出色,而且都为美国所用。
《新民周刊》:印度三分之一的人是文盲,据说他们最好的两所大学是尼赫鲁时期建立的印度理工学院(IIT)和印度管理学院(IIM),而这两所学校的录取率不到2%,远低于美国哈佛大学13%的录取率。印度这种非均衡的精英教育模式,其实我们通过2009年上映的宝莱坞电影《3 Idiots(三个傻瓜)》也能略窥一二。
张信刚:宝莱坞电影数目多,但有些也浅薄,印度的老百姓多数是看宝莱坞的。
《新民周刊》:宝莱坞电影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印度歌舞就能大量融进去。
张信刚:老百姓需要听歌,剧情不需要的也要唱歌。无缘无故就跳舞,无缘无故就唱歌,因为老百姓爱看歌舞。
他们的社会传统,绝大部分女性还穿民族服装,男的也有穿民族服装的,但是比较容易改。从印度开始,整个大中东地区这一片,女的一般还穿民族服装。可是我们东亚的人把民族服装不要了,穿旗袍或者穿长袍的很少很少了,男的穿小夹袄的也很少了。
《新民周刊》:印度和大中东地区这种着装和生活方式,是源于某种文化自信吗?
张信刚:跟宗教有关,它的宗教里面要求一些东西。中国没有那么多禁忌。比如婚姻,印度的知识分子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的极少。阿拉伯国家的婚恋绝大多数都是父母介绍的,自由恋爱的是少数。
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以及许多欧洲人对穆斯林的轻蔑,使得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力自1980年之后持续增强。以色列与西方的作为扭曲了大中东地区许多穆斯林的心态,也使本地区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腐败与无能得到了一个借口。阿拉伯联军跟以色列四战四败,造成阿拉伯人长期的压抑感,导致少数人非理性的思维和行动。海湾战争之后,美军进驻一向被沙特阿拉伯王室宣称为“伊斯兰圣地”的阿拉伯半岛,引起伊斯兰极端分子极度不满,恐怖主义因而得以快速发展。“9·11事件”中的19个恐怖分子中有15人是沙特阿拉伯籍,就颇能说明恐怖主义猖獗的心理背景。
有一次坐飞机,差不多离开伊朗领空时,我注意到飞机上的妇女们纷纷摘下了她们的头巾,有些人涂上了唇膏,还有人到洗手间里换上了时髦的衣裳。顷刻之间,我明白了,伊朗的未来就在这些有机会出国的人们的心中。
真正的学者
《新民周刊》:现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北岛有一个说法,说在香港做一个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
张信刚:香港有饶宗颐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一代的中年学者有张隆溪、郑培凯等人,这很不容易的,因为香港毕竟是用机会成本的概念考虑问题的地方。你要做诗人,你的机会成本就很高,你要利用这个时间去炒股票或者买卖房子,你可以赚到很好的生活。结果你花那个时间看历史书、写诗,你的机会成本就很高了。
香港前一阵子的经济形势,是属于瞎子炒股票都会炒赢的,只要有钱去买卖房子就一定会赚钱,所以做学问、搞艺术的机会成本很高。你不愿意花时间干这些,而是天天读书、思考、写作,这还是有一定道理,因为诗人不是不可以炒股票,但喜欢炒股票的人肯定做不好诗人。
《新民周刊》:香港一些名士气很重的资深媒体人会给大明星的畅销书写序或做各种推荐。也有个别人利用一点学院背景,穿梭于学院、媒体和演艺圈。这些当然都是媒体工作的需要,但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如何保持与媒体的适当距离如何保持足够的独立性,仍然是一个问题。
张信刚:香港社会是一个更表象的形态,还要容忍百年孤寂。我比较佩服的是饶宗颐先生,他不挂名,90多岁还亲自办书画展。香港最高的勋章是大紫荆勋章,董建华、曾荫权有,他也有。饶宗颐先生绝对配得上这个勋章,他几十年前的书画和学术研究还是很有力度的,他研究敦煌学,他是做学问的,这样的人在香港是比较少的。
你要光是看名字不行,因为香港的媒体炒作比较厉害的。香港很多时候都是把包装弄得很好,所以你得分清楚谁是真有学问,谁是假有学问,谁骨子里就是学者,谁外表是学者骨子里是商人。
我们心里都有一把尺,人不外乎这几种情况——政客型,他是以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高下为他的核心价值,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商人,不管他对你倨也好,恭也好,油嘴滑舌也好,他的目的是赚钱,他对信仰不是特别在乎,他的价值观决定了这个。学者,不管他孤傲也好,或者平易近人也好,他是对真理执著的,他喜欢某些知識,饶宗颐先生就是这样的。还有流氓型的,黑社会闹结帮,只要我三个人能揍倒两个人,我就揍你一顿,然后把你的利益拿去。
所以,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名片写得多好,你认得多了之后大致可以认出来这个人是政客还是学者,还是商人,还是流氓。但是,那个梨要咬好几口,或者对某一个人得有足够的认识。现在的社会,很多人经过包装之后,内心都是复合型的,没有一个人生来就爱做流氓。有些人仗义执言,有些人够义气,当官的人都图一个什么,当然他心理也不平衡,他对家人也不平衡,可是基本上他的价值取向到底怎么样,到了危机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就像自私自利的人碰到火灾的时候,碰到要翻船的时候,他到底让不让妇孺,真实不真实,就可以看出来。

